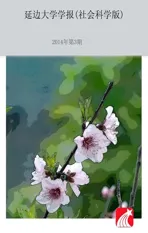浅谈宝物折射出的地域文明
——以中国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宝物故事为例
2014-03-06刘淑珍
刘 淑 珍
(中国传媒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24)
宝物是民间故事的一个古老主题,是指民间神奇故事或幻想故事中出现的具有神奇功能或魔力的物件,有魔物、魔宝、灵物等诸多不同称谓。其实这些称谓反映了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宝物重在“宝”,强调人们对物体的态度;魔物重在“魔”,强调物体发生作用的方式;魔宝被看做是物之“魔”的作用方式与人之“宝”的褒扬态度的结合;[1]灵物重在“灵”,强调物体本身具有某种灵性或神性。宝物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从功能角度看,宝物可以分为万能宝物、神奇自然物和魔力器具;根据起源的同一性,宝物可以分为五大类:起源于动物的物件,起源于植物的物件,以工具为基础的物件,由多种成分构成、具有独立的力量或人格化力量的物件,与死者祭祀相关的物件。[2]根据物质形态,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的宝物可以分为植物、自然山水、动物的部分肢体、工具武器、生活物品五大类。
一、植物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宝物故事来看,以植物为宝物者居多,占到宝物总类的1/3;植物宝物中以药草者居多,占到植物类宝物的1/2;药草宝物中以人参者居多,占到药草类宝物的1/2。其中,因为满族起源于白山黑水,植物以人参见长,所以一半以上以人参做宝物的故事均来自于满族。具体地说,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的植物宝物主要有花草、瓜果、树木三大类。其中,花草类宝物以人参为最多,水仙、浮吐兰、灵芝、月季等次之;瓜果类主要有桃子、菇娘、红果、葫芦以及香瓜等;树木类以松树、桦树、柳树等为主。
花草类宝物被赋予的神奇功能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包治百病,造福百姓;二是变形为人,救助弱者,惩治恶人。以人参为例,由于向来采挖不易,人们便赋予其神异的色彩,说它能够“转山”,能够幻化为人形,或变成白发老翁,或变成俊俏的姑娘,或变成在山间嬉闹的胖小子,编织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幻想故事。满族的《三砬子峰》、《扇子参》、《萨满捉参》、《小马倌与敖赫达》和《棒槌鸟》,赫哲族的《人参娃》和《棒槌姑娘》,锡伯族的《灵芝姑娘》等诸多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情节均围绕人参宝物的这种功能展开。
作为宝物,故事中的瓜果能够“长期永久”地解决饥饿、治愈疾病或者生殖异质物质,如锡伯族故事《放牛娃和仙女》中的桃子、《鹦哥》中的桃子和《燕子》中的南瓜,满族故事《手鼓的传说》中的红果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数量可观的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憋宝故事中,开山宝物极具地域特色。例如,黑龙江省阿什河流域阿城流传的憋宝故事《金瓜打金牛》和《北团山子没破》等中,常见的开山宝物是香瓜。这是因为阿城河东小红旗(“八百垅”)出产一种甜瓜,色黄如金,个头匀调,稀酥杠脆,进嘴就化,正如当地谚语所说“八百垅的瓜,阿城的蒜,玉泉的菇娘不用看”。
从民间故事中以树木为宝物来看,松柏乃为长寿之树,关于其能言、能走、能化形为人的幻想,中国历代志怪杂记早有记载。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对松桦的神奇幻想,明显受到了道教物老成精思想的影响。同时,它也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居住地域森林密布、松桦居多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自然崇拜、植物精灵崇拜习俗密切相关。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树木做宝物,其神奇功能是开口说话,指示主人公,告知宿敌仇家姓名、神秘武器所在地以及寻仇的方法途径等。以鄂伦春族故事《白嘎拉山的故事》为例,主人公卡图艳回家发现弟弟的尸体后伤心恸哭起来,这时,大青松说话了:“救活你弟弟不是没有办法,你先用我身上流出的松脂洒在他身上,好让阿尔塔内的尸身不烂。然后再去找个骑射能手,到天边的大海中间的岛子上去找萨尔古岱,他有三个女儿,有办法救活阿尔塔内。”大青松看她确实像个英俊的骑手,落下了些枝叶,立时变成一匹活蹦乱跳的大花马。卡图艳骑上这匹骏马,按照大青松所指的方向飞奔而去。[3]
总体而言,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的植物类宝物及其功能充满山野之风,折射出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世居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长白山、大小兴安岭以及天山山脉之间,植被丰富,尤以人参见长的地域特色,寄予着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天然气息和朴素愿望。
二、自然山水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世居高山密林、草场河畔,对周边山川河流了如指掌,满怀深情。在与自然的较量中,他们积极探知大自然的各种奥秘,渴望得到治愈伤病的灵丹妙药,渴望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于是他们通过幻想将自然山水的功能加以夸大,使之成为故事中生动有趣的宝物,寄予了他们的完美理想,也表达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与赞美。
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天然的泉水和石头常常被赋予疗伤、治百病的神异功能,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鄂温克族的《蓝色宝石》和《公鹿河的传说》、锡伯族的《阿克图和巴克图》和《狠心的哥哥和嫂子》、鄂伦春族的《白依吉善的故事》和《白衣仙姑》,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水和石还有一种神奇功能:人舔舐之后能够听懂一切飞禽走兽的语言。例如,在鄂温克族故事《樵夫和蟒蛇》中,樵夫上山砍柴,迷路误入蛇洞,并且模仿蛇群喝了几口石头上的水。
一晃春去秋来,粮食收获到家。一天,樵夫和妻子把粮食晒在外边窗下,樵夫坐在屋里,看见两只家雀在窗下粮食上边吃边叽叽喳喳地叫着,樵夫听懂了它们在说什么。
一个说:“你赶快吃呗,干嘛一边吃一边扒拉,一会儿主人该来撵我们了。”
一个说:“你说的不对。今天来有吃的,明天天气不好了,主人不晒粮吃什么?我现在一边吃一边把粮食埋在土里,明天来还有吃的。这叫两全其美!”
嘿!想的可倒周到。樵夫听了心里暗自好笑,不由得咯咯笑出声来。[4]
三、动物的部分肢体
作为宝物,动物的部分肢体最常见的神奇功能就是虽然已经脱离了动物本体,但是依然能够发挥该动物原有的能力。例如,满族故事《勇敢的阿浑德》中的翎羽,《女真定水》中的龙角,能够带着主人公飞翔;鄂伦春族故事《小红马》中,小红马牺牲后,五脏和骨头变成了成群的牛马猪羊,头变成了一匹小红马;鄂温克族故事《顶针姑娘》中,宝马死后,它的皮变成了一座金房子,尾巴变成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筋变成了大马圈,头变成了无数匹马。
然而,在另外一些故事中,动物肢体类宝物则远远超越了以上基本功能。那么,这些动物肢体是怎样被赋予神力,并且逐渐变得神力无边,最终造成了肢体本身和功能之间的不对称、不确定呢?这需要从它的民俗起源谈起。人类早期,氏族部落为了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会定期举办各种祈天祭祖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常常包含一项重要的内容,即礼授未成年人经过某种特定仪式洗礼的圣物,以期保佑他们健康成长。早期这些圣物常常就是动物身体上某些可以被人方便携带的部位。青年人获得这份圣礼后将它随身携带,坚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该动物会从天而降,救助自己。这种信仰习俗在故事中就表现为占有了动物的部分肢体便获得了召唤支使该动物的能力。后来“你心里想要的一切”这个公式取代了早期较古老、较确切的愿望,故事中动物部分肢体的功能被无限扩大,如羽毛由原初带主人公飞翔发展到能够满足主人公的一切要求。
四、工具武器
顾名思义,这类宝物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们亲手制造出来的物件,其神奇功能往往由人们通过想象将其原始功能加以夸大而成。例如,满族故事《桂花岭的传说》和《女真定水》中的斧子,鄂伦春族故事《小白兔娶媳妇》中的猎刀和锡伯族故事《破石磙》中的宝剑,都能够劈石石开,断水水分;满族故事《金斧银斧》中,神斧刚刚举起,柴禾就自动倒地,像风吹的一样,用神斧凿制的家具犹如聚宝盆,里面的东西永远也用不完;鄂温克族故事《毡帽、羊鞭和口袋》中,口袋装东西无数,羊鞭“指哪里到哪里”;锡伯族故事《勤劳的法依勤阿》中,拨火棍能够听从主人命令自动棒打盗贼,等等。后来,工具武器类宝物的功能范围被无限扩大——发生变形,生殖财富,甚或变成有生命的动物。例如,鄂伦春族故事《仑巴春巴》中,3个鞍韂分别变成了3匹骏马,帮助主人公赢得比赛;赫哲族故事《姑娘和猎人》中,磨石变成了一座光滑的大山,帮助姑娘躲避了刺猬精的追击;锡伯族故事《把“奇怪”拿来》中,木棒变成了龙马,帮助小伙子在赛马中超过了县官。
显然,这类宝物体现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劳动人民大胆而美丽的幻想,表现了他们对于最大限度地减轻劳动、提高生产效率的无限渴望以及对于自身无穷创造力的满怀信心。因此,这类将人们劳动成果加以神化的幻想富于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具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正如有些学者说的,宝物不过是人类知识和技能的物质化罢了。
五、生活物品
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生活物品类宝物占到宝物总类的一半以上,形式多样,功能各异,有祭祀物件、器皿口袋、服装头饰、乐器及工艺品等。以生活物品做宝物的故事,其情节始终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中心,最直接地体现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朴素的生产愿望、生活理想和道德追求。
祭祀物件包括用于祭祀的神偶木偶、做法事的法器和神物等。作为故事中的宝物,它们的神奇功能多种多样且不确定,可以具有某一项特定功能,也可以是万能的,可以与神圣的祭祀活动相关,也可以只与世俗的日常生活有关。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故事中用作宝物的手鼓、镜子、嘎拉哈等物件都充满了原始萨满教的信仰色彩,体现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独特精神内涵。例如,满族故事《手鼓的传说》中,多伦玛发用神物柳枝浇灭烟火,神鼓盖住火山口,使灾难得以消除,百姓从此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器皿口袋作为宝物经常被赋予“聚宝盆”的神奇功能,用以盛物且所盛之物变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例如,满族故事《北极星》中的泥盆和《泼雪泉》中的温凉盏,鄂温克族故事《神奇的瓦罐》中的瓦罐等。可以说,宝物的这一功能以最直接的方式体现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劳动人民朴素的民以食为天的生活愿望。器皿口袋类宝物被赋予的第二大功能是能够生殖世间万物,如满族故事《桦皮篓》中,桦皮篓里面每天会跳出3个仙女给哥俩做饭;鄂温克族故事《小鸟、老鼠和獾子》中,金箱子里面奔出百万匹马,还走出一位美丽的姑娘;鄂伦春族故事《珠拉图讷》中,金盒子里飞出宝驹、宝剑和宝垫;锡伯族故事《瘸子驸马》中,口袋里变出了龙马宝驹和礼帽长衫等。故事中能够生殖万物的宝物,罗菲称之为“‘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物”,他认为这类宝物虽然形状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都是可以包容他物的容器,体现着一种包容与蕴含的功能,而且在故事中,它们又经常以葫芦以及与之相似的壶、罐形象出现,有力地回应与暗示了“葫芦生人”的神话原型意象。[5]
服饰类宝物的一个经典功能就是隐身,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不乏此例,如锡伯族故事《扎鲁山与梅翠》中的上衣,鄂温克族故事《毡帽、羊鞭和口袋》中的毡帽等。再则,头饰做宝物,一项最普遍的神奇功能就是变形成各种路障阻止妖魔或坏人的追捕,帮助女主人公脱险。例如,赫哲族故事《姑娘和猎人》中,姑娘的木梳变成了密林,篦子变成了荆棘丛,镜子变成了大湖,类似的场景还出现在鄂温克族的《顶针姑娘》和锡伯族的《放牛娃和仙女》等多则故事中。表面看来,头饰类宝物能够变形成各种障碍物,固然与其自身形状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头饰本身之“密”、“利”的特点使之具有了武器的性质,因此头饰也很自然地成为女人的防身之物。所以,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头饰类宝物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生活现实是如何被巧妙地编入到故事中的。
音乐总是和生命、爱情息息相关,所以乐器类宝物也总是关涉这两个主题。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组以乐器做宝物的故事具有几乎相同的故事情节,都讲述了悲惋的爱情故事,如满族的《玉杯的故事》、锡伯族的《芦笛》、鄂温克族的《会唱歌的酒盅儿》。从情节结构看,这三则宝物故事均属于“不死的爱心与会唱歌的酒杯——‘不见黄河心不死’型故事”。[6]而赫哲族故事《口弦琴的传说》则讲的是,瘟疫降临人间,无数百姓病死,勇敢的姑娘弹着口弦宝琴,回到死城,一路走一路弹,于是凡姑娘经过的地方,所有死去的人和动物都复活了。口弦琴是赫哲族劳动人民独创的乐器,它取材方便、制作简易、吹奏简单、携带便捷,是赫哲族人为大众讲唱伊玛堪或个人生产劳动之余娱乐的重要乐器。在这则宝物故事中,赫哲族人民赋予口弦琴以复活生命的神奇功能,寄托了他们对其独特深厚的感情。
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充当宝物的工艺品主要有布艺、剪纸、面人、绘画等,其神奇功能也是多种多样,无奇不有。例如,赫哲族故事《巴托力与爱赫恩》中,爱赫恩姑娘用白布剪出两只天鹅,在她被逼成亲当天,和爱人双双骑着布天鹅飞上了蓝天;《聪明的媳妇》中,梅花鹿姑娘用面捏了一匹马,吹了口气,面捏的马立刻变成一匹神速骏马。类似的宝物故事还有鄂伦春族的《蒲妹》、锡伯族的《放牛娃和仙女》、赫哲族的《木竹林救姐姐》等。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类宝物的书写更多地倾向于赞美女主人公心灵手巧、善良勇敢的各种美德。
古今中外的民间故事中,画做为宝物有一个古老而经典的神奇功能,就是画中的人物或动物走到现实当中,参与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这类宝物比较少,只有满族故事《美人图》有涉及,小伙子助人为乐得了一幅美人图,在回家途中,画中的姑娘走出来与他成了亲。其实,这一现象恰恰反映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早期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长期以游猎游牧为生,常常逐水草而居,所到之处,只搭建一些类似于马架子、仙人柱的临时住所,随迁随拆,并且这些住所内空间窄小,光线不足,所以也就很少粘贴或悬挂一些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画幅类装饰物。
六、结语
民间故事中的宝物是现实与幻想的统一体,解读中国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宝物故事,可以了解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在自然环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独有特点。具体地说,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故事中的宝物本身并不奇特,都是现实中常见的物体,有自然界的花草树木、蔬菜瓜果、山石流水,也有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斧头、猎刀、弓箭、羊鞭、泥盆、瓦罐、桦皮篓、桦皮图、狗皮垫子等工具用品,以及毡帽、皮袄、发卡、簪子等服装饰物。但是这些看似普通的物件被赋予了各种神奇功能,它们能够开山劈海、日行千里、变化形体、隐去身形、治愈百病、复活生命、繁殖财物、驱使自然力,等等。不仅如此,有的还能够明辨是非、识别善恶,从而帮助人们奖善惩恶,过上幸福生活。
[1] 万建中.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的主题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
[2] [俄]弗·雅·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242.
[3] 隋书金.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鄂伦春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48.
[4] 王士媛,马名超,白杉.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鄂温克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188-190.
[5] 罗菲.关于民间“得宝故事”的神话原型解读[J].衡水学院学报,2010,(2).
[6]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