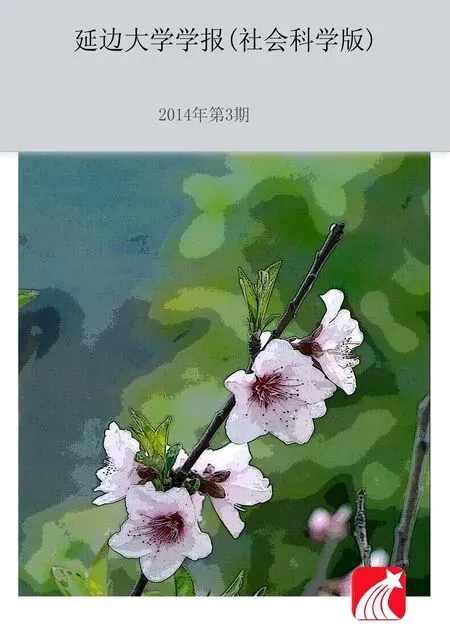刍议构建幕藩体制的基本要素
2014-03-06张波
张 波
(延边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吉林 延吉 133002)
自1953年古岛敏雄首次提出“幕藩体制”概念后,学界针对幕藩体制的内涵进行了广泛研究,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狭义上讲,幕藩体制就是建立了由幕府和藩国共同管理的一种体制。从广义上看,幕藩体制是指政治上构建了以幕府集权与藩国分权的二元体制;经济上建立了石高制及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思想文化上强调了封建伦理道德和朱子学,以“合理化”理论麻痹各阶层的人们;社会关系方面确立了严格的士、农、工、商的四民身份秩序;在对外关系上实行了锁国政策等五个方面。本文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幕藩体制,即构成幕藩体制的政治要素、经济要素、思想文化要素、社会关系要素和对外关系要素,这五个要素成为构成幕藩体制的关键性支柱。
一、政治要素:幕府的集权与藩国的分权
关原之战使德川家康以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征服和怀柔了所有大名,在江户设立幕府,指挥和控制全国,日本列岛由此出现了表面的“和平”及“统一”。但这种统一模式不同于中国的大一统模式,而是将军凭借占有全国近四分之一领地的经济实力,成为其他各大名无法比拟的一极,但是将军的经济、军事等实力又不能彻底征服各大名,必须保留诸大名的实力。这种力量集中且又分散的格局,迫使德川家康采取了独特的统一模式,即幕府和将军掌握全国的最高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幕府为中心实行幕政;但大名在各藩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各藩实行藩政,俨然是一个“小国家”。由此形成了幕府集权与藩国分权相统一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制度框架内,幕府必须始终保持强大的综合实力,才能有效管理各自独立的二百多个藩国,如果藩国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推翻幕府的时候,幕府的统治将难以为继。因此,幕府为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采用了多种手段实现其“强本弱末”的目的:
1.挟天子以令诸侯。天皇在日本国民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万世一系的特性。因此,德川家康在建立自己政权时,依然效仿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保留天皇的存在并迫使天皇任命其为“征夷大将军”,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但德川幕府在控制天皇方面远远超过了前两个幕府,通过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天皇的职责,限制天皇的行动。法度中明确规定天皇在等级秩序的社会中应完成的“任务”就是作为日本的精神象征,传承和发展文化,研究和实践礼仪等。因此,法度是对天皇及公卿贵族权力的限制和削弱,不是彻底剥夺他们的参政权,而是规定他们仿效先人,不得试图扮演政治“主角”。可以说,《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实施是日本制度史上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相当于日本的宪法革命。法令的制定者是幕府,从法律制定者是主权者角度看,天子和朝廷作为日本实质的主权者的历史在事实上终结了,是武家主权真正的开始。[1]
幕府不仅通过法度规制了皇室的权利,而且还设置了京都所司代,以负责和监视皇室的动向,并在京都筑“二条城”,作为将军的行辕,以监视朝廷的活动。由此,朝廷成了幕藩体制下的摆设,天皇仅仅成为将军统治全国的精神支柱,在将军和天皇、幕府和朝廷之间的关系上,将军和幕府结成了绝对的权力核心,天皇和朝廷则成了绝对的精神象征。将军凭借其强大的势力,成为了事实上的“君主”。
2.控制大名。尽管德川幕府的建立推翻了战国时期领主制的运动法则,但是由于有二百六十多个独立大名的存在,使幕藩领主间的矛盾不可能完全消除,特别是江户幕府和西南雄藩之间的矛盾更是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因此,幕藩体制建立之初,作为封建领主统治的最高权力者——将军,最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统御大名,尤其是控制外样大名,这关系到幕府生存的重大问题。为此幕府将二百六十多个大名分为亲藩、谱代和外样大名三类,对他们进行不同的管理。由于亲藩是德川家康的子孙后代,因而他们有权继承将军职位和参与幕府决策,只要是军事要地、政治中心和经济富饶地区,皆安置亲藩大名,作为江户幕府的屏障。谱带则是关原之战以前一直臣服于德川家康的大名和武士,对将军忠心耿耿,因此有资格就任幕府高级官僚,担任大老、老中、若年寄等将军直属要职。他们的领地多分封在位置险要、土壤肥沃之地,控制了关东、中部以及京都—大阪一带等重要地区,形成了拱卫江户的态势,是幕府统治的支柱。外样大名则是关原之战结束后被迫臣服于幕府的地方势力,他们中一部分是织田、丰臣氏属下的大名,如筑黑田氏、细川氏、前田氏等,另一部分是旧“战国大名”,如岛津氏、毛利氏、上杉氏、伊达氏等,他们在家康开幕以前的地位是和德川氏平起平坐、对幕府统治最具威胁的势力。因此,幕府不仅不允许他们参与幕政,而且都配置在离江户最远,靠近外海,便于幕府防范、监视的地方。不仅如此,家康还将谱代大名的封地配置在这些具有离心力的“外样大名”周围,进行监视和牵制,使其难以相互联系,无力联合反抗幕府。
幕府为控制大名和武士,还制定了《武家诸法度》,从法律上明确了上下主从原则,规定:“江户颁布之一切法令,全国各地,均应遵从”;“领内政务,应严守清廉,诸事均须依法办理”。[2]同时《武家诸法度》还规定了各藩不可私藏土地,不可参与他国之事,不可私自结党结盟,藩国之间不可私缔婚约,穿着要符合规定,禁止私设关所,不得建造大规模船只,一国一城等。使法令成为了幕府对大名统治最权威的工具,避免了地方势力扩张,使每一个藩国内都无法形成互为犄角、互为应援的军事攻防体系,防止了动乱发生,维护了“安定”局面。
3.实施参觐交代制度。幕府为增强集权统治,规定大名每隔一年在江户伺候(请安)及回到领国居住,江户伺候(请安)之事被称为参觐,回到领国之事被称为交代,并通过《武家诸法度》将其制度化。按照规定,各藩参觐规模是20万石以上385—450人,10万石以上230—240人,5万石以上167人,1万石以上53人。[3]但事实上,各大名为炫耀自己的实力,实际派出的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甚至有高达三至五千人浩浩荡荡的参觐队伍。浩荡的人马需要有巨额的资金作为保障,仅大名行列费用、江户献礼费用和江户生活费用,一般就要占据各藩年财政费用的60%,外样大名比谱代和亲藩的花费会更高,因为他们大多地处边境地带,大大增加了旅途费用。参觐交代制度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它是大名经济陷入贫穷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大名的政治实力,因为大名们每隔一年(个别藩是半年)居住在江户,使他们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无心顾及藩国的发展,失去与将军对抗的斗志。如日本学者芳贺徹所言:“参觐交代制度是在世界史上其他国家都很难见到的制度,形成了日本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这种巧妙的支配制度,近乎完全控制了大名反乱的可能性。”[4]
二、经济要素:石高制的广泛实施
石高制是以战国时代的太阁检地为契机而形成的,它是通过检地确定土地面积和等级,以稻米作为衡量收益量的标准,计算出各等级土地的标准稻米产量,根据生产力换算为稻米生产量的石高而形成米年贡制。它谋求将水田、旱田及山林等土地都以稻米的生产量为基准进行核算,即以米谷的收获量来表现土地生产力及年贡额的方法。是将军分封大名、大名分封家臣的计量基准量,领主和武士收取赋税和领取俸禄都以实物米来计算,成为构成幕藩体制社会的基本原理。是以将军为顶点的知行地(领地)体系建立的根本,组成幕藩体制的各个群体正是在层层分割占有的年贡米的流动作用下“粘着”起来的。正如日本学者井上准之助所言:“石高制对百姓来说成为贡租征收的基准,对大名而言是承担军役的基准,这两个特性将下至百姓上到大名都编入到了幕藩体制的社会统和中。”[5]具体表现如下:
1.石高制使兵农分离成为可能,是幕藩体制建立的前提。幕藩体制建立的前提就是要克服战国时代以下尅上的混乱局面,形成以幕府为中心的高度权威的统治。而造成以下尅上的根源是兵农合一,农民手中握有兵器,武士拥有土地,使他们可以随时起义反抗幕府统治。为此德川幕府通过法令的形式,强制大名及其武士离开土地,聚居城下町,靠领取年贡米或俸禄为生,农民则被固定在土地上,没收他们手中拥有的武器,并规定永世不得拥有武器。而这种兵农分离制度的实施是以石高制为前提的。因为若要让大名、家臣、武士都自愿离开属于自己的土地,就必须让他们获得与“私领”相应的收入,否则他们是绝不会放弃土地居住城下町的,而将土地与生产量连接起来的制度就是石高制。幕府通过检地,确定每一个领主的土地生产量和石高量,将土地交给农民耕种,每年按照比例给土地领主上缴税收。这样,尽管大名、家臣、武士离开了土地,但仍能保证自己获得稳定的税收,他们每年都能从农民那里按照石高数领取年贡米。总之,以石高制为前提实现的兵农分离制,铲除了日本社会以下剋上的社会根源,使幕府集权的统一政治得以巩固,从而保证了幕藩体制顺利实施。
2.石高制是将军与大名、大名与家臣团之间主从关系确立的基础,也是农村社会关系形成的条件,是幕藩体制建立的保障。石高制的实施,使各大名、家臣团的领地不论面积大小、生产力状况如何,都可以用具体的石高数量表示出来,比如贺藩前田家拥有120.5万石的领地,萨摩岛津家拥有72.87万石的领地等,即使是最小的大名也都有具体的石高数领地。这种将领地以石高数确定的方法,使主君之间的“御恩”关系得以实施。所谓的“御恩”就是将军赐予大名及家臣领地即“御”,大名和家臣领取土地后要对将军、大名尽相应的义务即“恩”。在“御恩”关系中,义务的多少,由他所获得的领地的量的多少来决定,获得的领地多,承担的义务就要多。而把获得的领地与承担的义务联系起来的关键因素就是石高,幕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一定的石高量及应承担的义务量。比如,从各藩向幕府服兵役的情况看,幕府规定,1000石的旗本应出军役枪2支,弓1张,铁炮1门,总人数23人的阵容;1万石的大名骑兵10骑,炮20门,弓10张,枪30支,旗2本等规定。[6]其他应承担的义务如参觐交代等也都根据其拥有的石高量来决定,使将军与大名的主从关系被牢固确定。
从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来看,领主将领地授予农民耕种,农民则以“一地一作人”的制度被固定在土地上世代耕种,但要根据自己耕种土地的石高量向领主缴纳税收,一般是按照五五或六四的比例缴纳。这就改变了以往“本家—领家—庄官—名主”等重叠支配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从而消除了农村的土豪劣绅等中间阶层对农民的剥削,农民成为土地实际耕作的主人,成为拥有土地使用权的阶层。
3.石高制是改易转封策略实施的基准,是幕藩体制建立的关键。改易就是没收大名领地,转封就是转换大名领地,改易和转封政策是幕府控制大名的重要手段,它使幕府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撤销对自己有威胁的大名、产生新大名及将不同大名配置在不同位置,一方面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加拥护自己的大名力量,另一方面减少敌对大名的数量和力量,是幕藩体制建立、巩固、发展的保障。改易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幕府强有力的统治,但是要保证转封政策的实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如何实现被“命令”转封的大名及其他必须带领的家臣、武士一起转封,使他们从某一领地转封到另一领地,而获得的收入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确保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失,使他们“和平地、心甘情愿地”转封。否则,让他们无条件地放弃“私领”转封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幕府必须采取一种能掌握他们在自己领地获得收入量的方法,然后在确保他们收入不变的(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幕府大都通过转封减少外样大名的收入)情况下进行转封,从而使他们愿意接受幕府的转封安排,也实现了幕府对大名的控制。石高制的实施满足了幕府和大名这种客观需要,因为通过石高制使每一块儿土地都被标识出米的生产量,确定大名地位的标准不再是占有土地的量,而是石高量。因此,将军可以将大名任意转封,发配到任何一个地方,也可以通过改易后出现的剩余土地产生新的谱代大名,从而实现自己的集权统治。
4.以石高制为基础,建立了幕藩体制下的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从纵向上看,不同于日本封建社会的大化改新时期的土地国有制——班田制,也不同于中世纪时期的土地私有的庄园领主制。从横向上看,它不同于中国和西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贯彻始终,实现全国土地的大一统的形式,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小农。西欧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贯彻始终,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庄园,封建领主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国王只是一个大封建主,作为国王的封臣,大封建主的领地超过国王者并不鲜见,中央王权衰落,地方分裂割据严重。而幕藩体制下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则具有其鲜明的独特性:第一,将军独揽全国土地所有权,实现土地的集权性管理。将军不仅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领地,全国所有土地都建立在将军分封的基础上,大名的土地是由将军授予来“管理”的,即所谓的恩赐。将军和大名之间以石高制的形式联结起来,将军有权转封和改易大名。正如延宝五年藤堂氏在一个告示中说:“我等暂时的国主,田地乃侍候幕府之物。”[7]直至大政奉还,将军的这种集权地位一直保持着。第二,封建领主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却失去了使用权。大名在接受了幕府的恩赐后,得到土地,并与将军形成主从的御恩关系,按石高数的比例服兵役及其他杂役,但藩国无需向幕府纳税,并有权在本藩制定法律、支配土地收入等,尽管这种权力是将军授予的,是替将军管理土地,但毕竟赋予了其相当的权力。但是,领主却要按照居住城下町的原则,被迫离开土地,成为远离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群体,使其成为“盆栽花木”。第三,在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下,农民成为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者。由于石高制的实施,使武士离开了土地居住在城下町,因此他们只能拥有土地,但却不能使用土地。而百姓却是使用土地的主人,尽管他们没有所有权,但他们在经济上可以在自己的份地上从事生产并收获产品,法律上这种经济权是世袭的,即拥有世袭的耕作权,这样就带来了权力与财富的逐渐分离。
三、思想文化要素:朱子学的官学化
朱子学理论是一种小自日常起居大至世界本体,都遵循的上下等级之分的理论,这种等级贵贱是天意、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在朱子学的影响和熏陶下,人在思想上会麻醉并完全沉醉于这种尊卑观念的统治。天理与人性,气与人欲,法规与规范,物与人,人与圣人,知与德,德与政治,这些都直线式连续着,在道德优位之下,都显示出一丝不乱的排列。“便在它那里有着一种冲击一部就几乎能破坏全部结构的整体秩序性。”[8]朱子学伦理道德,正好为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这种发端于中国大一统的封建制度的土壤中、成为中国封建君主统治有力的思想武器的朱子学最初传入日本之际,只是附庸于佛教的单纯理论。由于幕藩体制的完成,改变了以往不同的封建制度形态,形成了“将军—大名—家臣—百姓”的中央集权统治。政权的统一性和集权性,必然带来世界观和日常伦理的变化,也随之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当时,尽管有比较发达的佛教和神道教等各种思想体系,但是幕藩体制建立起来的以将军及大名为最高顶点的被细分化的家臣团的身份构成体系、成为幕藩体制支柱的“士”相对于农工商三民绝对优越的四民等级制度,要求严格的思想强化为根基时,朱子学的等级观念和尊卑伦理道德是佛教和神道教等思想无法替代的。因此,这种大一统天下和过去大大小小的天下共存的镰仓幕府、室町幕府不同,为幕府系统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学一元政治伦理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体制基础。[9]这样,长时间从属于佛教、只是被贵族和僧侣所感兴趣的朱子学,成为幕藩体制下政治的学问和实用的学问而独立起来,其最大的使命就是克服了中世“下尅上”为主流的世界观,解决了德川幕府建立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从将军与天皇之间关系看,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吸纳了朱子学理论,使将军相对于天皇的权力变得合理化。天皇在精神领域依然具有最高位,为了成为精神权威的象征,天皇的主要任务就是钻研书卷,将礼仪发扬光大。而其他的社会职能如管理社会安全、经济发展、外交等一切事物均由天皇授权“征夷大将军”行使,同时为了确保将军能够完成“管理国家、保护国家”的使命,就需要有广袤的领地作为财政的保证,需要有一切政治的大权等,这样将军的权力就变得神授化、合法化。而朱子学的理论中强调上下尊卑,维护等级秩序具有合理主义思想,无疑给将军对全国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缓和了将军的霸权统治带来的社会矛盾。
2.从将军与大名、大名与武士及四民等级秩序上看,朱子学的尊卑观念为大名服从将军、武士服从大名、下级武士服从上级武士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将军、大名、武士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御恩、忠诚的原则下被确定下来。
当时的学者称整个日本为“天下”,诸藩一般被称为“国”或者“国家”,统治天下的是天子,统治各国的是“国主”或者“国君”。但是,天子授将军以统治权,对于国君来说,称将军为“大君”。关于天子或者大君与国君的关系,《本佐録》中记载:“国主之预国如天子之顺天道而预天下。是又可思为安稳万民,为天下之尽忠也。”[10]由此看来,二者是上和下或者全部和部分的关系,当时,天下也好、国家也罢都是从超越的主宰者“天”那里获得权力,这是普遍的共识。这种王权神授的观点,如山鹿素行所论:“三民兴起,专己之欲。农欲全养而怠业,或凌弱而侮少;百工欲高利而疎器;商贾逐利而行奸曲。是皆湏己欲而不知其节。盗贼争论不已,从其气质而失人伦之大礼,故立人君以受其命,因风俗而行教化。故人君为天下万民立其极,非为人君一己之私也。”[11]文中所谓的人君是大君和国君的统称。作为接受天命的人君的职务如熊泽蕃山所言:“要有像人民的父母般的仁爱之心,施行仁政是其天职。”[12]即所谓的实行“仁政”,人君必须是“仁君”。当时的政治没有法治,基本上都是以德治为基准。但是,不论是怎样的“仁君”也都不可能独自行使权力,必须要由有能力的人士担当各个部门的职位,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臣”,具体来说就是武士阶级,臣的天职是辅佐人君施行仁政。武士的作用已不再是征战疆场,而是通过儒学的教育使他们成为教化阶级,即前文山鹿素行文中所言,“教化风俗因所”的意义,对于人君而言,是辅佐人君的武士阶级更为妥当。由此可见,朱子学成为协调将军、大名、武士关系的重要思想武器。
同理,农民种地、商人经商这是天经地义的,为主君服务,不得有非分之想。这也是在朱子学万物“理”的支配下形成的思想观念。因此,朱子学就成为解决德川幕府遇到诸问题的钥匙,成为麻醉人们的思想工具。如曾经是一位禅宗僧侣、后来成为儒家思想教导者、德川幕府的学者兼书吏的林罗山就曾这样论证武士统治的合法性:“天在上地在下……任何事物都有一种秩序来把在上者与在下者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就不能允许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弄乱……武士、农夫、工匠和商人这四个阶层的区分……就是天理的一部分,是圣人(孔子)所教之道。”[13]
四、社会关系要素:四民等级秩序
为了保证社会有序地运转,使社会各层面的人都能够各尽所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再去篡权夺位,不再你争我斗,避免下剋上的局面。德川家康夺取政权后,完全继承了织丰政权确立的兵农分离制,利用朱子学的等级尊卑观念,在制度上和精神理念上将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分成等级不同的四类群体,即士、农、工、商,每个阶层间都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自己的范围内,各尽其责,世袭相传,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1.武士阶层
武士阶层是四民统治秩序的最上层,即统治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6%。他们是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有权威、受尊敬的阶层。德川时代是在战国纷乱的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将军与大名、大名与大名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依然离不开武力和残暴的斗争,社会的主角理所应当是持刀上战场的武士,加之这些武士也是德川政权的奠基人。因此,德川政权赋予武士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权威和地位,其权威性表现在,一方面,所有武士均可以佩刀,而且对平民可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佩刀既是权威也是一种荣耀和光环;另一方面,武士可以称姓,在日本社会普通人是不可以有姓的,因此能够称姓是其崇高地位的象征。
2.农民阶层
农民即百姓,占总人口的80%—85%,在四民等级中是仅次于武士的重要一级。由于兵农分离而确定的兵农主从关系,使农民阶层处于被强制耕作、强制负担、紧缚于乡村土地上并禁止拥有武器的被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百姓身份是一种职业、负担、居所等被固定的身份。[14]他们世代耕种于土地上,是封建领主、武士和商人的社会支柱,但农民依然无法改变的是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地位。为了确保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禁止农民移居,从丰臣政权开始就制定了《身份法令》(1591年),限制百姓、町人的流动。家康时代幕府又制定了《乡村法令》(1602年、1603年),制止农民的逃散等,1635年《武家诸法度》的修改,使农民强制性地被固定于土地上,百姓的支配地位被确定。在百姓身份、地位被确定的同时,幕府还通过强化尊卑的身份观念实现对农民的统治,一方面强化礼仪的秩序,一方面从服装上限制农民。
3.町人阶层(工、商阶层)
工、商阶层是四民等级秩序中的最底层,工指手工业者,商指商人,商人和手工业者又统称为町人。关于町人的含义,北京大学刘金才教授指出:所谓町人,在广义上通常指自中世纪初到明治维新以前,居住于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狭义上则专指近世的城市商人。[15]本文所指的是广义上的町人。德川时代町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世袭身份等级,他们被强迫居住在城下町。町人阶层是四民等级秩序中地位最低下的,即政治侏儒,仅比贱民高一级,这是因为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腐蚀剂,商业的发达则直接威胁幕藩领主体制。但是尽管幕府想尽办法将商人置于社会底层,但幕藩体制本身却为商人的生存和强大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町人阶层在商品交换中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成为经济巨人。在德川时代末期,有一半或者将近三分之二的(农)产品是以不同形式在市场上销售的,使商人垄断了社会财富。正如美国学者康拉德所说:“尽管在统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伦理层级中,他们的正式位置是在最底下——“士农工商”的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控制着最多的自由决定财富的社会成分,仅次于高级武士自身。”[13]因而有“大阪的富商一怒,大名为之心惊”[16]之说。
五、对外关系要素:锁国体制的确立
幕藩体制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保持二百多年的持续稳定,除以上论述的内部要素外,还得力于外部条件即锁国体制的实施。
在实施锁国体制之前,幕府是非常鼓励对外贸易的。家康继承了秀吉的政策,期望和世界各国实现广泛的和平贸易往来,或者请英国人做政治顾问,允许在江户设立荷兰及英国的商馆;或者给外国来的商人颁发朱印状,招聘造船设计师等,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兴盛。然而,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对幕府的统治却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形态和经济两个方面:
1.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基督教传入日本并得到迅速传播,到天正十年(1582年),信徒总数达15万人,大小教堂有200所左右,传教士75人之多。各地都设有神学校、修道院等教育机构,可谓盛况空前。[17]这是因为日本人民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乱,给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当他们接受基督教后,感受到了心灵的抚慰,因而积极投入到宗教世界中。同时,当时战国林立的各诸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也不惜奖励与贸易密切相关的传教活动,尤其是得到了织田信长的保护,使其得以迅速传播。然而,基督教宣传上帝的权威与人人平等的思想,却违背了幕府的神国思想及等级身份制度,尤其是天主教强调神权高于世俗权力这一点,威胁着很多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信仰,要求人们对于很多长期以来备受推崇的传统价值追求作出重新判断。尤其是西部的很多大名及家康身边也有十几个大名都虔诚地信仰基督教,这是统治者家康极其畏惧的事情,因为具有离心力的外样大名的藩统治从一开始就威胁着幕府政权,他们的思想解放意识对幕藩体制的稳定有巨大的威慑力。因此,基督教思想的广泛传播是统一政权的德川幕府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将基督教看作是一种具有潜在颠覆力的宗教,出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目的,幕府决定下达锁国令。
2.经济方面。基督教最初传入日本之际,尽管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但统治者没有限制其发展,因为这种教义的传入是伴随着西方商业和贸易开始的,正所谓“商教一体”。家康又是一个非常会理财、具有极强经济头脑的政治家,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因此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奖励的政策,内外交流颇为活跃,发展了朱印船制度,扩大了海外贸易。但是,对幕府的统治而言,海外贸易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壮大了幕府实力,但另一方面却给幕府的统治带来了挑战,体现在外样大名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前文所论述,幕藩体制是幕府和二百六十多个藩共同占有国家土地而形成的封建等级制度,这种制度的维持是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依靠幕府强大的实力和各藩相对弱小的实力来实现的。因此,控制藩国的经济发展并保护自然经济、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幕藩体制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而日益扩大的海外贸易在壮大幕府经济实力的同时,更使大名尤其是西部大名在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这对幕府统治形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海外贸易促进了商品的交流和货币的流通,导致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这些都不是幕府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在幕藩体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与贸易引发的日益增长的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下,在幕府和藩国力量此消彼长的角逐中,幕府决定实施锁国战略。
基于此,幕府决定锁国,但是锁国的过程是漫长的。面对日益发展的基督教及其对幕府统治带来的危害,幕府于1612年向直辖领地发布了禁教令,并于1613年把禁教令推及到全国,展开驱逐教士、毁坏教堂、强迫改宗等大规模破坏活动。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打击信教人和禁止贸易等事件,如1621年禁止日本搭乘外国船出国和进口武器,1622年将平山常陈等人处以火刑,使长崎发生大规模殉教事件,1623年英国关闭平户商馆,1624年禁止西班牙船入境,1628年滨田弥兵卫在台湾与荷兰总督斗争,1629年长崎开始“踏圣像”以考验人们是否信基督教,1630年禁止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入境,1631年规定“奉书船”制度等。在这样一系列政策的基础上,幕府于1633年至1639年先后颁布了五道“锁国令”,于家光时代最终完成了锁国体制。
六、结论
综上所述,幕藩体制是一个以将军占据权力最高顶点的、由藩国共同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经济上通过石高制建立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思想领域建立了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对外制度方面实行了锁国政策。在这个制度框架下,幕府和藩之间始终有一个实力的角逐,幕府集权是幕藩体制实施的强有力保障,在幕府和藩的天平中幕府实力始终要高于或远高于藩的实力,才能确保幕府的集权统治,因此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强本弱末,维护其统治;经济上,以石高制为基础建立了以将军为至高点支配全国土地,以大名为重要支柱分管近四分之三的领地,形成了幕府和藩、将军和大名、大名和本百姓之间的封建主从关系,它排除了中世纪的多重剥削阶层,使剥削关系变得单纯化。日本学者北岛正元指出:“处于金字塔式封建所有制顶峰的将军集中了全国的土地所有权,所以石高统治的确是最恰当的统治形态。”[7]因此,石高制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产生的基础,而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则是幕藩体制建立的重要经济基础。思想文化方面,朱子学的官学化成为封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后,有力地协调了天皇和将军、将军和大名、大名和家臣、上层阶级与被统治的百姓阶层之间的关系,使各阶层能在一个“和平”的理念中生存,士、农、工、商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因此出现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避免了个人游离于国家和社会,促进了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形成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成为了支撑幕藩体制强有力的思想支柱。社会关系方面,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秩序的建立,避免了战国时代下尅上的社会现象,使社会各个阶层的每个人都被固定在一个点上,各尽其责,服从和效忠幕府的统治。锁国政策一方面否定了西国外样大名过去以来一直保持的外国贸易权,由于海外贸易带来的经济富裕化被阻止,纳入了幕藩体制的体系之中。[18]另一方面阻断了外部的影响,是幕府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领域等制度实施的保障,起到了维护封建制度壁垒的作用。
在幕藩体制框架中,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要素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干扰的,相反它们之间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的。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他们是系统中任何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随之带来的就是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个体制将随之瓦解。因此,幕府为了幕藩体制的长治久安,维持自己居于至高点的统治,就要小心翼翼地呵护这个庞大的系统。
[1][日]高桥富雄.征夷大将军[M].东京:中央公论社,昭和62.148.
[2]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M].北京:三联书店,1957.5.
[3][日]忠田敏男.参觐交代道中记[M].东京:平凡社,1994.8-63.
[4][日]芳贺揙.文明偲偟偰的德川日本[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3.136.
[5][日]井上准之助.近世封建社会的研究[M].东京:名著出版,1993.12.
[6][日]佐藤信,五味文彦,等编.详说日本史研究[M].东京:山川出版社,2010.243.
[7][日]北岛正元.土地制度史Ⅱ[M].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序言,5.
[8][日]丸山真男著.日本政治思想史[M].王中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9.
[9]潘畅和.朱子学在日本江户时期急速兴起的原因及特色[J].东北亚论坛,2005,(5):83.
[10][日]日本经济大典:第3卷[M].东京:史志出版社 ,1928.17.
[11][日]内田繁隆.解题《山鹿素行集》(《近世社会经济学说体系》)[M].东京:诚文堂新光社,1935.172.
[12][日]野村兼太郎.解题《熊泽蕃山集》(《近世社会经济学说大系》)[M].东京:诚文堂新光社,1935.9.
[13][美]康拉德·托特曼著.日本史[M].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9,226.
[14][日]峰岸贤太郎.近世身份论[M].东京:校仓书房 ,1989.101.
[15]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
[16][加拿大]诺曼.日本维新史[M].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56.
[17][日]坂本太郎著.日本史[M].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59.
[18][日]藤野保.德川政权论[M].东京:吉川弘文馆,20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