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佛在重庆
2014-03-06孙群豪
孙群豪
陈之佛在重庆
孙群豪
1942年3月,陈之佛在重庆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这场名为“陈之佛国画展”的个展在夫子池励志社举行。一共上下二层的展厅里,挂满了陈之佛的代表作和新作一百余件,其内容全是精心创作的工笔花鸟画。在此之前,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作品都是零星展示,参加一些书画邀请展览,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展出却是第一回。
与预想的相比,陈之佛的画展在画坛和艺术界引起的震动超乎寻常。画展吸引了很多参观者,可以说观者云集,盛况空前,每天都有不少参观者一直观赏到闭馆时间已过,仍不肯离去,还有一些参观者要求主办方延长画展时间,言辞极为恳切。当然,社会各界如此热切于陈之佛首度个人画展,也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抗战已经进入持久阶段,人们需要一种定力来平衡自己的心境,而观看画作显然是个极好的选择。感受到社会各界对自己的厚爱,感受到众人对自己创作成果的高度肯定,陈之佛欣喜不已。对于一向不善流露骄傲的他来说,尽管表面上他仍显得淡然,但心里也不免充满了自豪和欣慰。
画展举办期间,不仅画坛和学术界的人士为之吸引,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社会名流都极为佩服,并纷纷为陈之佛的作品以及这次画展题诗作词,其热烈的反应前所未有。如作家郭沫若,一口气为陈之佛的多件作品题写下了诗作,给画作《梅花图》题诗曰:“普天皆冰雪,依旧要开花。花开能几时,转瞬逐风砂。但能图快意,自我为荣华。刹那即悠久,悠久亦刹那。”给画作《梅花宿鸟》题诗曰:“天寒群鸟不呻喧,暂倩梅花伴睡眠,自有惊雷笼宇内,谁从渊默见机先。”给《碧桃月季》题诗曰:“月季何娟娟,碧桃殊绰约,纵无知音赏,双双有黄雀。黄雀常相伴,花开永不落,任寒暑易,此情相照灼。”又如画家陈树人为《竹菊图》题诗道:“谁知现代有黄筌,粉本双钩分外妍,艺术元凭人格重,似君儒雅更堪尊。”艺术家汪东、沈尹默给《玉兰鹦鹉图》题诗云:“肯以颓唐趋俗媚,要从刻划见天真。老莲家法君余事,直逼黄筌与问津。”孔子嫡传后裔第七十七代孙,且受封为世代相袭之“衍圣公”的孔德成,也为陈氏《茶梅寿带》画作赋诗一阕:“琼葩难拟雪衣裳,悄立东风一树香,但有落花飞数片,还应点作寿阳妆。”除此,傅抱石、柯璜、李寅恭、张宗祥、方东美等名流也纷纷题诗,诗中多有赞语。他们认为,陈之佛画法独具、意境深远,不但继承了五代时期徐熙、黄筌的优良传统,又广泛汲取了宋元时期钱选等诸家之长,并受明代吕纪、清代恽南田的影响,既博采众家之长,又独树一帜,把传统的工笔花鸟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贡献非凡。
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人持不同意见。当陈之佛凭着这次画展,更享盛誉之时,国画界的一些人士却对陈之佛过于借鉴某些外国技法而颇有微词,认为陈氏再这样画下去,很可能会丢了中国传统的笔墨技法,甚至会带动画坛的风气,导致盲从外国技法的风气。事实上,这些微词都是因为他们旧的习气过深,思想保守造成的。
针对这些论调,一些专家、学者主动撰文,对陈之佛的画作进行艺术评论或学理分析,以充分肯定的方式给予正名。他们认为,陈之佛在艺术创作上成就卓著,应该在当今画坛乃至艺术史上享有较高的地位。这些专家、学者的评论文章,多半发表在影响颇巨的《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如美术评论家李长之在一篇题为《从陈之佛教授画展论到中国花卉画》的长篇论述中,这样写道:
陈先生的画风,值得称道,因为他的画可以说够得上不苟了。……陈之佛先生的画,却有许多地方是新的,例如他的树干,全然超出前人的蹊径的。《暗香疏影》一幅,很可作这纯粹新作风的代表。他惯于用细线条,又因为造诣于图案者之深,他的树干故意写作平面之形,精细到连木纹也看得出来了。……在花卉中开辟了这样崭新的作风,把埃及的异国情调吸取来了,这是使人欢欣鼓舞的!我盼望陈先生充分发挥它,千万不要惑于流俗而放松它。艺术是有征服性的,但新的作风必须以坚强的意志为后盾。
著名学者潘菽在《从环中到象外》这篇文章中评述道:
陈之佛先生是我所认为当代作手中最具艺术风度的一个人,他的工作态度是很认真、沉着的。他在作画时确守着规矩、准绳,不让自己的步伐有一点错乱,这是他每一幅画面上无论谁都能看到的,他已由熟而巧,浸浸乎出我入纪了。譬如这次展览的作品中,颇有几张足以与前人名作什臂人林。……他的作品从未公开展览过。我们希望社会人士能认识到他这次的展览是数年来最具特色而值得注意的一个。我们更热切地盼望中国画风的转变将自此而开始。
而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则评论说:
陈之佛先生运用图案意趣构造画境,笔意沉着,色调古艳……能于承继传统中出之以创新,使古人精神开新局面,而现代意境得以寄托。
画展影响巨大,很自然地引起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关注。在画展举办期间,一些政府官员,甚至是教育部长都来参观,还自己掏钱买了陈之佛的作品。陈之佛一向坚守清白,从不阿谀,与政界也极少往来,所以对政府官员的前来“赏光”并不过于热情,但他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变得匪夷所思。
约莫在画展结束的几个月后,陈之佛忽然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来函,对他提出邀约,请他前去教育部谈话云云。因陈之佛不知原委,也是礼貌起见,便抽空去了那里,方才知道原是好友吕凤子先生出于好意的推荐,后经教育部同意,准备请他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也算是教育部“名人治校”之一项。陈之佛闻之不由得大吃一惊,怔在那儿,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
其时,因日寇侵华,原在杭州的杭州艺专西迁,途中受命与北平艺专合并,成立了国立艺专,且落脚在重庆璧山。经过这一番折腾,国立艺专的规模已大不如前。吕凤子曾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组主任、教授兼该大学研究院研究员,与陈之佛相熟。后吕凤子创立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并任校长,日军侵占丹阳后他率部分师生西迁,创办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后又在1941年2月兼任国立艺专校长。据记载,1939年,吕凤子曾为美国总统罗斯福作过一幅人像,栩栩如生的神态,把中国画的墨韵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罗斯福极为赞赏,除来函表示感谢之外,还捐赠2000美元,而吕凤子即将此款用于正则艺专的办学。1942年7月,吕凤子坚辞国立艺专校长一职,把精力集中投入正则艺专之中。
陈之佛知道自己的“底细”,也有他的办事原则,那就是一辈子不做官,也不愿意做行政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擅于此道。教育部长陈立夫对他提出这一提议后,他稍加冷静,便毫不犹豫地推辞了。陈立夫一再劝说,而他仍一再推辞,两人各持一端双方僵持了好久。为了顾及对方面子,陈之佛最后说我回家再考虑考虑吧,到时会给部长答复。回家后的陈之佛开始着手写一封谢辞信,准备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陈立夫又派了顾毓琇教授前来劝说,希望他能够听从教育部长的安排,他接下这个差使,尽管对顾毓琇教授陈之佛表示尊重,可对这项提议他仍然抱定宗旨,坚辞不受。
那时的傅抱石常来陈之佛家中叙谈,这天同样来到陈家拜访,陈之佛便跟他说起此事,并就该怎样推辞,听听他的意见。傅抱石仔细听完陈之佛的讲述后,觉得可以采取将计就计之法,即我可以接受这一提议,但教育部也应该答应我的请求,尽管我的请求要价比较高,但都是为了办学。傅抱石说,如果陈立夫答应这些苛刻的条件,那么你就干,反之就不干。陈之佛认为此计可行。经两人一番商议,陈之佛遂向教育部提出三项较为苛刻的条件,并认为这三项条件对方是无法予以满足的:一是把国立艺专从目前较偏僻的璧山,迁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即与沙坪坝和中央大学隔岸相对;二是政府掏钱,较大幅度地增加学校经费;三是把国立艺专改成学院,扩大招生规模,同时提高学校品质。
三项苛刻的条件送上去之后,陈之佛起初还有些自鸣得意,觉得如此一来,等于把皮球踢给了对方,只需静等对方表示无奈即可。未料,这三项条件送上去不久,教育部即有回音,说这些条件都可以满足,陈教授无须多虑云云。等到当年7月,陈立夫连聘书都送了过来。谁让他先开条件呢?如今全都满足了你,你还有什么话语可说?此番情状下,陈之佛只能硬着头皮上任。
陈之佛一向信守承诺,办事又非常认真,他认为既然接任了校长一职,那就只能全力以赴把学校办好,把一切事务都处理好。自己不图别的,只图为国家多培养一些人才,这不也是自己多年前的愿望吗?这样一想,他的内心便安宁很多,占满心头的唯有关于办校的各种念头和设想,心里也涌动起干一番事业的激情。
有了教育部的允诺,陈之佛首先着手迁校。磐溪依山面溪,环境幽美,交通还算便捷,刚修筑启用的汉渝公路即从磐溪经过。陈之佛在磐溪借用了龙脊山麓的果家园,还租用了一家庄姓大宅院——这座大院以院墙又高大黑而在当地闻名,被当地人称之为“黑院墙”,房舍较为宽敞——把学校迁到了这里,然后又花大力气延揽人才,强化师资力量。他专函发往贵州,请来好友丰子恺来这里担任教务长,又请傅抱石担任校长秘书兼中国画史、画论教授,请画家黄君璧担任国画科主任,画家秦宣夫担任西画科主任,画家王道平担任应用美术科主任,还请来吴作人、李可染、赵无极、蒋仁、邓白、王临乙等画家来此任教,可谓名师云集,在重庆艺术界顿时声名大振。
陈之佛一心扑在办学上,不惜到了人财尽空的状态。由于忙于办学,他无暇再著书作画,简陋的画室里再也不见他的身影;而当学校一旦需要经费时,他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家里的钱,不求归还地投入了进去,那场“陈之佛国画展”上的卖画所得全都贴补到办学经费之中,仍有缺额,他恨不得以个人名义四处借贷。由于学校百废待兴,陈之佛经常要与人商量各种事情,他的家里经常聚集了很多人,每餐吃饭都要开两桌,热闹非凡,使不得不为之忙成一团的夫人胡竹香感叹:“我开包饭桌哉!”即便为了学校已经付出了这么多,陈之佛始终毫无怨言,相反,学校每一项进步都让他颇为欣喜。
然而此时的教育部却越来越不像话了,除了同意陈之佛把校址迁到磐溪之外,另外的两个条件都不再兑现,陈之佛数度催促,仍未予重视。由于经费申请石沉大海,连基本的办学经费都到不了位,教学设备、材料都无钱购买,即便勉强开了课,也是缺这缺那,连教材之类都没有,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得悉学校发生了困难,个别债主还找上门来要求还钱,此时的学校和陈之佛已无力还债。而在乱局之中,傅抱石又提出身体欠佳,不能再到学校履职,使得办理校务人员奇缺,陈之佛只得调派蔡达代办若干秘书工作。诸事缠身,穷以应付,陈之佛被搞得苦不堪言,原本羸弱的他更加消瘦,连痔疮的老毛病都犯了,经常大量出血,疼痛难忍。但为了学校,为了那么多的师生,他只能强打精神,忍着病痛坚持工作,经常往返于沙坪坝和磐溪之间,身边只有蔡达陪伴。蔡达十分担心陈之佛身体不支,会突然间病倒。
让陈之佛颇觉欣慰的是,艺专的师生们十分支持和信任他的工作,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陈之佛也一向尊重教员,爱护学生。他还在繁忙的事务中尽最大可能腾出精力来,革新课程设置,提高教学实效。为了着重培养学生的造型和创作能力,他在国画专业中增开“实象模写”一课,相当于西画的素描,即当场面对预先布置的折枝花木,用笔双钩,画白描写生画,训练学生对基本物象的认识,以提高写生能力和笔墨技巧。陈之佛规定,新生进校后的第一学年,首先就学这一课。本科生入学考试时,除了自由作画一幅外,也增考这一项内容。事实很快证明此法确实有效。艺专毕业生、后为台湾著名画家的张光宾后来回忆道:“雪翁待人诚恳谦和,平易近人;治学精勤恒毅,严谨踏实,凡是接近他的人,都会感觉到他的仁厚慈蔼,如沐春风化雨之中,受他教的人,莫不为他敬谨恒毅的治学精神所感悟。”张光宾回忆,那时的他还经常与同学们一起,来到沙坪坝陈之佛寓所,在他的简陋画室里观其作画,以“亲炙风仪”。可惜,一年半后因陈之佛的去职,这样美好的情景就此不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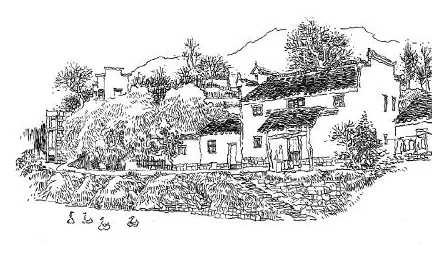
正如张光宾所言,艺专学生心目中的陈之佛,永远是那么的慈祥亲切,那么的谦和平易。在校园里,只要他出现,就会有男女学生上前围住他,向他问好,向他请教,哪怕是没有事情也希望能与他说上几句,以此获得温暖。此时的学校已面临诸多困难,无疑也影响到了学生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可是因为陈之佛已把学校遇到的困境实事求是地对学生们说清楚了,学生们也不再有怨言,反而觉得校长的不易,对他又添了几分敬重。
一位名叫叶文熹的学生——后来的他曾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编室主任——在回忆那段经历时十分感慨。叶文熹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河北保定辗转逃亡到四川綦江的,因爱好美术,写信托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学同学替他在国立艺专报了名。他说:“当时的我来报考艺专,因交通不便,赶到考场已经迟了,文化课已考试结束。可是我由乡间出来,是抱着宁肯饿肚子也要学美术的决心赶来的,便提出要见校长,不见不肯走。接待的老师被我的决心所感动,就带我到陈校长那里。可是我心里很害怕,因为到底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乡下孩子。但一见校长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顿时觉得轻快不少。待我说明原因,陈校长一直端详着我,看到我那一双经过长途跋涉、后跟已磨破的草鞋,和农村孩子的简单行装,看得出老人家深深感动、对我同情了。他让我坐下,并倒了一杯水给我,和教师一起看了我的画,轻声议论了几句,便对我说:‘我们破格同意你马上去参加素描考试。’并叫我第二天到他家中单独为我作文化课补考。次日,校长亲自为我监考,叮嘱家中孩子不要打搅我。见到这样亲切的校长,真使我激动不已,更给我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顺利地答完试卷。我终于考上了艺专,还是榜上第六名。这喜悦,这兴奋,实在无法形容。几十年来我总是怀着尊敬的心情回忆这段往事,陈校长的为人、品德,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激励着我奋发地为艺术事业而奋斗。”
在国立艺专,凡是与陈之佛有过交往的师生,有类似叶文熹这样感受的人自然不止于此。可以说,在国立艺专历任校长中,尽管陈之佛在任时间短暂,但在动荡的年代相对稳定,这与他的沉稳、内敛、宽容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然而当局非但没有力解学校之困,反而接二连三地来找麻烦,让陈之佛忍无可忍。第一件事是给学校发来一道密令:“要防范《新华日报》推销;要求调查异党分子。”陈之佛虽非共产党员,他一向坚守独立、自由的品性,但对当局迫害青年学生的行为深恶痛绝,当训导主任问他究竟如何应对时,陈之佛的回答是:“坚决抵制,不予执行!”他还说,“我们应爱护青年,怎能让青年无缘无故地遭到迫害?”态度十分坚决。
第二件事是强迫各院校的校长集中受训35天,进行“防赤化”洗脑。接到这样的通知,陈之佛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也是对所有校长的极大侮辱。他当即拒绝去受训,宁可不当这个校长。
正是当局这次强令校长集中受训的做法,才使得陈之佛下定了辞去职务的决心。1943年10月7日,陈之佛正式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国立艺专校长职务的呈请,郑重地递了上去。然而教育部没有回应。此时的陈之佛已经铁了心,对方没有回应,他就再次递交辞呈,一而再,再而三地递交,前后一共递交了六次,都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回音。此时的陈之佛又累又烦,痔疮的老毛病再次作乱,出血量很大,无法下床视事,只能在家里养病。当局这才意识到确实无法挽留陈之佛,遂于1944年4月同意其去职。由此,陈之佛在国立艺专校长任上的时间一共为一年零九个月。陈之佛的辞职,自然引起了师生们的无限惋惜,但他们依然与陈之佛保持着密切的联络。
辞去职务后的陈之佛仍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然而担任国立艺专校长的这一经历,着实伤了陈之佛的元气,即便在很长时间之后,陈之佛也很不愿提及此事,以免心头郁闷。这是因为他不仅为校务累出一场大病,还因艺专办学期间所欠下的大笔债务弄得焦头烂额。这笔高达国币数十万元的债务虽然都用于办学,但陈氏认为是自己担任校长期间欠下的,理应由自己归还,不把负担转嫁继任者。后来,这笔巨额欠债直到几个月后陈之佛特意举办了第二次画展,用卖画所得的钱才勉强还清。郁闷的心理需要宣泄,陈之佛便画了一幅《鹪鹩一枝图》,以作品的形式记录自己这一年零九个月的遭遇。陈之佛把西晋大臣、文学家张华的《鹪鹩赋》抄录在该画作上,表达对当局的愤慨以及自甘清贫、淡泊自守的立场。
接任陈之佛担任国立艺专校长的是潘天寿。当潘天寿接受当局的任命,与画家谢海燕、倪贻德一起从浙江南部辗转来到重庆,来到沙坪坝“流憩庐”拜访陈之佛。陈之佛向潘天寿详细介绍了艺专的情况,包括迁址办学经过、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今后可能会碰到的问题等,言辞真诚。末了,陈之佛慨然叹曰:“唉,潘先生,不好办啊,我是苦头吃足了!”果不其然,潘天寿担任国立艺专校长之后,各种麻烦事蜂拥而至,他穷于应付,仍然未能让各方满意。此时的他真有一种骑虎难下之感。
时局仍然持续动荡着。1945年2月,重庆发生了“校场口血案”,郭沫若等人因要求民主、自由,在重庆校场口集会。国民党特务闻讯而来,与郭沫若等重庆文化界人士发生冲突,郭沫若等人遭到了殴打。由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拟发表《文艺界对时局的进言》一文,声援遭受殴打和迫害的文化界人士。发表之前,重庆文化界掀起了签名运动,陈之佛毅然在《进言》一文上签了名,以言明自己的立场。《进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后,国民党当局看见了陈之佛的名字,便派人三番五次地登门,强迫他发表退出声明,并刊登在报纸上,被陈之佛严词拒绝。4月,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一个所谓的“反签名运动”,又派人登门让陈之佛签名,被陈之佛再次拒绝。陈之佛的态度让当局十分恼火,多次派人对他进行恐吓,可陈之佛毫不畏惧,甚至做好了被中央大学解聘的准备。后来,随着形势越来不利于国民党当局,加之陈之佛在艺术界和社会上的巨大名望,当局不敢对他再有所轻举妄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山城重庆顿时沉浸在欢庆之中。而对于陈之佛一家来说,这日子是喜上加喜,因为恰逢陈之佛虚五十寿辰。画界朋友们得知陈氏寿辰来到,纷纷表示庆贺,当然同时也为抗战胜利而喜。徐悲鸿、吕凤子、汪东、柯璜、陈树人、赵少昂、黄君璧、傅抱石、杨仲子、傅狷夫、张安治等画友聚集在沙坪坝“金刚饭店”内,为陈之佛设宴庆贺,并纷纷泼墨挥毫,为寿星献出佳作。陈之佛极为感动,想到这几年多亏朋友相助,才让他历经困境而终有所成。
不久后,陈之佛接受了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等老朋友的邀请,前往成都举办画展,以庆祝胜利。在成都的文艺界人士特地举办了一场文化茶座,热情地欢迎他。此时正值抗战胜利不久,人们的心情都很激动,都认为从此以后不会再有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国家的一切也都会好起来,何况此时又逢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谈判,还签订了“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会议纪要”。因为每个人都对前途抱有极大的希望,因此无论是老友相见,还是谈论时局,人们总是相互微笑着,祝愿着。
陈之佛成都画展于12月1日开幕。开幕那天,花篮摆满了展览大厅外宽阔走道的两侧,是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四川省主席张群、女作家谢冰莹等各界名流前来参观,并向陈之佛表示祝贺,观赏的人群络绎不绝。这是陈之佛第三次举办个展,其盛况再次证明了陈之佛的艺术创作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可以说,这三次画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奠定了陈之佛“工笔花鸟画大师”的重要地位。
让陈之佛没有想到的是,日本虽然已经投降,但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乌云还没有散去。随着“双十协定”的被撕毁,内战即已开始,局势再度陷入混乱之中。陈之佛厌恶战争,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脸上堆满愁云。愤恨、苦闷、忧虑、彷徨……他甚至已不知道自己在这种情势下该做些什么。
按照当局的安排,中央大学及许多西迁的院校与国民政府机构一起,将陆续迁回原地。然而这么多人要走,想要找到交通工具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有权有势的大官、富豪们已经捷足先登,把原本就少得可怜的交通工具都抢占了。与其他教职员工一样,陈之佛一直在等待着返回南京的船票。直到1946年5月,陈之佛一家才分到了轮船上的一席之地——这是真正的“一席之地”,因为分配给他们的舱位只有一张床铺和一个只能席地而坐的位置,位置之间用粉笔划分,长不足丈许,宽仅三四尺。没办法,一家七口只能轮流到床位上去“享受”,其余的只能挤坐在放置在地上的箱笼包裹之上。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轮船甲板上跑动,直到该睡觉了也不肯回到船舱这沙丁鱼罐头里,而满腹心思的大人们则一声不吭地坐在船舱里,想到未卜的前途而忧心忡忡,至于轮船所经过的三峡美景,他们根本无心欣赏。
也就在这次行程中,乱世陋相又让陈之佛感慨万端。途中常听见有人在江边呼喊,那是因为轮船撞到了江中木船,被激流冲走的木船和尸体让陈之佛看得触目惊心。而在轮船上,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却在欢歌笑语、饮酒作乐,老百姓的苦难丝毫不会顾及。多灾多难的中国何时才能平安祥和啊?老百姓的苦难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陈之佛在心里默念着,紧锁的眉头始终没有舒展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