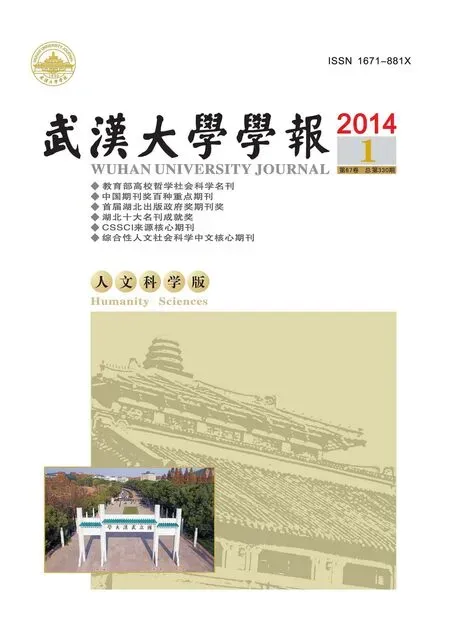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嬗变
2014-03-04吴正锋
吴正锋
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艺术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便被喻为“文体作家”*苏雪林:《沈从文论》,载《文学》1934年第3卷第3期。,长期以来其叙事艺术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并得到由衷的赞誉,但是对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艺术作全面的考察,特别是对其叙事艺术的发展变迁进行探究尚待深入。其实,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艺术也有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直至完美的过程,大致经历了由影子作者叙事占主体逐步转换为非影子作者叙事占主体、由情感的宣泄到客观化写作、由结构上的散化到实现情节的“突转”与“发现”、由正常时序叙事为主体到不乏叙事时空的错综颠倒等过程,表现了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的重大变迁和逐步成熟,同时也展示了其丰富多彩的叙事艺术形式。沈从文通过自己的艺术探求,将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一、 影子作者叙事与非影子作者叙事
按作者“自己的成分”的多少,我们可以将沈从文小说划分为影子作者叙事与非影子作者叙事。影子作者叙事指的是作品中出现有作者身影的叙事,而非影子作者叙事指的是没有出现作者身影的叙事。
沈从文早期小说创作中影子作者叙事特征较为突出。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描述自己初入都市的生活困苦,一是对乡村童年生活及军旅生活的忆往。这些小说叙事带有较明显作者“我”的自叙传性特征,其影子作者的叙事特征都较为突出。沈从文往往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进行叙事,为此,可以表达真情实感,但是作者也因此常常受到实际生活的局限,缺乏情感的节制,在艺术体裁结构方面也就无暇顾及。譬如沈从文都市影子作者叙事小说总体给人的感觉是事实写述的少,琐碎而雷同,沉闷而缺少变化,情感基调是悲苦的,所抒发的感情也比较直露。沈从文乡村题材小说虽然也真实地传达出童年及军队生活的独有情趣,故事清新,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是,由于作者过于拘泥于自己亲身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第176页。,必然带来结构上的拖沓散漫。由此可见沈从文影子作者叙事小说存在重大的艺术缺陷。
沈从文这些“自己的成分稍多一些”的小说,受到读者乃至于编辑的批评和抵制,沈从文自己也似乎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他在具有自传性的作品《一个天才的通信》里说道:“你们(指的是杂志编辑——本论文作者注)不希望知道我的生活的一切,他们(指的是读者——本论文作者注)更不希望知道这个……因为他们似乎觉得若果人的生活是如此,这平凡病痛的自曝是不可容忍的丑事”,“在过去,凡是我自己的成分稍多一点的,你们就不要,试问,不要,我还有勇气写下去吗?”在书店和读者两方面的压力下,沈从文对影子作者叙事题材小说的写作方式发生了严重动摇。
沈从文小说影子作者叙事的转变,更是他自身对创作艺术进行探索与思考,艺术观发生重大改变的结果。1928年10月,沈从文开始自我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他说:“冷眼的作旁观人,于是所见到的便与自己离得渐远,与自己分离,仿佛便有希望近于所谓艺术了。这不过是我自己所觉到的吧。”*《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冷眼的作旁观人”,“与自己分离”,即叙述者外在于人物世界,采用外部聚焦,采取第三人称叙事;或者采用人物视角叙事。这种通过非影子作者视角叙事,就能改变影子作者叙事仅仅局限于自身生活的描写和自我情感的宣泄,由影子作者叙事重视自身真实生活的描写和真实情感的抒发,转换到非影子作者叙事就有可能达到艺术的虚构与情感的节制,也即“有希望近于所谓艺术了”。可以说,《阿黑小史·序》的创作标志着沈从文创作艺术在理论上的自觉,预示着叙事视角的转换对沈从文小说创作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很少有评论家关注到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从此,沈从文创作开始改变拘泥于自己亲身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的叙事方法,非影子作者叙事的小说第一次占据主体地位,影子作者叙事的小说便开始退居次要地位,并一直保持到1938年,这是沈从文创作艺术的成熟期。沈从文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包括《边城》《萧萧》《丈夫》《贵生》等大量的艺术杰作。非影子作者叙事小说,作者采用“与物观物”的形式,作者的声音降低到最大限度,一切凝结为具象,借助于客体来表现主体,借助于具体事物的非目的性来窥视一切,呈现一切,去除一切人为的意识与目的,让读者去体验和感受,更能取得最大的艺术效果。譬如《丈夫》开篇写道:“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河中涨了水,平常时节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离岸极近,船皆系在吊脚楼下的支架上。”这里似乎不带任何主观情绪,而是一种客观呈现,这种无自我色彩的写作方式,一切随顺自然,叙事艺术达到极高的水准。沈从文这时期影子作者叙事小说明显减少,特别是那种第一人称“主人公”类型的小说就更少了,即使出现叙述者“我”,但也往往作为故事的参与者或者见证者,“我”的思想情感生活不再作为故事叙述的中心或主体。譬如《灯》《来客》《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年》《若墨医生》等便是如此*1939年之后,沈从文影子作者叙事小说又重新占据主体地位,非影子作者叙事小说又退居次要地位,这时沈从文小说叙事重新又显得凌乱芜杂,仿佛重新退回到1928年以前的叙事水平,其小说艺术成就整体呈现下滑趋势。。由于非影子作者叙事的成功运用,有力地推动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走向成熟,并形成属于沈从文个人的独特的艺术品格。
沈从文小说由影子作者向非影子作者叙事的这种转换是符合艺术规律的。朱光潜说:“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9页。这里“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在叙事视角上表现为由影子作者向非影子作者叙事转换,这样便有利于从叙事的“有我”转换为叙事的“无我”,从而达到艺术的“无我之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认为境界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而“无我之境”要比“有我之境”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因为这样便可以实现“物”“我”的浑然一体,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我想用此来说明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对其艺术的成熟也是十分恰当的。
二、 童真叙事与客观叙事
沈从文早期乡村题材和军旅生活题材小说的童真叙事较为明显,作者往往采用的是纯朴无知的儿童叙事态度,对故事作津津有味的叙述,显示出特有的“趣味”,沈从文早期小说的“趣味”的来源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与作者的童真叙事态度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童真叙事态度中,有时出现叙事的复调现象,作者表现出两种口吻叙事,一种是以少不更事、天真顽劣、蒙昧无知的经验自我进行叙事;一种是成熟以后的自我回首往昔生活,以成熟口吻叙述少年往事,即以叙述自我叙事,这两种叙事态度相交织,构成一种戏剧性的张力,形成一种复合的叙事态度,也就是叙事的复调现象。例如《更夫阿韩》中写弟妹们对阿韩为死去的流浪儿讨捐的反应。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两种叙事态度:一是少不更事、蒙昧无知的儿童叙事态度,嘲笑韩伯假慈悲,认为他“流老猫尿”;二是成年叙事态度,对儿童叙事态度的否定,称弟妹们为“不懂事”,并称他们的行为是“油皮怪脸”,表现了一种正义感。两种叙事态度相互交集,构成一种复合叙事,形成一种复调叙事。
有时,沈从文甚至只以少不更事、蒙昧无知的儿童叙事态度叙事,而将成年叙事态度隐而不显,但通过读者阅读后,是非感正义感自然而然产生,形成与一种反讽的更强烈的艺术效果。譬如《我的教育》写道:“今天又送来七个。大家似乎都很欢喜,因为这些土匪由团上捉来,一让我们分别杀戮或罚款,并且团上对于匪徒的家事全很清楚,不会遗漏也不会错误,省事许多。”作者是以少不更事的少年士兵的口吻叙述出来,有意将善与恶,是与非等等问题进行悬置,但读者却从这带着轻松甚至幽默的叙述口吻中,不难感受到其中的公平与正义、义愤与抗议,对于这地狱般黑暗的生活,作者以经验的自我展开轻松的叙述,越发显出反讽的效果。
沈从文早期都市题材小说具有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那种主观直露抒情的特点,结构与文字上的不节制是其最大的弊端。后来沈从文认识到这种写作方式的缺点,他说:“为愤怒(生活的与性格的两面形成),使作品不能成为完全的创作,对于全局组织的无从尽职,沈从文一部分作品中也与之有同样的短处。”*《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
沈从文在《阿黑小史·序》中正式亮出了“客观”写作的大旗,他说:“这一本小小册子,便是我纯用客观写成。”他在《一个母亲·序》里对于“客观”的创作态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只是以我的客观态度描写一切现实。”由于沈从文认识到“客观”对创作的重大作用,使他开始逐渐克服早期郁达夫自叙传创作的那种弊端,致使1928年之后,沈从文客观叙事在其作品中开始占据主体地位,艺术水准也大为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化写作是沈从文创作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沈从文小说的“客观化”是以冷静节制平实的态度展示人物的哀乐,也即是沈从文所说的“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契诃夫等叙事方法,不加个人议论,而对人民被压迫者同情,给读者印象鲜明。”*《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26页。契诃夫的这种客观叙事态度给沈从文以巨大影响,也是沈从文成熟期小说创作的主要叙事态度。
当然,沈从文的“客观”,绝非没有感情的倾向,并不是客观主义,其“客观”也不是没有道德评判。沈从文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页。然而这种感情倾向和道德评判并不是作者直接从中点明出来的,而是通过叙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沈从文“客观化”创作态度,不仅是他自己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也使他与20世纪30年代其他作家创作态度相区别。沈从文批驳那些不能客观写作,不能节制感情的写作方式,沈认为郭沫若“他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55页。。沈从文告诫巴金:“我意思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必需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你感情太热,理性与感情对立时,却被感情常常占了胜利。”*《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21、223页。沈从文批评蒋光慈等革命作家“便是模仿那粗暴,模仿那愤怒,模仿那表示粗暴与愤怒的言语与动作”*《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4页。。沈从文并认为五四之后十年来中国文学普遍存在“浮薄而不庄重的气息”,挹“讽刺”“诙谐”于各样作品的弊端*《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217页。。
三、 散化的结构与情节的突转
沈从文早期小说存在因随笔化而导致的散漫的艺术缺陷,而他成熟期小说那种芜杂散乱的结构有了极大的改观,作者开始对一些芜杂的枝蔓进行有意识的“修剪”,特别是沈从文有意地安排了情节结构的“突转”与“发现”,住往具有“一峰突起,照亮全篇”*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第311页。的作用,从而使作品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何谓“突转”呢?亚里斯多德认为:“‘突转’指行动按照我们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亚理斯多德:《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3~34页。亚理斯多德认为“突转”不是读者可感受到的由顺境到逆境或由逆境到顺境的逐渐进行的转变,“突转”是在读者预先没有感知,主人公一直处于顺境或逆境中,但是到了某一个时刻情势的突然转变,这种转变是事件意外地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
沈从文成熟期小说结构上表现出大量的“突转”现象。沈从文运用“突转”艺术更为成功地表现在,他让读者沉浸在田园牧歌的情调之中,却突如其来地将其从梦中摇醒,让人感受到美的短暂和易失以及人生命运的无常。譬如《阿黑小史》、《媚金·豹子·与那羊》、《菜园》、《三三》等作品情节的“突转”都有生动的表现。这里重点分析《边城》的“突转”结构。作者在对湘西民情风俗、自然山水、纯朴人性作最动情的抒写,最后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一下子将人从田园牧歌境界的陶醉中震醒,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一方面使读者更加留恋那幻美之梦,另一方面也让读者感受到好梦之后命运的无常;诗意的创作由此获得了社会历史的基础和人生哲学的厚度。正是因为沈从文有了“突转”这一艺术结构,一方面他可以尽情地抒写理想的人类乐园图景,另一方面也使其创作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不至于使其成为离开人世间的空幻世界。
“突转”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发现”。沈从文小说不仅生动地表现了“突转”艺术,而且也出色地表现了“突转”背后的“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就指出“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此二者是情节的成分。”*亚里斯多德:《诗学·诗艺》,第22页。那么什么是“发现”呢?亚里斯多德指出:“‘发现’,如字义所表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那些处于顺境或逆境的人物发现他们和对方有亲属关系或仇敌关系。”*亚里斯多德:《诗学·诗艺》,第34页。我以为“发现”也就是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对自己的真实处境和事情的原委由不知到知的这一过程。在《边城》中,最后的那一场雷电交加的大暴雨和老船夫的突然逝去,小说实现了情节上的“突转”,特别是杨马兵给翠翠讲述她先前所不知道的一切,这就是“发现”,翠翠从不知到知,正是这种“发现”才使她坚守在渡口,等待二老傩送的归来。《丈夫》中丈夫毅然决然将妻子带转回去,是因为丈夫发现自己的夫权已经被完全剥夺殆尽。《如蕤》中如蕤放弃自己苦苦追求三年才得到的男子的爱,是因为她发现这个男子因为爱她而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丧失了那种征服如蕤的骄傲与光辉,沦为她所熟悉并超乎其上的“痴妄者”之一,如蕤的不辞而别颇显意外而又在情理之中。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发现’如与‘突转’同时出现,为最好的‘发现’”*亚里斯多德:《诗学·诗艺》,第34页。在此得到生动的体现。
四、 自然时序的叙事安排与叙事时空的错综颠倒
热奈特说:“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连续顺序。”*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4页。这里区分了两种时序,一是叙事时序,一是故事时序,叙事时序是文本展开的时序,而故事时序是被讲述故事的自然时间顺序,是故事从开始发生到结束的自然排列顺序。故事时序是固定不变的,叙事时序则可以变化不定。
在沈从文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时序是故事事件发生的先后与它们在叙事中呈现的次序是相应的,即叙事按照故事事件发生的先后展开,我将此称为自然时序的叙事安排。这种放任自流的叙述时间,是沈从文最常见的叙事方式。沈从文都市自叙传小说,日记体小说等,往往是较为鲜明的流水账似的叙述方式。《阿黑小史》小说按自然时序春、夏、秋、冬、春五季安排“油坊”、“病”、“秋”、“婚前”,季节的一个轮回,人物经历了恋爱、婚前、发疯等生命历程。《萧萧》《一个女人》等更是以自然顺行描述了她们生命历程的几十年。
沈从文按照自然时序进行叙事,一方面内容决定形式的表现,如刘洪涛所说“湘西小说中的人物屈从于命运,受制于造化,时间就成了命运和造化的显在形式”*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沈从文的艺术追求,即他对艺术的“自然天成”的审美愿望,企望打破人为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呈现生活的原始真实。沈从文说:“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来了。”*《沈从文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当然,沈从文在叙事时间的处理方式上,决不只是用一种方式就能涵括的,其创作在保持主色调的同时,也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不少小说显示了叙事时空的错综颠倒,出现了预叙,插叙,倒叙等方式。
首先,预叙在沈从文小说中得到重要的表现。预叙是指对未来事件的暗示或预期,用热奈特的话说,是指“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第17页。,预叙事先揭破故事的结果,对事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中国话本小说的作者常常在故事开头三言两语将故事的大致经过,包括结果,预先告诉听众,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然后再从容详尽地展开故事,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沈从文一些小说中预叙也得到比较鲜明的表现。譬如《丈夫》在具体写老七的丈夫时,还对黄庄其他的一些丈夫作了预叙,写他们如何将自己妻子放在城市里河船上做“生意”,又是怎么样探视自己妻子的情形都作了预先叙述,这样便使读者对后面老七的丈夫的行为方式有了初步的了解,不至于过于突兀或让人不理解。又如《顾问官》小说在具体写顾问官赵颂三如何弄到烟苗捐监收人的委任状进行“夺弄”的故事时,开篇便对少数在部里的红人如何进行“夺弄”进行了预叙。由于预叙的成功运用,在描写上对后面的故事有了交代和铺垫,并形成一种前后参差的对比和烘托,使读者获得单次描写所无法得到的艺术效果。
沈从文不少小说也使用倒叙的手法。这种手法在讲故事的叙述框架中表现得最为普遍。如《若墨医生》《灯》《厨子》《医生》《媚金·豹子·与那羊》《说故事的人故事》《老实人》《第四》《松子君》《猎野猪的故事》以及大型佛经改编故事《月下小景》等,这些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的时间都在故事的讲述之前,讲述人对此进行回叙。这些讲述故事的小说都是倒叙手法。沈从文还有一些回忆性的小说也属于倒叙,如《槐化镇》《入伍后》《堂兄》等。沈从文不仅广泛使用倒叙手法,而且倒叙手法表现的方式各异。在沈从文的倒叙手法中,最常见的往往先是故事的引入,然后展开倒叙,然后对故事主体进行讲述,最后又回到讲述的现场,讲述完成之后小说往往并不结束,还要作一定的情节发展。例如《灯》《松子君》《老实人》《猎野猪的故事》《入伍后》《厨子》等。也有的小说在倒叙完成后,只是简单回到叙述的现场,故事不再向前发展,如《若墨医生》《说故事人的故事》《媚金·豹子·与那羊》《医生》等。还有的小说在倒叙完成之后,整个小说也就结束了,如《槐化镇》,这种倒叙方式最少。而《月下小景》佛经改编故事中有的故事讲述人讲述的就是自己的故事,这些叙述就是倒叙,而在倒叙完成之后,往往还要进行辩驳议论。可见倒叙手法在沈从文小说中也得到了异彩纷呈的表现,取得了可喜的艺术成就。
插叙和补叙在沈从文创作中也表现得较为突出。插叙就是在主体故事之外插入一部分的叙述。插叙在沈从文创作中特别是他早期小说中有着比较突出的表现。作者往往在故事的主体情节之外大段地插入一些风土人情的段落,乃至一些议论等等。例如《山鬼》第四部分关于猫猫山民众剧场的描写,就是在主体故事之外插入带有民情风俗的描写,《更夫阿韩》中插入了小城镇过年风俗的描写,等等。补叙就是对主要故事作补充说明的叙述。《生》的末尾便是很好的补叙。
《边城》则在多方面展示了其高超的叙事艺术成就。《边城》以自然时序叙事为主,但又有倒叙,补叙等多种形式。譬如小说第四、五节翠翠对前面两个端午节的回忆,第七节祖父对翠翠母亲的回忆,都是倒叙。而小说对傩送、天保在碧溪岨唱歌求爱的描写,只是从侧面描写祖父、翠翠对歌声的反应,然后对傩送和天保唱歌求爱之事进行补叙。《边城》的自然时序叙事又表现为多种形式,譬如小说描写端午节这天早上祖父上城买东西,翠翠过渡来往行人,小说重点写翠翠的过渡,而对祖父在街上所遇到的种种事情则以翠翠的想象进行虚写;白天看龙舟竞赛,祖父与一个熟人到河边看碾坊,翠翠在吊脚楼上看龙舟,这里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方法,即“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这两部分都是按照自然时序叙述,讲述同一时间里祖父与翠翠的事情,但叙事方法是不相同的,显示了沈从文叙事方式上的不予雷同。《边城》还显示了叙事时间的快慢的精巧安排,譬如小说对端午节龙舟竞赛和唱歌求爱的描写,叙述时间很缓慢,小说分别在几个章节中进行叙述,显示了这些事件在整个故事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而小说写老船工安葬,白塔重建,时间由夏天转到了冬天,历时半年,只用了一节进行叙述,叙事速度就很快。总之,《边城》在以自然时序为主,又具有叙事时空的错综颠倒,以及叙事时间快慢的精巧安排,显示了高超的叙事艺术技巧。
以上我们探讨了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态度、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时间等方面的艺术变化及其表现,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发展变化及其异彩纷呈的叙事艺术表现形式。我们可以说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小说叙事艺术传统特色,而且大大推进了其现代转型,对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其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艺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