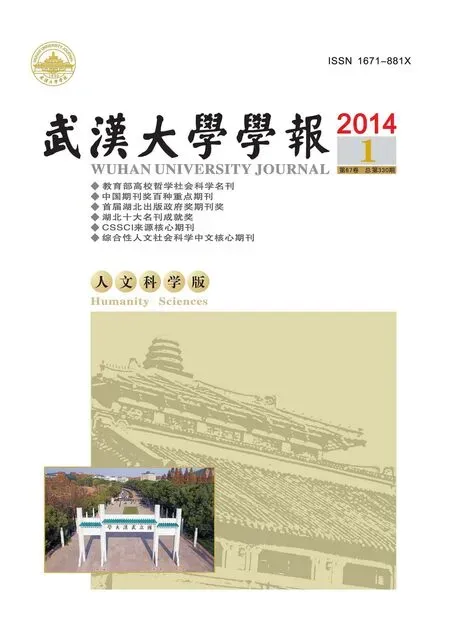沈从文1940年代创作的晦涩
2014-03-04张森
张 森
1940年代的沈从文创作了大量“抽象”类作品,如《烛虚》、《水云》、《看虹录》,与之前的湘西叙事比较,作品充满了抽象玄思,呈现出一种晦涩的写作特征。这类作品并不为当时文坛看好,以至沈从文日后还屡次为这些作品的晦涩辩解①《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9,108页。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特殊境遇,他在这里对作品晦涩的解释并不完全客观,与他在1940年代对诗歌“晦涩”的理解有差异。。近年来,研究界对他这类创作中出现的新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不过,研究者也普遍认为沈从文的这类作品不如他之前的湘西叙事技巧圆熟,有着明显“实验”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品尽管探讨了自然、生命等一系列充满哲性色彩的命题,但其内涵又显得极为晦涩模糊。值得反思的是,沈从文此期作品的晦涩是否仅仅源于创作技巧的不成熟,还是存在其它的原因?
事实上,除了因作家创作能力以及读者自身的阅读障碍引起的“晦涩”外,晦涩还被视作一种独有的文学品格。李金发的诗歌、鲁迅的《野草》、废名的《桥》,都是公认的晦涩之作。1940年代,深受西方诗学批评影响的袁可嘉将晦涩视作中国诗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②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第94页。。沈从文也曾为新诗的“看不懂”辩护③《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他说:诗从“抒情观点出发,以为需见出个人性情和风格,即不知不觉成为晦。”④《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77页。沈从文认为作品的晦涩并不一定是作者创作能力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极有可能是因为作品“有个人性情和风格”。他此期的作品与其说是因“实验性”写作而晦涩难懂,不如说作品“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晦涩与作家的个体生命经验、现代存在境遇、与作品独特的表现内容和个性化的表现手段存在密切关系。
一、难以言说的内在世界
不同于湘西小说的传奇性,沈从文此期的写作呈现出明显的向内转趋势,他笔下的生命世界虚实相间,呈现出重重的悖论和冲突,内在世界的复杂和不确定导致作品晦涩难解。
小说《看虹录》的第二节用第三人称讲述了“奇书”的内容,即男客人和女主人在雪夜共处一室。人物姓名、身份缺失,故事在两人的对话(潜对话)和独白中进行,这里的对话不是正常情形下的情侣轮换说话,而是将表层语言与内心活动同时呈现。金介甫曾认为读者因此看到的是两个复杂而又分裂的自我形象,彼此的关系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①金介甫:《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故事高潮是男客人在对女主人身体的“皈依”中见到“神”——生命的最高形式,小说将这一情节隐含在女主人阅读男主人写的雪夜猎鹿的小说中。同时,小说中的“我”一面对“奇书”中男客人的“神性”体验极为留恋,一面又刻意营造一种非现实的幻境,不断暗示这一故事的“空虚”。“我”始终处在一种游离不定且矛盾重重的状态。
散文《水云》同样是多个自我与多重叙事的交织。叙述中既贯穿着“我”如何创作故事的经历,同时又交织了“我”与几个“偶然”(即女人)的关系。上述叙事都是通过两个相对立的“我”的对话来表现,一个是为“理性”、“意志”控制的“我”,一个是为“情感”、“偶然”控制的“我”,一个是在“梦想荒唐幻异境界中”的“我”,一个是现实中的“我”,两个“我”始终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彼此辩难,互相审视。两者交锋所暗示的不仅是“我”面对“偶然”时的选择取予,更是对自我生命存在方式的追问。然而,生命究竟是应按理性计划进行还是任“不可知的宿命”主导,是应沉浸在抽象中还是回到现实,《水云》对此并未提供确定答案。散文集《烛虚》②本文中所引的《烛虚》中的文字,均出自《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中的“我”则在生与死,过去、现在与未来,绝望与希望互相缠绕的世界中游走奔突,却始终无法获得一明晰确定的自我③关于《烛虚》中刻画的充满悖论性内在世界,可见拙文《〈烛虚〉:在“抽象”中探寻生命的意义》,载《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可见,沈从文这些作品的晦涩不仅源于叙事本身,更是由于作品表述的是这难以言说的内在世界,背后则是沈从文此期思想的复杂性。1940年代的沈从文历经了对湘西世界的失望,在《湘行散记》及之后的《湘西》、《长河》中,都可见他对湘西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人性变异的焦虑。对都市和乡村的双重失望,促使他选择遁入“抽象”境界,在“神之解体”时代重造生命的神性。在上述这些抽象之作中,不难看到沈从文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沈从文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重造的神性尽管美好却难以在现实中实现。比如,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沈从文提到他人对小说的批评④《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2~347页。,他深知“在肉体中发现神”必将为人诟病,小说似幻似真的笔法既是由于题材为时人忌讳难于直说,更是他对“神性”的现实处境的清醒认知。沈从文此期内在世界的矛盾也是由此而来,他既力图重造神性,同时又意识到这一努力的虚无;既不愿接受目下虚伪沉沦的现实,又不愿沉溺在抽象中而不顾现实,个体在现实与抽象世界间游走奔突。从这个角度说,沈从文创作的晦涩就类似于袁可嘉所说的是传统标准崩溃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⑤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第94页。,是在价值解体时代,个体试图重造新的价值体系时面临的困境的真实显现。
二、不可言说的神性体验
如果说沈从文重造神性时遭遇的困境,导致了作品在表现这一内在世界时呈现出晦涩的一面,那么这一神性本身的不可言说性,则进一步加剧了作品的晦涩程度。此期神性重造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身体,一是自然。
《看虹录》是从身体一途体验到生命神性的代表性文本。小说凸显了“我”面对女主人美丽身体时的极致体验,“我”仿佛“见到了神”,体会到“神的意志与庄严的情感”。然而,这一神性体验又是不可言说的,“一切文字在此都失去了他的性能”。《摘星录·绿的梦》是与《看虹录》主题极为类似的一篇小说,小说在描述女主人身体时也指出身体“尤近于一种神迹”,然而,这蕴含神性的身体无法用言语形容,“恐唯有神妙美妙的音乐,可以作到。”⑥沈从文:《摘星录·绿的梦》,载《十月》2009年2期。以下所引《摘星录·绿的梦》的文字均出于此。在《七色魇》、《烛虚》、《水云》中则描写了”我“由对“自然”的凝眸进入神性体验的过程。在与自然对面时,“我”无不感受到生命的存在,鱼虾在流水中是“各尽其性命之理”,豆麦田在一起一伏中“充满生命自得的快乐”,“耳目所及都若有神迹存乎其间”⑦《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1~122页。。然而,这一经由自然而体验到神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沈从文同样难以清晰地说明。
除了借助身体或自然获得神性体验外,沈从文也有对抽象境界中的神性体验的直接呈现。这种境界往往充满空灵虚幻的色彩,类似于一种超现实的梦幻体验。比如《生命》中出现的一篇“小文”①《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3页。省略号为原文所有。,其内容相当模糊晦涩,可意会却无法言说。
散文《烛虚》中引用了《新约·哥林多书》②这段话实出自《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2章,沈从文在《烛虚》中所言有误。中的一段话:“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的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③《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1页。《每日研经丛书》中解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奇妙的经验,“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一切宗教经验的最大目的是神的远象并和神合而为一。神秘主义者的目的,往往是在奇妙经验的一刹那,‘见的和所见的合而为一’……他的意思只是说他的灵上升在无可超越的神秘状态中与神接近。”④《每日研经丛书》,载http://delve.bodani.cn/New%20Testament/47%202Cor/47ET12.htm。沈从文说的神性体验与保罗的奇妙体验有着相似之处,两者同样玄妙、难以为言语说明。保罗说的“第三层天”被认为可能指天上最高最完全的境界⑤《串珠圣经注释》,载http://delve.bodani.cn/New%20Testament/47%202Cor/47GT12.htm。,而神性也是沈从文意旨的生命最高境界。两者进入各自认为的生命最高境界时的过程也极为相似,都具有瞬间性与忘我性特点。沈从文曾将此过程描述为:“如中毒,如受电,当之者必喑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4页。更重要的是,这一体验都具有不可言说的隐秘性,两者都是在灵魂(生命)上升至无可超越的状态中与神接近或直接体验到“神”。因此,神性体验的不可言说还在于生命的最高层次本具有难以为语言表达的神秘之处,“是人不可说的”如果不仅仅视作一种宗教说法,则应是这一体验已经逾越了人类理性与语言的边界。沈从文此期就表现出明确的语言焦虑感,他多次谈到,当接近生命至性时语言最无力,“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⑦《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5页。可见,他采用“抽象”的语言描绘神性体验也是不得已为之,作品的晦涩也不言而喻。
三、“梦”与“抽象”的言说方式
难以直说的内在世界与不可言说的神性体验,造成了沈从文此期创作内涵的晦涩,同时也一定程度导致作品言说的困难。正是如此,作品多以“梦”与“抽象”为主要话语形态,营造出一个个梦与现实相互交叉、晦暗不明的奇特世界。
《看虹录》呈现出清晰的“现实——梦(或回忆)——现实”的回旋结构,小说有意将第二节“奇书”内容处理成一个类似于梦的非现实情境。《摘星录·绿的梦》对两人性爱过程的叙述更为细腻,但同样将故事梦境化。小说标题就隐喻着情事如“梦”,在写到一个美丽的肉体躺在撒满野花的被单上,小说称“一个梦;一种荒唐到不可想像艳丽温柔的梦!”在两人情感高潮处,小说又说道:“一切应当不是梦,却完全近于一个梦。”这里所说的“梦”更像是一种如“梦”般的感觉,而非虚指。在故事结尾后,小说又添加了一个“后记”,向读者强调这个故事并不是真实的,而是“我”臆想中由欲念转化的“梦”。
不过,在沈从文此期的创作中,可以明显觉察到现实与梦境界限的作品并不多见,更为普遍的是梦与现实往往交融在一处,其时间指向更为模糊晦涩。小说《摘星录》⑧《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文中引《摘星录》的文字均出于此。重点写一个年轻女子的情感生活。其中写到女子翻看老朋友和大学生写给她的信,信的内容像是在回忆两人相处时光,但叙述又一再将此做梦境化处理。比如一封信中写到:“我今天真到一个崭新境界里,是真实还是梦里?完全分不清楚,也不希望十分清楚。散在花园中景致实在希有少见。”这“景致”从情节推测应是读信女子的美丽身体,从信的内容也不难看出这里叙述的又是一出类似于《看虹录》中“从身体中见到神”的绝妙体验。之后写信人称“这一切似乎完全是梦,比梦还缥缈,不留迹象。”女子在看信时也提醒这是“一千个日子”前发生的事,那么信中所写的是关于两人情事的回忆吗?然而,写信者似乎正担心有人如此解读,在结尾处又说道:“有些人生活中无春天也无记忆,便只好记下个人的梦。”指出他所记录的不过“是梦的一种形式而已”,也是“一种生命形式”。《摘星录》原名《梦与现实》①沈从文:《梦与现实》,载《十月》2009年2期。,从小说整体内容看有关“梦”的内容并不明显,显示出“梦与现实”难分难解的正是女子所读的几封来信,信中有意模糊现实(写实性回忆)与梦的界限,营造出一种似幻似真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说,《摘星录》的核心故事应是女子与老朋友之间已经逝去的情感,女子此时正在过去如梦般的情事与平庸无聊的现实间挣扎,但小说对此处理得极为隐晦。
散文集《烛虚》中则出现了大量抽象境界,这里的“抽象”同样是非现实的。作品中既呈现出完整的“现实——抽象——现实”的体验过程,也有现实与抽象的交互交融、难以分辨。《烛虚》中写到“我”离开现实世界后进入到另一抽象世界,这是一幅“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的画面,最后“我”回归现实,“明窗绿树,已成陈迹”②《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5页。。《生命》中沈从文描绘了一幅极美的画面:“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翣,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这一段描写有极为清晰具体的现实存在物,但从前文中一再说道:“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之想象,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似乎又可推断沈从文这里描写的不过是他美妙而虚幻的抽象体验。
显然,梦与抽象在沈从文这里不仅是虚化的,更是“美与爱”交融时的神性体验,是“我”希冀的理想之境,而现实则是“我”愈逃避却又无法逃脱的处境。沈从文既迷恋这一抽象的梦的境界,同时又不能不直面当下的现实,因此选择“梦与现实”相交叉的叙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它不仅可以任作者尽情地构筑一个理想境界,也时时提醒自己这一世界的非现实性。事实上,梦与现实相融也是沈从文在文学上的自觉追求,他在《短篇小说》中曾说:“必须把人事与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③《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93页。尤值一提的是,沈从文在三篇爱欲小说中都有意将情事虚化,这当然是因为回忆往往指实,而梦则无凭据。然而,不论这些小说是否真以现实人事为背景,在“梦”的叙述背后都透露出他此期难言的悲哀和痛苦。尽管他一再驳斥了他人对作品“不道德”的评价不过是虚伪的表现,但他仍将“从身体(或自然)中见到神”塑造成虚化的梦(抽象),在这晦涩的叙述背后,隐藏着他难以释怀又不得不掩饰的过去、他对现实的失望乃至绝望,当然更有他对理想的激情与守护。
四、现代与传统的多源交汇
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晦涩往往与西方现代派文艺相联系。1940年代沈从文创作呈现出的晦涩倾向,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当时身处现代氛围浓厚的西南联大。联大是当时各种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汇聚地,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燕卜荪、奥登等,都曾在联大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外,当时在联大的一批年轻学者、作家如冯至、卞之琳对西方文化也极为熟悉,并做了大量译介。穆旦、袁可嘉、杜运燮、汪曾祺等人的创作也都极具现代主义色彩,同时不乏晦涩之风。从目前留下的资料看,沈从文对这些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应极感兴趣,金介甫曾提到,沈从文对伯格森的生命论非常熟悉,“卞之琳等人翻译过乔伊斯的部分作品,但沈在听到这种新思路后,就在讲课教材中作了介绍”④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对此,沈从文在后来的检讨中也这样说到:“照当时教英文的同事中欢喜谈到的乔依思心理分析派的小说写恋爱”⑤《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49页。,这里说的“写恋爱”小说显然是指《看虹录》这类作品。他还称,当时更容易与他个人情感结合的,“不是马克思条理谨严的,为人类社会的新设计,却是个人中心的纪德、尼采一些断片印象感想。”⑥沈从文:《我的学习》,载《大公报》1951年11月14日。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时西南联大关于晦涩的理论探讨也极常见。施蛰存、孙作云、金克木、王佐良、陈敬容等都参与过对晦涩的讨论,据说穆旦曾翻译了麦克尼斯的长文《诗的晦涩》⑦张松建:《文下之文,书中之书:重识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论述》,载《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10月。,袁可嘉也撰文讨论“晦涩”的问题⑧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沈从文则为“看不懂”的诗歌辩护,而他此时的作品也开始走向晦涩。不过,尽管沈从文说过他照乔伊斯的方法写恋爱小说,但要一一去指证他的作品是如何受西方现代文艺的影响却费力不讨好。沈从文很少去生搬硬套西方文艺理论,更何况他的创作鲜明地融注了个人生命体验。在沈从文的这些作品中,大量运用了元叙事、意识流、叙事时间和人称的不断转换、内心独白替代故事、模糊现实与虚构等前卫的叙事手段,而这更多是因自身复杂的生命体验而来的一种选择,金介甫因此认为沈从文的这些作品“从主题到技巧都充分证明了沈从文现代主义特征的一面。”①金介甫:《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载《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不过,沈从文作品的晦涩绝不仅仅是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他此期的情爱小说以及神性体验,看似都远离了那个古朴原始的湘西,但其根依然深植在此。他笔下的“神性”与湘西巫楚文化中的“神”有着相通之处。早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神之尚存”的世界,这个世界保留有原始神话的特征,“神”是原始边民的素朴信仰,他们敬神也娱神。在《凤子》、《神巫之爱》等作品中,沈从文多次描绘了一幅幅人神相悦的狂欢场面。卡西尔在《人论》中说,神话和原始宗教“的条理性更多地依赖于情感的统一性而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法则。这种情感的统一性是原始思维最强烈、最深刻的推动力之一。”②卡西尔:《人论》,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不难看出,沈从文重造神性的最重要手段都不是通过科学的逻辑方式获得,不管是从自然还是从身体一途体验到神性,都是出自一种对“美”的“爱”的情感,只有这一情感达至疯狂极致状态时,生命神性才凸显出来,这显然暗中承接湘西巫文化中人神沟通时的情感状态。从这个角度看,《神巫之爱》、《凤子》中“悦神”的狂欢与《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中因爱欲而来的神性体验就有一种奇特的联系,人神沟通时情感的“悦乐疯狂”、忘乎所以乃至模糊现实与梦(神话)的距离,都是两者所共通的。此外,卡西尔还认为:“神话是情感的产物,它的情感背景使它的所有产品都染上了它自己所特有的色彩。”“对神话和宗教的感情来说,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生命的社会。人在这个社会中并没有被赋予突出的地位。”③卡西尔:《人论》,第135~137页。这一点与沈从文此期由对自然的凝视进入抽象世界,进而体验到“神”的状态也极为相似。他在一切“有生”如仙人掌这类普通植物中发现生命、意识到神性,与神话宗教情感中的自然成为“生命的社会”不谋而合,两者不管是在思维方式还是在内涵上都有着极大的一致。
可以说,以沈从文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为核心,湘西巫楚文化的“神”与尼采的哲思、乔伊斯的现代小说等西方现代文艺哲学思潮的交汇,形成了沈从文1940年代创作的晦涩风格。实际上,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鲁迅也曾将西方非理性思潮与民间吴越之风、佛文化相结合,创造出《野草》中奇诡晦涩的意象,废名小说的“不懂”与禅文化也有着极大关系。毋庸置疑,中国现代诗学的构建离不开西方诗学话语的影响,但一种诗学范式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则不仅仅是吸纳西方诗学资源可行,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沈从文的抽象之作或许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