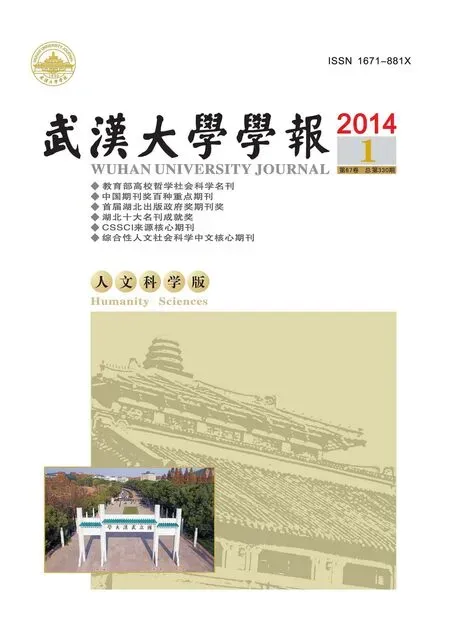沈从文的“现代”忧惧
——《长河》纵论
2014-03-04周仁政
周仁政
一、 周作人与沈从文:“古老的忧惧”与“现代”的忧惧
1944年,周作人谈到自己当年创作《小河》一诗的动机时说:“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他们不幸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是将来的忧虑。”*《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周作人所谓“古老的忧惧”是指农夫筑堰御水,破坏了水的自然流动,任其在堰前呜咽乱转,岸边的稻和桑树,担心会有一天,水从它们身上大踏步过去,它们和水再也做不成好朋友了。
这种“古老的忧惧”周作人以为是对时事的预知,多少还算得上一种“未卜先知”的智慧,较之“旧诗人”们望洋兴叹要好多了。亦如水和桑树,“将来的忧虑”多少总是无奈,毕竟“筑堰的人,不知哪里去了”。
沈从文说,“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在这条河上筑坝的人大概从来都不是知识分子,只是帝王将相们。民是水,知识分子是鱼。水常常可以冲决堤坝,鱼却只能望坝兴叹。周作人写《小河》想起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沈从文写《长河》要告诉人们的却是一条河流的历史。载舟覆舟,这条河流几千年来波澜不惊。这就是沅水。这是一条自然的河流,河流上生活着一些历史以外的人们,他们假舟楫为生,在风浪中出没,游走在这条生命之河和各自的命运之舟上,成也好,败也罢,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的更是这条“长河”。多少年来它与岸上的稻和桑树和平共处。没有好事的农夫来筑坝。人是鱼,船是家。上岸是停,入水是走。没有水,生命就失去了流动;没有岸,流动的生命就没有了方向。这是另外一种河流——生命的河流。这是另外一种历史——“有情”的历史。
1933年严冬,沈从文告别新婚的妻子张兆和,为探母病回到阔别十年的湘西。当他独自从桃源租了一条窄窄小划子,同一个年老的艄公溯沅水上行,一路边走边看,边看边写,满心的情爱与满目的鲜活都融在了一条温润的沅水里。这条河给了他力量,给了他对生命与历史的新的理解:小河两岸“美丽动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一到这船上,便无不朗然入目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两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
水里面也有“历史”——一块烂船板。它记载的是水上人的命运:一个吃水上饭的,船下青浪滩时折楫沉舸,货失人亡,浪里白条撞上凌厉的礁石,命运的弦断了,梦想戛然而止。
一块破败的船板让沈从文出神。他想起“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我感动得很!……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我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爱了世界,爱了人类。”*《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19、188页。
“爱了世界,爱了人类。”《长河》便成为沈从文另一种生命阅历中的爱的记载。它不是出自周作人所谓“古老的忧惧”,却抒发了一种“现代”的忧惧,指涉着一个“将来”的无爱的世界。
二、 悲悯为怀:《长河》中的“事”与“情”
《长河》记载了一个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的生活史和情感史。甫一落笔,沈从文想起了两千年前那个楚国逐臣屈原,乘了小小白木船,溯沅水上行,一定就见过这两岸的橘子树林,方写出了那篇《橘颂》。“两千年来这地方的人民生活情形,虽多少改变了些,人和树,都还依然寄生在河两岸土地上,靠土地喂养,在日光雨雪四季交替中,衰老的死去,复入于土,新生的长成,俨然自土中茁起。”人们厌倦了地面上生存,便斫木为舟,干起“水上漂”,俨然鱼虾一样,“吃水上饭”。橘子园主人滕长顺和守祠堂的老水手都以干这种营生出身。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末了一成一败。滕长顺先作水手,“后来掌舵把子,再后来且作了大船主。”“不特发了家,而且发了人。”最后在萝卜溪安家落业,在村子里做员外。公共事业中常做个头行人,“居领袖地位”。老水手呢?年青时也吃水上饭,娶妻生子后,有两只船做家当。“前途大有发展时,灾星忽然临门”:夏天里为了一个西瓜,岸上的母子三人两天内全害霍乱病死掉了。两只船一只换了母子三人的棺材钱,剩下一只勉强支撑,不出三个月,当满载桐油烟草下常德时,在沅水中部青浪滩出了事。“在大石上一磕成两段,眼睛睁睁的看到所有货物全落了水,被激浪打散了。”真是“行船走马三分险,事不在人在乎天。”老水手空捞回一柄桨,失意人一样,向远方跑了。十五年后再回到吕家坪,头发业已花白,面貌憔悴,一无所有。
滕长顺怜惜他并接纳了他,先是延至自己家中寄养,让小女儿夭夭认老水手做干爹,后有人出钱在枫树坳建了新的滕家祠堂,这老水手便被分派做了坐坳守祠堂人。老水手乐得其所,从此过起了清静闲宜的日子。
老水手和滕长顺成了一家。真可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成败穷富,如果不是刻意张扬和无限夸大其间的差别,终得殊途同归。面对历史和人生,沈从文其实在追问:什么是成,什么是败?两千多年前,在楚国,屈原政治上是败,文化上却是成——屈原哀郢沉江后千余年,唐代陶翰《南楚怀古》诗云:“南国久芜漫,我来空郁陶。君看章华宫(按:故楚王宫),处处生黄蒿。……独余湘水上,千载闻《离骚》。”历史上,人们争成好胜而有政治,但多少斫斫杀杀的故事,成也好,败也罢,留下来的少不了人亡政息的教训,国破家亡的悲哀。在沈从文看来,这种“事功”的历史代替不了“有情”的文学。“有情”是人与自然相处而有敬畏,人与人相处而有爱怜。这才是切合人类本性的力量,也是文化不死的灵魂。文学追随“有情”,因而与“事功”(政治)的历史有别。
在《长河》中,沈从文表现的仍是他一如既往的文学理想:人性之爱与社会和谐。滕长顺和老水手的不同命运和趋同的人生结局,是构成这种“有情”人生和和谐社会的基石。和谐不是同一,成败兴衰是人生的应有之义。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仿佛受命于天的人际差池。用政治的方式固化这种差异,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兴起革命的波澜,这固然可以用强力一时间地抹平社会的贫富分野,但人之为人的“不忍”和爱,将无由在这个世界上存续。一旦差异性在新的土壤上滋生,“斗争”或者革命就成为一种造就人们政治敏锐性的历史惯性,社会的和谐和安宁永无回归的希望。
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从文是想告诉人们:正视差异——那只是命定,用爱来理解人生,勿用恨来隔绝人生。像滕长顺和老水手那样,成也好,败也罢,把人生看得同样庄严。成不足畏,败不足恤,殊途同归。“有情”诚为有命,爱人恰如爱己。
三、 政治与文化:人性中的“憎”与“爱”
五四以降,20世纪中国的政治主题是“革命”。从鲁迅等开始,启蒙就把一种“憎”的政治基因,注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因此,从对传统的否定和批判开始,到为了革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划分敌友,“传统的”和“有产的”,都被文化和政治判定为革命的对象——以“现代”革传统之命,这是文化革命;以无产者革有产者之命,这是政治革命。从历史本身来看,这不无合理性。但是,在革命的意义上,文化和政治的同盟关系,却一方面赋予现代政治革命以无坚不摧的威力,另一方面,从文化本身来看,否定了传统就是斩断了自己的根脉。爱和“不忍”之心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记忆中被简单割舍,却只是为了展示各自认同或向往现代革命的政治情绪。情绪,即使充沛着如何不容置疑的道德激情,都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理性。失去了理性,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本分,从而也就与自己的“天职”告别了。
沈从文永远对政治怀有疑惧之心。这不仅是对于现实,更主要的是鉴于历史的教训:
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了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5页。
他不由记起二十余年前在芷江街头看到的一群“新剪过发辫的桃源女师学生”,“不意十年后,这些书读不多热情充沛的女孩子,却大多很单纯的接受了一个信念,很勇敢的投身入革命的漩涡中,领受了各自命运中混有血泪的苦乐。”他自己呢?却用芷江县熊公馆中“几十本林译小说作桥梁,走入一崭新的世界,伟人烈士的功名,乡村儿女的恩怨”,都在他笔下得到更新的生命。这也就是历史,是人生——不是轰轰烈烈的政治和革命,却是理性评判历史和认真思索人生。温习一种似断实续的过去,把握一种不易把握的现实,难免感慨系之*《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
数年以后,沈从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接踵而至的政治厄运。但今天看来,这倒不一定是他的悲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成了一个固执的,也是最后的政治批评家——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学家。
沈从文的政治批判来源于他的非政治化的文学思考。早年,他离开湘西一是为了求学,更内在的原因则是厌倦了军旅生活。多少同乡朋友,幼有大志,投笔从戎,结果不是糊里糊涂死于非命,就是“气运”不济,昏昏庸庸糊日子。草菅人命是一切旧军队的本性。从军六年,沈从文“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这也正是旧中国政治的本色。沈从文要做叛逆者,从这种愚蠢的生活和所谓“尚武”的文化中脱离出来,试试如何处置自己的生命更得法。
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自谓:“为信仰而来”——“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革命”,在沈从文看来“是要推翻一个当前,不管它好坏,不问用什么手段,什么方式。这是一种现实。你出力参加,你将来就可做委员,作部长,什么理想都可慢慢实现。”可这到底是些什么“理想”呢?“年青人欢喜说‘学习’和‘争斗’,可是有人想到这是一种什么学习和争斗!”显然,这种“现实”的理想与沈从文的信仰无缘。
所以,沈从文宁愿承认自己“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在杨墨并进时代”过一种“游离”的生活,通过文学表达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74、379、376、373页。。
“好”和“坏”,“现实”和“抽象”,沈从文于是便有了自己的标准。抗战前夕沈从文再次回到湘西。去乡十八年,“一入辰河(按:沅水)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已被“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所替代。“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被常识所摧毁,但“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印象。”“现实”竟如此,不如向过去凝眸,把生活中一点不易改变的东西看成人性本然。既然一切都在变,“变动中人事乘除,自然就有些偶然和凑巧的事情发生,哀乐和悲欢,都有它独特的式样”*《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1页。。
枫树坳老水手忧心“新生活”来临,像过去“来了又走”的各色各样势力,搅得吕家坪人不得安宁,急急忙忙过萝卜溪去向好朋友滕长顺报告点“注意事项”。滕长顺在桔子园中取笑他且安慰他,干女儿夭夭延他到家中坐上席,吃菌子炒腊肉,喝烧酒。看到滕老板一家其乐融融,老水手这才知道“新生活”不是什么魔鬼,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忧心“新生活”的老水手其实是感到在“变”中讨生活的不易。一生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人与天斗还不算,还要如此自相折腾,何必呢!
做“员外”的滕长顺也不是没有忧心事,好端端一园桔子成熟了,但水泡泡的东西在本地不值钱,运下河去世道不安定难算计。做点人情给老亲家商会会长摘一船送送礼,没想到惊动了新来的“保民官”保安队长。保安队长在师爷的嗾唆下想来占便宜,明卖暗夺也想要一船桔子下河投机,且要和商会会长一样办理,不然派人砍树毁园,让滕长顺为了难。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没有这个保安队长,吕家坪一派和谐。成败穷富不是问题,只要人们还有点敬天畏命的本色,不强吃强占,自助助人,一条沅水长河数千年来波澜不惊。倒下的完事了,茁起的还会好好过日子,有气力下河,无气力上滩,各得其所,无怨无艾。近二十年来一切“变”的世事侵入这里,老一点的未免难于应承,年轻一代便难免心浮气躁。长顺家的三黑子总是愤愤不平地和保安队过不去,不把那个“保民官”放在眼里,这和老一辈人的处事方式就有了距离。
似乎这就是“革命”的因子,但沈从文不以此为理想。他认同老年人的处世态度:凡事求和。商会会长是调解的高手,一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那个“保民官”最终放弃了索要一船桔子的念头,接受滕长顺白送十担桔子了事。尽管去滕家时在桔子园看到夭夭,动了邪念,但对于这个天真又有点泼辣的“黑中俏”终究无计可施。一切都在“变数”中,但“常”的生活和人心总会有点含苦咀辣的涵育力和耐受力。善对恶,爱对恨,忍对争,四两搏千斤。“常数”在握,人心所向,世事总不至于变得太坏。这点信念支撑着沈从文必然对历史和未来作出新的理解。到末了,一场滕长顺出力出资的“社戏”,把吕家坪人的生活又引向了人神同乐的境界。
“人神同乐”就应有点敬天畏命的精神,有点宽厚待人的美德。不以成败论英雄。“抽象”的是人心,“具体”的是世事。前者是历史的锚锭,后者是现实的浮华。沈从文看得清楚。
四、 现代的“忧惧”:沈从文的政治悲悯
不以“憎”为计,不以“革命”为念,长期以来,沈从文的创作理念难免边缘。对他的创作的理解,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文学和崇尚“阶级斗争”的革命文学之间沉浮。沈从文常不免自我嘲解:“买椟还珠”的读者和评论家们,“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谓自己“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人性”之成为文学的主题,对沈从文而言是他超越了“国民性批判”的绝对性和“阶级斗争”的狭隘性而赋予文学以新的品质。这应该是现代文学的第三种“质”。其基础是沈从文的生命意识和文化观。就生命意识而言,他不想使自己成为常规生活的奴隶,在习惯和惰性中消耗自己弥足珍贵的生命,因此“逃异地,走异路”;就文化观而言,沈从文的信仰与暴力和野蛮无关,与政治无缘。在敬畏生命和关爱人生的意义上,他惟愿用爱与宽容来理解人生和解释人性,也以此观照历史和现实。他的文化观是超越性的爱和“有情”的生命史观。在敬畏自然和感悟人生中体认爱与美,在观照历史和生命本色时以悲悯为怀。从而人生百态及宇宙万象,无不油然而现庄严与寥廓,引起一种“抽象”而严肃的感印。
因此,在创作中,沈从文崇尚“抽象的抒情”。生命在运动中,不能凝固。物质生命的凝固就是死亡或近于死亡,但转化为文字或形象,生命凝结成另一种形态,却有望成为一种新的存在和延续方式。对人而言,文字是精神的呈现,是灵魂不死的明证。文学对于人类亦如此。通过创作,沈从文意欲引导读者:“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由“我”及“人”,性灵自见;以“人”照“我”,悲悯为怀。这不同于政治。因为“政治学权力第一”*《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93、394、378页。。“在某一时历史情况下,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的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成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这和社会事实是不符合的。”*《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34页。
以超越性的爱来理解人性之外,沈从文所谓“抽象的抒情”还表现在以自我为中心,由我及人,用“有情”的眼光打量历史,检视人事。1933年以前,沈从文的创作以“我”为中心,“我”的怀念,“我”的梦想,“我”的哀怨,以至“我”对都市生活的愤慨和绝望跃然纸上。郁达夫式的“自我暴露”成为创作的主调。这时的沈从文是一个有梦想、但更多哀怨和绝望的浪漫主义者。1933年以后,以创作《边城》为标志,沈从文把写“我”的笔触转向写“人”,用自己在爱情和事业上的成功春风化雨润诸笔端,“爱了世界,爱了人类。”《边城》因而成为一首人性美的赞歌。正如李健吾所说:“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仿佛有意,其实无意,他要读者抛下各自的烦恼,走进他理想的世界,一个肝胆相见的真情实意的世界。”*《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55页。尽管仍有《八骏图》式的都市批判,但淡淡的讽喻只像轻烟一样拂向人性的暗面——知识阶级的自我背叛和纯朴乡民的自我守护恰成表里。沈从文以为,文明的进程制造着人性(文化)的悲剧,有爱,人生庶几可以更纯粹一些,更自然一些。这时的沈从文,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现实中,冷漠的都市鄙薄弱者青睐强者。文学上的成功使沈从文有机会跻身强者之列,但他无意傲慢,反觉倍增谦逊。过去的苦难,世事的历练,使他倍感天地的辽阔,生命的庄严。以己及人,他要借文学表达的,是无限的温情和暖意。这正是《边城》和《湘行散记》等作品的主题和内蕴所在——“我”,从此“消失到一切偶然的颦笑中”。他说:“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人’,体会到‘神’,以及人心的曲折,神性的单纯。”这正是《边城》中“抽象的抒情”。
1937年抗战爆发后,民族苦难的命运更增添了他的人生悲悯意识,使他再无意于津津乐道个人的悲欢离合。“抽象的抒情”从而变得凝重。他说:“我不惧怕事实,却需要逃避抽象,因为事实只是一团纠纷,而抽象却为排列得极有秩序的无可奈何苦闷。于是用这种‘从深处认识’的情感来写战事,因之产生《长河》,产生《芸庐纪事》。”*《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20、121页。对“人事”的关切和对历史的审视强化了他创作的现实感,因而散文中的哲理表达和小说中的现实化倾向构成此期沈从文创作的新质素。但这并非意味着沈从文从此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现实,就其政治化品质而言,永远处于沈从文文学精神的对立面。他“向现实学习”的始终是抵制和抗拒。因而他写《长河》,表达的仍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现实观感——拒绝革命,扩展同情,叙说悲悯。
金介甫认为,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沈从文以迹近对政治的无知来否定和批判政治,表达的正是一个朴素而天真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政治情怀。抗战前后,他把民族内部不同政治集团间的“革命”或战争视为“民族自杀的悲剧”,这种浓郁的非战主义思想某一时期甚至发展到荒谬的程度。1948年,当北平围城的炮声轰然响起,这个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主义者却提出了把北平变成一个不设防的音乐王国和花园城市的梦想。金介甫认为,这“不只是对旧政权的变相批评,也是对近在目前的北京之战的悲悼。”*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1年,第251页。但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沈从文一如既往的政治悲悯和现实批判。
当革命的政治横扫一切的时代,不认同革命就是十足的“反革命”。沈从文因此受到了以郭沫若为首的来自左翼阵营的猛烈批判。他与朱光潜、萧乾等被视为“反动文艺”的当然代表,预告将在“人民文艺”取得完全胜利的一天“自行消灭”。但是,在政治中被消灭的东西适时条件下还会在文化中复活。这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犹如周作人当年借《小河》一诗表达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老忧惧。在《长河》中,沈从文的“现代”忧惧无疑是指涉那种摧枯拉朽的革命政治的。历史地看,此种“忧惧”并非多余。“革命”,无论如何势如破竹,毕竟成就不了一种人性的生活,一个“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