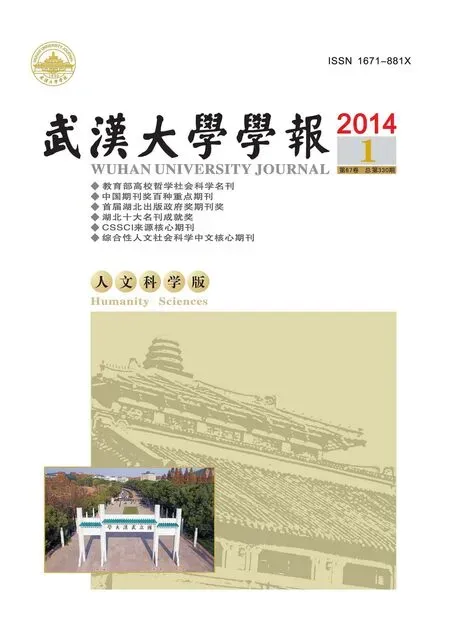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论的至诚之美
2014-03-04刘金波
刘金波
如果说电影《非诚勿扰》的高票房和江苏卫视的娱乐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高收视率表明了“诚”在爱情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在哲学、文学、伦理以及审美领域,“诚”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范畴。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论领域,“诚”是一个文论关键词,是一个基本的审美概念,它代表着纯真,代表着至善,代表着大美。在中国美学中,虽然美有众多范式,不单唯“诚”是举,但“诚”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美。这里所谓的“诚”,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强调的是诚,是信,是实,是自然的客观存在,是事情的本然状态,是人心对事物的真实反映,不枉不纵,不诈不欺。所以,以诚为美就是以至诚为美。
“至诚”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美学观念,也是较早出现的一个美学范畴。语出《礼记·中庸》: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这段话强调极端真诚可以预知未来的事,认为极端真诚就像神灵一样奇妙。龟甲兽骨一直在古代卜巫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在蒙昧时代,人们心智未启,信奉神明,相信前知。上述一段话实际上就是讲蓍龟之类可以预测福祸。如何预测福祸?靠至诚;其理论依据是什么?是至诚。人们只有达到至诚的境界,就可以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甚至包括国家兴亡一类的大事。善——好的情况,不善——坏的情况,都能够依靠“至诚”来预先知道,正所谓心诚则灵。人只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就如同有神明相助一样,既可以因神而明之,也可以未卜而先知先觉。
至诚之美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形态之一,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社会、人生、艺术等诸问题进行思考的一种美学追求,是人们艺术再创造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天道与人道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主张。
一、“诚”之溯源
诚,从言,成声。本义即真实,诚实,无妄,真诚。甲骨文中并无“诚”这个字,它出现于何时已然不可考。其出现多半和宗教祭祀对神灵的虔诚膜拜有关。从范畴学意义对它进行词源学考察,“诚”源于西周的《诗经·大雅·崧高》:
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
“谢于诚归”意思就是到谢城去安家了。作为审美范畴,“诚”即是自然之真,本然之心,纯然之性和超然之德。其原初意义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诚即信。诚,是一种生活理念。以诚心诚信了解自然、哲学、个人和社会。“诚”和“信”意义相通。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言部解释“诚”言:“信也。从言成声。氏征切。”《说文》将“诚”和“信”互训,“信者,诚也。”《论语·子路》:“诚哉是言也。”意即,诚就是信。《礼记·郊特牲》言:“币必诚。”诚,即诚信。《荀子·乐论》:“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古代哲人先贤要言不烦地说明“诚”的至要至高的地位,不厌其烦地阐释“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说明礼的原则就是表达诚心,去掉虚伪。
其二,诚即审。诚,是一种处世手段。诚就是规矩方圆的绳墨之审,人们需要用“诚”来观察体认社会。《史记·礼书》:“故绳诚陈。”郑玄注《礼记·经解》:“规矩诚设。”诚犹审也。
其三,诚即实。诚,是一种客观存在。诚包含有形而下的对某一事物某一具体事项的诚实诚信,但它显然不是美学所谓的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的形而上的那种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本真的纯然呈现。人的本心本性秉性纯直,布行贞实,无虚伪,真实无妄是诚;宇宙自然通过人的本心无杂质地率然呈现也是诚。《易·乾·文言》:“闲邪存其诚。”“修辞立其诚。”《论语·学而》:“敬事而信。”何晏集解引包曰:“与民必诚信。”朱熹《中庸章句》:“诚,实也。”无妄就是至诚,就是天理之本然,就是人真实不二的本然之心,就是圣人之德。戴震:“诚,实也。……善之端不可胜数,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德性之美不可胜数,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诚。”①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19页。仁义礼智信等在“诚”的境遇构成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真诚仁爱的美学精神,是强调一个人内在的修为。
其四,诚即成。诚,是一种生存方法。它是一种超越文化观念藩篱,实现天人合一的方法。中国古典美学对“诚者自成”十分推崇,如儒道释,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顺应自然,顺情适性,特别是圣人,能够与自然万物相合一,正如《周易·文言传》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何在“礼”(理)的层面保持本真,保持个体人格的尊严、自由和完整,既能理解自然宇宙的运行规律(天行之道),又能掌握自身在自然界的生存原理,实现自身价值(人行之道)?《礼记·中庸》提供了方法:“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说:“诚者自成也。”《礼记·经解》:“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注:诚,犹审也。或作成。”《大学》释“诚”为“勿自欺”。诚实无欺强调的是外在的修为,以什么样的修为去处世?“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宇宙万物的本然,只有修身养性以待天命,以天下之至诚来尽万物之性,既诚,又诚之,“不诚无物”,天人合一,内外合一,只有这样才能诚者自成。
其五,诚即和。诚,是一种美学追求。诚是手段,和是目的。诚与和的统一,就是真善美的至诚与大和之美的统一,就是主客须臾不可分离的真我之道。《书·大禹谟》:“至诚感言。”诚,就是和。
二、文以诚实
尽管中国古代一朝有一代之文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家迭出,风格迥异。众多文论大家的学术观点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诚”最初虽然是自然规律或者说是宇宙规律,但滥觞于《礼记·中庸》的“至诚”这一关键词,一直为后世众多文论家推崇、庚续与创新。本文试图对“诚”、“至诚”之流变略作梳理,以期对“诚”之文论演变理路作一个大致的概括。这一理路也就是“诚”在文论中逐渐丰富、逐渐充实、逐渐完善的过程。
(一)修辞立其诚
先秦典籍多从自然本真的角度对“诚”做多层次多侧面的精要论述。如《论语》的温柔敦厚的文质观:“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为政》篇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批评标准——“中和之美”:“《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尽心上》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反省自己并达到“诚”的境地,提出了“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观念。
《庄子》对“诚”的论述比较全面而具体,特别强调“法贵天真”。其“真”即“精诚之至”。语见《庄子·渔父》: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
《荀子·不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这里还把诚视为道德政治的准则。还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大学》引申《中庸》关于“诚”的学说,以“诚意”为修身、正心、齐家、治国的根本。《中庸》的思想精髓、核心观念、逻辑构架全部以“诚”来展开。《中庸》第二十章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诚之者”是实现“中庸之道”的核心要义。作为天道本体的“诚”也是生成万物的本体,正如“礼”(理),是宇宙万物的本然。但是本于太乙的“礼”(理)却是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天籁,而“诚”则是加入了人类思考的自然之真(这个“真”可能因人因时而异)。而“诚之”则是人们如何认识自己的本性,如何诚于自己的本性以合乎天道。通过“诚”来体认天道,把握人道,构建天道和人道的桥梁,实现“天人合一”的完美结合。“诚”这一精神实体起着化育万物的作用:“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质之终始,无诚不物。”
先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易》关于“修辞立其诚”的主张。语出《周易·乾·文言》: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诚”,从言。自然的本真不经过“人”(作者)的内心的激荡将大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经过加工过的思维通过言说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它还是“礼”的层面,体现不了“诚”的意义。强调“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的《周易》顺性命之体,修辞立其诚,不仅是在道德的高地上讲语言的修辞,讲文章的风格,讲艺术的辞章,而且是对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具体规范,要信,要实,要审,更是以“天地人”的“三才之道”说深刻阐释“文”“道”关系,“天”“人”的关系。以《易》学中关于“圣人”作《易》、读《易》、用《易》的事实和君子道德智慧修养的论说,通过创作心理和思维方式的艺术层面的思考等自然而然地影响并延伸到了文艺创作主体论的方方面面。
(二)疾虚妄,务实诚
汉魏多强调“诚”的本真意义上的本心,涉及文学的创作论、鉴赏论等多个方面。以王充、刘勰、钟嵘等为代表。王充《论衡》“疾虚妄”,倡“真美”,“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强调的是“疾虚妄,务实‘诚’”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刘勰《文心雕龙》在“祝盟”、“奏启”篇多次提到“诚”。他说:“修辞立诚”、“感激以立诚。”“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虽然所论不多,但是在修辞立诚以外,刘勰强调风骨,“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强调“神思”,“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无不与“诚”密切相关。
钟嵘《诗品》言:“《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钟嵘把咏情性、巧构形似、自然声律、自然直寻确定为五言诗的常体。他对风力(骨)树立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直寻自然”,以自然英旨为宗——“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这个“自然”,自然是“诚”。无论是佛家拔思(超拔之思想、想法),还是文学之妙思、神思、精思,都是“诚”的表现。
(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唐宋时期对“至诚”做深刻阐释的代表人物有李翱、朱熹等。唐代李翱将“诚”从道德论上升到了本体论,以尽性或复性为“诚”,这种思想观念将儒、佛思想加以综合利用,认为纯善的人的本性(“性本善”)因情的遮蔽而不诚,所以必须去情、“复性”,使“其心寂然,光照天地”,寂然而又沉静的内心状态正是“诚”的至静至灵的表现。他说:
子思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李文公集》卷二)皎然主张诗歌“取景”,“取景”而重情重诚。他在《赋得吴王送女潮歌,送李判官之河中府》言“乃知昔人由志诚,流水无情翻有情”。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一品专论“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
俱道适往,着手成春。
如逢花开,如瞻岁新。
真与不夺,强得易贫。
幽人空山,过雨采苹。
薄言情悟,悠悠天钧。
北宋周敦颐认为“诚”为人之本性。《通书》言: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
纯粹至善者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他认为,源于乾元的“诚”,为一切道德(万物)的基础——“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只有“诚道”才可以得信用;君子只有“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才可能达到“诚”的境界,它是宇宙之源,更是道德之本。天道之“诚”的生、正、真的综合便是人道上的纯粹的善了。道德上的他律与自律也就成为了具有艺术意蕴的他律与自律。
程朱学派认为“诚”是天理之本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注》里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朱熹将“诚”与“性”、与“理”进行统一,他的《晦庵集》对“至诚”多有所论:
至诚之至,乃极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晦庵集》卷四十《答何叔京》)
至圣、至诚非有优劣。然圣字是从外说,诚字是从里说。(《晦庵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
这些论述既含有“诚”的主体论,也含有意境论、风格论和创造论等。
(四)诚与道,异名而同实
明清以来“诚”的文学理论呈现出既多元而又有迹可循的发展状态。对“诚”之美的追求,在诗文理论中体现为对真、情与自然的追求,广泛涉及文学本质、主体精神、艺术特征、审美风尚等领域。这一“诚”的脉络具体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因时代背景和学术风潮的影响,呈现不同的风貌。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出“诚与道,异名而同实”。他所说的“诚”既可以表示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又可以表示物质世界的实在性。他说:
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尚书引义·说命上》)
王世贞《艺苑卮言》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以他进一步强调“修辞立其诚”。李贽“童心说”、袁宏道“性灵说”都是对“诚”的创新性阐释。李贽认为童心是一切作品创作的源泉,“童心”即“真心”,是表达个体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更是衡量文学之真假、高下价值的首要乃至唯一标准。他在《童心说》一文中言:
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去真人。(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
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倡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里看来,“性灵”和“童心”在审美价值的判断上是一致的,是唯一的——那就是“真”,也就是“至诚”的最高价值标准。
清代桐城派姚鼐对真实的“诚”的境地极为看重,他说:
文家之事,大似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此中
自有真实境地,必不疑于狂肆妄言,未证为证者也。(姚鼐:《尺牍与陈硕士》)
可见,得鱼而忘筌,与作家而言未尝不可。“形而下”的“法”以外,还有更高的“形而上”的“道”的追求;弥漫于作家生命情感中的那份涌动那份澎湃,实际上是与作者生命习性、生活阅历密切相关的那份神思的真实写照;恣肆狂妄的语言下面流淌的正是真实可信的“至诚”之境。
三、章以诚和
尽管在先秦,文章或“彣彰”并不归于一统。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中言:“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者。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但是,无论何种主题,哪种体裁的艺术作品,却往往因为它在艺术上的“至诚”之味而获得荡涤心灵、沁人心扉、给人回味无穷的审美意蕴。笔者认为,这种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诚以礼存,自然之真
《礼记·中庸》开篇便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道即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即人道。万事万物无诚不在。“诚者,物之始也,不诚无物。”朱熹是对“诚”作深入阐释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庸章句》注释中对“诚”做了充分的论述: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
朱子于此释“诚”为“理”,天之道也就是天理的本然流行状态,达到“诚”之境便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圣人境界。《礼记·仲尼燕居》言:“礼也者,理也。”广义的礼(理),含蕴万物,包罗万象,这也是诚的广义的内涵,它不仅有自然的本真在里面,更包容着对自然本真的追求乃至自由天地的向往;狭义的礼(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诚的现实反映。从这意义上讲,诚既为天道,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客体之源,亦为人道,就是圣人之道,就是人类这个道德主体寻求道德之本源,之滥觞。理想层面上,诚依存于现实之礼(理),是去芜存菁没有任何人为因素没有任何思想杂质的自然本真,天籁之境,是天理的最高体现,是圣人之德的最后归宿,是天人合一的终极手段。可是在现实层面上来说,人非圣贤,极难达到“从容中道”之境界,所以儒家思想便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就有了修身养性以至圣贤境界之必要。因此,《中庸》不仅告知我们“诚”为何物,更重要的是告知我们在未达圣贤臻境的情况下以何种现实途径去“诚之”——这也就是《中庸》所言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如何去存天理以养其德成其圣成其贤;于作品而言,便是存之以礼,写自然本真。当然,作者反映的自然本真乃至作者的写作真诚都要通过对艺术真实加以考察才能获得,“艺术真实也只有从作品本体的功能质转化为鉴赏主题的心理感受,即真实感,才算获得完全的实现”①朱立元、王立英:《真的感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
(二)诚以情实,本然之善
诚是自然之本。但是不经过“喜怒哀乐爱恶惧”之七情(《礼记》),这个本真也很难表现出来。实际上,求“真”(“自然”)与重“情”同为“诚”之审美观的两端。所谓“真”即真情实感,发自性情,流于胸襟,不矫揉造作、拘守成规。真与情的完美结合就成为“诚”的本然之善。这在明清文论中表现尤为突出。
明代中叶以后,前后七子先后掀起复古主义的思潮。在此风潮中,尊情、重情成为复古派的一条文学思想主线。开复古文学先河的茶陵派领袖李东阳认为,诗有“天真兴致”,故反复讽诵诗歌可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麓堂诗话》)。前七子代表李梦阳重视真情对于文学的意义,提出“真诗在民间”的口号。在《诗集自序》中,认为诗歌是“天地自然之音”,主张诗人应由情感丰沛转而善用比兴为诗。与之“真诗”主张有关,他在诗歌本质和创作缘起等方面有较为切实而可贵的看法。如:“情者,动乎遇者也”(《梅月先生序》);“诗者,感物造端者也。”(《鸣春集序》)此说虽然是对汉代以来物感说的吸收与继承,但其强调情之“真”与“自然”的思路是十分明显的。此后,徐祯卿论诗重情贵实,反对徒事华藻。其《谈艺录》明确地以“情”为主,以“格”为从,提出“因情立格”说。
明代反复古流派虽然也肯定“情”的重要性,但却对此持批判的态度,对“真”与“自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主要代表为明代后期的李贽、公安派和竟陵派。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导致了反传统、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新思潮。李贽在文学上力主“童心”说。公安三袁受此影响主张“变”与“真”,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和个性化,指出文学和语言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袁宏道提出“物真则贵”(《与丘长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要求创作具有真情实感,有独创精神,反对陈规格套,反对虚伪矫饰,反对因袭模仿和盲目崇拜古人,并由此推崇真诗与民歌。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都主张“求古人真诗”,求古人“真有性灵之言”(《诗归序》)和“得古人之精神”(《再报蔡敬夫》)。他们在学古与性灵之间寻找调和之道,既学古,又求“真”。
清代袁枚将求真、重情这一统一认识加以发展。袁枚别标“性灵”,以追求真情和灵趣为诗歌创作的真谛。他说:
尝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故曰“诗言志”,又曰“修辞立其诚”。然而传巧不传拙,故曰“情欲信,辞欲巧”,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古人名家鲜不由此。今人浮慕诗名而强为之,既离性情,又乏灵机,转不若野氓之击辕相杵,犹应风雅焉。(《钱玙沙先生诗序》)
虽然“巧”是袁枚性灵说的新内容,也即在抒写个人真实情感、思想时重视艺术的灵趣,但性情的真实诚信又是其诗歌学说最重要的基础。
(三)诚以中和,至诚之美
人既是美的创造者,更是美的欣赏者。作为一种审美追求,至诚之美就是行中道,致中和的执两用中的艺术的中和之美,也就是以诚的手段达到中和目的的至诚之美。“中和”是天道的本然和法则;“诚”是行天道和人道的手段和方法。
“中和”一词始出于《礼记·中庸》: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关于“中和之美”,笔者曾有详论,在此不赘①刘金波:《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和之美》,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3期。。朱熹完善儒学心性修身理论,他对儒家学说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基于《中庸章句》创设了“中和之悟”,提出了“诚”与“中和”的完美结合。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宋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俱含有追求“至诚”之理的意思。“诚”于自然,但是显然高于自然。即便是写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因为作者的思想旨趣与写作方法不同,文学的表现主题、思想旨归便迥异。很难想象阴暗的、低级的、庸俗的等等现实会无所取舍无所保留地真“诚”地表现在作品中。恰恰相反,反映丑是为了表现美,揭露黑暗是为了表现阳光。自然虽真,但是并不完美。如何让它完美,这便是如何“诚之”以中和的问题了。朱光潜先生曾说:“艺术的功用在于弥补自然的缺陷,如果自然既已完美,艺术便成赘疣了。”②朱光潜:《朱光潜谈美》,金城出版社2006年,第29页。艺术并不是真诚地再造自然——当然也不可能再造,妙肖自然,而是表现自然——诚之。因为诚,艺术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作品不会言之无文,文之无物,而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为诚,作家触景生情,以情写景,情景交融互藏其宅,构建艺术作品的和美境地;因为诚,意与境浑思与境谐,艺术作品体现出造景之工写真之全;也因为诚,刚柔相济美善相乐,思想与境界达到极度升华的“和”畅境地。
总之,至诚之美强调内容美,强调心理感受,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从自然而至生理,从生理而至精神,它是自然之真,本然之心,纯然之性和超然之德,讲究尽真尽善尽美。对“诚”的不懈追求形成中国古代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美,形成中国古代特有的以“至诚”思想为特征的美学观。艺术上的水墨山水画、花鸟工笔画以及镌刻、书法,建筑上的中轴对称,宏阔宽敞,五行互补,讲究功能、结构和审美的完美统一,文学作品的历史小说、写实散文、随笔等诸多艺术样式,都反映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本真、诚与理、情与思、诚与和的关系,体现出对“至诚”之美的喜好与追求。这种“至诚”追求渗透到古代社会人们对自然、人心、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至诚”之美既体现在天地之序,又体现在道德伦理,还体现在艺术追求、个人修养等多个领域。它所理想的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至真至善和至美的完美和谐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是对当下文学的某些无根化现象来讲,还是对诚信缺失的社会现实来说,仍然极具价值;这种结合存乎天地之间存乎心灵之中形成为中国历来所追求的最高的艺术美— —“天人合一”,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