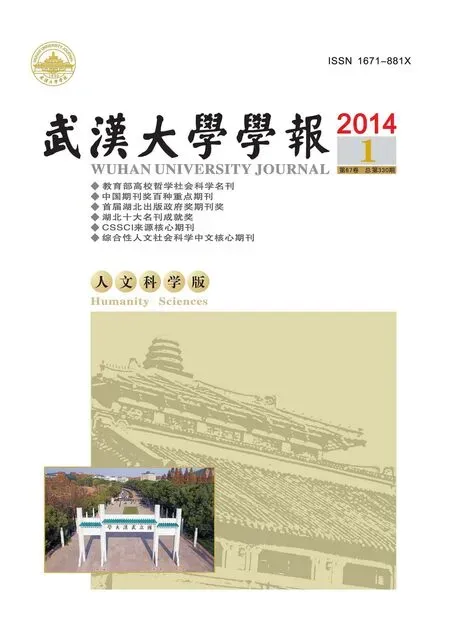九转丹成道者言
——缅怀恩师萧萐父先生
2014-03-04李大华
李大华
吴根友
转眼间,萧先生仙逝四年多了。在那之前,我回武汉参加华中师范大学的会议时去看望他,知道他有时还下点围棋,我当即许诺,以后每年回去陪他下棋,没想到竟无法兑现了。从那以后,无时不在想念他,然而,却不曾写过任何有关他的文字,直接的原因是有关先生的文字并不好写。先生的文章素来诗哲并重,情理兼达,学风精思凝重,文风却行云流水,这既表明他的才高,又表明他的实行,因为情的表达总是作者身心的倾注。可是,情最伤人。这也是我不愿触及的私心。但根友兄嘱我为先生写点纪念的文字,自知这是难辞之责。
我想,先生是大家,学通古今中西,在中国哲学领域,他也贯通儒、道、佛、易,从学弟子中,依各自所好皆有所开通,于是会形成如此的格局,从事于儒者说先生是儒家,从事于道者说先生是道家,从事于佛者说先生是佛家,从事于易者可说先生是易家,又可有人说先生是启蒙家,这可以说是先生学术的复杂与泛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先生是一个道家。这么说不是要为道家抢山头,而是为要确切地道出他的学术价值倾向与心意所往。记得许多年前,与学长齐勇兄谈起先生的时候,他说道:萧先生在思想倾向上是道家,在为人上他是一个儒家。我想这么说大概是实情,这或许是他的生活经历与个性修养造就了如此的格局。说他是儒家,不仅因为他为人的信义、德性的修养以及伦理规范的讲求,更因为他对中国人现实处境的倾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心,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参与。而要说他是道家,则又是由于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哲学反思,尤其是对于儒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反思,对现实生活中人生百态的洞察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不过,这是一个主动选择与实现的结果。这如同说,立于儒家的土壤,却生出了道家的果实。
萧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反省,应当是延续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他推崇那个时期从传统儒学中来,却充满了历史理性、批判与反叛精神的思想家,诸如李贽、何心隐、戴震、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傅山、唐甄、颜元等,认为他们主张“相反之论”,反对“以水济水”的思想,是特定条件下封建主义的自我批判,是旧思想即将崩溃、新思想快出现之前的先声,是一种启蒙的运动。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启蒙运动虽然曲折坎坷,没有完成,但毕竟出现过。故此,应当继续完成这样的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完成“补课“任务。我们知道,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是通过不断地自我批判与反省才实现的,没有沿着一条永不改易的路线走下去。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其近代化与现代化,正是在于出现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大革命,以及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界,则有理性主义及其非理想主义的迭起。至今在西方思想界看来,一个社会丧失了自我批判能力是非常危险的,如同人类丧失了反思的自我意识。中国社会之所以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止步不前,如同做着类似简单重复的游戏一样,从哪里出发,还回到哪里,永在原地打转,就在于缺乏像西方社会所发生的那种思想解放运动。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儒家的思想,尤其是道学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能不反思的。
对待儒家,萧先生的确是多有批判,但是,他并非不加分别地批判。在《传统·儒家·伦理异化》这篇重要论文中,他根据《韩非子·显学》所指出的“儒分为八”的史实,质疑后来的儒家所宗奉的传统到底是哪个“统”?就董仲舒所宗奉的那个“统”来说,是把儒家的宗法伦理意识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举贤良对策》),并由此织成了“三纲”的大网,网罗百代。而程朱、陆王等理学家所宗奉的那个“道统”与“天理”,无非是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传统,加以自家“体贴”,从本体论与功夫论上落实了董仲舒的“道”与“统”。然而,“这种伦理至上主义,绝非人文精神,相反的,乃是一种维护伦理异化,抹杀人文意识的伦文主义。它不仅取消了人的主体性,尤其抹杀了人的个体性,把个体消解于异化了的群体人伦关系之中。”正是根据这个总体的认识,萧先生强烈主张,只有冲破伦文主义的网罗,才可能唤起人文主义的觉醒。与此相关,他认为,将儒家文化作为整个传统文化的代表,把传统文化单一化、凝固化和儒家化,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对于道家文化精神,萧先生可以说是心向往之。他为何向往道家文化精神呢?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赞赏道家学者的那种社会批判意识。他对道家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在他晚年写的一系列重要论文中,诸如《道家·隐者·思想异端》《道家风骨略论》《道家学风述要》等,认为道家“植根于没落贵族下降而形成的逸民或隐士集团,以失势退隐的在野派自居”。也就是说,道家的社会基础在于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身份却是布衣的群体,他们被褐怀玉,“学而优却不仕”,这些“避世之士”往往是一些奇才。他们总是处于被罢黜、受排斥的境地,然而,这些遭遇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信念,反而遭遇使其更显“风骨”,他们与权力结构保持距离,保持独立不阿的批判态度,“固执天道自然,抗议伦理异化”,故而一直被视为思想异端。道家对社会、自然的观察采取了一种客观冷静的观察、研究态度,因而它比儒家把“道”局限于伦理纲常的伦文至上、及其道统心传,更具有理性价值,更接近于科学的智慧。道家虽然对社会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批判态度,却从不褊狭,也从不视他者为“异端”,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一种开放包容精神,像老子所崇尚的“知常容,容乃公”,庄子所坚持的“物论可齐”,司马谈所推崇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皆为道家学风的典型性表达。如果一个社会异口同声,万马齐喑,听不到一点异样的声音,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缺乏批判力,也就是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这正是萧先生在晚年大声呼唤道家精神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主张“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研究现实要有历史感”的具体体现。
在学术界有一种现象,一个学者从事于某个研究领域,这学者也就逐渐变成了这个领域的学者了。不过,这只是所从事的研究对象给一个人带来的改变,如同做了某个方面的研究,就吃这碗饭了。要想成为研究对象那样的人,拥有那样的人格,需要两个条件,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价值观念上的认同,也有生活经验上的相通。萧先生向往道家风骨,人所共知,然而,萧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个道家学者,则要归因于个性化的经历,尤其是晚年的生活经历。记得在跟他做学生的时候,许多其他专业的同窗经常说起先生,说他有一身傲骨,我们也是认同这样的看法的。然而,要做有傲骨的人,就要为有傲骨付出代价。没有经过考验的傲骨,只是外在气象上的;只有经过了考验,而且挺立住了,那才是透骨的超越人格。先生一生经历过许多自不用说,没想到的是,到了晚年还经历了人生的大考验,无意当中被漩进运动洪流当中,“小路寂寞觅多时,尘埃散尽报春迟”。在那个需要耐心和等待的岁月里,先生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不计个人得失,只关注民族国家前途命运,始终拥有丹柯一般火样的心和澎湃的热情,翘首以望未来,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先生有一篇文章,专谈船山的人格美,我想那是他借船山故事勉励自己和学生,所谓“师生同好”吧。此前不久,我又一次与齐勇学长谈起先生的时候,我说道:先生晚年的那些遭遇,正好成全了他的人格。这话得到了齐勇学长的认同。跟随先生学习,自然是受益很多,但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那个格、那个范,还是最大的。
最后那次去看先生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他拿自己的经历,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好像刚刚开始,却马上就要画句号了。能做的事情赶紧做!”这成了先生对我说过的最后的话,这时常在耳边响起的声音,也成了永久的记忆。
浅谈萧萐父先生的子学*“子学”,此处并不局限于“先秦诸子”,而是指包括先秦诸子在内,在汉以后“经学”之外的百家思想。刘勰“博明万事为子”的“子学”定义,大体上可以作为本文所讲的“子学”概念的内涵。而从外延来讲,“子学”是包含了先秦诸子与汉代以后经学、史学、集部以外的“子部”之学术,大体上可以《四库全书》中的“子部”典籍为其外延。如果我们要认真地梳理中国学术史的话,经与经学要给予恰当的分梳。“六经”(实际上是“五经”)是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然而关于“六经”研究所形成的“经学”,则可以看作是广义的“子学”著作——尽管这些著作多是“依经立义”的。至于汉代以后,儒家的少数子部著作被升格为“经书”,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与子、经学与子学的关系变得异常的错综复杂,但“子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未能恰当加以研究的部类学问,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在今天,有人提出“新子学”(方勇)的概念。我想,这也可以促进我们认真研究“子学”以及经与子、经学与子学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对萧萐父先生的子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也可以看作是对子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思想
吴根友
记得萧先生晚年多种场合都拒绝别人以“国学大师”的称号来称他。这其中的原由还有待仔细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萧先生对中国传统“四部之学”皆有自己的独特心得。现已经出版的三卷本《吹沙集》可以为证。仅就经学的研究而言,萧先生对《周易》与易学可谓是别有会心,他提出的“人文易”观念,以及“人文易与民族魂”的关系问题,可谓是当代易学研究中非常值得深入开掘的思想观念与学术问题。而在史学方面,他虽然未对任何一部具体的史学著作发表研究论文,但他所写的《古史袪疑》《历史科学与历史感情》(演讲稿)《历史科学的对象——冯友兰先生史学思想的商兑之一》《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等一系列史学与史学理论论文,以及一系列有关中国哲学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论文,均体现了萧先生在新史学方面的学术成就。集部之类的研究文章也很少见(早年有《原美》篇,晚年有《序方任安著〈诗评中国哲学史〉》),但萧先生的诗歌创作本身就体现了他在集部与文学方面的深厚涵养,非一般研究集部类的学人所能企及。而现行的三卷本《吹沙集》,最能体现萧先生在中国传统学术方面的成就,但是用力最多的,还是子学。
晚年的萧先生,在发表的文章与私下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要敢于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将中国传统的“子学”概念加以泛化,用以描述当今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现象。在《世纪桥头的一些浮想》一文中,萧先生要求我们把“‘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两化’实现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解构、重构,作出新的综合和理论创造,从而有充分准备地去参与‘百家争鸣’”*萧萐父:《吹沙二集》,第66~67页。同一说法,在《东西慧梦几时圆——1998年11月香港“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文亦重新得到阐发。参见萧萐父:《吹沙三集》,第8页。。很显然,萧先生将当今世界范围内各家各派的学术争论,视为当年发生在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的争鸣。这种带有比喻性质的说法,体现了萧先生深邃的学术洞察力与以平等的眼光对待西方,以及其他各民族的思想的学术态度。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正可以从萧先生的子学思想中吸取思想的启示,活化熊十力先生“以平等心究观百家”的学术平等精神,平视西方哲学各流派的思想,并要用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哲学中的诸观点与方法,做到为我所用,而不是亦步亦趋。
平实地讲,萧先生对子学有精深的研究,然未必有明确的子学思想。本文仅想通过萧先生的子学研究的具体成就,结合他晚年一再谈到的“文化包容意识”、多维互动、杂以成纯的诸观念,对其诸子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以求正于诸位学兄及学界的同行。
一、 中国文化的多源发生与多元并进
要理解萧先生的诸子学思想,首先当理解他对中国文化发生与发展的观点。萧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多源头发生的,这就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将是多元并进的。《古史袪疑》一文,一方面要批评西方学者、前苏联学者关于中国人种、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另一方面要扬弃近百来的疑古与泥古思想,走向科学的“释古”,以期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作出比较符合科学的、考古学的描述与说明。通过对上古文化的研究,萧先生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即史前的中国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文化区,“即海岱文化区”、“河洛文化区”、“江汉文化区”,而这些文化区,“大约在距今七千年——五千年都已经确立了父权制,产生了私有制,走到了阶级社会的门槛。”*萧萐父:《吹沙集》,第120页。这三大文化区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炎帝、黄帝、少昊时期,颛顼到尧、舜、禹时代,夏王朝建立的时代。因此,统一的夏王朝其实是经过漫长的多元文化区的历史融合而形成的。
对于春秋战国以后中国文化多元并进的客观历史的描述与论述,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两篇代表作——《传统·儒家·伦理异化》《道家·隐者·思想异端》之中。前一篇文章主要从传统的多元并进的角度,揭示传统文化并非铁板一块,更不是儒家文化一家独大。儒家文化仅是传统文化的一环。而且,更进一步地说,儒家文化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多元并进的。他极力反对儒家内部的“道统”说,对儒家夙以善“杂”见称的历史文化现象情有独钟,仅就先秦儒家而言,《荀子·法行》篇讲:“夫子之门,何其杂也!”《韩非子·显学》篇则指出了“儒分为八”的现象:“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面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裁委员会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至于汉代的儒家也非一统,经分今、古文,而即使是今文经学内部也有分歧,如“三家诗义”与“公羊春秋”在政治主张上就是对立的,而且学术争论还导致政治诛杀*萧萐父:《吹沙集》,第134页。。
宋元明清以后,首先是儒、释、道三教分立,各成一系。而儒家内部更是学派林立,从未有过一统局面。就儒家文化的传统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儒经的传统”、“儒行的传统”、“儒学的传统”、“儒治的传统”。而这四个侧面的传统,也都是学派林立,稳中有变而自成体系,并不是纯而又纯的一家一派之学。
后一篇文章则主要从道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法家的分与合、合与分的复杂过程的揭示,以及儒道互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等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相互影响、多元并进的历史进程,显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活力与诸多面向。
在该文中,萧先生首先揭示了“道、法由相分而分驰”、“儒法由相乖而合流”、“儒、道由相黜而互补”的复杂历史现象,接着着重论述了作为中国思想传统“异端”的道家文化,如何抗议“伦理异化”,对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所做出的异于儒家文化的贡献。下面一段文献的引文稍长,但基本上能比较完整地反映萧先生对道家文化传统的正面价值评判。他说:
在中国,自秦汉统一,汉承秦制,儒术渐尊,儒法合流,形成了封建法统与学统的正宗以后,道家思想以其被罢黜、受排斥的现实遭遇,更以其固执天道自然、抗议伦理异化的理论趋向,便一直被视为思想异端。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百年之中以思想罪兴两次大狱,一诛吕不韦集团,一诛刘安集团,株连镇压大批优秀学者,尤其道家(如“淮南八公”等)遭到严酷打击。但道家并未因此而掩旗息鼓,相反地,历代道家学者仍然以与封建正宗相对立的异端身份,倔强地从事于学术、文化的创造和批判,不断地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尤其在发展科学、文艺和哲学思辨方面作出了超迈儒家的独特贡献,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别树一帜的道家文化传统。*萧萐父:《吹沙集》,第162页。
作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相对立的道家思想,在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潮中也发挥了作用,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便是傅山。傅山旗帜鲜明地批评“奴儒”,明确地宣称是一个道家之徒:“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转引萧萐父:《吹沙集》,第162页。对于傅山这位早期启蒙思想家,萧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他是“继承道家传统的思想异端,挣脱封建囚缚而转化为早期启蒙者的典型人物”*转引萧萐父:《吹沙集》,第166页。。不仅如此,萧先生在《傅山三百周年祭》一文中,别出心裁,用组诗(共14首)来纪念傅山的人品与学术,将傅山放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历史交响乐之中加以评价:“船山青竹郁苍苍,更有方、颜、顾、李、黄。历史乐意凭合奏,见林见树费商量。”*萧萐父:《吹沙集》,第312页。
二、 重视非正统与“异端”思想家的研究
在萧先生的子学研究中,特别重视对非正统思想的研究。上文所说的对道家思想的研究,是其中的突出表现之一。除此之外,萧先生还对早期阴阳家思想,魏晋时代杨泉、鲁褒、何承天、禅宗中的慧能学派,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刘禹锡等作了研究。一般思想史上基本不讲杨泉(三国、西晋时人),他是该时期“与玄学思潮相比较而存在的另一种思潮的一个优秀代表,是当时哲学上两条路线相斗争而发展的一个环节,乃至一个重要环节”*萧萐父:《吹沙集》,第233页。。
鲁褒则是西晋的隐逸之士,其所作的《钱神论》,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统治阶层口谈玄理、而心在多钱的虚伪本质。何承天则是晋末到刘宋时代的一位科学家,祖冲之继承了他的科研成果,确定了岁差推算和回归年、交月点等天文数据。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而最能体现佛教中异端的当数慧能创立的禅宗及其后来法脉。萧先生对弘忍、慧能、石头希迁均有文章论及。早年(1962年)写的《禅宗慧能学派》一文带有很强烈的时代印痕,即站在唯物主义立场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将慧能学派看作是宗教唯心主义的一种理论代表。但即使如此,萧先生仍然高度肯定了慧能学派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环节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肯定了慧能所代表的禅宗学派的思想对于后来“不少的进步思想家”起到了正面的、积极的作用*萧萐父:《吹沙集》,第281页。。晚年在两次禅宗会议上的发言稿,更多的是肯定新禅宗对于中国思想界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略论弘忍与“东山法门”》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中国禅宗开创者的独立开拓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勇于破旧立新的改革精神,二是善于取精用宏的创造精神,三是敢于广开法门的宽容精神。而这三种精神,则“属于传统文化中至今仍具有活力的文化基因”*萧萐父:《吹沙二集》,第302页。。在《石头希迁禅风浅绎》一文中,对石头希迁在中国南禅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整个禅学理论的影响,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石头希迁始终循着中国化佛教的致思途径去推进禅学的发展。他从理论上契入佛慧,首先是从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精品《肇论》得到启发”*萧萐父:《吹沙二集》,第308页。。而且,由于“石头禅强调‘唯达佛之知见’,重视理性思维,坚持禅宗既‘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传统,善于把遮诠和表诠巧妙地结合起来”*萧萐父:《吹沙二集》,第309页。。尤其是在石头禅学影响下的曹洞宗风,提出了“权立五位”、“正偏”、“明暗”等的辩证联合,正可以为灵动地解决“有语”与“无语”、“知识”与“智慧”、“认知”与“体知”的关系问题,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哲学启迪,进而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证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长期对立,无法会通的哲学现象,提供一种新的哲学致思思路*萧萐父:《吹沙二集》,第311页。。
在对非正统与异端思想家的高度关注方面,当然是他在对明清之际诸反理学思想家的高度肯定与赞扬方面。他对黄宗羲、傅山、王夫之等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高度肯定与赞扬,最能体现他子学思想的鲜明倾向性,而他对王夫之哲学思想的系统阐发,对王夫之人格美的高度赞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达了萧先生自己的学术理想与人格理想。他对王夫之哲学的深入研究与阐发,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一个无法绕过的“典范”,亦可以视为他在子学研究方面所树立的一种新典范。
三、 “文化包容意识”与“杂以成纯”的文化理想
与重视子学思想具有内在精神联系的是,晚年的萧先生特别重视“文化包容意识”与“杂以成纯”的文化理想。子学思想极其丰富,很少有“正统”之说,也很难建立所谓的“正统”。无论是从子学的内涵还是外延来看,“子学”本身就是文化、思想多元的一种隐喻。子学研究本身就需要一种文化的包容意识。
集中体现萧先生“文化包容意识”观念的是在对“文化中国”观念*该文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分”“合”“一”“多”与文化包容意识》,载萧萐父:《吹沙二集》,第3~11页。阐述的一文里。在该文中,萧先生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合”与“分”的历史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发生、多维互动、多途发展的实际进程。学界习惯地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看作是宋学的主流。萧先生不太认同这一习惯性的看法,而是给我们揭示了宋学多元化的实际状态:“实际上,北宋新儒学一产生,就有范仲淹等凸显‘易庸之学’,王安石父子又独创‘荆州新学’,周敦颐创‘濂学’,张载创‘关学’,司马光创‘朔学’,二程创‘洛学’,三苏创‘蜀学’,他们之间的各种观点,复杂对立;到南宋,既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之间的激烈论争,又有陈亮、叶适别倡经世事功之学;郑樵、马端临更首辟文化史研究新风,一反‘欺天欺人’的心性空谈,而独步当时。”*萧萐父:《吹沙二集》,第5页。
从上述这一段相对完整的学术史叙述与分析之中可以看到,萧先生将两宋学术内在的复杂性、多维关系及其多途发展的实情揭示出来了,展示了后期中国社会诸子百家争鸣的实际样态。这比学术界惯用“宋明理学”的概念更能揭示两宋学术的实际情况。
萧先生的“文化包容意识”还涉及到对世界上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吸收,这里既包含对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的思想、文化的吸收,也包含着对其他民族思想、文化的吸收。如他对“文化中国”的范畴作这样的解释道:“‘文化中国’这一范畴,既涵摄世界华人文化这一综合性概念在内,又包容了世界各国学者、作者和友好人士对中华文化日益扩大和深化的多种研究成果,这就使其内涵广阔而生动,富有而日新。”*《吹沙二集》,第9页。
很显然,萧先生对“文化中国”范畴的解释,恰恰是对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当中对于中国文化有特殊兴趣与研究的那部分学人的贞定。
仅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言,萧先生虽然赞同百家争鸣,并且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的行列当中,但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及其前景的预测,不同于《庄子·天下》篇所悲叹的“百家往而不返”的结局,而是趋向于“同”。只是这种“同”是以“异”为基础的“同”,如王船山所说,“杂统于纯”,“异以贞同”。当中国文化在过去经历了一段必要的分殊发展之后,“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兼综并育的整合期”*《吹沙二集》,第9页。。而这一“兼综并育”的新文化,即是在中西、古今的交汇中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时的中国文化将是一个“矛盾、杂多的统一”的“和”的文化状态*《吹沙二集》,第5页。,而不是单向度的纯之又纯的新文化。
四、 结 语
仅就思想史、哲学史而言,“子学”其实就是研究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自己的主流,但并不因此而能过多地奢谈“正统”,争抢所谓的“正宗”。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恰恰要在诸子百家争鸣的状态下才能健康地向前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很少有西方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传统,但诸子百家的争鸣在实质上就反映了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实质。在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探讨他的子学思想,对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的自由精神,对于新世纪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都将会从中获得新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