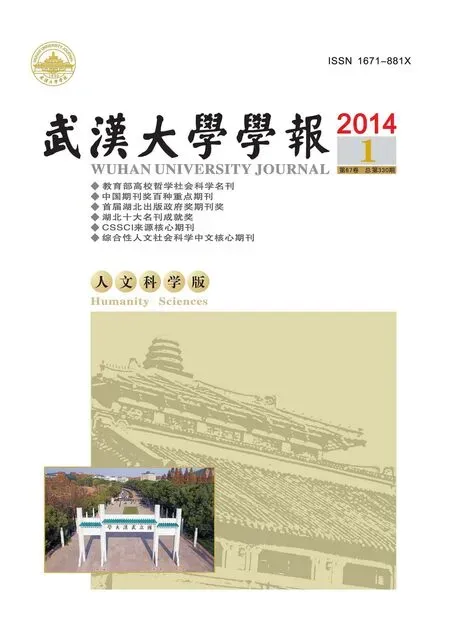哲学家视角下的佛学研究
——读萧萐父先生的佛学研究论著
2014-03-04蒋国保
蒋国保
我藏有几千本书,平时乱堆乱放,每每为找要用的书而烦,唯独萧先生的书很容易找到,因为我总是将他的三部《吹沙集》放在我书架的显著位置,一眼就能看到。为了撰文纪念萧先生90冥诞,我从书架上取下三部《吹沙集》翻阅,希望先确立一个泛泛的论题,再仔细研读与之有关的论文。再三翻阅之后,我决定写研读萧萐父先生佛学研究论著体会方面的文章。之所以从这个方面写文纪念萧先生90诞辰,是因为我认为对萧先生佛学方面的研究,我们尚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不利于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萧先生的学术思想。这只要对萧先生的学术有全面的了解,就不难理解。正如师门学兄所强调的,萧先生“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其学术思想明显具有儒释道融会贯通之特色,若不了解其佛学研究,势必使其融会贯通儒释道流为空说,也就不能准确地把握其学术研究特色。
萧萐父先生的佛学研究论著,刊发者共9篇,即收于《吹沙集》的《禅宗慧能学派》;收于《吹沙二集》的《浅析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源流》《关于〈大乘起信论〉的历史定位》《佛家证悟学说中的认识论问题》《略论弘忍与“东山法门”》《石头希迁禅风浅绎》;收于《吹沙三集》的《序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一书》《佛教哲学简介》。认真研读这9篇论著,细致推敲其中的奥义,就不难体悟萧萐父先生的佛学研究具有三大特征:
首先,萧先生的佛学研究,较之诸多佛教史、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不是以宗教家、史学家的眼光研究佛学,而是以哲学家的眼光研究佛学。在某些自负的佛学家看来,以哲学家的眼光研究佛学,未必不是“‘史’不够,‘理’来凑”,然而若如此看待萧先生的佛学研究,则大谬。就学养讲,萧先生对佛教与佛教思想之历史及其典故的了解相当全面而系统,例如对小乘佛学到大乘佛学的演变历程以及小乘佛学与大乘佛学在仪轨及教义和学理上的差异,大乘佛学之空、有二宗的形成历程及其思想差异,禅宗兴起于东山法门而衍为五家七宗的历史,中国化佛教形成发展历史及中国化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差异等,萧先生都把握得十分准确而系统,甚至对《坛经》4个本子的先后及其优劣、对《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对“乘”(车)、“般若”(音读作“波惹”)、“真如”或“如如”(如实的那样)的含义与读音、对法藏的“五教”判教说、对禅宗的五花八门的公案等,萧先生也都能如数家珍,道个明白。由此可明:萧先生完全具备了著述佛教史、佛教思想史皇皇巨著的学养与学识,他的佛学研究之所以未循这个方向进行,完全是因为他不想在佛教史、佛教思想史研究方面锦上添花,而希望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开垦处女地。这个愿望,萧先生自己说出来,当然说得十分谦虚:“我这次讲的很粗糙,很多资料没引用,有的问题只点了一下。但是,我有个想法,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哲学史上的这些问题,从而反过来思考一些马克思主义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这样才有意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马克思说的,应该把哲学家的语言,还原为现实的语言,把看来很玄的哲学问题,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史论结合,古今通气,这样学习,才能锻炼和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萧萐父:《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第391页。
这番话,是萧先生在“佛教哲学”课结束时对听课的研究生说的,从中可以看出萧先生以哲学家的眼光研究佛学所关注的重点:非一般地研究佛教,而是重在研究佛教中国化;非一般地研究佛教中国化,而是将中国化佛教纳入中国哲学史范畴来研究。其具体的做法,就是透过佛学讲哲学,将很玄的佛学问题还原为一般的哲学问题,将佛教哲学的语言还原为普通的哲学语言。这种性质的还原,贯穿于萧先生佛学研究所有论著,显示了萧先生佛学研究在形式上的鲜明特色。概而言之,其特色有三:(1)将佛学特殊名相还原为一般哲学概念,诸如以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解“心、尘”名相,以共同性、差别性解“一、多”名相,以结合现象、分离现象解“成、坏”名相,以部分、全体解“别、总”名相,以自我意识本身解“真如(心体)”名相等,就属于这类还原;(2)将佛学问题还原为一般哲学问题,例如大乘佛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对“真如”的证悟,它被萧先生论述为试图回答两个哲学问题:“一个是‘本体’和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主体和‘本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萧萐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第255页。;(3)将佛学思辨还原为哲学思维,例如佛学之“二谛义”,本来贯穿于佛教一切经论,是佛教用来解决它所说的“真理”和常识之间的矛盾,以便强调用常人的眼光观世界与以佛教世界观来观世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观到的只是“假象”,后者观到的才是“实相”(真相),但在萧先生的论述里,它被解释为:“把人的认识进行了一番多层次的分析”,且它之分析绝非全是诡辩,实际上触及到“认识无穷深化的问题”,即“接触到了认识过程中的本质和现象,由现象到本质,通过现象排除假象而接近本质,由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萧萐父:《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第255页。等认识深化问题。
其次,注重研究中国化佛教,使萧先生在选择研究对象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向,就佛学经典而言,被中国佛教徒比较重视的《金刚经》《大般若经》《维摩诘经》等,他并不十分看重,反倒十分重视《肇论》《大乘起信论》《华严原人论》《坛经》;就宗派而言,他未论述三论、法相、天台三宗,却对华严、禅宗二宗情有独钟,专门论述。这一选择,其实取决于萧先生关于中国化佛教形成过程的独特认识。在萧先生看来,华严宗和禅宗为中国化佛教的典型,然而在臻于典型之前,佛教中国化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先是印度佛学本体论的中国化,其标志为《肇论》;其次是印度佛学心性论的中国化,其标志是《大乘起信论》;然后是印度佛学人生观、价值论的中国化,其标志是《坛经》。此后,禅宗与华严宗在宋代以后基本合流,予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一个(华严宗)“直接成为程朱理学的理论来源”,一个(禅宗)“直接成为陆王心学的理论来源”*萧萐父:《吹沙三集》,第389页。。正因为萧先生对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如此认识,所以他有那样的偏向就不足为奇。但必须强调的是,萧先生有那样的偏向,只反映他当下的佛学研究偏重之所在,并不意味着萧先生的佛学研究从根本上轻视三论、法相、天台三宗。
再次,以哲学家的眼光研究佛学,决定了萧先生的佛学研究尤其关注从认识论上分析佛教思辨结构,揭示其所包含的合理的辩证认识因素。萧先生认为,佛教基本上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哲学,从哲学角度把握之,它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以及对于本体的证悟论;佛学之证悟“本体”(真如),其实就是通过佛学思辨以确立“自我意识本身”,此确立过程,被萧先生论述为“自我意识”之“思辨循环”。根据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自我意识之循环的分析,萧先生进而大致描述了其循环步骤:“最初是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上升为一个脱离人的、绝对的自我意识;而这个自我意识再进一步到第三步,就转化为一个客观的绝对的本体,客观世界就是有一个绝对本体在背后支持它;第四步,人又要去认识这个绝对本体,人这个主体又要去和这个本体冥合,最后复归为人的意识,重新回到自我意识中去,这时已经是被神化了。”*萧萐父:《吹沙三集》,第335页。
萧先生关于佛教思辨结构既有上述宏观整体分析,亦有微观具体剖析。后者最值得重视的是他关于禅宗思辨结构的分析。禅宗标榜“不立文字”,其思想资料主要就是由故事以及简单对话构成的“公案”。透过“公案”胡话把握其所说之真实含义,已近似破解天书,若再进而把握其真实说法背后的内在逻辑结构,就难于破解天书。然而萧先生却对禅宗的思辨结构做出了独到的分析。按照萧先生的分析,禅宗思辨就结构看大体上有三个相贯的环节,即由“即心是佛”(本体论)转入“亲证顿悟”(认识论)再转入“凡夫即佛”(境界论)。就思辨的内在逻辑讲,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的联系就取决于禅宗以“无念”为宗。“无念”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时不把“想”对象化。非对象化的“想”也就是念念不著相,直接顿悟人“心即真如”,觉悟了普通的人也可成为佛。俗人与佛的区别,就看有没有这个觉悟。
就上面三点而论,萧先生的佛学研究之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可如何去评价它在佛学学术研究史上当有的地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萧先生的佛学与方东美、牟宗三的佛学研究做简单的比较,因为方牟也是以哲学家的眼光研究佛学,他们三者之间有可比性。
方东美的佛学研究著作为《中国大乘哲学》《华严宗哲学》,牟宗三的佛学研究著作为《佛性与般若》。研读这三部著作就可发现方牟佛学观之同异。其“同”显著者有二,一为他们都将中国佛学纳入中国哲学史来研究;二为他们固然都承认禅宗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然都未专门论述禅宗思想,究其理由,当是因为他们认为“禅家多对境施宜,驰骋机锋,闪烁灵明,莫由划归统一之理趣”*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中华书局2012年,第12页。,与他们的佛教研究旨趣不合;其“异”显著者有三,一是方东美承认佛学中国化,而牟宗三则强调“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序》,台北学生书局1997年。,只承认中国佛教是佛教继续发展的最后阶段;二是方东美基于机体主义哲学立场,判华严宗哲学代表中国佛学的最高水平,而牟宗三则基于“二层存有论”的哲学立场,以为天台宗哲学代表最高成就的中国佛学;三是方东美固然以为《大乘起信论》产生之后对佛教后期许多如来藏系统的经典衍生有重要的影响,然而断定它不能算是纯正的佛教,其“二元论”(一心开二门)思辨未能消解“《楞伽经》中谈到善恶二元对立”*方东美:《中国大乘哲学》,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464页。,而牟宗三则予《大乘起信论》以十分高的评价,以为自《大乘起信论》依如来藏系统的经典而“提炼出一个真心后,佛教的发展至一新阶段”*牟宗三:《佛性与般若》,第475页。。
将萧先生的佛教研究与方牟的佛教研究一比较,不难明白,萧先生与方牟二先生固然都是以哲学家的视角研究佛教,但萧先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而方牟二先生则站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在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上萧先生与方牟二先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此外,萧先生认定《大乘起信论》为中国学者所著,以为它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这与方牟二先生关于《大乘起信论》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明显不同;萧先生还着重从认识论层面对佛教思辨及其结构,尤其是对禅宗思辨结构的分析,一定程度地弥补了方牟二先生佛教研究内容上的缺失,推进了中国现代佛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正是从这三方面来看,我们认为萧先生的佛学研究在中国现代佛学研究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席,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