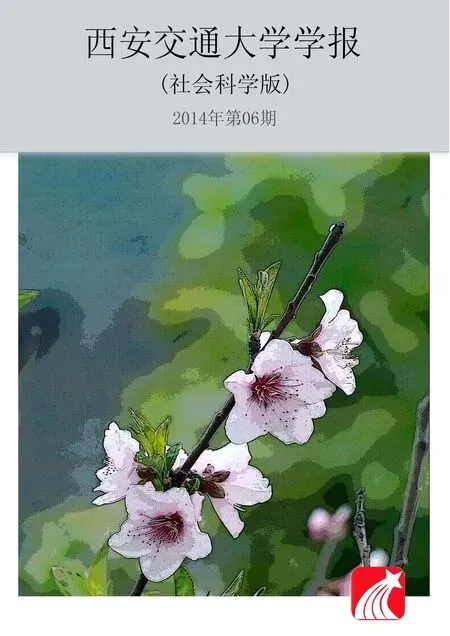《周易·履》卦礼法系统考源——“虎”的星象数术说新论
2014-03-04周兴生马治国
周兴生,马治国
(1.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2.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一、《履》卦词中“礼”与虎关系的必然性之问
礼法根源问题是传统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可参酌的基础文献是《履》卦词:“履虎尾,不咥人,亨。利贞。”经训以“礼”训“履”不能解答此问题。在“虎尾”与“礼”之间为何存在必然联系,礼学研究迄今未曾澄清。其讨论有助于解答礼法根源问题。为此,我们不仅必须澄清前儒述《履》卦词等的礼法义项,而且必须解释卦词涉及数术的必然性。
今择六种涉“虎”文献,以定考察范围。《易本命》孔子云:“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孔子训《乾》“九五”:“风从虎。”《海内西经》:“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西次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国语·晋语》:“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嚚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
《易本命》孔子易虎论“三九”、“七主星”、“星主虎”的主旨,在礼学界已失传。王聘珍引卢辩注云:“二十八宿,方各七也。虎炳文似星也。”[1]卢氏以四垣二十八宿说解“三九二十七”说,属谬说,经言二十七,非二十八。《周易研究》1999年第2期刊乌恩溥先生《〈周易〉星象通考》(一)用“二十八”宿说,亦非。《山海经》神话研究又未曾揭示“虎”与数术、星象的必然联系[2]。
在“法”义上,此文从《尔雅·释诂》“法,典”说,“典”以“数”为核心。其数值确定性是华夏上古以来理性思维的高度浓缩。此文不用“规范”组合,因为“规”不合“典”内直(值)的观念。
二、《〈周易〉集解》诸说检讨
(一)卦词诸训释检讨
《履》①此文唯以书名号引重卦名,指单卦不用书名号。构造:兑下乾上,卦画:。卦词:“履虎尾。不咥人。亨。利贞。”虞翻云:“谓变《讼》初为兑也,与《谦》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刚。《谦》坤为虎。艮为尾。乾为人。乾、兑乘《谦》。震足蹈艮。故‘履虎尾’。兑悦而应虎口,与上绝,故不咥人。刚当位,故通。俗儒皆以兑为虎,乾履兑,非也。兑刚卤。非柔也。”[3]
虞注基于易象说,《说卦传》无象虎说。这表明,卦词“虎尾”并非迳自易象得出,虞氏旁通说回环曲折。虞说有三个节点:一是卦变、二是旁通,三是易象私测。其义如后:第一,卦变指变《讼》初为兑,《讼》卦构造坎下乾上,卦画。“《讼》初”谓重卦《讼》卦下单卦自坎卦变为兑卦,其初阴爻变为阳爻,则得兑下乾上《履》卦。第二,虞氏“旁通”说大要是,“阳爻通阴,阴爻通阳,谓之旁通。”[4]阳爻通阴、阴爻通阳,谓上下两卦之一次第相同而阴、阳爻相反。“通”依许慎《说文解字》训“达”,在此谓阴阳相达。虞说《履》卦与《谦》卦旁通,谓《谦》艮下坤上之上卦与《履》卦相通:《履》卦上卦为单卦乾,今《谦》卦上卦为坤,《履》下卦为兑,今《谦》下卦为艮。纯阳通纯阴,二刚通二柔,一柔通一刚。此谓次第相同而阴阳相达。乾宫通为坤宫。第三,虞言“以坤履乾,以柔履刚”述旁通後重卦要义。《谦》卦易象是坤在上而艮在下,其物性要义是柔胜刚。
虞氏复以旁通述易象。其一言“坤为虎”。此“坤”言单卦坤。其二,“艮为尾”。其三,“乾为人”。其四,述“履虎尾”之故:“乾、兑乘《谦》”言《履》卦上乾下兑恃通而结系而迄《谦》卦。《〈周易〉释文·屯》:“乘马,绳证反。”“《子夏传》音绳。”[5]“绳”训结系,谓筹算。“震足蹈艮”言《谦》内卦二为震,来者为震,今在下而立。震在上,艮在下,故言蹈。前既言坤为虎,而《谦》卦之第三爻为阳爻,第四、五皆是阴爻。以艮为尾,而坤为虎,今连属二者,即得“虎尾”之象。
虞氏以“兑悦而应虎口,与上绝”述“虎不咥人”之故,他又以刚当位驳俗儒之失。今案,虞说不能被《说卦传》证实。他以“旁通”求通卦词,我们也不能附议。理由有三:第一是其易象说偏颇。第二是象数之述不妥。第三是人事之论不备。
首先,他未发明《说卦传》内兽类易象体统,而大有打破易象系统之嫌。虞说“坤为虎”出自先、师训教,还是心得,今不明。事实是,《说卦传》无坤为虎象说。以“坤为虎”是虞氏旁通说的验证,不是卦词旧义,更非《履》卦体统含义。《革》卦第五阳爻述“大人虎变”使其说全盘失据:虎性属阳刚,非坤柔。而且,虞氏适用《说卦传》“兑为刚卤”为说,他选择的场所有误。“兑为刚卤”专指地下水位上升且维持较长时段,土地盐碱化,不宜耕作。上世纪八十年代陕西咸阳礼泉东、兴平北部地下水上升,耕作难继是其例证。
《说卦传》:“艮”“为狗,为鼠”。此语有系统含义:狗为犬科兽,鼠为小啮齿动物,取象都是张口而暴露阳刚。鼠不啮则齿穿脑必死,犬科动物犬齿之性陷肉,是为《洪范》“刚克”说。于兽,虎为王。言齿刚,莫甚于虎齿,故而此卦取象于虎,以述礼法之性无所不克。《说卦传》无虎,《履》卦词有虎,而且完全符合易象。据此可知,自《说卦传》卦象等学说形成迄卦词塑造,存在系统性训解与增补。马融言周文王作卦词,这完全可信,周文王要么发挥了《说卦传》象例,自犬科动物犬齿象例引申出猫科动物虎犬齿象例,这是他的创造,要么传下了先辈珍贵的易象说。其易学史价值不菲。
虞说以《乾》为“人”不合《说卦传》:《乾》、《坤》合而为“人”,《乾》不独为人,《坤》亦不独为人,由于父母象乾坤,产子为人。
其次,卦词取象於虎,其义深远:许慎训虎为山兽。兽亦守也,守者,保其数也。山之象为艮。《说卦传》:“成言乎艮”,此谓八卦次序、时序、数术以得艮卦可以推导结论。山之守者为虎,虎又为教令适用结果的守护者,故是礼法的守护者。
许慎训“尾,到毛在尸后,古人或饰系尾,西南夷皆然。”段氏云:“‘到’者,今之倒字。人可言尸,……人饰系尾,而禽兽似之。”[6]段说约略符合许说。俗语“倒毛”述此,谓毛的疏密依季节更改换过。此说凝结了察兽毛数变动以知节气的认知系统。尾又为後之象,“後”指推导所出[7]。孙诒让训鼎文为“求”是其明证[8]。在无後字的时代,以尾象谓产出,引申义即继嗣。“到”又出自“至”,谓以至日历算。
终了,连属“虎尾”两者,则知象出数,数用于推导。不独推导数字,而且用于推导人的血缘牵连疏密。这是《说卦传》內世系名的别样表述,也是《尧典》九族说的数术基础。
概括前述,虞说曲折回环,不足为凭,《履》卦词旧义集中于历数、辈数上,宗法上的族系含义依解析得以证明,旧说未发明易虎说。
(二)《彖》词说检讨
《彖》首句:“履,柔履刚也。”虞曰:“坤柔乾刚,《谦》坤籍乾。故柔履刚。”荀爽曰:“谓三履二也。二五无应,故无元。以乾履兑,故有通。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利贞也。”
《彖》次句:“说而应乎乾。”虞注:“说,兑也。明兑不履乾,故言应也。”《九家易》曰:“动来为兑而应上,故曰说而应乎乾也。以喻一国之君,应天子命以临下。承上以巽。据下以悦。其正应天。故虎为之不咥人也。”
《彖》第三句:“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九家易》曰:“‘虎尾’谓三也。三以说道履五。之应上顺于天。故不咥人亨也。能巽说之道,顺应于五。故虽践虎,不见咥噬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亨谓于五也。”
《彖》末句:“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虞注:“‘刚中正’谓五。谦震为帝。五,帝位。坎为疾病,乾为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见。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前既检讨虞说,知其唯从旁通例,其易理偏差绝难修正。虞氏又依《说卦传》“兑为刚卤”解《彖》首句“履,柔履刚”。“柔”谓“坤”,“刚”为兑。此说非《履》卦《彖》词旧义。虞氏以“兑”为水,“坤”为土,其象是水在土上,其性就下,此象不合《履》卦词义,也不合《师》卦义。倘使以“水土和”而万物生为训,此乃《论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说,绝非“礼”本身,用“礼”者为《师》,其卦坎下坤上,非兑下乾上。今案,《彖》词“柔履刚”是被动句,言“柔为刚履”,即刚在上,柔在下。
荀爽训“三履二”述重卦之下卦第三爻为阴爻,在第二阳爻之上。此是谬读“柔履刚”所致解释。“利贞”述乾之二德。次句“说而应乎乾”之下未见虞翻实质性训释。《九家易》则述《兑》阴应《乾》阳,自此引申出君臣上下相称,此为秩序之纲的要义。“承上以巽”述风化出自上,即君师肩负教化之责,其含义是《礼三本》君师礼教。
《彖》第三句依《九家易》说,第三爻为阴爻,第五爻为阳爻,此为“上顺于天”。後则承上句。“践虎”、“不见噬”、“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云云,是美化太平时代,这是从易象之虎引申动物虎性,欠妥。《九家易》以“噬”训“咥”,与《释文》合。但训“人”为今“人”则不确,今“人”是泛指,古“人”谓“尸”,即尸祭之尸,主宰礼法与教化。
对于《彖》末句,虞说以“五”述“帝位”,此是易理通例。他又据旁通《谦》为说,旁通说不合《说卦传》旧义。而《履》卦《彖》词含君师教化之义,所教为礼法。
(三)《象》词虞说检讨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虞注:“君子谓乾。辩,别也。乾天为上。兑泽为下。《谦》坤为民。坎为志。《谦》时坤在乾上,变而为《履》,故辩上下,定民志也。”
今又见虞氏依旁通训,虞氏明指“乾”、“泽”之间有上下之别,其说不完备,由于“上天下泽”语例是教令,即命令句。首“上”字是动词,与后一字构造命令句,后两字是并列命令句。今训:“必须名天为上,名泽为下。”“履”在此表方位,谓足践之所。“履”是“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的基础,不依此而训,後释必生舛夺。
“乾”与“泽”的上下位置含自然规律:“兑”象水泽,水泽在地。“乾”为天,水汽生成而凝聚在上,降于地则为水泽。水泽为鸟类栖息之所,附近有草木,故《象》词的引申义是天地能生。《礼三本》讲“天地”为“性本”,其实概括了《象》词要义。
“辩”、“辨”固通。《荀子·富国》:“人归之如流水,……,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杨倞注:“辨,明察也”。郝懿行以为,应训“遍”,王念孙以为应训“平”。[9]我们采杨注,“上下”是方位词,察之者知其永不能平,不辨彼此,則无所谓遍或不遍。
“辩上下”谓明察“上下”。汉以降,经说不述“辩上下”之义。而此义恰突出了《象》词体用观。“上下”有三义:第一,自然界星象上下。其代表有二:一是日出落、月出落。二是北斗七星斗柄上下。前者是动物能察之事,后者唯为君子、巫者所知。第二,地气上下与动植物上下。地气上,则催动植物上,为萌发,惊蛰则冬眠动物出,从地下登地上。第三,势位上下。“上”谓即位,“下”即逊位,如《尧典》“将逊于位”。欲判定《象》词述何者,或俱述三者,或用引申义,须先澄清“定民志”含义。
“定”训正,使之毋倾。“民志”之“民”非谓今日庶民,或众庶。依《国语·楚语下》,古者“民神不杂”。少昊氏前,天下唯有“民神”,无“人”:民为小巫,但不是无知、无名、无能的众庶。《象》词以“君子”指司训教者,他们与民之间存在“志应”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他们的认知力协同,此点为《蒙》卦《彖》词证明:“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君子与巫者的头脑被知识武装,故而能够在认知上相协。
“志”依许慎说训“意”,“意”非谓欲念,而谓推断力形成之前思维的指向。《墨子·大取》:“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参照“定民志”可知,涉及推断力之事不是众庶事务,而是君子事务。他们须在“辩上下”上具备洞悉深层因果关系的能力,否则不能够折服“民”,邑内众庶的秩序倾覆。“上下”是思维方法,出自第一义的引申。
概括前解,“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的本义是:父母为上,子女在下。君在上,民在下。这是两组人伦关系,是都邑聚落秩序的根本。
依《象》词“上天下泽”察“履”在交往上的含义,又知父母为天,子女为泽。父母为先,子女为後。父母为刚,子女为柔。对于父母,子女是以骨肉表现的人身之实,得之则悦,故为兑,孕妇诞子为证。这表述《礼三本》“先祖为类之本”的思想。迄此,“虎”与礼法的关联仍不明。
(四)帛书《履》卦校读检讨
关于《周易·履》卦的出土文献,今见马王堆帛书与与战国竹简《周易》,後者朽残,不能辨识。
帛书《履》卦词:“礼虎尾,不真人,亨。”对于何谓“真人”,“六三”爻词云:“真人,凶。”于豪亮先生曾检讨“帛书的古字古义”,但未重视“履”、“礼”相借之故,迳用今本“履”字[10]。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也未检字义,以为帛书之“真”即传本之“咥”。[11]易学界未曾发掘卦词底蕴。
(五)小结
卦词诸说的检讨显示,“虎尾”涉数术,可用于计算血缘关系。这与《说卦传》世系基础名相通,也是《尧典》九族说的基础,有宗法含义。《彖》词训释的检讨揭示,君臣上下相称是秩序之纲,君师教化之义与《礼三本》“治本”说相合。《象》词诸说检讨揭示,邑内秩序出自“上下”之辩,庶民因此获得行动方向指示。旧说无奠基性创见,不能解释“虎”与礼法之间的必然联系。
三、孔子易虎说暨礼法考源
(一)“三九”、“七主星”考
“三九”、“七主星”是孔子易虎说的基础。“三”何谓是其中的关键。依孔子述,星象是重要话题。
今案,“三”指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说的基础是紫微垣。在天文学界,陈遵妫先生以为,三垣之天市垣较之二十八宿说迟起,其出现应在战国时代。其证据是,天市垣星名都以战国时代的国名命名[12]。我们不附议此说。
陈先生未曾为其判定供给立足点:倘使他能证明国名早,则其论点成立。而我们认为,星名早,国名迟。占星图吉是通例,占其名,再以星命邑里,後有國名,地名与國名之间不存在樊篱。占星者又以星象之吉教化、诱导徒属、庶民,承传数世,闻令者听从,故而出现“國”名。“國”的内涵是“闻命”,通“馘”字。此间结论是星名早而国名迟。三垣说涉及的占星远早于战国时期,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出土含有星象认知的蚌图等,其时代是仰韶文化末期。我们断定,孔子“易虎”说之“三”指三垣之数。
关于“九”,《乾·文言》云“乾元用九,天下治也”颇涉此题。李鼎祚案云:“此当三皇五帝礼让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他未曾考究“乾元用九”之义。先是,王弼也不曾解释。前儒未得“天下治”句的含义。我们认为,“天下治”述礼教发挥功用,故而天下归治。“用九”又与礼法相关。
“九”义有二端:自然数九与汉字九。但“乾元用九”之“九”犹如常数或曰常法,其数必须稳定。以此数为自然数,卜的精确性有保障。以数指地上之物,物亡则数亡。季节变动,曾存在之物亦亡。倘使能在苍穹恒见九物,此数不为地上物象变更而变更,又与“九”恒相称。检索华夏天文学史,知自然数九出自四方加北极星五星,四方观念又出自斗柄四季指四方。斗柄所指是方向,而且它四季旋转一周,其义是度满。
隶定汉字“九”出自甲骨文,《甲骨文编》录《殷墟书契前编》“四·四〇·三”字状如。减省其上的撇,其右下反方向摹画则是商承祚先生《殷契佚存》第二八字的狀[13]。此字形颇怪异。丁山、李孝定先生等以为,九字是肘字的象形字[14]。我们认为,此说绝无恒定依据,由于手臂伸屈不定。
检“九”的构字模样,似带钩状线条。此线条是紫微垣北极星右边六星连线的勾勒。天文学上称勾陈。今察甲骨文“九”字构造,勾陈星数,知占卜用“九六”之数是天文数术,不是盲目形成。勾陈是汉字九构字象形的根本,其义是许慎所讲“九,易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段玉裁引《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广雅》并云:“九,究也”。[6]参酌两说与天文学,我们认为许说近是。“屈”者,未伸也。勾陈六星之状确乎屈曲不展,这是易数变化伸屈的可能性所在,也是数术对古圣人吸引力的概括。将自然数九与四方加北极星五星对称,则两者统一,自然数化为天数九。斗柄四指而且旋转不休,自此抽象出其准数,此数是四九,即全角三百六十度。如此,九数有两义:自然数九是最大数九,易教以九为阳极的准则出自此筹算。
将欲求的数值与已知数联系,又将待求数值视为屈而未申之数,则得勾陈宿之象。勾陈象征的“九”指待求之值。《西次三经》“神陆吾”故事中的“天之九部”是明证。
华夏历史上,谙熟此说的部族是《楚语·下》所记“九黎”,此部族将九族说引入邑内。“九黎乱德”隐藏的信息是“尚黎”的邑众引入“九族”人伦观。这导致了宗教史上重大进步,易礼法被大幅度引入遗传学,它日渐形成邑邦统治的种系基础。
以“九”与“三”相乘,得数合二十七,符合孔子“三九二十七”之数。乘三的缘由是,圣人察星象基于三垣,三垣的创设依据是日东升之所。这个处所选定毫无神秘可言:大猩猩也知太阳初升的处所,但圣人知向东察星象,及其环转。
关于“七主星”,必须结合前述斗柄四指解释。斗柄四指的特点是全角星象观。自然数“七”与汉字“七”,也是两个主题。“七”数是目测计算北斗七星之数的结果,其甲骨文是“十”,此字含苍穹全角之义。以北斗七星四指为星区,以北斗七星之七为范数,每星区求得大星七颗,合计得二十八宿,这是星象学的演进。卢谬注的原因在于,他不知三垣、四垣先后次序,以及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故不知孔子“七主星”说的桥梁作用。
(二)“虎主星”考源
《海内西经》述“兽”:“开明兽身大类虎”、“九首”、“人面”;《大荒西经》述“人”:“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开明兽”与“戴胜”都是司马迁在《大宛列传》所言虎类“怪物”。袁珂先生等同看待“开明兽”与《西次三经》记“神陆吾”,他未考究戴胜出没的易候含义[15]。
经文作者用词交叉,不能掩盖二故事的相似性:“开明兽”、“身大、类虎”、“人面”。后述“人”、“虎齿、豹尾”。“兽”、“人”之间尸教史上相通,尸教必须的道具是“豹尾”,尸刻意绑缚豹尾于臀部,此事的明证是江苏程桥东周墓发掘所得铜器图案残部。
《大荒西经》含易教阴阳消息说,所教为易候,施教者是尸:“戴胜”是鸟,清明后十日降于桑。戴胜不降于桑,政教不中[16]。“戴胜”与“西王母”连属,则得西王母头有戴胜顶羽毛的形象,这是《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述鸟官之治的图景。据此,西王母是“女尸”,她施教主题是易侯。
开明兽的“九首”颇难解释。准乎前已揭示的“九”义,“九首”两字是同位语,述开明兽求天数,旨在定岁首。“首”依《尔雅·释诂》训“初”,“初”通“朔”,指岁首之月第一日。
经言“开明兽”“类虎”,此谓“开明兽”即“立虎”。依《韵镜》,“类”字属“内转第七合”,入“至”韵。“位”,“遂”等亦入“至”韵。“类”是舌音,“位”是喉音,音位变迁,因此两音相通,义亦通。“位”用如动词,谓立身。“类虎”即“立虎”,谁立虎?前后文显示,尸教者立虎。但问:立虎于何处?解答云:立虎于三垣之紫微垣,天皇大帝星之旁。
“星主虎”谓察紫微垣星宿而知二虎立于勾陈左右。比较三垣星线形状,唯紫微垣勾陈左右弧状星带的形状与虎某种身姿相似[12]。勾陈左右弧状星带有相扣趋向。参酌地上虎的弓背身姿,以每弧为老虎起身弓背时的曲线,则见老虎立勾陈左右的粗略形状。弓背在西谓虎面东,弓背在东谓虎面西。勾陈星左侧有天皇大帝宿。连属诸名与星象,“星主虎”的含义是,天皇以勾陈象征的“九”布算而发令。两文献旁证此事:《晋语》记虢公梦“神人面白毛虎爪”,布天帝之命。《墨子·明鬼》记周武王虎贲之卒四百人,虎贲是天子左右卫。
(三)“神陆吾”即“申履”易教考
《履》卦含礼法,但“虎尾”如何与“礼”搭上关系,这难以解释。《西次三经》“神陆吾”供给解答基础:“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虎尾”陈述天数推求的严肃性。
“是实惟帝之下都”,郭璞谓为“天帝都邑之在下者。”袁珂先生案云:“郭注‘天帝’即黄帝。”郭氏注“神陆吾”云:“即肩吾也。庄周曰:‘肩吾得之,以处大山’也。”袁珂先生案“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云:“此神即《海内西经》之开明兽也。”郭璞注“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云:“主九域之部界、天帝苑囿之时节也。”[15]
今案,“西南四百里”述地理。“昆仑之丘”是此地望内代表性地名,也述星空。“丘”、“虚”两字相通。空即苍穹,后世分野出自星区与地区对称。郭云“天地都邑之在下者”半是半非:他言“在下者”,此是。言“天地都邑”而不别处所则非。
袁先生引王念孙以为,“是实”中“是”字是衍字。我们认为,“实”是衍字,本应只有“是”字,如帛书《系词》所言“戏是”之“是”。“帝”有二义:第一,方术。第二,掌握方术的统帅。“戏是”是《系词传》中最早的“帝”。“是实惟帝”谓“是隹帝”,知时与方术者,是伏羲氏。“惟”、“隹”古通,述逐阳气者为鸟,引申义即“知时”。“帝”指方术。甲骨文有“帝”字从口部之例,“口”谓方,指方术。
“之下都”训达地面宗庙,“之”训达,“下”述自天而降。其在天上即天皇大帝星。“都”依《说文解字》训邑有先君宗庙,“下都”谓下有庙祀,是祈求天数法度之所。
“神陆吾”之“陆吾”、郭注引《大宗师》“肩吾”都涉“履”(礼)古读音,此读最迟出自大禹时代,以字定声应出现在周代中晚期。郭璞以《大宗师》“肩吾”训“神陆吾”,但不言其故,袁先生又未补缺。
郭璞以《大宗师》“肩吾”训“陆吾”,事涉华夏以虎为礼教之守的故事。“肩吾”又涉“夷坚”,夷坚与肩吾在历史上可能是一名递变。《列子·汤问》记怪物的阅历者云:“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刘歆《上〈山海经〉表》讲“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刘歆言“益等”指伯益与其徒属。《论衡·别通篇》以为:“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参酌三者,见《汤问》与刘歆二说接近。事多、地远、语音依族系新旧、旧教传承不一,又无伏羲氏那样的全才,我们倾向于认为,明确分工是《山海经》形成的前提。《汤问》说可从,即夷坚参与记传,知大禹、伯益事迹。
夷坚之“坚”即“肩”,读声相通,义亦近。《释名》:“肩,坚也”。[17]《逍遥游》有“肩吾”,也有“连叔”。庄子将二读音并列,以为陈述者,此二读音是一人之名。“连叔”与“陆吾”是一个读声的两记。“连叔”缀读发长声“陆”,与“陆吾”读声不异,所述初非人名,而是勾陈六星。六者,陆也。
以“肩吾”解“陆吾”,知三者本指早期礼教:“肩吾”缀读“屦”,“陆吾”之“吾”、“五”都是牙音,清音,“吾”入“姥”韵,“五”入“模”韵,韵近而通。二者都属“内转第十二开合”。姥韵与语韵发音相近,故“陆吾”又可读履。屦、履相通[6]。故肩吾、陆吾二名指一人,连叔与此同。
神陆吾的作为是礼教:“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其施教涉历数之教,含“典”义,兼备星象与人伦纲领。“九尾”述勾陈为数术之要,“尾”述易教用九为自然数,以行推求,揭前训“尾”。“人面”谓“尸”宣讲数术的确定性。
“虎爪”是主谓词组。虎除了卧下、打滚之外,其他时段以四爪立地,“虎爪”有执土之象。爪之质为角质,其性刚,土之性柔,此是刚在柔上之象,合《履》卦兑下乾上之义。以爪执猎物,又合此象:兑柔在下,乾刚在上。兑即悦,拿猎物凭爪勾入肉,得猎物,故悦。准此,“神陆吾”是申述“履”的大巫或尸。“神”通“申”,此为礼教之神。
“九尾”与“虎爪”之间存在易历数的确定性:以九为自然数,《履》卦是算式:《履》卦有阳爻五,以九乘五得四十五日。准乎岁三百六十日易历法,除以四十五,得八卦之八。这是八分日行轨道的由来。
此“神”“司天之九部,与帝之囿时”。“天之九部”之“天”谓苍穹,是星宿之所。“九部”谓紫微垣勾陈为距度标准判别天区。《史记·历书》:“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谓分部二十八宿为距度。”[18]“帝之囿时”指天皇大帝之苑囿。
从此可以推断,肩吾、陆吾、连叔三者是一名的递变,有其名者是大巫。《履》卦礼法出自巫教,此卦与虎的必然联系有两点:第一是大巫教徒属以数术。数术之本在星象。紫微垣勾陈有虎卫。第二,数术的高度抽象是《履》卦,为突出其数术的必然性,必须突出卦内数术的天数确定性。虎还是《履》数术的严格与精确的象征,故是礼教的坚实基础。
(四)“履虎尾”暨尸赴大难以行礼教考
传本记“咥人”,帛书谓“真人”,此异应依《西次三经》“虎爪”说统一。经训以“噬”训“咥”固是,但“履虎尾,不咥人”应依“虎爪”的象数严谨性训解:“履”谓精絜以祀,从其数。“虎”言岁时、天命的守护者。“尾”述至则定祀,不至则不可祀。“不咥人”训“否咥人”,言“否,数术如虎,将噬为尸(巫)者”。此是天命处罚“尸教”者,尸教者面临这样的惨境。
帛书:“《礼》虎尾,不真人,亨。”易学界迄今未曾体训此句。今案,“礼”从“履”训,谓步迹以时。“虎尾”,如前。“不真人”之“不”训“否”,“真人”固谓仙人登天,但在此合谓不从岁时数术者被祭献,即尸或巫被祭献,巫者不畏死,这是通例。
检《韵镜》“外转第十七开”齿音,清音“臻”、“真”、“津”三字入“臻”、“真”韵,属精母字。“親”字属“真”韵,是清母字。“神”、“真”,入“臻”韵。“神”是浊音,应属“床”母,可读如“陈”。而“辛”字也入“真”韵,是“审”母字。三字韵读与表义关联足以发明旧义:“真”字入“臻”韵,而“津”、“親”字入“真”韵,“辛”也是清音,又入“真”韵[19]。三字的韵读关系是:臻韵统真韵,真韵又统親、辛二韵。“臻”即《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中的“荐臻”之“臻”,训至,与“咥”唯差口部。
親字入真韵,于文字史有据。检季旭升先生引殷契文、周早期金文,真字状有、。季氏引裘锡圭先生“字从贝”,“应是‘颠陨’之颠的表意初文”为说[14]。裘说值得考究:殷契“真”字上是尸字侧面,下为鼎,非贝字。周早期确有从贝的金文真字。鼎镬为食物汇集处,钟鸣鼎食都涉祀。尸字又转而为匕,反映妣教源于尸祭:父母为親而施教,“親”字入“真”韵。“辛”也入“真”韵,辛述罚、辟。于幼童,“親”为太初施罚者,故親字从辛。
许慎记“仙人变形而登天,……所以乘载之。”季氏以为“甚无谓”。季说非是,许说含珍贵的史前礼教信息:母教者或死于教化之艰难,或献身于教化而牺牲。後人久而知先辈告喻的要义,故而纪念。寄托纪念而饰传其事,此即登仙说。
准此,“不真人”一句是较迟版本,其证是“真”有“鼎”部。“鼎”是器物,鼎上有图案,是法象。以鼎图施教是夏殷周铸造发达後大事,但“咥”所从的“至”字涉“止”,出自半坡字系,早于“真”字数千年。“真人”训牺牲“尸”以祭。“不真人”谓“否,牺牲尸。”即某种历算结果不合易教数术,尸教者将被杀祭,以此知古之尸教者献身教化。《乾》“九五”:“风从虎”是教化的又一明证,伏羲氏风姓,易教体统本于伏羲氏,礼法是其主干。
传本“履虎尾,不咥人”早,帛书本“礼虎尾,不真人”迟。两版本差异还在于,述尸教者牺牲的处所不同:“咥”字左取象于凵,而“真”字取象于鼎。大型容器鼎迟出,而凵早。廖名春先生训《周易·履》卦词云:“老虎在后面行走,而不被老虎咬伤,亨通。”[20]他避免了基础讨论,其训不涉礼法本源。
概括前述,卦词含义是:虎爪之象为乾陷兑,应从此求阴阳之数,不从之,尸将牺牲。
(五)“礼法”戮罚说考源
礼含刑之义见于《晋语》述蓐收为天之刑神。此神“虎爪”,“执钺”。“钺”有扇面,甲骨文耳字状从此派生,今暂不考其易教义源。“钺”谓天命诛杀而不可免。且舟之侨告其族两点都有礼法义:第一,君必须有度。第二,小国服大国之教,则是服。倘使不服教,则犯教,大国将诛。依礼则有救赎,悖礼则杀罚,礼教是救赎的根本途径。
“立于西阿”即《海外西经》言蓐收所在的西方:“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左耳有蛇”述惊蛰而蛇动。经籍之蛇非谓阴险狡诈物种,而谓历纪尚孟春。以蛇为闻天令之象,故言“左耳”。“乘两龙”谓阳气以“帝车”行进。“两”训“辆”,述星象之“帝车”。“龙”训阳气动。蓐收是杀戮者,以秋分後杀伐,《吕氏春秋·孟秋纪》为证。据此知易侯说已含刑,而法律史学界“以礼入刑”欠妥,正确理解是,礼法含罚典。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古墓第45号,墓主右有蚌壳虎图。依C14测算法计算蚌壳虎图距今约6400年。墓中见北斗七星、帝星等图。以墓主头面南解方位,虎在西。这符合文献记载。方酉生先生以为虎图是威武之象[21]。我们认为,虎是帝令的护卫,帝令的内涵是礼法。周初武王护卫为虎贲,是其世俗佐证。
四、结论
《履》卦词“虎尾”深涉数术,其适用范围延及血缘关系,是《尧典》九族说的数术基础。《彖》词旨在宣教君臣上下相称是纲常。《象》词旨在陈述邑内秩序出自“上下”之辩,庶民因此获得行为方向上的指示。前儒旧说并无奠基性创见,不能供给“虎”与礼法本源信息,以致卦词礼教史含义不明。
《易本命》孔子易虎论的训释揭示,“三”指远古星象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自然数九出自四方加北极五星之数,四方出自斗柄四季四指。“九”的构字模样出自紫微垣勾陈六星连属。自然数九是天数之纲:斗柄四指旋转不休,为全角三百六十度,囊括各天区。“九”“三”乘积合易虎论“二十七”。“星主虎”谓紫微垣勾陈左右立二虎。音训揭示,《西次山经》“神陆吾”即“申履”,肩吾、连叔、陆吾是一名的递变,皆谓尸教宣讲《履》卦天数。卦词谓虎爪象乾陷兑,从此卦画求历算,得天数。倘使未得,尸将牺牲。此故事显示君师前赴后继,献身易教。君师尚须为礼法牺牲,不从礼法的邦君也不得救赎。礼法的至高威望尽被《履》卦词概括。礼法的起源的时代应在仰韶文化早期,其理性的佐证是星象数术。礼法递变的线索是:巫者察星象而知数术,将星象数术延及地上邑众秩序,巫者与邦君亦受其制。
[1]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257.
[2]连劭明.中国古代神话与易经[J].周易研究,1993(1):57.
[3]李鼎祚.周易集解(1)[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69-70.
[4]杨履泰.周易倚数录.续修四库全书:第3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
[5]陆德明.周易音义.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02:738:402.
[7]周兴生.墨子·经上中“成”式法律推理约束力考论(上)[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2):19-20.
[8]孙诒让.古籀余论.续修四库全书:第243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16.
[9]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190.
[10]于豪亮.帛书周易[J].文物,1984(3):15-16.
[1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J].文物,1984(3):1-2.
[12]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6-197.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65:541-542.
[14]季旭升.说文新证(下册)[M].台北:艺文印书馆,2004:267:12-13.
[15]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2:349:466:56-57.
[16]张惠言.虞氏易候.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64.
[17]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32.
[1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261.
[19]陈彭年,等.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5-26.
[20]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1.
[21]方酉生.濮阳西水坡M45蚌壳摆塑龙虎图的发现及重大学术意义[J].中原文物,1996(1):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