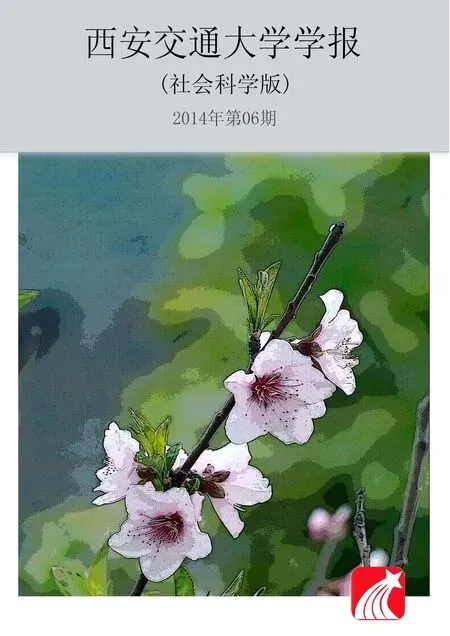哲学视域下的隐士品阅
2014-03-04舒英
舒 英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哲学视域下的隐士品阅
舒 英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隐士”是胸怀世道大略的高端哲思主体,隐士文化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隐士”,首先在于“隐”,而后才是“士”,不仅具备“隐”的特质,同时也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隐士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生活在主体之外、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相契合,且显示出了超人才能的“士人”。文章从“隐”的逻辑生成入手,探究了“隐”与“士”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考察“隐士”历史源流的基础上,准确地阐释了“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隐士;隐士文化;隐士哲学;传统文化
隐士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特殊群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朽的精神主题。飘逸、清雅、淡泊、高洁,是历代隐士所寄寓的形象。中国的历朝历代不论政治是否清明,都能列举出数量可观的隐士。自尧舜直至民国期间,按照蒋星煜的统计,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1]。稽诸正史,旁及笔记文集,研读今人著述,笔者发现学术界对隐士甄别的标准不明晰,“品目参差,称谓非一”(《宋书·隐逸传》)。因此,要深入探讨“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必须准确把握“隐”与“士”的内涵与特质。
一、“隐”之生成逻辑
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何其多,纵观林林总总的这些“隐士”,由于“隐”的范围和方式等方面表现得纷繁杂陈、千姿百态,进而使得“隐”的本身面目变得扑朔迷离,最终学术界在对“隐”的界定上显得迷糊不清、模棱两可,在评判的标准上更是莫衷一是、各持一端。以致于在“何为隐士”的认知及其判定中有众多的分歧,甚至还有对立的一面。笔者认为,所谓“隐士”,显然首先应该是以“隐”作为最为典型的标识来划分的。那么,如何界定“隐”呢?
纵观隐士的历史记载,最初的“隐”都被理解为“隐居”,并且以隐居与德才兼备作为衡量是否为“真隐”的标准。如《汉书》中说的“逸民”,颜师古注释说:“逸民,有德而隐居者也”,就是这个意思。“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蔽也”,段玉裁注释:“蔽茀,小儿也。小则不可见,故隐之训曰蔽”,[2]734《尔雅·释诂》中则说“微也”。无论蔽还是微,都具有不显山露水,与外界隔绝、封闭的意味。由此,很多学者认为,“隐”就是隐蔽的意思,隐居不仕即为“隐士”。[1]显然这种解释并不科学。
从现有历史有所记载的“隐士”来解读,便可得知,很多隐士并非是藏行敛迹的遁世之人,反而是位居高官、出入帝庭官府的知名人士,诸如“朝隐”的东方朔,自称“中隐”的白居易。而根据可查的资料文献,关乎隐士“隐”的行迹表现千变万化,“隐”的理论说明也是歧见纷呈,各持一端。可见,“隐”存在多重理解,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其中也包含了太多的道德情感与价值判断等无法衡量的因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读“隐”。
首先,从表现形式上看,“隐”是一个符号,也就是指一种潜在的身份。从历史上有所记载的史传来看,所有的隐士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生履历的轨迹几乎都相似,看了一个,另一个似曾相识。而且,所有记载隐士的传记也都是一个模式,套路都遵循着既定的范式。而且在不同时代所撰写的隐士传记文本,也存在着某种类似的内在联系。虽然隐士形象有着不同的流动或是变异,但是隐士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却是恒定不变的因素。比如德行,孝悌敏慧、恭谦礼让等。可见,“隐”只是个人的潜在身份,并没有绝对的优劣高下之别。
另外,从本质内涵来说,“隐”是针对“显”来说的,也就是主流对面的在当时不为众人所认可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主要是指其内在的知识涵养与人文素养。比如道者的“逍遥自由”、“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等理念,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它仍然以独特的魅力永存历史的史册,并为世人所传诵。同时也为人类在几千年精神文化的创造实践中,造就了“向死而生”的精神品格以及面对生存厄运,有责任、也有能力重新找回并坚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其前提即为全面审视、并重新确立人性本体意义上的生存价值观,同时建立对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因为生命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复杂而又多变,永远向前才是生命向力的最高理性,它是一种动力,不仅推动着生命的成长与发展,也推动着人类文明与进步。可以说,“隐”涵盖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气质上的许多特点:安贫乐道、卓尔不群、淡泊高雅等,喜好读书、倾心著述,以追求悠闲雅致的人生境界为终极目标。
总之,“隐”从外在的表现形式来看,是一种实践行为;“隐”从本质上来说,却表现为一种价值诉求。也就是说,实践行为是直观考量“隐”的现实依据,而行为由思想意识支配,价值诉求是一种思想理念,于是,“隐”的本质内涵,即由思想理念所反衬的价值诉求才是“隐”实践行为的积极推动力。因而,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式各样的隐士及其种种思想观念与价值诉求,共同汇聚成中国传统社会蔚为大观的隐士文化。
二、“士”之内涵与特质
从隐士的称谓来看,单凭一个“隐”字是无法回答“隐士是什么”,因而,不少学者在探究隐士的同时,都会把隐士的“士”作为参照,以此来揭示隐士的特质。可见,“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以致于近代以来的众多学者对“士”的历史源流、内涵特质等的研究枚不胜举,可谓纷繁杂陈。难怪余英时也感概说:“令人无所适从。”[3]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也是一个具有不断变化的概念。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士,事也。”段玉裁注释说:“凡能事其事者称士。”[2]20把士界定为有素质、有责任感的人。《白虎通义》中则说:“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4]也就是说,能任事且拥有知识技艺的人,才能成为“士”。在先秦文献中,与“士”相关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有百余种。这说明,早在春秋之前就产生了“士”,只是在西周时期,“士”是作为西周宗法家族制度之下的统治阶级的最底层级别的贵族阶层而存在。
从“士”产生的渊源来看,大多学者都认同“士”产生于春秋战国这个社会失序的时代,因为固有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社会阶层上下流动频繁,为“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得以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以致于到了春秋末期,“士”已经演化为阐发和传播礼仪的一种职业,不再具有贵族的外衣。“九流出于王官”,[5]周朝封建秩序的解体,使得在朝做官掌管礼乐的人转衍为民间私学的“士”,特别是在儒家学派中“仕进”的观念长期占有主导地位。这主要缘于孔子开创私人办学之风,使得学在官府的时代不复存在,为士人阶层的迅速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培育土壤,再加上当时小国林立,各诸侯国都想在竞争中强大,这就为“士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于是,士人阶层遂成为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政治力量。这便是余英时所说的“游士”,按照这个标准,可以说先秦诸子几乎都可称之为“游士”,即游走于各个小国之间,宣扬自己的治国主张。在秦汉实现大一统以后,逐渐形成了‘士大夫’阶层。无论是先秦“游士”,还是秦汉以后的“士大夫”,在余英时看来,都是“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3]
余英时直接将“士”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对应起来。他认为,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身份,不仅具有圣人之道的精神追求,也具有独立人格和作为“社会良心”的个人主体性。而“独立人格”,即为“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许纪霖从三个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说明:一是不盲从依附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和现实的政治势力;二是依据自身内心的准则独立判断真理及其价值;三是积极地参与政治,在社会实践生活中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6]。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最为重要的就是其人格的独立与社会批判精神。即不屈服于任何权势包括政治和学术而恪守社会的公道。
可以说,“士”是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人”的形态而存在的一个社会阶层,其独立性也体现的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志于道”,即遵从自己内心的准则,也即独立的价值判断;第二,不屈从于政治势力的自我判断和独立意识;第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士志于道”是孔子为中国“士人”规定的基本理路。此后,“道”成为中国士人的一种坚守和追求。曾子承继孔子之说,对“士”的品格及其责任规定得更为明白,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士”的基本品格是“弘毅”,“士”的人生使命是“弘扬仁道”,同时也是“士”应当肩负的责任。何谓“弘毅”?朱熹注解为:“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至其远。弘而不毅,则无规则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弘大刚毅,然后能胜重任而道远。”[7]所谓仁道,即正义之道,是一种超拔于人伦关系之上的尊重人心的美德。为实现弘扬仁道,“士”不可以贪图安逸,见利忘义,“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论语·宪问》)“辟地者不怀居以害仁”(张载《正蒙·有德》)不仅如此,“士”甚至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捍卫仁道,“士见危授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
中国士人对“道”的追求和坚守,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体现为不屈从于政治势力的自我判断和独立意识。事实上,在君主政治制度之下,“士”的出路大概有两种:一为学;二为仕。为学者,承继弘扬经典,评论古今。如同刘向《说苑》中所说“辨然否、通古今之道”(《佾文》篇)。意旨士人以道统自居,坚持道统高于政治统治的权威,并时常会对统治政权有所非议或是提出挑战。为仕者,依傍于现实,立足于统治阶级的政权,这才是士人的现实出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能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是说“仕”对于“士”就如耕地对于农夫一样,都是一种职业,士应该积极进入政治,为民服务。当为仕之“士”直接面对现实的政治势力时,依然应当体现出独立的士人精神和人格。天下有道,言论畅通,则批评讽谏,积极入世,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天下无道,言路淤塞时,“士”的独立则体现为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而选择归隐山林,即如孟子所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
“士”的独立人格还体现在“以天下为己任”,即“对于天下大事进行积极的参与并企图发挥主导的作用”的社会责任感。因为“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意志,当然具有坚强不屈的独立人格”。[8]的确如此,从孔子为“士”做出立于道的规定起,士人就不仅仅停留在“修身”之道上,更为重要的是要归于“治国”之道,修身是独善其身,是“小道”,治国则是兼济天下,是关涉天下生民的“大道”。 因此孟子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现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
总之,对于士人来讲,应该是胸怀天下苍生,而非一己之利。遵从道、尊重道德良知却是有正义感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坚守的精神操守,“铁肩坦道义”的精神至今仍不绝如缕。
三、何谓“隐士”
“隐士”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荀子·正论》中,说“天下无隐士”,意指“隐居不仕的人”,这与《辞海》中的解释颇为相符。据文献记载,中国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却并非都可以称为隐士。正如《易经·周文王篇》中说:“天地闭,贤人隐。”《南史·隐逸》中也说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也就是说,隐士是“贤人”,是有学问、有致仕才能而又不愿为官的文人士大夫,并非一般人。
“隐士”作为一种存在,很早就已经出现了。《论语》中所记载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等等,都是著名的隐士。近代以来,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隐士的著作是蒋星煜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文中近乎全面否定了隐士的思想及其隐士存在的社会价值。蒋星煜认为,隐士的出现从主观上看是由于个人主义或失败主义,而从客观上看却是一种逃避思想,并感叹隐士“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一无裨益的生活有何乐趣。”这显然是没有真正厘清“何谓隐士”,才会出现这种错误的理解。
“隐士”的称谓在中国古代可谓是种类繁多,其实这些各式各样的称谓都从不同层面反映出世人对“隐士”的认知和接受的程度。无论古今,对隐士的评判褒贬不一,有些学者甚至以“隐士”所受的隆遇来评判其声望影响。究其缘由是在不少隐士的传文中载录了帝王的诏文,因为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有礼敬隐士的倾向,并以此“作为打造明君圣主和政教清明的有效工具。”[9]比如宋孝武帝的诏文中对当时的隐士王素和朱百年难掩溢美之词,“廉约贞远,与物无竞,自足皋亩,志在不移。”并赞赏有加,“宜加褒引,以光难进。”(《宋书·隐逸传》)从这类诏文可以看出,帝王在发诏文之前,实际上这些隐士的身份早已被认可,在民间广为流传,官府只是以此为据进行征辟。也就是说,早已在社会舆论中得到认可的隐士,只是通过官府的这种征辟活动来提升其声望抑或是知名度。若是没有得到官府的认证,此人的社会声望评价便急剧贬值。可见,隐士是个人与社会双重建构的身份,与此同时,在被社会各个群体的接受过程中,“逐渐升华为一种意义符号和价值资源。”[9]
国内的学者一般是在官僚政治的框架中来界定“隐士”,普遍存在的观点即为“士人隐居不仕”;国外的学者却是另辟蹊径,一般在宗教信仰的视野中来界定,认为出于宗教动机而与世隔绝,即士人遁世修行即为隐士。可见,隐士的存在具有多样性,无论是以“不仕”作为界定“隐士”的根本特征,还是以“隐修”来说明“隐士”的本质内涵,都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这都与本文所阐释的“隐士”有着相当的差距。
唐德刚曾说过,“志气”和“前途”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性[10]。隐士作为有内涵的知识分子,必须有志向,其“志”当然与前途相关。在前途并不明朗的时候,显然必须坚守着志向。事实上,隐士是“士”阶层的一部分,准确的说是“士”中的优秀分子。余英时也没有把所有的“士”都视作知识分子,他认为,“士”是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历史来源。作为“隐士”,首先在于“隐”,而后才是“士”,不仅具备“隐”的特质,同时也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隐士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生活在主体之外、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相契合,且显示出了超人才能的“士人”。
其实,人的生命既属于个体,又属于社会,个体的生命是超越社会的。隐士所追求的是超越社会范畴的人生,自由自在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可以说,历史有所记载的隐士,没有哪一个是无人知晓、真正一辈子隐居山林,从未展示自己才能的。正因为如此,评判一个人是否隐士的标准,不能简单的用是否隐居,是否出仕,是否宗教等来论断。最主要的是其思想及其社会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就是他对社会主导性价值观而言,虽然在当时也许是另类,不容被世人所接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却能被后人所认同,并成为思想文化的宝贵遗产。
可见,真正的“隐士”是游离于政治权力体系之外,又拥有知识与道义的优秀士人。卓尔不群、宽容礼让是其外在表象,安贫乐道、淡泊名利是其内在标识。所以,隐士以德修身、以礼化俗,对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不可小觑。世人对隐士的接纳与认同使其具有的独特的道德整合功能,因为隐士自身的行为,以及社会评判隐士的标准,既是隐士个人表现出的价值内涵与人生态度,同时也是社会其他群体所认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准则。
因而,“何谓隐士”?仕与不仕,藏与不藏,宗教亦或是世俗都可以被称为“隐士”。判定的标准主要在于其所承载的社会价值理念是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由此可见,“隐士”并非隐而不闻,其存在看似隐性,实际上为显性。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哲学,还是在科学等领域,都有隐士留下的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因为,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修行。
[1]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1,94.
[2]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9-10.
[4] 班固.白虎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54.
[5]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 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1:3-4.
[7] 朱熹.四书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25.
[8] 张岱年.人伦与独立人格[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108-112.
[9] 胡翼鹏.“隐”的生成逻辑与隐士身份的建构机制:一项关于中国隐士的社会史研究[J],开放时代,2012(2):45-55.
[10] 唐德刚.中国之惑[M].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27.
(责任编辑:司国安)
ObservationandEvaluationontheHermitinthePerspectiveofPhilosophy
SHU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The "Hermit" is a high-end philosophical subject cherished with manners and morals of the time and great world strategies and the Hermit culture is also a unique landscap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s a "Hermit", the first implication consists in "hiddenness" and then "intellectual". He not only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ddenness" but also is in one line with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an "intellectual". As a member of a unique group of intellectuals, the hermit lives outside of the social main body, and is unable to fit with the official or mainstream value system, and also shows the talent of superman. Starting from the logic generation of "hiddennes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s and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hiddenness" and "intellectual", and then gives an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Hermit" culture phenomenon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hermit".
hermit; hermit culture; hermit philosophy; traditional culture
2014-03-12
舒英(1970- ),女,四川资中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B223.9
A
1008-245X(2014)06-00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