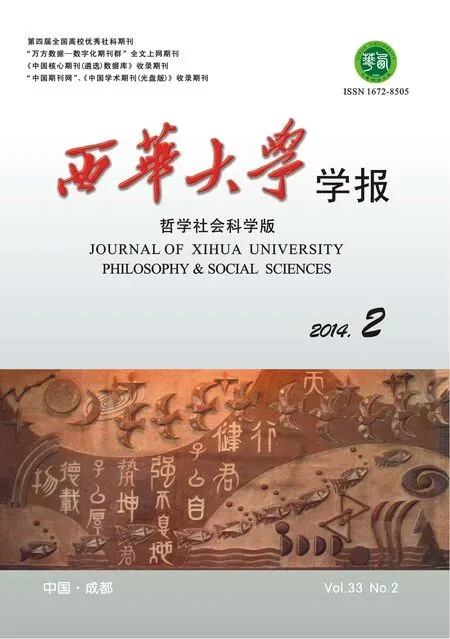澳洲华裔文化的民族渊源与历史记忆
2014-03-03郭志军向晓红
郭志军 向晓红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对中国人而言,隔洋相望的澳洲大陆是一块既富有原始气息又充满现代活力的神奇土地,而对于作为澳洲社会“边缘人”的华人群体而言,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遭遇和命运,折射出其复杂的心态和酸甜苦辣的人生体味。中国人究竟何时与澳洲大陆开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已经不可考究。1985年安德鲁斯在《中国与澳大利亚》一书中提及“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澳大利亚制造的天文观察设备。”[1]1879年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地区,人们发现了类似中国古代沉船的痕迹。可以推测,早在明朝时期,中国船只就曾经穿越印度洋经过帝汶岛,最终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有历史记载的中国人登陆澳洲应该从1848年开始,即清朝道光年间,第一批契约苦力劳工从厦门出发,开始了他们的澳洲坎坷之旅。在近200年的可考澳洲华人历史中,华人在澳洲从蛮荒之地到现代化国家的成长历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当代中国的快速崛起又带给澳洲华人怎样的启示和机遇?因为国情的差异和距离的遥远,中澳两国的华人传统文化究竟是走向分歧还是融合?这些问题亟待我们去思考研究。笔者尝试从不同的视阙,通过深入地发掘史料,呈现中国人从开始接触澳洲大陆到劳工移民以及其后的华裔文化的演变过程,揭示当地华人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剖析其背后的民族渊源与历史根源,并据此对中澳文化进行比较,促进两者之间的交流。
一、19世纪的中国“契约劳工”文化
今天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由100多个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据澳大利亚国家官方人口普查统计,截止2006年,“全澳华人为669890人,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3.4%,位居各民族人口排名第七位。”[2]追溯到1848年10月2日,第一批中国籍劳工漂洋过海抵达悉尼港,而后在1854年约2500名相继抵澳,根据每年收入大约12到24英镑的契约在这块原始而又年轻的大陆上开始了淘金之旅。起初的华人从事码头苦力、牧羊、种植业、矿工等体力行业,遍及澳洲各地,给当地注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同时也引发了中澳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鸦片战争洗礼后的近代中国,民不聊生,沿海地区的大量中国人为了逃离苦难,争先恐后逃亡海外,导致澳洲华人劳工人口迅速暴增。大多数契约劳工来自社会底层,文化素质参差不齐,聚众赌博、吸食鸦片等恶习被澳大利亚当局嗤之以鼻,深恶痛绝。《澳洲公报》在1881年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一个婴儿握紧拳头对抗一条面目狰狞的恶龙,题为“年轻的澳大利亚面对中国巨龙”,并把中国人描述为这样的形象:“中国人是半人半兽的怪物,卑躬屈节的废物,罪恶、无知、迷信的下等人,整天沉溺于吸食鸦片,只要一接触他们,自由开明的白人社会就会被玷污……”[1]。随着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把白澳政策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旨在反对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使大部分华人忍受不了欺压,被迫离开澳大利亚。直到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取缔了这项移民限制法案,采取多元文化政策,华人文化才慢慢崭露头角,传承并展示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纵观白澳政策时代,澳洲华裔文化就是后殖民主义时期的移民文化,同时也是反抗澳洲白人主流话语的文化。一方面,19世纪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外国侵略的脚步渐渐深入,清政府腐败无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在澳中国华工移民素质普遍较低,大多是沿海的苦难民众,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修养。“中国人是没有宗教观点的异教徒”,“中国移民教育程度低,卫生情况差,造成了麻风天花等传染病的流行”[3]等等报道在澳洲常常见诸于报端,甚至留在脑后的长辫子成了中国人愚昧落后的象征。此外,新生的澳大利亚作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商品输出地之一,鸦片也作为特殊的商品大量流入。在这个风云动荡的时代,社会物质匮乏,民众精神空虚,鸦片既是聊以自慰的身体麻醉剂,又是特殊的精神寄托物。“侨民不染嗜好者故多,而吸食洋烟者亦属不少,近四年澳洲政府禁烟入口,吸者渐少,然船上人往往私带烟膏到埠,暗为发售,故吸烟之徒尚未尽戒”[2]。以1891年的新南威尔士州为例,每个华人的年平均鸦片消费量达2.3磅,维多利亚州为1.7磅。鸦片“毒文化”对华人劳工的残害罄竹难书,使本来生活艰辛的华人群体雪上加霜。直到1905年,迪金总理宣布执行中央联邦的《禁烟定例》后,鸦片的毒害才没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澳洲白人对大量华人劳工的涌入惶惶不安。他们既担心其经济利益被日益蚕食,又唯恐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价值观受到东方文化的侵蚀。1854年到1861年期间,澳洲各地爆发了排华反华浪潮,乃至维多利亚议会于1855年通过澳洲历史上第一部移民限制法律,规定:“来澳船只每10吨限载华人1名;每个入境华人交人头税10镑;征收华人每月1镑的居住税。”[2]同时,政府通过语言考试改革,如增加听力考试难度来进一步限制华人移民数量。在国外种族歧视加重的情况下,没有强大的国家后盾,华裔劳工的待遇及地位每况愈下。可幸的是,1876年,郭嵩涛被清廷任命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其深知在澳华工的苦难遭遇,执意要求英联邦政府批准中国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虽未功成名就,却为后继者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人领袖梅广达等人成立华人商会组织,一边锲而不舍地要求清政府在澳设立领事馆,一边团结各地华人通过繁琐的程序向澳政府交涉以保护华工在澳利益,以勤奋、廉政和正义赢得各界人士的尊敬。同时,洋务运动的主创人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王荣和、余瓗等人赴悉尼等地考察,于1902年出版了《地球韵言》,首次详尽地向封闭的国人介绍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人文风情及华人劳工的境遇。在淘金运动的洗礼下,华人移民潜在的生存欲望愈发强烈,在各行各业都能看见中国人的身影。据“驻澳洲总领事馆梁澜勋详陈在澳华人民情形呈外务部禀文”中记载,20世纪初,维多利亚侨民已经超过6000余名,墨尔本侨民也达到3000名左右。梁澜勋在禀文中写到,“操业者以农圃为多,小本营生者次之,木工、矿工又次之,洗洋衣者又次之,商务无多,势且日削,乃复各设会馆,各分行头,畛域互分,是足以召外侮……。”[2]这份对澳洲华人生存状况的写实,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清末民初时期中澳关系处于新阶段的“起点”位置。从此,中澳之间贸易及文化的交流将渐趋突出,为华人移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的华人契约劳工文化,虽然不及澳洲早期流放犯书写的殖民血泪史那样悲壮,但是早期华工在澳洲的坎坷遭遇也可窥一斑,其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在新兴的澳洲大陆,华人在“白澳至上”的种族歧视及国内清政府的漠视下步履维艰地生存。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下,其生存的内在矛盾相当复杂。在逐步融入澳洲社会的同时,如何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成为华裔移民们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随着墨尔本的广东籍冈州会馆和四邑会馆成为华裔群体共同议事求发展的重要场所,越来越多地华裔群体团结一致,创办华文学校以培养学贯中西的双语人才,建立统一的组织,如“中华商务总会”,以促进中澳贸易的发展。综上所述,早期华裔移民在澳洲的奋斗史让人可歌可泣,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更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充满张力的反思空间。
二、澳洲华裔文学中的中西文化碰撞
在19世纪,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澳洲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联邦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只是零星的物物交易。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中澳经贸关系迅猛发展,两国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经贸的频繁交往促使华人移民澳洲的浪潮经久不息,大量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华人移居澳洲,其文学作品在澳洲文坛崭露头角,但很少有人关注其发展,只有零星的论文见诸于报刊杂志。许多著名的澳洲华裔作家如丁晓琦、方晓舒、施丽英、欧阳昱等,围绕中西文化的排斥与交融、多元文化下的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等主题进行研究,关注华裔群体自身的成长体验,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瞬间。众所周知,某一特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宗教活动、社会风俗习惯、吃穿住行活动等等都可以在其语言记录中找到痕迹,而文学作品则是文化的最佳载体。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产物的华裔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渊源,这有助于我们剖析澳洲文化中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进一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
首先,20世纪后半叶,从澳洲政府摒弃白澳至上的种族主义到实施多元文化政策以来,作为少数民族的华裔作家悄然崛起,其文学作品甫一出现就具有对抗澳洲白人主流文化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特征,同时也细述了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对中国本源文化的苦苦追寻。如桑晔的《龙来的那年》、方晓舒的自传小说《东风,西风》、吴丽莲的《吞云》等小说都共同描写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移居澳洲的坎坷经历,仿佛是一个世纪前淘金热时期中国移民遭遇的真实翻版。这反映了旅澳华人为获得同等的澳人权益而产生的种种焦虑、迷茫和遭受的挫折。毕熙燕的长篇小说《绿卡梦》中的女主人公在男性中心话语主宰的异国城市中,艰难地冲破传统世俗构筑的樊篱,通过与西方人联姻实现了自己的绿卡梦。在理想化的精神追求和世俗化的现实生活的矛盾中,新时代移民们的爱情观呈现出异质文化间的对立碰撞,甚至最终都不能达到妥协融合。毕熙燕的另一部小说《天生作妾》则表现出悲观主义的宿命论色彩。作家的结论是:在跨国文化、身份阶层、传统文化等命运逻辑的桎梏下,贤妻良母是女性的最佳归宿。毋庸置疑,作家虽然描述的是女性在异国他乡追求幸福生活过程中的种种艰辛、挫折和成功,但其作品的主题内容、人物形象等都处处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
其次,一部分华裔文学从身份的落差感介入,关注华裔移民从享受富裕生活的脑力劳动者跨度到异国的体力打工者的巨大转变,不断诘问移民海外的价值及自身的最终归宿。这批作家擅长“刻画小人物的故事,关注另类主题,旨在唤醒人们的良知,使其找回自我,找到理想的空间。”[4]如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以主人公罗伯特·刘在澳洲的求职经历为主线,并以其朋友的生活遭遇为副线,讲述了主人公放弃了国内优越舒适的环境到澳洲打拼,遇到了种种求职尴尬甚至是种族的歧视,最终不得不带着在澳洲收获的所谓精神财富回到祖国。另一作家武力的纪实文学,以敏锐的审美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当代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变,人们憧憬个性得到解放,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热爱。武力的《嫖客》中的主人公经历了中国极左政治路线时期的压抑生活,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留学澳洲。澳洲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于传统观念和制度束缚下的中国,性渴望的煎熬使他一到澳洲迫不及待地流连于风花雪月场所,寻求个性压抑的解放。最终,主人公只是通过金钱获得性的满足,并没有收获自己圆满的爱情,对移民海外的最终归宿陷入了迷惘。虽然此篇小说只是探讨了就婚外性行为方面中西在社会伦理道德上的差异,但从某一侧面折射出了思想观念的变迁所带来的心理焦虑与迷惘。作家也暗示了在物质生活丰富、个性充分张扬的当代中国,人们盲目地接受现代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很难理性地把握时代变迁的脉搏。
同时,虽然澳大利亚是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但占绝大多数的盎格鲁撒克逊藉后裔的白人文化既不同于西方的欧美文化,更迥异于东方的中国文化。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条件恶劣的丛林生活造就了澳人生性豁达、乐观向上、强调个性张扬的生活理念,而中国人相对比较保守内敛,注重群体意识。例如,毕熙燕在其作品中重新审视了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家庭矛盾,把中国式的婆媳关系放在澳洲社会去考量,对中西方传统意义上“家”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凸显了华人移民在和异族通婚后的生活磨擦与融合。张劲帆的中篇小说《初夜》里,女主人公白玫在金钱至上的都市生存法则下苦苦挣扎,经济的拮据、求职的艰辛、身体的羸弱使其身心疲惫,痛不欲生。白玫完全可以借助自己的美貌依附男人而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然而,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浸染的她拼死保住自己的处女贞操,直到委身于自己觉得可以托付终身的白人男子。白人男子却对白玫居然是处女的事实惊诧不已。在西方人眼里,贞洁观念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进行性禁锢的武器,是男权社会剥夺女性爱情婚姻自由的一种陋习。中国人则认为,妇女恪守贞操,绝对忠于丈夫乃是女性的美德。
最后,澳洲的中文报刊如《澳洲新报》、《星岛日报》、《澳洲日报》和《东华时报》以及《大世界》《焦点》、《原乡》等杂志,刊登各种题材的华裔作品或随笔,反映澳洲殖民历史、风土人情、经济政治等五彩斑斓的异国风貌。千波的《旅澳随笔》、王晋军的《澳洲见闻录》、张奥列的《悉尼写真》等作品从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视角,抒写浓厚的澳洲风景,演绎着充满魅力的澳洲生活。不管怎样,这些作品也或多或少展示了华裔移民如何适应、融入澳洲文化,并在澳洲文化中生存。
一言以蔽之,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研究文学语言尤其对该民族的文化研究不无裨益。华裔文学反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特征,不仅包含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气息,而且蕴藏着华裔群体的人生价值观、生活状况及思维方式。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文学属于“边缘文学”,直到1973年,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才引起世界文学评论界的关注。澳洲华裔文学更是襁褓中的婴儿刚刚起步。但笔者坚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通过中西文化不断的碰撞、调节并融合,大量优秀的华裔作家及其作品必定会登上舞台,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抒写中澳美好未来的新篇章。
三、多元文化主流下的澳洲华裔文化新发展
多元文化的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殖民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起源于黑人群体争取民权的美国,不断发展和完善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其核心内容是不同信念、肤色、语言、文化族群的相互融合且平等存在。多元文化是当今世界上令人瞩目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关照与思考人类历史文明的望远镜,又是探讨与审视当代各种社会与文化问题的显微镜”[4]。从1848年第一批中国契约劳工登陆澳洲,到1901年澳联邦议会通过“白澳政策”为指导方针的《限制移民入境法案》,再到20世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移民潮,澳洲华裔文化从无到有,最终在澳洲土地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随着中澳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凸显华裔文化的各类交流活动日新月异。近年来,澳洲华裔青少年在华的寻根活动,中国官方在悉尼、墨尔本等大学设立的孔子学院定期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中澳理事会在中国大陆各大学开展澳大利亚文化周活动等活动揭开了中澳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在早年的澳洲本土,华裔文化最显著的展示平台就是过年过节时唐人街的舞龙舞狮活动而已。近年来,具有高学历、艺术修养甚高的华人移民不断涌入澳洲,如今的澳洲国家芭蕾舞团、悉尼交响乐团等艺术领域里逐渐出现了众多华裔艺术家的身影,极大地丰富了澳洲的华人文化,给本地华人和主流社会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精神享受。在饮食方面,地道的中式餐馆把悠久的中华饮食文化带到澳洲,具有浓郁中国味道的西式菜肴在各地餐厅里也屡见不鲜,其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同时,澳洲各大中文报刊虽然在信息时代的冲击下日渐萎缩,但《澳洲新报》等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保留和宏扬汉语言文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还有一大批澳籍华人郭存孝等人,陆续发表澳洲历史、中澳关系等著作,或追忆历史或展望未来,为世人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推动着海外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澳大利亚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自诩为多元文化的国家,其两大政党除了在某些侧重点上有细微的差异外,都不约而同地支持这一政策,并以法律的形式沿袭至今。“2008至2009年间各国移民人口占澳大利亚人口增长数量的65%。”[5]大量移民的涌入促进了澳洲多元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多元文化的拓展也会促进移民的生存和发展。
一方面,鉴于多元文化对澳洲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华裔文化的发展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首先,中国正成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其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这无疑为华裔群体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回想华裔劳工登陆澳洲伊始,浪迹海外的游子们在筚路蓝缕的艰辛创业中,饱受异国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排斥,苦苦挣扎于种族歧视的迫害,直到1909年,中国政府在澳洲设立总领事馆,华裔群体的利益诉诸才逐渐有了保障。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各领域影响地位的提高,华裔群体更乐意抓住中国发展的机遇,促进自身的发展。其次,陆克文和现在的吉拉德工党政府保留了由霍华德政府于2006年更名的“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部”,从联邦政府层面肯定了多元文化政策的持续性。尤其是能说流利中文并精通中国文化的陆克文当选澳大利亚总理后,澳洲主流社会旋即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让唐人街、舞狮等中国文化元素再一次升温。最后,最新澳洲人口调查报告显示,在所有的各国移民中,华裔人口的数量和普通话的发展最为迅猛,且人口素质很具有竞争力。高素质的新一代移民摒弃了早期移民从事的矿业、餐饮、洗衣等体力的营生行业,开始在艺术、高科技领域甚至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其生活方式和人生的发展轨迹都在悄然地变化。
另一方面,华裔文化也面临危机和挑战。首先,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下,华裔文化难以保持其纯洁性,甚至出现与中华文化背道而驰的现象。如个别港台创立的报刊杂志为了扩大发行量而谋取利润,不惜刊登色情版面来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有些则是粗糙地翻译转载外文报刊内容,没有理性的客观评论视野,更谈不上是否能提高本地华人的中文水准。其次,囿于中国人浓厚的地缘和人缘关系,华裔团体力量的脆弱与不团结因素阻碍了文化的交流传播。在不同的城市,华商团体之间仍然我行我素,独行其是,抹杀了华裔的优势。最后,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华裔弱势文化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焦虑仍然客观存在。出生在澳洲的华裔后代不懂中文的比比皆是,连第一代华人领袖梅广达等人的后代也早已没有了中国人的特征。新老华裔移民的文化交替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创办华文学校,积极推进与中国大陆、港澳台、东南亚等国的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加强华裔群体的中文教育迫在眉睫。
综上所述,澳洲华裔移民一路艰辛坎坷,经历举步维艰的白澳政策时代,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调节并不断融合的进程中,迎来了多元文化下各国移民平等和睦共存的曙光,同时,抓住时代的契机为推进中澳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友好交流添砖加瓦。我们看到,在“地球村”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也是全世界必须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美国和加拿大等历史悠久的移民国家类似,澳洲华裔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无疑经历了“澳洲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有别于澳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异于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澳洲华裔文化。通过对澳洲华裔文化的民族渊源与历史记忆的刍议,笔者认为,只有认清华裔移民的民族立场和话语归宿问题,结合史料考据和缜密的逻辑推理来研究澳洲华裔文化,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E.M.Andrews.Australia and China: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M].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5.
[2] 郭存孝.中澳关系的真情岁月[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3] 沈永兴.列国志:澳大利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 陈达.一个“不可捉摸”的“网”——伊丽莎白·乔利作品“另类”主题初探[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 叶胜年.多元文化和殖民主义:澳洲移民小说面面观[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
[6] 戴维·卡特著,郭志军译.变化和挑战:多元文化与澳大利亚政体[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