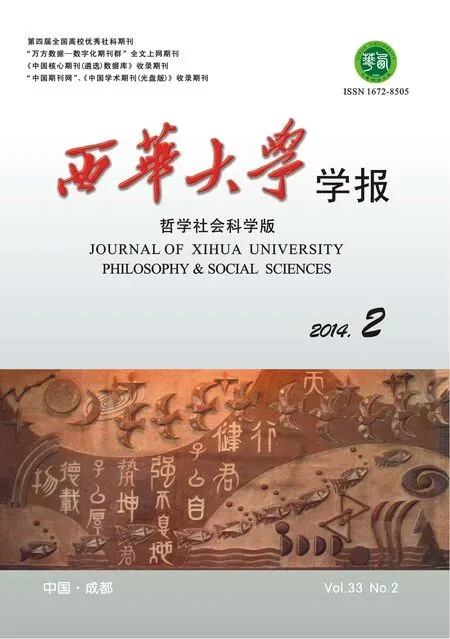库切与凯里写作视角比较研究
2014-03-03王敬慧
王敬慧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4)
一、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两位重要作家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两位流散作家:J.M.库切(J.M.Coetzee)和彼得·凯里(Peter Carey)。2003年,当在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很多人会将其归为南非作家,但实际上,他当时定居在澳大利亚(目前他是澳大利亚公民);关于凯里,人们会多将他归为澳大利亚作家范畴,但他目前定居在美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大潮下,众多作家在从中心向边缘流动的同时,也出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逆向流动。在这种双向的移民潮中,作家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界定变得越发模糊。同样,凯里与库切在身份认同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复杂性。研究分析两位作家的生平,我们会发现尽管他们目前都拥有澳大利亚国籍,但是他们的创作又不是完全澳大利亚化的,他们都有在其它欧美国家生活与工作的经历,特别是都有在美国大学教授创造性写作(Creative writing)的经历。在文学创作中,他们都受到卡夫卡、贝克特、乔伊斯、里尔克等作家与诗人的影响。在家乡与异乡之间,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能够频频获得多种文学奖项(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英语文学创作界最推崇的布克文学奖的颁奖史上,只有两位作家两度获奖,那就是库切与凯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在后殖民主义文化与欧美传统文化的冲突、交融中成长起来的。从某个角度说,他们都是在世界各地游荡寻根的流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但是,本文要将他们放入澳大利亚文学范畴里进行研究,主要有两个依据。第一,这两位作家目前都自认是澳大利亚公民,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第二,他们近阶段的大量重要文学创作都是以澳大利亚为背景的。研究澳大利亚当代文学,这两位作家是不能被回避的重要人物。
二、两位流散作家的新文化视角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由于经济的全球化,现代世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移民,更多作家或是被迫,或是自愿地走上了流散之路。在流散的过程中,他们的思维层面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态势,也可以称其为第三种文化。本文将第三种文化的包容性附加在流散作家的创作角度方面来分析。对于库切和凯里这两位流散作家来说,第三种文化首先来源于他们对母文化的再认识,这种认识与他们原来在母文化氛围所感受到的又不同,他们对母文化的理解已经到了更理性的程度。同时,在游走的过程中,作家们要在母文化和客文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很自然的会感到一种孤独,因为他们既不能成为客文化中的主流,也不能完全地接受与认同母文化的一切。库切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青春》中,有一个相当生动的描述:主人公从南非来到伦敦,“他身上仍然残留着一丝殖民地的傻气(南非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于是,他开始注意伦敦的时尚,那尖头的皮鞋、有许多钮扣的盒子形的紧身上衣、垂到前额和耳朵上的长发,使他开始为自己只有从开普敦带来的灰色法兰绒长裤和绿粗呢上衣感到窘迫,为自己那仍旧是童年时代乡镇理发师留下的有着整齐分缝的发型感到害羞。但当他为自己装备了一套同样的行头的时候,他却感到了一种未曾经验过的抵触情绪。他不能这样,这像是自己甘愿去做骗人的把戏,去做戏。”这种体验让主人公顿悟:原来自己并不是一个英国人。那么他们在身份和文化上的多重性和模糊性,使得他们在母文化与客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沟通和契合机制。此种机制决定了这种新生成的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三、文本事实与虚构界限之消融
文学并非仅仅被动地传达信息,而是主动地在读者与历史、个人与社会之间发挥媒介作用,形成人们对自我、对过去、对集体的感知,影响未来社会的记忆内容。两位作家是有国籍的,但他们的文本创作又是超越国界的。他们在流散的过程中对世界进行思考与比较,并诉诸于文本。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的视角具有一个共同内质——超然他者化的视角。库切的《福》与凯里的《我的生活犹如冒牌货》可以典型地体现两位作者的超然他者化创作策略。这是两部比较有难度的作品,而其难度对读者而言是阅读难度,对作者而言是创作难度。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是作者挑战常态的勇气,以及用超验他者的视角在对待小说与事实的关系问题的表现方式。他们的文本创作超越了那些已经范畴化、概念化了的时空关系或者时态所划定的界线。《福》这部作品的名字来自于《鲁宾逊飘流记》作者的名字——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这个人物名字本身表现了库切对历史的一个反讽。根据史料记载,笛福本姓Foe,他在40几岁的时候,为表示自己有贵族头衔,在自己的姓前加了一个贵族头衔——De,改姓为Defoe。库切在他的小说中,让笛福恢复本来的真实姓名——Foe。另外,从内容上讲,库切的《福》是对《鲁宾逊漂流记》这一经典作品的重写与反拨。鲁宾逊·克鲁索和野人“星期五”还是其中的人物,但是小说的讲述者不再相信与宣扬鲁宾逊·克鲁索,而是一位叫苏珊·巴顿的女士。小说主要是以苏珊·巴顿的角度来叙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克鲁索和不同的作者福。小说《我的生活犹如冒牌货》则以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厄恩·马利骗局——为背景。该事件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因为它导致了《愤怒的企鹅》最终停刊,对现代主义文学在澳大利亚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小说的叙述者也是一位女性,她是《现代书评》杂志的女编辑萨拉·沃德-道格拉斯。她要重新追踪这一事件,试图找出事件的真相,尽管真相是不存在的。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萨拉在倾听克里斯托弗讲述他的生活经历。克里斯托弗声称,诗人鲍勃·麦克其实是他编造出来的人物,但是他却突然复活了。鲍勃·麦克不仅败坏了他的名声,还抢走了他领养的女儿。他花了近20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寻找鲍勃和女儿的下落,历经艰难险阻……。萨拉将信将疑地听完故事,陷入了困惑的泥潭,分不清这故事到底是事实还是虚构。当然,陷入困惑之中的不仅是叙述者萨拉,还有读者,因为他们同样也无力分辨作品中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凯里在他的600页长篇小说《撒谎者》中,开篇就涉及到了事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该小说的叙述者声称自己139岁了,然后他又说自己是一个大骗子。但是该小说最具震撼力的是这句话:“我的年龄这个事实,你是要相信的,不是因为我自己这么说了,而是官方记录就是这样的。”[1]
超然他者化视角主要体现在两位作家在处理事实与虚构关系的态度上。在他们的作品中,事实是不存在的,作者的权威性是完全可以质疑的。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库切讲述了他儿时对《鲁宾逊漂流记》着迷的一个轶事。儿时的他相信小说中所记述的一切都是鲁宾逊·克鲁索真实的经历,也相信历史上真有鲁宾逊·克鲁索这样的人物。但是,在后来阅读其它书籍时,他发现原来鲁宾逊·克鲁索的一切是由一个叫笛福的人编撰的。库切的这段表述说明,他从童年就开始注意到历史的殖民性,语言的殖民性,更具体地说——作者创作的殖民性。这种质疑引发他后来致力于反拨历史与经典。和凯里一样,他们喜欢在作品里解构作者的特权。他们会在一部小说里,将一个故事从不同角度讲述很多遍,他们要通过作品告诉读者,“‘小说的本质与创作过程’这个问题也可以被称作‘谁在写’的问题。”[2]
库切的《福》与凯里的《我的生活犹如冒牌货》完全抛弃了作者的权威性,给我们展现了由无数作者创作的或者又可以说是无作者情况下创作的小说。正如库切在他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曾经引用他的研究对象——贝克特的一句名言:“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某人说,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3]在无数作者的情况下,具体事件的文本阐述有了更多的可能。他们这种超然他者化的叙述模式打破了事实与历史一对一的逻辑关系,历史的权威性与作者的权威性通过反拨经典的方式加以打破。对于作家来说,小说是真实事件与艺术的结合,所以库切在《福》中所做的事:还原作者的本来面目,展现他另一面的生活,描写他原来忽略掉的内容,进而让读者从中看出作者是不可靠的,而历史的记述则是不全面的。而在《我的生活犹如冒牌货》中,凯里更是对他童年时代身边发生的一个文学事件,一个众人皆知的骗局入手,大胆地假设:真有那么一个诗人,他所创造的人物犹如弗兰肯斯坦所创造的人造怪物一样真的复活了,那又会怎样?在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主张自己的叙述是真实可靠的,但是将他们的叙述放置到一起又有如此多的矛盾之处,而小说到最后,真相也没有出现。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就在于他们要展现的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要展示真相得不到的那种困顿。对于这两位作家而言,所谓的真相是没有的。要真相,只有一样是真实的,那就是书写本身。
四、超然他者化视角再思考
生成于高包容性的第三种文化——超然他者化的视角,让这两位作家质疑作者的权威性,质疑真相的绝对性,但是不等于他们不注重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喜欢从史实中寻找写作素材。《福》是以现实生活中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作家福为创作起点。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以及《凯利帮真史》是为人所知的以澳大利亚真实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根基所创作的作品。另外,两位作者的超验他者化视角还可以体现在作者尽力给边缘者发声的机会。在《福》和《我的生活犹如冒牌货》这两部作品中,叙述者都是女性,一位是苏珊·巴顿的女士,另一位是女编辑萨拉·沃德-道格拉斯。从文学创作来看,作为男作家,库切与凯里能从女性视角来叙述各自的小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从《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福的权力就在于他全权决定话语内容与表现形式。文字是历史的载体,历史是真实的,但是文字是抽象的,因为文字本身只是个符号。符号的不同组合表达着不同含义,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背景,可以进行不同的符号组合,而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又有不同的阐释,整个过程受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所制约,这就决定了文字与历史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按照米歇尔·福柯的观点,历史是掌握着权力和话语者的表述。他认为,“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他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它的系谱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4]。而这两部作品以女性作为个体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种他者化的历史角度去反拨那个已经成为一种常规意识形态的宏大历史。在对大历史的反拨方面,这两本书做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文本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同时开辟和展现出一条解构文本的路径。
[1] Peter Carey.Illywacker[M].New York:Vintage,1996:1.
[2] Tony Morphet.Interview with J.M.Coetzee[J].Tri-Quarterly 69(Spring-Summer),1987:462.
[3] Michel Foucault.What is an Author?[M]//Donald F.Bouchard.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by Michel Foucault,Ithaca,NY:Cornell UP,1977:116.
[4]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