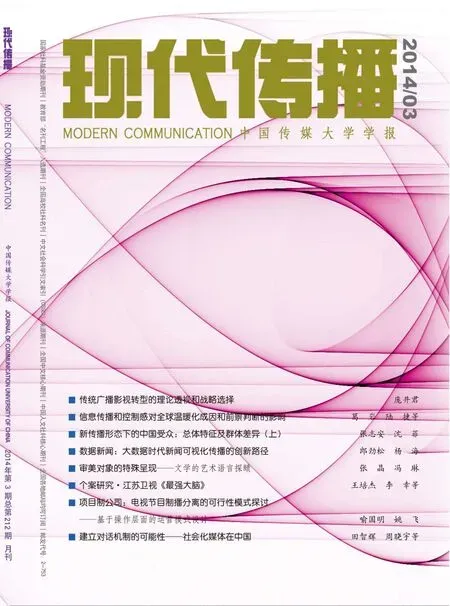《最强大脑》带给我们的思考
2014-03-03时统宇
■ 时统宇
《最强大脑》带给我们的思考
■ 时统宇
江苏卫视今年推出的《最强大脑》,让人们看到了电视也可以用具有强烈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节目去赢得高收视率的,甚至,科学对抗综艺不见得大败而归。而在高收视和高关注背后的涉及中国电视一些更深层次问题,更是这档节目的价值所在。
一、多学科的科学隐喻
《最强大脑》的“大脑”有通俗的特异功能和普通人的认知,但看这档节目时只要稍微动点脑子,只要稍微有点联想,所谓多学科的科学隐喻构成了《最强大脑》的非收视率价值与意义。
比如能够背出若干书价的实体小书店的年轻创业者。大家注意:这些书决非机场、车站的励志、经营、投资、八卦类的所谓畅销书,而是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是学术价值、文化含量、人文底蕴十足的小众类图书。所以,人们很难在电视上看到这些书的庐山真面目,即使是读书类的电视节目对这些书也是出于收视率的考虑而惟恐避之不及。而它们能够出现在高收视率的节目中,并且侧面地表现出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和艰难,以及坚守者的不离不弃,这就够了,这就是我们呼唤的电视的文化情怀和关怀。人们用如数家珍来形容主人对器物的熟悉和感情,书店的小老板能够背出其中的“珍”,这一刻,我们能仅仅把他看成是一个不那么得意的商人吗?
比如能够在众多双胞胎中快速识别的中学生。大家注意:“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有忘掉你容颜”,这是说爱情。而不少人(我在其中)就是多看了好几眼,甚至有语言的简短交流,也记不住你容颜,更别说似曾相识就是叫不出名字的尴尬。于是,真正的过目不忘是不是还有人类学、遗传学、社会学的含义?过目不忘在职场和人际交流中的价值几何?显然,这一刻,我们在惊叹中收获了思考。
比如“中国雨人”周玮。这个人物的出现和表现,引来了一些人的争论甚至争吵,其传播学价值早就超越了节目本身,甚至,这些争论和争吵比节目本身更让人关注。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说法比事实更具传播力,比如“我爸是李刚”“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一般群众不要给我打电话”等等。顺便说一句:自闭症和脑残人士在电视上最出彩的是当年的指挥家周舟,现在又出了个“中国雨人”,这“二周”可遇而不可求,实在难得。
二、电视知识分子的正能量
特别值得称道的还有《最强大脑》的主持人和科学家。同样作为电视知识分子出场,这两位分别来自中国著名大学的教授显示了与以往“学术明星”的不同之处。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表现出为科学、为节目的淡定,而不是为名气、为形象的焦虑和张扬。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提“电视知识分子”的话题。
我们知道,“远离电视”是西方电视批评理论最通俗、最大众化的关键词。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拒绝媒介,特别是拒绝上电视,他们似乎也恪守着中国学人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信条。
不过,布尔迪厄却堪称是一位“用电视的手段批评电视”的大师,他明确提出:“抱有偏见,断然拒绝在电视上讲话在我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我甚至认为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有上电视讲话的‘责任'。”①于是,为布尔迪厄带来巨大声誉的《关于电视》一书便应运而生,这本字数不过7万字的小册子是根据他的两次电视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的。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开宗明义地断言:“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电视对政治生活和民主同样有着不小的危险。”②由这一基本判断出发,他有力地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为此书的中文版作了译序的周宪认为,由此便构成了《关于电视》的两个基本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分析论证了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第二个主题,涉及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或者换一种表述,涉及到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僭越。”③
周宪认为:“布尔迪厄却提供了另一种策略: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与阿多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评媒介的方法相比,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破坏性,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人所忽略的那一面。难怪《关于电视》一面世,便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持续论争数月之久。”④
当然,正像电视具有两面性一样,对布尔迪厄的解读也是多元的。徐友渔就提出:“值得指出的是,布尔迪厄的书本身也表现为一个悖论。他应法国电视台之邀作了两次讲座,他的书就是根据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正是因为电视的影响力,《关于电视》一书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使得该书长期名列最佳畅销书排行榜之首。也许有人要问,布尔迪厄是在对电视作批判,还是与电视共谋?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电视的两种两面性,它既提供了信息,又可能遮蔽思想;它既体现了话语霸权,又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机会──如果没有电视,我们怎么知道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批判呢?当然,布尔迪厄对两个方面都有遭遇和体会,看来,电视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与它是处在垄断和竞争状态下很有关系。”⑤
这里,“布尔迪厄是在对电视作批判,还是与电视共谋”的问题提得十分有趣。我们认为,知识分子的拒绝电视应该是指拒绝电视的商业化和庸俗化,拒绝自己可能会因在电视上露面而成为这种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傀儡或帮凶。但是,知识分子,包括可以称作大家的知识分子不应拒绝将电视作为一个平台,一个鼓吹启蒙、启迪民智的平台。事实上,国外一些学术大家像布尔迪厄一样,并没有把媒体视为学术的对立物,而是将媒体作为学术表达的一个话语系统,并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比如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瑞思⑥系列演讲,像汤因比、萨义德等人,就曾在这个平台上作过著名的演讲。特别是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一书,就是他在1993年的瑞思系列演讲,其中那种知识分子的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跃然纸上。
知识分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是自由漂流、独立存在、保持一份清醒,还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这种追问永远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那些在商业化、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充斥日常生活,人们的心理普遍浮躁的今天,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学术操守的学者,哪怕他们终身没有媒体的光顾,他们仍然也应当获得社会的推崇和尊重。而另一方面,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力度的关键之一,恰恰在于应该给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在电视上出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电视传播这一影响最大的公共空间,将学术话语变为电视话语。这无论对知识分子的学术话语的完善和普及,还是对于电视的档次不断提升,都是不无裨益的。
三、中国电视制度安排的深水区探索
《最强大脑》的成功让我们对整个中国电视的现状产生了某些思考。
首先是卫视的核心竞争力。经过这些年卫视间的拼杀,逐渐形成了以一档节目为核心的卫视特征,比如江苏台的《非诚勿扰》、北京台的《养生堂》、天津台的《非你莫属》、江西台的《金牌调解》等等。并且,这些栏目承担了较大的广告份额,甚至,这些栏目作为一家卫视的招牌地位不可撼动。以江苏台为例,《非诚勿扰》后推出的几档节目基本上都是不温不火。而《最强大脑》具有与《非诚勿扰》相匹敌的影响和实力,“不吃老本,要立新功”,多少年前的这句老话,今天看来还是不断创新的大问题。
其次是“限娱”能否引入激励机制。我们知道,这些年对中国电视影响最大的是“限娱令”,而这样做的出发点是要解决中国电视的过度娱乐化问题。“限娱令”倒逼出一批好节目,比如公认的《爸爸去哪儿》和《最强大脑》。能否让这样的节目重回电视的黄金时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如此奖励对中国电视的引领一定是正向和健康的。毕竟,“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最后是节目制作的主体。这些年民营影视公司的风生水起让人刮目相看,而电视台嫡系的节目队伍却常常被边缘化。《最强大脑》的团队是江苏台《非诚勿扰》的班底,这是节目火爆背后十分令人欣慰之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一支充满活力和自信的嫡系队伍,是电视台的根本。
注释:
①②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2页。
③④ 见《关于电视》译序,第7、9;3、4页。
⑤ 《南方周末》2001年11月1日,第18版。
⑥ 瑞思于1922年任英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自1927年至1938年担任董事长,对英国广播业发展贡献良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