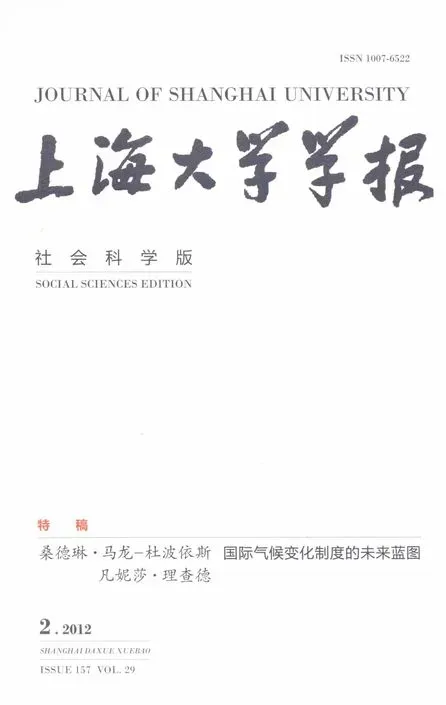实践与实践性理解: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主题与品格
2012-04-13罗朝明
罗朝明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南京 210093)
提及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人们一般会说是一种实践理论,大多数教科书都会对之冠以如是名号,而且,布尔迪厄也曾将其提出的理论知识类型之一的人类行为学知识,最终定名为关于实践的科学。[1]但是,当问及实践理论何谓时,人们谈论的却主要是惯习、场域、资本等等。毋容置疑,这是一种吊诡的现象。
之所以会出现如是状况,一方面,是思想的传播与接受所经常遭遇的困境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布尔迪厄思想发展过程本身的原因。对于前者,主要受到一种“拿来主义”或“实用主义”思想的毒害。华康德也曾认为,布尔迪厄思想在从欧洲大陆向英语世界扩散的过程中,遭遇到了零敲碎打的运用和断章取义的理解。[2]至于后者,则需要回到布尔迪厄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进行探究。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尤其是致力于阐述在布尔迪厄的思想中,实践扮演何种角色,所指谓何,如何理解实践等的研究则更少。
关于实践的上述问题,正是写作本文的初衷。首先,我们将以布尔迪厄主要著作的出版次序为线索,考察实践在布尔迪厄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着眼于实践概念本身,深描在布尔迪厄的意义上实践所指谓何。最后,探讨布尔迪厄如何理解其所谓的实践。
一、定位实践:文本脉络的探究
布尔迪厄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51—1968年的第一阶段,布尔迪厄主要是接受哲学训练,并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进入社会学领域;1968—1981年的第二阶段,是布尔迪厄确立其社会学地位和学术风格的时期;而1981年以后的第三阶段,布尔迪厄着力于展露隐藏在其科学话语中的政治关怀。[3]2-5在布尔迪厄不同阶段的著述中,我们主要关注其确立社会学秉性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即《实践理论大纲》(1972/1977)、《区隔》(1979/1984)和《实践感》(1980/1990),藉以分析实践的角色。
留心布尔迪厄核心理论概念之演化进程的学者,很轻易地就能发现其主要理论思想和概念工具,基本上就是在这三部作品中不断阐发和提炼的。在《实践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布尔迪厄明确提出并系统化了早在专门论述摄影实践的《一种中产阶级艺术》的导言中,已经提出但未曾加以发挥的实践理论。[4]148实践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实践性地把握社会实践,换言之,就是要摆脱主客观主义“以逻辑的事物代替事物的逻辑”的经院性做法。在布尔迪厄看来,主观主义的知识“想要明确地揭示社会世界之基本经验的真相”,但是,“却不对其本身进行反思,而且排除了其自身之所以可能的条件问题”;与之相反,客观主义的知识则通过预先假定与“信念经验”①关于“信念经验”,布尔迪厄有这样的论述:“内在结构与客观结构的契合,提供了直观理解的幻象,所熟悉之世界的实践性经验的特征,同时,它排斥关于那种经验自身之可能性条件的任何探索。”(P.Bourdieu,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Cambridge,Polity,第20页)。(doxic experience)的决裂,而排除了“使那种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问题”,最终使客观主义建立起了“社会世界的结构和基本经验的客观真理”。[5]3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知识,都不能把握社会实践本身,它们只是或者以局外人的立场旁观实践,或者唯意志论式地描绘实践。为了摆脱陷入主客观主义的困境,需要“将科学实践的所有操作归属于一种关于实践与实践性知识的理论之中”。[5]3
然而,尽管布尔迪厄致力于倡导一种有关实践与实践性知识的理论,并且在《大纲》中给予实践相当的重视,但是,对实践的这种关注也是通过批判主客观主义经院思维而体现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大纲》中布尔迪厄以概念工具的方式运用实践的笔墨不多,而且,在其他场合中(例如与山本哲思“关于实践、时间和历史的谈话”),当被直接问及实践的相关问题时,布尔迪厄也更多地转而谈论惯习的问题。惯习,作为结构化了的结构,是一种能够促结构化的结构,而且认知并组织着实践活动。[6]170如此看来,在布尔迪厄那里,实践是惯习运作的客观结果,是以本体论形式存在的实体,并且具有重塑惯习的功能。此外,在《大纲》中,布尔迪厄还通过批判主客观主义知识在认识实践时的“解释力贫困”,进而倡导了一种实践性理解实践的实践理论。如此说来,对布尔迪厄而言,实践不仅仅只是作为认识对象的本体论存在,还是一种在认识论上所追求的理论品格。
《区隔》和《实践感》是布尔迪厄淬炼其理论工具和形塑其理论秉性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两者的成书时间相差不远。在《区隔》中,尽管布尔迪厄提出了这样的公式:[(惯习)(资本)]+ 场域 = 实践,[6]101但是,理论性地讨论实践的章节并不多。尽管第二部分以“实践的经济学”作为标题,然而,即便对实践有较广泛讨论的第三章,布尔迪厄主要关注的似乎还是惯习的特性,即讨论了在许多不同的实践领域中,在生成了意义丰富的实践和认知的性情倾向与行动图式中,不同行动者或行动者阶层的惯习与品位是如何得以生成的。这些,无疑是上文所提及现象的回响,也就是在被问到实践时,布尔迪厄更多地转向了惯习的讨论。大体而言,《区隔》中的实践,在三种意义上被运用:首先,正如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实践”所经常被运用的那样,是相对于“理论”而言的;其次,这个术语被用于确认一些围绕着一种诸如高尔夫、服饰穿着等活动而形成的、或多或少连贯的实体。最后,布尔迪厄使用的实践只是意味着一种表演或表现(performance),是指一些行动或其他东西的开展。[7]6在上述用法中,我们再次发现了作为一种本体论存在的实践,而且,这种实践不是一种静止性的实体,而是能动性的活动,即一种有所指向的表演或执行。值得注意的是,在《区隔》中,除了实践和惯习概念仍然被频繁地提及之外,场域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也逐渐呈现出来。而且,在布尔迪厄看来,任何不同的实践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场域,相应的,场域也可以被建构在任何不同的实践之上,[6]209-211而在《大纲》中,布尔迪厄从未提及场域的概念。
《实践感》(英译《实践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实践理论的再确认与再阐释。《实践感》的第一卷是对“理论理性”的批判,其批判矛头和《大纲》一脉相承,主要指向的仍是主客观主义经院理论在认识实践上的“无能”;第二卷主要是运用“实践理论”对柏柏尔人和贝亚恩人的社会实践进行实践性的理解。人们在布尔迪厄的分析中,至少可以找到六种意义上的实践概念:(1)实践的观点与理论的和冥思的观点不同,这既体现在实践感的概念上,也体现在关于实践的逻辑而非逻辑学家之逻辑的思想中;(2)实践的与话语的相反,它是实践的行动而不是意义的创造与循环;(3)实践的和不切实际的相反,它指陈行动者在其所参与的活动中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践性精通;(4)实践牵涉到一种领域或系统;(5)实践可能涉及到任何的行为、执行或发生,不管是策略性的还是惯习性的;(6)实践是从惯习中产生出来的。[7]30从布尔迪厄的理论诉求和以上六种意义的实践,我们除了获悉实践的一些特性外,还再次确证了前两本著作中关于实践的认识。也就是说,在布尔迪厄对实践理论进行重申的《实践感》中,实践的角色几乎不是概念性的分析工具,而是被体现在这样两种层面之上:其一,实践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体认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指涉的是与“理论理性”相决裂,而代之以“实践理性”来理解实践;其二,实践体现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指陈的是行动者的社会存在形式。需要指出的是,在布尔迪厄看来,这种本体论意义的社会存在形式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更多地呈现为“关系性”的存在。也就是说,“日常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关系上更为成功……关于对象的话语所表达的不是对象,而是与对象的关系”。[8]231另外,就布尔迪厄对概念工具的提炼而言,在《大纲》中处于不被提及的边缘地位,而在《区隔》中崭露头角的场域概念,在《实践感》中已经上升到了理论分析的核心位置,再往后几乎成了一个统领性的概念,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就是:“场域才是首要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3]13
在布尔迪厄的主要著述中,实践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类似于惯习、场域、资本这样的操作性概念工具,而更主要地体现为:(1)实践具有本体论意涵,涉及行动者的社会存在,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诸如贝亚恩人的土地和婚姻实践;柏柏尔人的农事活动和仪式实践;不同的行动者或行动者阶层的生活方式实践等等。在实践中,布尔迪厄主要关注的是,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的“结构—行动”问题,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我的所有思考起始于这样一点:在不致沦为遵从规则之产物的情形下,行为是如何被规约的”。[9]65布尔迪厄对惯习概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且,在布氏的实践理论中,行动者嵌入在复杂的、与他人持续议定的关系网络之中;个体不是处于主导其行动的客观结构之外,而是处在其所熟练掌控的关系网络之中的。[10](2)实践性要求一种认识论反思,但这种反思是为了本真地呈现实践活动,而不是对实践的丰富性有所遗失。这是布尔迪厄所追求的一种理论品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分析路径。作为一种认识论反思或理论品格,布尔迪厄意指的是,社会学要超越客观主义的社会物理学和主观主义的社会现象学之间的二元抉择,进而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之外,建构一种能够把握住客观上依附于其身体资本与象征资本的“内在双重实在性”的社会学理论。[8]216-217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理论分析路径,布尔迪厄指陈的是如何反思性与实践性地理解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既指向行动者的日常社会实践活动,也指向社会科学家的科学实践活动。
二、实践何谓:本体论的深描
通过对三本代表著作的考察,我们明确了实践在布尔迪厄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作为本体论意义、认识论反思或理论品格的实践或实践性,在布尔迪厄看来是何具体面貌,还是尚未澄清的问题。
就对实践的本体论考察而言,布尔迪厄的工作并不是先驱之作。可以说,在各种差异甚微的名目之下(如社会互动、日常生活、社会行为等等),实践概念一直都是社会学经验性食谱中的一种主食。布尔迪厄的重要性在于,他试图构建一种社会实践的理论,这种理论比人们日常生活中认为理所当然的做得更多,但又要做得不致失去社会生活的丰富面貌。[11]41既然布尔迪厄对实践的研究并不是首创,那么,他站在了哪些巨人的肩膀之上呢?
毋庸置疑,布尔迪厄从马克思那里继承并再阐释了许多特定的主题,文化实践对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和永久化便是其中之一。[12]而且,从布尔迪厄在其主要著述中对马克思的援引情况也可以反映其所受影响之深:布尔迪厄在《大纲》中提到和引用马克思的有14处,《实践感》中有19次,而在《实践与反思》中也有8处之多。[13]但需要明确的是,尽管马克思对实践也持有本体论意义上的认知,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4]5然而,布尔迪厄的主要关注和马克思不同,他不是关注那些自主实体和由个体社会活动凝结成的统一产物,而是关心“实践的操作者”(practical operators),它通过自己的实践复制和变革着每代人所遭遇的社会结构,[15]即上文谈及的“结构—行动”问题。除了马克思的实践研究之外,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定义和行动规则等的实践性理解,无疑也是布尔迪厄对实践的本体论认识的思想基础所在。[16]300
基于前人的实践研究,布尔迪厄本人对于实践的本体论认识又有哪些独具的特色呢?在布尔迪厄的图式中,“实践是在一种特定的实践领域或场域之中进行的各种活动或游戏的丛结”。[16]287如此看来,如果场域是实践得以展开的空间背景,那么,实践则是不同形式的活动,是不同场域空间中的本体性内容。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至少具有三个特征:时空性、无意识性和目的性。[11]42-43
首先,实践具有时空性,即实践处在空间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在时间之中展开。时间性,时间的无情流逝,是实践的一种原则性特征:时间既是社会活动的一种限制,也是社会互动的一种资源。更有甚者,实践“从本质上讲被其节奏速度所限定”。[5]8时间以及时间的意义,当然是社会性建构的;但是,它是从自然周期之中被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白天与黑夜、四季、人类的繁衍、成长与衰老。同样的,而且更为立竿见影的是,社会实践活动需要花费时间,而且,它们发生在空间之中,换言之,实践在空间之中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具有空间的隐喻,而在从《大纲》到《实践感》的概念提炼过程,即一种从理论建构到经验分析的过程中,场域的分析工具作用逐渐凸显,而且大有取代实践概念的势头,这种变化似乎蕴含着布尔迪厄的某种思考,即作为经验分析的概念工具,场域似乎比实践更为顺手,这也可以从布尔迪厄对各种具体场域的分析中得到佐证,在那些讨论中,实践似乎作为场域的内容而存在。总而言之,时间和空间都能被不同的方式形塑,因此都是社会性的构造,但是,空间中的行动总是牵涉到时间中的行动。实践作为一种有形迹的、客观的社会现象,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得到理解。由此,关于实践的任何恰当分析,都必须将时空性(历史性)作为实践之本质的核心特征。
其次,实践具有无意识性,即实践不是有意识地,至少不是完全有意识地被执行或开展的。实践的无意识性,显著地呈现在布尔迪厄实践感或实践逻辑的概念上。实践逻辑只能在行动中,亦即在时间运动中被领悟,但时间运动致使实践逻辑被分解从而将其掩盖起来,所以,实践的逻辑缺乏逻辑学的逻辑所具有的严密性和恒定性。实践的逻辑不是一种逻辑学的逻辑,而是一种自在逻辑,它既没有意识性的反思,也没有逻辑的控制。实践逻辑概念是一种逻辑项矛盾,它无视逻辑的逻辑。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是任何实践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任何实践感的逻辑。[8]143实践感以及实践的无意识性恰切地体现在游戏感的隐喻之中,即“实践性地掌握一种游戏的迫切必然性或者逻辑——通过游戏的经验,以及一种运作于意识的控制与话语之外的经验(例如,身体技术的应用所采藉的方式)而获得的一种熟练掌控”。[9]61这种实践的逻辑具有两个层面的意涵:其中之一是“生活世界中必需品的迫切性”。[17]这种必需品的迫切性可以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解释,即尽管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中创造历史。这说明在社会世界的环境结构中,实践受到客观结构的制约,并蕴涵着实践或实践感的紧迫性。必需品的迫切性也是这种事实的说明,即行动者不仅仅只是遭遇他们的当前环境,他们也是那些环境所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行动者在其中实践并获得了一套实践性的文化技能,这也是行动者的能动性所在。这些文化技能使得行动者将他们自身和社会世界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是说,行动者不会有意识地考虑实践,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考虑。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自然态度正是社会生活得以实现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担负不起质疑生活之意义所需花费的时间,而且社会的紧迫性也不允许我们如是为之,但是,紧迫性的存在又潜藏着使实践成为客观认识对象的可能性。另一个层面,是实践逻辑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必要的即兴之作的技能”就是对其很好的说明。[5]8社会生活由于其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不可能在规则、脚本和标准模型的基础之上得以实现的。在这里,布尔迪厄暗示的是,将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应对可能遭遇到的每种情境的规则或处方都“归档”的不可能性,[5]29,73这种不可能性与实践的事实性存在之间的吊诡,说明了行动者具有应对实践的自在逻辑,否则,实践的持续存在是难以想像的。但是,这种自在逻辑显然不是明确的行动规划,因为正如上文提到的,行动者担负不起为其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种行动都制定明晰的计划所花费的时间。把实践作为一种即兴表演的描述,将我们带回到了时间性:即兴表演是对停顿、间隙和迟疑的利用,这种策略性的利用是行动者具备能动性的又一确凿证据。而且,也就是这种毫无准备的即兴之作,充分地说明了实践是非理性计算的、无计划的、无意识性的,还充分地体现了充斥在实践之中的紧迫性。
最后,实践具有目的性。换言之,实践是有目标的、行动者有其所追逐的利益或赌注。在布尔迪厄对社会世界的理解中,尽管绝大部分实践的实现不是有意识的,但是,实践并不是没有其目的的。实践的目的性,指涉的是实践的指向和实践的意义问题,而实践的无意识性,强调的是实践的运作过程并无理性的计算。实践的目的性,很好地呈现在贝亚恩人的“土地与婚姻策略”和卡比利亚人“亲属关系之社会用途”。仅就贝亚恩人的婚姻策略而言,“继承人首先避免娶一个经济状况比自己好的女人……首先是因为收到的陪嫁财产的数额对地产构成一种威胁,也是因为家庭关系的平衡受到威胁……婚姻交换的逻辑表现为经济的要求和外在于经济的要求,即源于价值体系给予男性的优先要求之间的交织。经济的差距决定了实际的不可能性,文化的要求则决定了权利的不相容性”。[18]由此看来,贝亚恩人的婚姻实践是具有一些具体目的取向的(例如维持地产完整、平衡家庭关系等),而这些目的又是通过策略的运用而得以实现的,这种策略的运用既是行动者能动性的体现,更是实践之目的性的呈现。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上述“‘优先’婚姻不应再被认为是遵守规范或符合一个无意识模型的产物,而是一种再生产策略,其含义来自一个由习性生成的、趋于实现相同社会功能的策略系统”,“结婚仪式不只是被理解为一组象征行为……而且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策略,其定义取决于它在一个旨在获取最大物质和象征利益的策略系统中的位置”。[8]24值得一提的是,布尔迪厄对实践之目的性中策略性的强调,针对的是结构主义以规则作为解释社会实践或行动之蓝本的经院性做法。结构主义“通过创造一种文化地图来弥补实践性掌握的不足”,[5]2然后把这套静止的、永恒的地图作为一种客观规则体系存在的证据,并将之无情地强加在社会互动和实践之上。策略概念正是针对这种做法而提出的,它将行动者实践的来源安顿在了他们关于社会现实的经验、他们的实践感或实践逻辑之中,而不是在社会科学家建构出来解释实践的分析模型之中。也就是布尔迪厄在“从规则到策略”中所说的,“这是一个不应该将社会行动者的实践置于一种理论之中的问题,因为那种理论是人们为解释实践而不得不建构出来的”。[19]
以上论述指认了在布尔迪厄的思想中,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所具备的规定性。然而,实践的角色并不止于此,实践还具有认识论反思与方法论上的意涵。但是,这些意义的实践,似乎都可以归结于这种面相,即对本体性实践的实践性理解。那么,这种层面上的实践或者实践性,在布尔迪厄的视野中又是何种具体面貌呢?这涉及到布尔迪厄所谓的“如何才能既不夸张又无须以事后重建的方式谈及自己长期从事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又逐步改变了对行为和社会世界的全部看法,从而有可能‘观察’到用以前的看法完全看不出来的全新的事实?”[8]24的问题。
三、实践性理解:认识论的进路
通过对实践所扮演之角色的梳理及其本体论意涵之特征的深描,我们发现,如何理解实践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从《大纲》到《实践感》中对涉及实践的相关问题,布尔迪厄主要借助于惯习、场域的工具性概念来阐释,而且,本体论实践的时空性、无意识性和目的性,又致使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本体论的契合关系,这些导致了无论是普通行动者还是社会科学家,都很少自发自觉地对实践进行反思性的观照,以使实践对象化为外在于主体的客体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实践为对其自身之理解所设置的上述障碍,催生了布尔迪厄所谓的完全看不出全新事实的“以前的看法”。以自发社会学、社会现象学和社会物理学为代表的这些“以前的看法”,在对实践的把握上,如果说具有相当的信度,那么,其效度则是值得商榷的。显然,布尔迪厄并不屈从于上述理论对实践的理解。那么,布尔迪厄所理解的对实践的理解又有哪些进路呢?
前文提及实践理论的前身,是人类行为学知识;而且,布尔迪厄对本体论实践的探究,旨在解决“结构—行动”的难题;此外,在布尔迪厄看来,实践也主要表现为不同的行动者所践行之各种行动或活动的丛结。由此可见,作为实践主体的行动者是任何实践的主角。那么,行动者及其行动自然是理解实践的节点所在。然而,在行动者的各种属性中,作为感知与体验世界之最先者的身体,应该就是实践性理解实践的关键所在。对布尔迪厄而言,身体的感官和智力,使之得以存在于自身之外的世界之中,经受着世界的影响与持续改变,并且从一开始便长久地遭受着世界之规则的形塑。身体的这些特质,不仅是世界可以被理解并天然具有意义的原因,也使沉浸在世界之中的身体获得了一种契合于世界之规律性的性情系统。这种性情系统倾向于并且能够借由一种身体的知识(corporeal knowledge)在行动之中实践性地预测世界的规律性。这种身体的知识,提供了一种迥异于有意识的意向性识别行为的对于世界的实践性理解方式。[20]135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身体知识是行动者于其中进行实践活动的世界结构的产物,也是行动者通过实践塑造世界结构的经验资源所在。
熟悉布尔迪厄思想的学者,也许已经意识到身体的知识与身体素性①在布尔迪厄看来,身体素性是具体化的、身体化的、成为恒定倾向的政治神话,是姿势、说话、行走,从而也是感觉和思维的习惯(布尔迪厄:《实践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07页)。(bodily hexis)之间的相似性,也觉察到了其与惯习之间的亲和性,这种认识是不无道理的。仅就惯习与身体知识之间的关系而言,有学者就认为,在欧洲思想中,惯习出现在黑格尔、胡塞尔、韦伯、迪尔凯姆和莫斯等人的著作之中,莫斯在1935年出版的《身体的技术》中将其引入了人类学,而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大纲》中只是对其进行了提炼和再介绍。[21]甚至有学者认为,布尔迪厄的惯习就是莫斯的著作中运作于不甚清晰的情境之下作为一种已然习得之技术的身体概念。[22]布尔迪厄也曾明言,“习性是稳定的一致、难以抑制的忠诚的处所,即身体精神②在布尔迪厄看来,身体精神是一个社会化身体对社会机构的发自内心的赞同,社会机构造就了社会化身体,社会化身体与社会机构结成一体(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刘晖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第170页)。(其中家庭精神是一个特殊状况)的一致和忠诚的处所”。[23]170如此一来,也就解释了前文所发现的,当被直接问及实践的相关问题时,布尔迪厄更多地以谈论惯习作为答复的原因所在了。
布尔迪厄认为,为了深入对实践性的理解,“应该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能够按照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③英文原文为Theses on Feuerbach,通常译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此处译者译为《费尔哈论》,恐有误。——编者注中表达的愿望,重新在唯心主义中汲取唯物主义传统曾经抛弃的实践认识的积极方面”。[23]159这种被唯物主义抛弃而被唯心主义发展了的积极方面,也许就是关于感性活动的认识与思想了,也就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14]3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唯心主义发展了旧唯物主义所忽视的能动的方面,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从唯心主义中汲取这种实践认识的积极方面呢?
追随马克思的愿望并致力于对实践性理解的理解,布尔迪厄援引黑格尔的观点,阐发了作为“个性化原则”与“集体化原则”的身体意象,即“由于具有向外界开放、暴露给世界并受到外界影响的(生物的)属性、身体受到其从开始便被置于其中的物质和文化存在条件的形塑,身体经受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个体化本身就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自我的独特性在社会关系之中并被社会关系所塑造”,[20]134同样地,“身体也能很好地应对世界之所是,适应这个世界以及呈现在世界之中可被直接看到、感到和预感到的事物,身体也可以通过对世界产生一种适当的反应而控制和掌握世界,把世界当作一种触手可及的工具来利用”。[20]142这种实践认识的能动的积极方面,很好地体现在作为结构化之结构与促结构化之结构的惯习概念之中,即惯习“将一种生成的、统一的、建构的和分类的权力归还给行动者,同时强调,这种建构社会现实的能力①在布尔迪厄那里,建构社会现实的能力就是行动者的身体实践能力,这种能力是社会结构的产物,而这种能力也是构造社会结构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是通过能动身体和主体实践活动应用于客体的,而且这种构造社会结构的过程是一种历史进程,不论对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对象与实践的结果而言,皆是如此。身也是社会建构的,它不是一个超验主体的能力,而是一个社会化的身体的能力,这个身体投入到其社会性地建构组织原则的实践中,这些原则是在一种地点和时间明确的社会经验过程中获得的”。[20]136-137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作为感知与建构世界之主体的能动的身体,不仅是践行实践活动的执行者,其属性特征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也是理解实践的关键所在。
除了通过身体或身体知识来认识与理解实践之外,基于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的身体及其属性而言,实践性理解实践的另外两种主要维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首先,是历史或历史感的维度。在布尔迪厄看来,行动的原则存在于两种社会状态之间的共谋中,即身体化的历史与物化的历史之间。更确切地说,是以社会空间或者场域结构的形式在事物中客观化的历史,和以惯习的形式在身体中具体化的历史之间的共谋。惯习,作为一种历史性获得物的产物,是能将历史遗产据为己有的东西,它同与生俱来的世界之间的信念关系是一种归属与占有的关系。在其中,被历史所占据的身体直接地占有居处在同一种历史之中的事物。[20]150-152场域,作为事物构成的历史,即被客观化的制度,是行动者践行实践活动的结构化空间和背景结构,也是身体化的历史成其自身与生产再生产物化历史的可能性空间所在。惯习与场域的这种共谋关系,或者说身体化历史与物化历史之间彼此占有与包含的关系,是行动原则的栖息之所,也是实践活动或历史创造活动之生产与再生产的原则所在。这种关系所蕴涵的可能性与制约性,可以用前文提及的马克思的话语来概括,即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之中创造历史,然而既定的环境却也是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所可资利用的资源。但是,关于这种关系的历史动态过程,布尔迪厄则有更详尽的阐述,即“实践活动在其合乎情理的情况下,是由直接适合场域内在倾向的习性产生的,是一种时间化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行动者通过对往昔的实际调动,对以客观潜在状态属于现时的未来的预测,而超越了当下”。[4]151实践,就是在这种源于过去、处在当下、指向未来的状态中,惯习与场域、身体化历史与物化历史之间彼此持续角力的历史过程。基于这样两种历史之间的相遇,及其通过行动者的实践而历史性地创造历史的事实,历史的维度将是实践性地理解实践所必需的一种重要视角。而且,这种维度体现出来的场域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之可能性与限制性空间结构的特性,也契合了从《大纲》到《实践感》中,场域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显著性不断凸显的变化过程,以及布尔迪厄在谈论实践时,所关切的“结构—行动”的核心主题。
其次,是符号暴力,亦即社会或象征炼金术的维度。在这种维度中,布尔迪厄向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充斥着区隔、分类、对立、统治、顺从、审查、幻象、利益、共谋等等的实践图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幅更为真切但却往往未被或难以被深切认识到的实践画面。对布尔迪厄来说,在作为实践运作空间的场域结构中,“最严肃的社会命令不是面对心智,而是面对身体的,身体被视为一种记号……制度的常规不过是所有明确行为的界限,群体竭力通过这些行为反复灌输社会限制,或同样地,灌输社会区分,并以身体上的区分形式如身体素性、性情倾向将这些限制或区分自然化。人们希望身体素性和性情倾向像去不掉的纹身印记,与共同的观念和区分原则一样地持久”。[23]165①此处译者“disposition”翻译为“配置”,这是不符合布尔迪厄的意图的,应该译为“性情倾向”。此外,笔者对此段译文的个别标点符号也作了调整。此外,借鉴帕斯卡尔的结论,布尔迪厄认为,由于(政治、国家或统治者等)无法(更多的是不愿)让人民了解关于社会秩序的解放真理,因为这种真理只会威胁或毁灭这种秩序,因而应该欺骗他们,向他们掩盖“篡夺的真理”,也就是法律植根于其中的创始暴力,让这种暴力看起来好像是真实而永恒的。[23]197问题的关键在于,行动者生而沉浸于其中的这些实践结构,具备着使行动者视上述的暴力为理所当然的各种手段。而且,这些手段无需是有意组织的宣传行动或者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刻意为之,社会结构刻写在行动者身体之惯习中,惯习具有服从与认可这些秩序的性情倾向。然而,这些建立在欺骗和粉饰基础之上的服从与认可,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经历了象征炼金术之后的“误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误识”为何得以存在,其存在样态怎样,如何才能对其进行“解蔽”?
布尔迪厄认为,性情倾向作为被纳入身体之中的一种统治关系的产物,是产生上述误识的媒介所在,也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神奇界限的实践认识和认可行为的真正根源所在,象征权力的魔法作用起着一种契机的作用,但却引发了实践认识和认可行为。[23]199被统治者往往不知不觉地,有时甚至是违心地通过实践认可促进了对其自身的统治,这种实践认可往往表现为身体感受,这种感受常常与一种向过去的关系即童年关系和家庭空间关系的回溯有关,也就是说行动者的社会轨迹及其家庭的社会空间位置,和他们对社会权力秩序的误识有密切关联。总而言之,行动者对社会实践结构的误识之所以存在,除了作为统治者的各种机制运作之外,象征暴力与象征权力的魔法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象征炼金术则是通过被统治者的赞同与合作,亦即共谋才得以建立起来的。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赞同、合作、共谋、服从是通过身体的模仿而再生产的,而不是涉及一种精神关联的意识行为,也不是人们通常置于“意识形态”概念之下的东西,而是产生于身体训练的惯习使之成为可能的一种默许的和实践的信仰。[23]202象征炼金术正是通过上述这样一种借助于身体的规训,使得践行实践的行动者将充斥着限制、区隔、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误识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真实而永恒的存在。这些秩序具备着各种各样的存在样式,诸如不同社会阶级之生活方式的区隔、男女两性的行为举止规范和社会角色期待、不同种族之间的区别及其不同社会机遇、学校等机构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应征者的遴选与排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这些秩序已然被行动者的默许和实践信仰认定为具备合法性的合理存在,所以他们往往对之采取一种不言而喻的自然态度,故而不会或很少自觉地对之采取反思性的立场,进而沦为了宰制其自身的统治秩序的帮凶和同谋。这些正是象征炼金术作为一种统治技艺的妙处所在,也是既存的统治秩序往往具有难以抗拒的稳定性的原因所在。解蔽误识进而揭示社会秩序的原本面目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集体性事业。然而,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但是并没有消除人类飞行的梦想!事实上,我们只有真正弄清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我们才能找到解放的可能”。[3]21对象征炼金术的解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弄清宰制我们但却往往不被我们察觉的束缚,还原实践的本真面貌,寻找到解放自身之可能性的有效路径之一。
四、总结: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意义
布尔迪厄对实践的本体论定位、实践之本体性特征的深描和实践之实践性理解的阐述,是源自作为其全部学说之出发点的哲学人类学假设的题中之义。布尔迪厄所秉持的哲学人类学假设使其以解蔽形形色色的社会“共谋”和“误识”为学术志业,然而,人们经验到的社会现实已经是遭受了社会炼金术的符号暴力所锻造之后的所谓“次级事实”。因此,还原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实践的本来面目就成了布尔迪厄完成其学术志业的必由之路,而实践理论就是布尔迪厄这种解蔽历程的必然结果。
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是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中的“实践转向”的组成部分。尽管当代思想的实践转向更多指涉的是由“理论”向“实践”转向的层面,但是,这种转向实践本身所侧重的正是对实践及其意义的发现与重视,是从观察者的立场转向实践者的立场,是对社会世界之生成性构造的合法性的承认。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所关切的正是还原实践所固有的本体论性质,倡导将“实践理性”替代“理论理性”作为对实践进行实践性的理解而非经院理性式理解的一种路径。由此可见,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正是当代理论思想的“实践转向”在社会学理论中的体现。此外,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还具有超越或克服主观主义知识与客观主义知识之间的二元对立的重要意义。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悉了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提出所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传统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在认识社会世界上的“解释力贫困”。正是在这种认识与批评中,布尔迪厄特别重视发掘实践理论对于实践性理解实践的功能。
总而言之,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一方面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即让行动者对现实社会结构进行反思,解蔽形形色色的共谋与误识,寻求拯救自身的解放之道;另一方面具有重要的学科理论发展史意义,即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既是当代理论思想的“实践转向”在社会学理论中的体现,也是社会学理论致力于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二元对立的重要代表。
[1]Pierre Bourdieu.The Three Form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J].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973,12(1):53-80.
[2]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康,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4.
[3]成伯清.布尔迪厄的用途[C]//皮埃尔·布尔迪厄,等.科学的社会用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2.
[4]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M].谭立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5]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6]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State[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7] Alan Warde.Practice and Field:Revising Bourdieusian Concepts[J].CRIC Discussion Paper,2004,(65):1-32.
[8]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9]Pierre Bourdieu.In Other Words: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0]Anthony King.Thinking with Bourdieu against Bourdieu:A 'Practical'Critique of the Habitus[J].Sociological Theory,2000,18(3):417-433.
[11]Richard Jenkins.Pierre Bourdieu[M].London:Routledge,1992.
[12]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5-47.
[13]宫留记.场域、惯习和资本:布迪厄与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不同视域[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7(3):76-80.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Richard Nice.Preface to the English Edition[C]//Bourdieu.The Craft of Sociology:Epistemology Preliminaries.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1:v-ix.
[16]Theodore R Schatzki.Practices and Actions:A Wittgensteinian Critique of Bourdieu and Giddens[J].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97,27(3):283-308.
[17]Loīc Wacquant.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J].Sociological Theory,1989,7(1):26-63.
[18]皮埃尔·布尔迪厄.单身者舞会[M].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0-21.
[19]Pierre Lamaison,Pierre Bourdieu.From Rules to Strategies: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Bourdieu[J].Cultural Anthropology,1986,1(1):110-120.
[20]Pierre Bourdieu.Pascalian Meditation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
[21]Farnell Brenda.Getting Out of the Habitus:An Alternative Model of Dynamically Embodied Social Action[J].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2000,6(3):397-418.
[22] Lash Scott.Structure,Agency and Practical Knowledge[J]. Contemporary Sociology,1992,21(2):155-156.
[23]皮埃尔·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M].刘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