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时代的评论策略
2014-02-20青锋
青锋
虚无时代的评论策略
青锋
从“学院式评论”的特征出发,本文讨论了大学教育中建筑评论的重要作用。而虚无主义对评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本文指出可以通过“目的性解释”的策略应对这种威胁,并且结合实际的案例讨论了该评论策略的意义与价值。
巴别塔,学院式评论,虚无主义,目的,英雄

1 阿塔纳休斯·科尔舍(Athanasius Kircher),巴别塔(Turris Bable),1679年(图片来源:Http://digi.ub.uni-heidelberg. de/diglit/kircher1679/006)
巴别塔
“大学的立足点与市场没有关系……这个职业属于市场,而建筑属于大学……职业当然会不断变化,但建筑不会变”[1]。我常常引用路易·康的这些话来为自己辩护,为何一个没有多少建成作品、主要关注历史与理论的教师仍然能够在大学教授建筑设计。原因在于大学所教授的不是随势而动的市场经验,而是关于建筑的不变的“本质”,只有理解了“本质”才能做出真正出色的建筑,并且能够坚定而从容地应对市场的挑战。当然,这一推论的前提是要承认,这种“本质”是存在的,而且能够通过大学的研究与教育去探讨、去传授。对于路易·康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人们常常提及“秩序”、“光与静谧”等康为人熟知的词汇,但在这位古典主义者的建筑思想中,“本质”(nature)才是最具决定性的,由此才有康与砖、与秩序、与豪猪等等的对话。他认为一切存在的“本质”可以从任何事物中得到揭示,因此他无需引用任何哲学家的理论,仅仅通过设想的对话就可以让“本质”呈现出来。
按照康的逻辑,大学所教授的应当是关于建筑的“哲学真理”(philosophical truth)[2]8,这或许是大学——研究所有知识的机构——与专门化的职业技能学校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否认同这种区别将会对教师,对建筑学院、乃至于整个大学体系的教育倾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已经不能被“理论结合实践”的模棱两可所掩盖,任何一个教育者都不得不进行抉择。显而易见,本文的所有讨论及其根据都是建立在认同这种区别的基础之上。虽然我们并不完全接受康过于强烈的古典浪漫主义立场,但是建筑可以,也需要更深层次“哲学真理”的探讨这一观点是我们所认同的。
不难想象,这种观点很容易被指责为“精英主义”或者是象牙塔中的自我陶醉。对于前者,另一位学院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回应道:“那些最投入的人,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早晚会被指责为精英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并不总是很清楚,而且常常被用来使无知变得可以被接受”[3]27。而对于后者,如果将象牙塔换做巴别塔(the Bable Tower)的话就可以欣然接受。巴别塔直达天界的企图不正象征着大学学者们试图抵达“最终真理”的梦想,而这一未完成的工程也正对应着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那就是“最终真理”可能无法企及。巴别塔建造者们的“自我陶醉”并非盲目的逃避,而是仍然对这个梦想抱有热忱。因此,即使面临重重阻碍,即使难以预见成功的曙光,即使需要一代代不断传承(如同中世纪大教堂的建造一般),巴别塔还需要继续建造(图1)。
评论的普遍性
以上的讨论看似与本文讨论的主题“建筑评论的工具与方法”无关,但实际上它解释了一种特定评论策略的立论基础。这里不妨称之为“学院式评论”,其主要特征自然是对“哲学真理”的特殊诉求。“学院式评论”的概念之所以需要特别提及,是因为“学院”与“评论”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比表面看起来要深远很多。可以说,从一开始,人们对“哲学真理”的探索就是建立在“评论”这一有力工具之上的。
在西方学术传统的起源之一,亚里斯多德的论述中,评论就是展开分析最常见的起点。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亚里斯多德往往要列举其他人就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且加以分析评论,指出其优点与不足,使之成为辩护自己观点的证据。例如,在《物理学》(Physics)一篇中他就评论了巴门尼德(Parmenides)、麦里梭(Melissus),安提丰(Antiphon)、 吕哥弗隆(Lycophron)、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等人关于事物本源的观点,进而才展开自己立场的论述。通过综述评论,不同的学术观点能够进行比较,学术讨论能够不断延续,形成承前启后的学术传统,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时至今日,综述评论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通行规范,甚至沉淀在每一篇研究生论文的文献综述当中。
而在建筑领域,评论的作用则远远超越了论文撰写这一狭窄的领域。在这一学科的三大核心领域:历史、理论、设计当中,评论的作用都无法替代。而且,无一例外,这3个领域中的评论都属于“学院式评论”的范畴,也就意味着除了建筑物之外,需要对理论、对思想进行深度发掘,直至我们的能力所能抵达最底层。比如,在历史研究与教学当中,评论和解释伟大建筑作品的价值与内涵,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对史实的表述,否则我们甚至无法论证为何这些建筑被选入历史叙述而不是其他。而像密斯·凡·德·罗这样沉默而深邃的建筑师,更是需要仔细、深入的评论分析才能在“通过践行律法而获得自由”这样的言辞中找到其建筑思想的中枢[4]。而在当代理论教学中,面对彼得·艾森曼这样认为“概念”(conceptual reality)比现实建造(built Model)更为重要的建筑师[5],仅仅展现其形式操作的策略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他艰涩而强硬的理论论述展开分析评论,才能评价其立论的合法性,衡量其观点与实践的价值。这些历史与理论评述最终也将融入设计教学中。尤其是那些渴望研习某些建筑师、某种建筑现象的同学,教师负有责任去展现这些范例的价值所在,这同样依赖于结合理论文本的剖析,比如,结合“发现陌生的神奇,以及显而易见的事物的独特性“这样的话语解释阿尔瓦罗·西扎建筑作品的独特品质[3]207(图2)。相比于亚里斯多德先评论再论述的方式,建筑学教育中的评论更接近于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在对各种观点不断追问与评述中拓展认知的边界,评论本身成为最为重要的操作工具之一。

2 黄也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12级),清华大学工会俱乐部改造设计,2014年1月
虚无
巴别塔未能建成是因为建造者们之间沟通的障碍,这似乎并非什么无法逾越的难题。但如果整个建筑的根基出现问题,那就将是致命的。我们甚至无法开始建造,或者是始终生活在工程随时会崩塌的焦虑 (Angst)中。如前文所说,我们将大学中对“哲学真理”的探寻比作巴别塔的建造,那么这一梦想也面对着基础性的威胁,那就是被尼采称作门外“最为诡异的客人”(uncanniest of all gests)的——虚无主义(nihilism)。
尽管其历史至少能够被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与怀疑主义者,但虚无主义在现代最重要的论述者仍然是尼采。谈及自己与时代的关系时,尼采说过:“明日之后将为我而来。有的人在去世之后才出生”[6]。他对虚无主义的讨论显然印证了这句话,在他去世多年之后,这一讨论仍然是我们关切的核心,尼采的影响也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在“明日之后”才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3 阿尔布雷德·丢勒(Albrecht Dürer),画家绘制躺着的女人(Draughtsman Drawing a Recumbent Woman),约1525年。
“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尼采自问,并且回答道“最高的价值都摧毁了自己的价值。没有目标;‘为什么?’找不到答案。”[7]4而法国哲学家雅斯培(Carl Jasper)给予了更为生动的描述:“我们相信的所有东西都变得空洞;所有东西都是有条件和相对的;没有地基,没有绝对,没有存在自身。所有东西都是有问题的,没有什么是真的,任何东西都能够被允许。”[8]简单说来,虚无主义认为我们通常所认同的知识、信仰、价值都缺乏绝对稳固的基础,因此并不存在我们可以信赖的根本性出发点。在19世纪早期,虚无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认同客观世界独立于意识存在的观点。而在此之后,虚无主义所关注的更多是道德与价值的虚无,如果所有的信仰与价值都受到了动摇,那么生命本身也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噩梦”。正是在这一伦理意义之上,涉及到人们如何生存的问题至上,尼采称虚无主义是“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人性最深刻反思的时刻。”[9]43
之所以虚无主义的危机最为严重,是因为它并非一种单纯的个人意见,而是得到了强有力的哲学传统的支持。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尼采所论述的“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就像阿尔布雷德·丢勒(Albrecht Dürer)的画中所描绘的(图3),要得到一个准确的透视图,艺术家必须通过一个固定的视点去观察事物,所得到的景象与场景都以该视点为基础,如果出现视点的变化,整个图像也将发生变化。虽然人们不再使用这种器具作画,但透视法背后所隐含的确定视点却是不容否认的。“透视主义”将视点与图像的关系扩展到认知与价值领域,认为我们所建立的知识与价值体系也都基于某种特定的视点、立场或假设。但如果这些视点、立场或假设本身却缺乏确凿的基础,那么“透视主义”就会放大成为虚无主义的有效工具,对我们所认同过的各种真理与价值展开攻击。从尼古拉斯(Nicholas Cusa)的“洞察的无知”(Learned ignorance)到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生存意识”,再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与权力的分析,无一不是从透视主义的前提出发,对既有的思想体系形成无法忽视的冲击。在当代,通过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思想家的进一步推动,虚无主义已经不再被视为什么新鲜的事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为一种常识。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尼采的预言才被广泛的认同。虚无主义是如此的普遍与重要,我们甚至可以用“后尼采时代”来取代“后现代”等稍纵即逝的概念。
在建筑界,透过与“解构”(deconstruction)理念的联姻,虚无主义在20世纪末期曾经对全球建筑理论的图景形成巨大的冲击。但实际上,虚无主义的渗透早在解构主义潮流之前就已发生,最为典型的是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在1970、1980年代的一系列论述与设计实验。在他著名的“后功能主义”(Post-functionalism)、“古典的终结、起始的终结、终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End of the End)等文章中[10],艾森曼对以往建筑理论的各种基础信念加以批判,指出它们不过是一种基于某种视点的“透视”效果,而这些视点则并无绝对正当性。因此,以往从外部基础论证建筑的尝试都只能失败,建筑在虚无的漂浮之中只能满足于独立自足(Autonomous)的形式操作。由此可见,并非艾森曼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中找到了源泉,而是艾森曼本已抱有的虚无主义立场在“解构”理念上找到了新的支持。
然而,即使是像艾森曼这样无畏的探索者,这样勇于拥抱虚无主义的理论家,也难以摆脱尼采所预言的“严重的危机”。艾森曼坦承,在完成了住宅十(House X)之后,他陷入了抑郁之中,经过心理治疗他发现自己与“土壤和大地(ground)的现实脱离了接触。”从1978年的威尼斯卡拉雷吉奥(Cannaregio)项目开始,艾森曼的作品与大地产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近期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文化城(City of Culture outsi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项目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大地一方面是指字面意义的场地,另一方面也是指一种基础性的意义。在卡板住宅后,具有强烈意义象征的元素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艾森曼的作品与试验中。这或许可以被视为在虚无主义的危机之后,艾森曼回归到某种局部范围意义的传达,而非像之前一样拒绝任何这种约束与意义认同的绝对虚无立场。
艾森曼的例子说明,以虚无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既存的一切攻击批判、挥斥方遒固然是畅快淋漓的,但真正困难的却不是攻击,而是能否承受攻击成功的后果,也就是说接受虚无主义的后果。如同艾森曼这样强大的斗士都不免有难以承受之惑,其他人自然也无法逃脱这一拷问。如果不能驳倒虚无主义,那么如何能在这个虚无时代继续实践与生活?
目的论
如尼采所说,在虚无主义的条件下,由于缺乏可以信赖的基础,我们无法对“为什么”做出回答。因此要应对虚无主义的威胁,为自己的生活与行为找到某种根据,我们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而这是否可能?
在这里,必须承认,本文依赖于一个较为粗略、也未能得到足够充分论证的假设,那就是对所有“为什么”的回答模式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种是必然性的,一种是目的性的。
所谓必然性的解释,是指存在某种确定的规律和原则,决定了两件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就可以借用这种必然性的规律来解答“为什么”。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体系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这种必然性的规则体系之上,而这些领域的解答也只有求诸于这一规则体系才被视为合理的,比如,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就是绝佳的范例。
而目的性的解释,是指用目的关系来作为解答,通过提示被提问事物所服务的目的来解答其存在的理由。这种解答的合理性主要不依赖于既定的原则与规律,而是目的自身的合理性。回答是否能被接受也取决于人们对目的本身,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否认同。
必须注意的是,之所以将所有的“为什么”归为这两类,是因为这两类解释是无法互换的。比如对宇宙的整体存在的问题,物理学家们自然倾向于必然性的解释,使用各种理论工具将这一解释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然而,无论抵达什么样的程度,也仍然有人会继续追问“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想要的实际上不是物理解答,而是一种目的性解释,他们想要知道这个宇宙是因为什么目的,什么意义而存在的,这显然是无法通过相对论、量子力学或者是任何数学公式来获得的。能够满足他们的是宗教提供的解答,比如基督教的某种解答之一,世界上所有的为什么都可以被一个简单而完美的回答所降伏:因为主想要这样(Quia voluit,拉丁文,英文翻译为because God willed it)[11]。一切都被归因于主的意愿与目的,但是由于主远远超越了人的认知能力,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意愿是什么,或者它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的更深层次的意愿在起支配作用。我们只能满足于接受这个有限度的终极解释。毫无疑问,对于某些虔诚的宗教信徒,这种目的性解释是完全足够的,而对于那些想要必然性解释的人来说,这种回答则是空洞无物的。
有趣的是,艾森曼巧妙地利用了这两种解释的差异来完成攻击以往建筑理论基础性解释的任务。对那些强调理性基础的建筑理论,艾森曼指出,那些所谓必然的理性解释其背后都蕴含着目的与利益,因此实际上还是一种目的性解释,也就不具备原来所声称的必然性权威了。而反过来,对那些以目的为基础的建筑理论,艾森曼反其道而行之,指出某些学科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些事物的发展与规律是必然的,比如语言,与人的目的无关,因此目的性解释,以人为中心的目的性解释也应该被抛弃。简单地说,艾森曼是利用两种解释的不相容来逐一击破,攻击A的时候使用B,攻击B的时候使用A,这种摇摆不定也恰恰是他理论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1)[10]
回到之前的讨论。如果上面的两种分类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应对虚无主义就可以从两条路径探寻“为什么”的可能解答。在建筑领域中,必然性解释显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在现代主义阶段,人们曾经认为功能、结构或者材料能够为建筑提供必然的基础,就像洛基耶神父(Marc-Antoine Laugier)所憧憬的那样。伴随着正统现代主义的衰落,这种信念已经很少再找到支持者。而在更大的哲学范畴,自休谟(David Hume)对因果关系展开质疑以来,人们就无法再去设想一个简单而必然的世界结构,而康德(Immanuel Kant)对休谟的应对也不是在物质世界中重新找到因果关系的基础,而是将这种必然性联系归因于人的认知结构。这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必然性解释的基础,因为人成为这一切的起点。
另一条目的性的道路似乎要容易一些,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硬的必然性要求,而且目的本身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在历史上,这种目的性解释获得了一个专用名称:目的论(teleology),其辞源来自于希腊语telos,意为目的、用途。主要通过亚里斯多德的理论,目的论成为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流派,时至今日仍然在功利主义、新亚里斯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等理论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相比于必然性解释,目的性解释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来应对虚无主义的攻击。
对于目的性解释,或者说是目的论,虚无主义的攻击性力量来自于“上帝死了”这样的论断。如果Quia voluit不再被接受,也不再有任何绝对的目的与意图受到认同,那么不管什么样的目的论也都缺乏绝对稳固的基础。但是,应该注意到,相比于必然性解释,目的论其实对绝对性、唯一性、必然性的要求要弱得多,它所需要的是一个终极目的以及其他次要目的与终极目的的关联性,而对于这个终极目的是否是唯一的、绝对正确的,目的论并无特殊的限定。所以,一旦我们放弃对Quiavoluit这种唯一、绝对终极目的的诉求,那么也就可以避开虚无主义的锋芒。而这恰恰是尼采个人所采纳的,应对虚无主义的策略,如朱利安·杨(Julian Young)所说,虽然“缺乏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却没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建构一个个人叙事(personal narrative)……在我们的后‘上帝死了’的时代,这取决于个人去建构我们自己的‘英雄’自我”[7]87。这里的宏大叙事是指的建立在绝对目的基础上的对所有事物的解释,而个人叙事则是建立在个人所认同的目的基础之上的,致力于给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的目的论体系。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一生所追求的目的有清晰的认同,那么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就可以循着这一目的获得价值。如果接受这种论断,那么虚无主义反而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试金石。它摧毁了人们对终结解释的信赖,迫使人们去主动建构个人叙事,进而不可避免地做出抉择,哪些价值才是真正值得去获取的。“我们必须体验虚无主义才能发现这些‘价值’到底有什么样的真实价值,”尼采如此写道[6]。
这么看来,在必然性解释与目的性解释这两条道路中,后者更有利于应对虚无主义的冲击。我们要做的是放弃对绝对解释与绝对目的的声张,但是认同个人目的与个人解释的合法性。或许我们不能用所有人都统一的语言建造唯一的巴别塔,但并不妨碍我们以不同的、更加个性化的语言建造无数个不同的巴别塔。
以这样的理解为基础,我们也就获得了在虚无时代可以采纳的一种评论策略:1)接受虚无主义的正当性;2)放弃将必然性解释以及绝对目的作为解释建筑现象的可考基础;3)挖掘建筑背后所隐藏的建筑师的个人叙事,也就是个体化的目的论,以此作为评论分析的基础与核心关注。
建筑师
对于这种评论策略,路易·康提供了最好的注解。在谈论建筑的理解时,他提出了3个层次,分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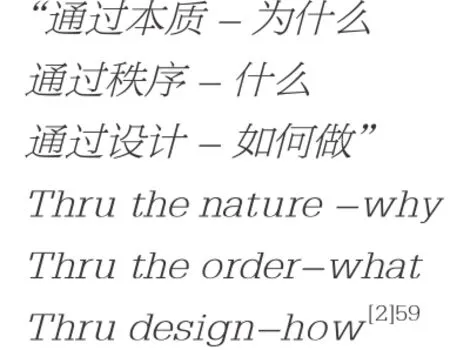
从他其他大量文字中不难看出,即使人们都在谈论康的秩序,这3条中最重要还是本质(nature),它为“为什么”提供了答案。而“本质”是什么?康有时会用“存在意志”(existence will)来指代,
所谓意志就包含一种意愿、一种目的和一种选择的能力,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康这样的话语:“建筑师应该在事物的本质中——通过他的领悟——发现一个事物想要成为怎样[2]82。”在康的理论中,只有领悟到这种“存在意志”才能建立建筑的根基,而秩序与设计则会在根基之上自然浮现出来。
康的3个层次是理解建筑的3个层次,也自然是评论的3个层次。一个“学院式评论”应该在3个层次上对建筑展开分析,而最重要的还是对根本性的“本质”的讨论,这当然不能理解为某种永恒不变的性质,而是康所强调的“意志”。就像Quia voluit理念指代的是神的自由与意愿,“意志”当中所蕴含着是建筑师的目的选择。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虚无主义,如果只有一座巴别塔,那么评论将变成乏味的重复。如果有成千上万座各式各样的巴别塔,评论也才有了可以操作的空间。即使康的3个层次看似有些模式化,但建筑师们“意志”与选择上的巨大差异,足以弥补同一模式的单调。今天,在中国建筑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引人入胜的丰富性。
比如刘家琨的胡慧姗纪念馆,其根本目的是对个体生命的纪念,并且籍此触动人们反思日常生活的价值。在秩序的层面,他选择采用双坡住宅的原型与厚重的纪念性建构,而设计手法上则包括特殊的光线控制与展陈布置。
王澍的象山校区则有完全不同的体系,建筑师试图以中国文人传统的诗意世界取代当代生活方式,这当然是他最根本性的意图。在总体性的设计策略上,建筑师选取了传统建筑原型、游历式的组织方式以及强烈的厚度性特征,并且辅以采用回收材料等具体的设计手段。
北京的OPEN建筑事务所同样有着清晰的目的诉求。但是,他们并不认为需要退缩到个人生活或者是在失去的世界寻求解答,而是抱有坚定的启蒙信念,继续追索现代主义的经典价值。开放性、灵活性、效率等原则构成了他们的建筑秩序,而底层架空、开放平面、标准化等设计手段则为这一目的的实现提供着支撑。
这3位建筑师与事务所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评论者的责任在于能将这种差别追索到最根本性的起源,也就是他们对本质、对意志、对目的的不同理解。按照康的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对建筑的全面理解,才能判断一个建筑的价值所在。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每个建筑师都提出自己的目的论,那又依据什么共有的原则来判断哪个更为优秀呢?如果没有这个普遍性的原则,我们实际上仍然处于盲目之中,虚无主义的威胁仍然如影随形。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多样性的目的论是构建个人叙述所必需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凭空创造出一种价值追求,而是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选择自己的英雄”,他们在一些典型性的范例人物身上找到特定的价值体现,然后加以比较选择,并最终融合构建出自己所认同的价值体系,塑造自己人生叙事。建筑师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所提供的也是这样的范例,以及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不管是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对诗意世界的怀旧还是对启蒙理想的坚持,人们需要这样的多样性来作为选择的基础。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英雄的选择”也不是完全由一己之力凭空决定的,人们之间的共性实际上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这潜藏在我们所共同使用的语言当中,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说,选择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共享一种语言的人们在价值选择、行为模式、理想渴望上有着强烈的关联性。他们往往面对着相似的问题,也有着相似的憧憬,这也意味着他们的选择可能是相近的。而那些最能得到认同的,将是能够对当下人们面对的普遍问题做出最有力解答的价值模型。“没有什么犁沟比那些在当下人性的地面上所撕裂的更深”[12]。尼采的话意在说明,只有那些对当下人性的关切做出回应的人才能获得更深刻的认同。评论者应该将这些“人性的犁沟”展现出来,而人们则可以甄别出哪些更有深度,哪些最值得当下的关注。
结语
虚无主义在今天早已失去了曾有的光环,如美国学者凯伦·卡(Karen L. Carr)所指出的,“虚无主义不再是我们必须逃避的东西,它已经失去了潜在的转变或救赎的作用,而是成为一种简单的对人类状态的枯燥描述”[9]7。如果说重复几句“上帝死了”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话,在“上帝死了”之后该如何继续才是真正重要的,需要严肃对待的,却仍然还没有完美解答的问题。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某种绝对的基础,但尼采的“个人叙述”在目前看来是更具有说服力的解答。康显然属于有绝对信仰的建筑师,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建筑属于时代,或者属于个人,它们只是绝对本质的领悟与体现而已。这也让他的思想显得格外古典,甚至比在他之前的现代主义大师都离我们更为遥远。但无论怎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英雄”,一个有着坚定信念与执着追求的范例,也仍然在激励着那些有着独特形而上学情怀的模仿者。而刘家琨、王澍与OPEN有着同样的坚定,很难说是他们信念的力量还是建筑的力量更为打动人,按照目的性的解释,这两者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
同样,虚无时代的评论策略所侧重的不是对抗,而是帮助人们探索如何在接受虚无的前提下,去建构并不虚无的生命。评论者的任务,也不在于告诉人们应该怎么样选择,那就会落入塔夫里所称的“操作性批评”(operative criticism)的陷阱,而是向人们展现“英雄”的力量,以及光环之下的阿基里斯之踵。它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人们建造自己的通天之塔。
注释:
1)尤其是在“古典的终结:起始的终结,终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End of the End)一文中,这种攻击策略的不相容性体现得非常明显。
[1] Robert McCarter. Louis I. Kahn. London ; New York: Phaidon, 2005: 386.
[2] Louis I. Kahn, Alessandra Latour. Louis I. Kahn: Writings, Lectures, Interviews.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1
[3] Alvaro Siza, Antonio Angelillo. Writings on Architecture. Milan: Skira ; London : Thames & Hudson, 1997: 27.
[4] Fritz Neumeyer. The Artless Word : Mies Van Der Rohe on the Building Art. Cambridge, Mass. ; London: MIT Press, 1991: 328.
[5] Iman Ansari. Interview: Peter Eisenman, Architectural Review, 2013.
[6]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 And the Anti-Christ. Penguin, 1990: 126.
[7] Julian Young. The Death of God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3.
[8] Karsten Harries. Infinity and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 London: MIT Press, 2001: 12.
[9] Karen Leslie Carr. The Banalization of Nihilism : Twentieth-Century Responses to Meaninglessnes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10] K. Michael Hays.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Cambridge, Mass. ; London: MIT, 1998.
[11] 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Cambridge, Mass.; London: MIT, 1983: 151.
[12] Hans Blumenberg. Care Crosses the Riv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75.
The Strategy of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Nihilism
QING Feng
Starting with the academy,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i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t recognizes that nihilism constitutes a great threat to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riticism. It argues that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can be utilized as a strategy to cope with such a threat and, in several examples, illustrate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such a strategy.
Babel, academic criticism, nihilism, telos, hero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2014-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