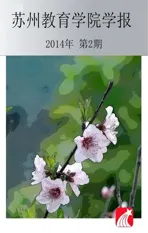从北京话AB式拟声词看现代汉语的两种构词原则
2014-02-16高永奇
高永奇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从北京话AB式拟声词看现代汉语的两种构词原则
高永奇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北京话中AB式拟声词遵循一种语音原则,即语音在后一音节上得到延展或突出。而汉语中“名+名”式合成词的语义原则是“语义值大→语义值小”,当语义原则跟语音原则发生冲突时,这类合成词在语音上就会作出适当调整。汉语方言中的嵌-l-词,本质上是一种语音构词,符合汉语构词的语音原则。
拟声词;语音原则;语义原则;分音词
近年来,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大都认为: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的词序与尊卑有序的观念有关。如:游汝杰认为“有些成对的并列结构构成一个词或词组时,先后的次序不能任意更换。”[1]78他举例:凡含“天地、男女、长幼、尊卑”之类两字的并列结构(词成词组),一般都是“天、男、长、尊”在前。[1]79孙志伟[2]也认为这些词先男后女、由尊及卑的语义构词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杨智慧认为不但汉语如此,其他语言也有这种现象:“语言中的次序并不是任意的,而符合人的认知心理过程的。”如“husband and wife,Adam and Eve,king and queen.”[3]
其实,较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陈建民[4]123,但随后王宗炎就提出了质疑:“汉语并列词的结构并非只有一种格式。自古以来,汉语说‘男女、乾坤’,可也说‘阴阳、雌雄’;说‘(男)婚(女)嫁’,可也说‘嫁娶’;说‘兄妹’,可也说‘姑嫂’;说‘伯仲’,可也说‘叔伯’;说‘上下’,可也说‘左右’(古时左为下位,右为上位)……“在这些反证中,古老的伦理观念、封建的等级层次虽然存在于汉人心中,可是分明没有‘投影’在词语结构上面,因此‘文化结构分析法’不适用。”[5]
本文从语音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汉语中有这些“正例”和“反例”。同时,也试图解决汉语方言中的另外一种构词现象。
一、AB式拟声词与拟声原则
孟琮曾详细讨论过北京话的拟声词,其中“AB式由两个不同的音节构成。如:吧唧bājī,呱嗒guādā,噗通pūtōng,嘡啷tānglāng,刺溜cīliū,等等”[6],他认为AB式拟声词的两个音节的语音特点
大致如表1:

表1 北京话AB式拟声词两音节的语音特点
朱德熙曾分析北京话单音、双音、三音、四音节拟声词之间的关系[7]:

丰竞把双音节拟声词分为:(1)只有连用式而无叠音式的双音节拟声词,如:吧嗒、喀吧、喀嚓、喀嗒、啪嚓、啪嗒、啪啦、哇啦、咕嘟、咕噜、呼噜、滴沥。为变声叠韵式,特点是“第二个音节的韵母都为或或”。而变声非叠韵式,如:吧唧、啪唧、呱唧、咕唧、咯吱、呼哧、噗哧、吭哧,其特点是“第二音节韵母变为或后,其声母即受[i]或的同化,一律变为或或。”(2)有“ABB”叠音式的延音拟声词。又有甲类:呛啷、当啷、咣当、哐啷、噌楞、玎玲、丁零、轰隆。特点是两个音节都为鼻韵母或或或。乙类,咕隆、咕咚、扑通、扑棱、咯噔、嘎嘣,特点是第二个音节保留第一个音节的元音,再加上鼻韵尾。丙类:唰啦、呱嗒、哗啦、吱扭,特点是延长第一音节中的[a]或后加[u]。[8]
朱德煕先生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北京话的拟声词可以通过音节的“重叠”和“变声”、“变韵”等语音形式进行变化。我们认为,“重叠”也是一种语音的延伸,是整个音节的延伸。“向前变韵”的情况是使得前一音节的韵母开口度小于后一音节韵母的开口度,形成开口度“小→大”的特征。丰竞在分类时,则把“延音”作为一个标准。可见,语音在后一音节上的延伸发展是AB式拟声词的一个特点。
我们对134个北京话的AB式拟声词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9]。
统计结果显示,A部分声母使用频率较高的前几位是k(25个)、kh(23个)、p(15个)、ph(14个)、h(14个);韵母使用频率较高的前几位的是u(29个)、a(23个)、u(a14个)、(i11个)(9个);声调部分则以55调为主。B部分声母前几位的是(l51个)、(t21个)、(15个)、th(10个)、9个);韵母部分前几位的是:(a41个)、(17个)、(i12个)、(12个)、(11个),声调也以55调为主。这些特点多数跟孟琮先生的结论一致。

表2 北京话的AB式拟声词语音统计 个
北京话的拟声词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似AA重叠式的结构,如:(驴叫声)、(物体合拢声)、(重物落地声)、(木材断裂声)、 (轻物碰撞声),这类字的特点是改变声母的送气不送气特征或改变韵母中的元音为近似元音,拟声词仍然成立。如“轻物碰撞声”可说成。这类词数量不多(我们称之为“少数类”),我们在统计时没有区分开来。另一类是A、B两部分各有不同语音特点的拟声词(我们称之为“多数类”)。尽管我们在统计中没有把这两类区别开来,但仍能通过统计表看出“多数类”拟声词A、B部分的特点。
从表2我们看出:A部分的特点是声母以“塞音为主”(k、kh、p、ph),韵母元音起始开口音较小(u、i、ua)。其中韵母为a的数量也不少,许多为“少数类”词中的音。B部分的声母又分为两类:(1)“延音型”(l、、);(2)“塞音型”(t、th)。B部分的韵母开口度不小于A部分的开口度。也就是说:从前一音节A到后一音节B,一类是延音型,音长在B上可以延展
伸长;另一类是塞音型,前一音节A为塞音类声母,B音节也用塞音声母,使得音响在B段得到明确。我们把这种从前一音节A到后一音节B的语音特点称为AB式拟声词的“拟声原则”。
二、并列式“名+名”合成词的语序
其实,一些学者观察到的现代汉语的并列结构的词序前尊后卑的情况并不错。为了便于讨论集中,我们这里只限定在并列式“名+名”合成词的范围内。我们再多观察一些这种结构:
眉目 语言 窗户 树木 门户 根本
国家 江山 领袖 仓库 虎狼 师生
…… ……
前一成分比后一成分不仅仅是“尊”和“卑”的问题。有些是前一成分比后一成分常用:如“树”跟“木”、“门”跟“户”之间;有些是前一成分比后一成分重要:“国家” “师生”。可以说是前一成分比后一成分的语义值“大”[2]。当然,其他“名+名”并列式结构也有类似现象。如“龙腾虎跃”中“龙”与“虎”,“雕梁画栋”中的“梁”与“栋”。张彦群、辛长顺认为:“汉语并列结构组成成分排序大致遵循如下原则:时空原则、感知原则、文化原则、语音原则、逻辑原则、语境原则、语言习惯等。”[10]其中文化原则包括由尊及卑(君臣、师徒、师生、主仆、官兵、干群),由长及幼(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妻儿、翁婿、叔侄、儿孙、子孙、姐妹、祖孙、姐弟、老中青),由男及女(父母、公婆、夫妇、夫妻、爸妈、弟妹、哥姐、哥嫂、兄嫂),由亲及疏(姑嫂、姑舅、亲戚、叔嫂)。
我们把他们说的时空原则的“前—后”、“上—下”,认知原则的“大—小”、“高—低”,文化原则的“尊—卑”、“长—幼”等可以总括为:语义值大→语义值小。跟前面的拟声原则相对应,这一原则不妨称为“语义原则”。
“语义原则”与“拟声原则”有时候并不一致。就汉语的“名+名”并列式合成词来看,多数情况下“语义原则”为主,即语义构词,但也有不按照语义原则而是按照语音原则构词的,这便是语音构词。
语义原则跟语音方面的冲突首先便是上面提到的“反例”。王宗炎举的多数反例是符合汉语语音原则的(绝大多数为非名词性成分的组合,但语音方面的制约仍可以看出来)。这些例子有:
阴阳、雌雄、股肱、幽明、输赢、斜正、偏正、消长、低昂、俯仰、寒暖、阴晴、轻重、悲欢;
嫁娶、曲直、难易、毁誉、损益、继续、迟速、生熟、虚实、悲喜、贫富、祸福;
姑嫂、敌我、叔伯、迟早、死活、苦乐、离合、冷热、哀乐。
上述例子中,第一组的后一音节为鼻音尾-或-n收尾音节;第二组后一音节为-i、-y、-u收尾的音节;第三组后一音节主要元音(无鼻音韵尾韵母)的开口度比前一音节大。显然,这几组词在语音上都跟我们前面说的“拟声原则”是一致的(“伯”有bó、bāi两读,在“叔伯”中,也许是受语音条件的制约,读轻声的bai)。[11]
在拟声原则跟语义原则相矛盾的时候,有些词语会在语音上进行一些调整,以适应语音、语义两方面的要求。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不符合语音规则的“名+名”复合词在凝固为一个词的过程中进行内部的语音调整:(1)符合语音规则的,结构凝固得比较紧密,后一音节常常读轻声;(2)不符合语音规则的,结构不太紧密,后一音节往往不读轻声。如:
弟兄dìxiong—兄弟①xiōngdì;②xiōngdi故事gùshi—事故shìgù
言语yányu—语言yǔyán(“言语”为非轻声的yányǔ时,表示其他意义。)
以上例子中左边的词语我们认为是符合语音规则的,右边的词则不符合语音规则。
三、方言中的分音词与嵌-l-音问题
现代汉语方言中有所谓嵌-l-词(或叫“分音词”“切脚字”)问题。“分音词是连绵词(字)的一种,是指一个单音节词用一个双音节词的形式来表示,这个双音节词的两个音节相切正好是这个单音节词的音。这种情况跟文献上所举的‘蒺藜’切‘茨’,‘囫囵’切‘浑’,‘葫芦’切‘壶’,‘窟窿’切‘孔’相类似。”[12]如陕北方言中的分音词[13]:
关于分音词的研究已不少,目前涉及问题包括:(1)汉语哪些方言中存在分音词?分音词的形式是否相同?(2)为什么分音词的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多数为-l-?
第一个问题有待汉语方言调查的不断深入。第二个问题也有人从音理等方面作出过一些解释。如竺家宁认为边音[l](或卷舌音[r])成分作为拟声词的初始发音成分,似乎是某些语言的共通性质。[14]
为什么是这样呢?从发音性质上看,[l]是舌尖抵住上齿龈,气流由舌两边流出。这个发音动作比气流爆发的塞音、气流挤出的擦音以及发音方式为二者结合的塞擦音轻松自然得多。因此,几乎所有的语言都能找到[l]这个辅音([r]可以视为它的变体,二者同属流音,流音较塞音、擦音易发出,且具有响音[+sonorant]之效,它可称为“基本辅音”。乔姆斯基与哈勒在《英语音系》中列出边音[l]的语音特征为:[+辅音、+响音、+浊音、+连续、+舌冠、+龈前、+宽阻];卷舌音[r]的语音特征为[+辅音、+响音、+浊音、+连续、+舌冠、+宽阻]。[l]同基本元音[a]、[i]、[u]结合,发音时,力度最小,发音难度最低,因而表达自然界声音的拟声词顺理成章地选了这些音节来组成。
其实,从现代汉语AB式拟声词的拟声原则中,已可以看出:之所以分音词选择[l]作后一音节的声母,是因为这样的语音形式符合“音长在B上延展伸长”的基本要求。不论[l]或[r],都有[+连续]的语音特征。
由此也可看出,汉语方言中的“分音词”其实是一种语音构词。同时,它的第二个音节也要符合语音构词时应遵循的其他要求。如:韵母开口度大并且可延展(a、i、)等。换言之,如果第二音节的音(声母、韵母)不具备“[+延伸]”的性质,那么该分音词不成立。如李蓝总结的晋语的分音词的构造规律如图1[15]:

图1 晋语的分音词的构造规律
我们所考察的所有汉语方言中的分音词都符合上述语音构词的要求。
拟声规则的实质是语音得以延展。可延展的方式大致以下几种:
(1)重叠。整个音节反复以示语音的延续。如儿童习得母语时的所谓“保姆语”:“桌桌” “椅椅” “饭饭”。再如汉语中许多亲属称呼语多用此形式,“爸爸” “妈妈” “哥哥” “姐姐”。
(2)叠韵。重复音节中响亮、可延伸的部分以示延伸。如演唱时的拖音lai(来)……ai……ai……。
(3)后音节增加响度。后一音节选择听觉上有延伸感的韵母、元音,如a、i、u及-韵尾。
(4)后音节选择声母部分有延伸感的声母辅音。这样的辅音多为-l-、-r-。如方言中的分音词。
(5)增加和延伸语音的后缀(或词尾)。如方言中的“么”。北京话“他多厉害。” “他多么厉害。”陕西方言“那里咋那多人。” “那里咋那么多人。”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疑问代词“甚” “甚(么)” “什么”。
四、小结
本文从并列式“名+名”合成词说起,探讨了现代汉语(北京话)AB式拟声词的构造方式,分析了不符合汉语语义原则的“名+名”合成词,并论及方言中分音词的结构特点。认为:
1.AB式拟声词的“拟声原则”是:从前一音节A到后一音节B,音长在B上可以延展伸长;或者前后音节都为塞音类声母,音节B在音响上得以突出。
2.就现代汉语“名+名”组合形式的复合词来说,前一语素比后一语素的语义值大,是并列式合成词的一条语义原则。不符合语义原则的词语,往往是语音规则在起作用,后一音节在语音上往往发生一些变化。
3.汉语方言中的“分音词”其实是一种语音构词,它的第二个音节要符合语音构词时的要求。
[1] 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 孙志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思想与并列式成语的语义构词原则[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52-55.
[3] 杨智慧.语言和社会文化中的性别歧视[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5,7(9):63-65.
[4] 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5] 王宗炎.一门新学科的诞生[J].读书,1990(6):10-19.
[6] 孟琮.语法研究和探索: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20-121.
[7] 朱德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J].方言,1982(3):174-180.
[8] 丰竞.双音节象声词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3(4):82-84.
[9] 阚兴礼.AB式拟声词及其重叠形式的多角度考察[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26(5):82-85.
[10] 张彦群,辛长顺.并列结构组成成分排序原则及原因初探[J].天中学刊,2002,17(4):69-73.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 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24.
[12] 汪敬尧,杨美芬.晋语子长话的分音词合音词逆序词[J].榆林学院学报,2003,13(4):101-102,105.
[13] 张子刚.陕北方言中的分音词[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6(1):103-104.
[14] 竺家宁.论拟声词声音结构中的边音成分[J].国立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1995(1):1-13.
[15] 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J].方言,2002(1):41-59.
(责任编辑:施建平)
The Two Principles of Word Formation in Modern Chinese Seen from the AB Type Onomatopoeia in Beijing Dialect
GAO Yong-qi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The AB type onomatopoeia in Beijing Dialect follows a kind of phonetic principle, which means the sound in the latter syllable becomes longer or prominent. The semantic principle of the “noun+noun” type compound in Chinese is “from the big semantic value to the small semantic value”. When the semantic principle conficts with the phonetic principle, the sound of these compounds will make suitable changes. The embedded words in Chinese dialects are a kind of phonetic word-formation in essence, following the phonetic principle of Chinese word-formation.
onomatopoeia;phonetic principle;semantic principle;sound-divided words
H14
A
1008-7931(2014)02-0038-04
2013-12-2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YY049)
高永奇(1966—)男,河南浚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