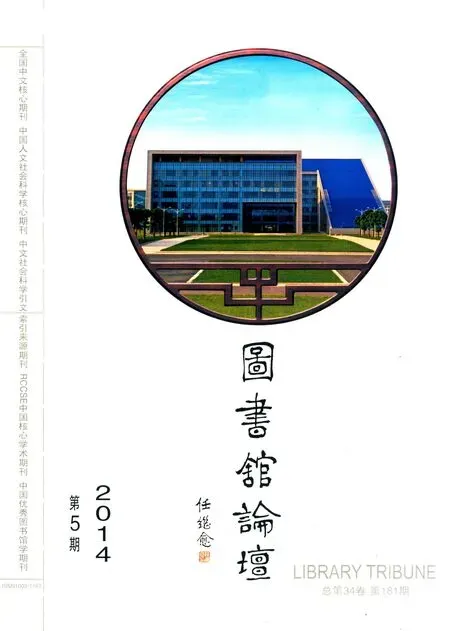美国《图书馆权利法案》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2014-02-12王静芬
王静芬
1 美国《图书馆权利法案》精神溯源
在美国的建国史中,《五月花号公约》《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独立宣言》和《美国联邦宪法》作为初始重要的文件体现着契约、自治和平等精神。其中,《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基本精神是人的平等性,并阐述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他各州权利法案的示范”[1],“如同一座灯塔”[2]对其后许多政治文献产生影响,如1776 年的《独立宣言》、1787 年的《美国联邦宪法》 乃至1791 年的《美国权利法案》[3-4]。
美国图书馆协会委员会(ALA Council)于1948 年6 月18 日发表了《图书馆权利法案》(The Library Billof Rights)(以下简称“《法案》”)。作为一种历史产物,《法案》必然带有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承袭美国历史传统精神和价值取向。“可以肯定的是,佛雷斯特·斯波尔丁在使用‘Library’s Bill of Rights’这个题名时,可能受到了英国1689 年颁布的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文件《权利宣言》 和美国1791 年通过的宪法补充文件《美国权利法案》 (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甚至美国1776 年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The Virginia Declarartion of Rights)的影响,因为这些权利法案是美国人研究和起草有关‘权利’文件的基本文献和依据”[5]。
2 美国《图书馆权利法案》的历次修订及内容
2.1 美国《图书馆权利法案》的诞生背景
《法案》提出的背景事件可以追溯至1937年,当时的美国社会正遭受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对言论的限制以及图书审查制度的控制相当严格。蒙大拿州立大学图书馆馆长飞利浦·基尼(Philip O. Keeney)因不愿意剔除校方要求的具争议性图书而遭到解雇[6]。这一事件引起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的注意,ALA 的图书馆员薪资、职员及职位委员会(Board on Salaries,Staff,and Tenure)向蒙大拿州立大学校长提出抗议,要求校方尊重图书馆员的专业以及权利。但是因为当时社会对于图书馆员的专业认知不足,协会抗议的影响力不大。1938 年,爱荷华州德梅因公共图书馆(Des Moines)馆长佛雷斯特·斯波尔丁(Forrest Spaulding)有感于自由言论的限制以及图书审查制度所造成的日益偏执的观念,必将影响该馆所服务的读者权利,因而提出了《免费公共图书馆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 for the Free Public Library),其内容为:(1)由于图书和其他读物的购置得到公共资金的资助,因而选书应以德梅因市居民的利益及其兴趣为立场,不应以作者的种族、国籍、政治或者宗教观点作为选书标准。(2)在图书馆可收集的资料范围内,对存在不同观点并有争议的问题的图书应平等地对待。(3)对组织、宗教、政治、兄弟会或者地方社团的正式出版物或宣传品,其收集不应有所区别,而应将其视为馈赠并供读者取用。由于购置图书和读物的经费贫乏,图书馆不可能购置所有团体出版物。如果仅购买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另一部分,存在歧视之嫌,因此,必须制定这一政策。(4)应以平等原则向所有非营利团体提供图书馆会议室,不收取费用,不应排斥任何人[7]。这个法案主要从四个方面来阐明图书馆的服务政策:(1)选书立场,应平等地选择读物;(2)对争议问题的处理,应平等地面对有争议的图书;(3)对各种组织或社团出版物或宣传品的收藏政策,应平等地收集社团赠品;(4)会议室的开放原则,应基于平等条件开放图书馆会议室。这四个观点全部都提到一个词:平等,针对社区图书馆馆藏以及馆舍的利用做出平等服务的政策规定。
这一法案对当时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服务提供了一个示范样例。这并不是仅限于某一社区图书馆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的图书馆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限定及保护图书馆的平等权利。这一法案最终由德梅因公共图书馆理事会提交到美国图书馆协会理事会予以审议,并最终成为《法案》的雏形。
触动ALA 并使之制定读者服务原则和政策的事件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环境下,社会上出现的禁书毁书事件。1939 年,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美国社会纪实文学《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着重描写加州中西部农业民工被农场主压迫的困苦状况,反映美国一代破产农民怎样向产业工人转变的现实问题。美国各州统治集团对此相当不满,施压于公共图书馆。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和加州等地区图书馆被迫将这部小说列为禁书。同年,据加州的报章报道,当地政治委员波默罗伊(Harold Pomeroy)曾非常自信地说:“本州协会将支持在公共图书馆禁止这本书的任何行动。”[8]而加州克恩县免费图书馆(Kern County Free Libary)馆长倪芙(Gretchen Knief)则提出:“这样的审查制度将是图书馆历史上的第一例。让我担忧的是‘它能在这里发生’。如果这本书被禁止,那么明天什么书将会被禁呢?”尽管言辞恳切,但倪芙迫于董事会的压力,最终还是将此书从总馆和分馆的书架上抽离[9]。由禁书事件引发的图书审查逐渐发展为对图书馆服务价值和传统的挑战。重视图书馆权利的呼声日涨,推动了美国图书馆协会以《免费公共图书馆权利法案》为蓝本,经适当修改后,成为《法案》的1939 年版本。
2.2 美国《图书馆权利法案》的修订历史
为了更好地宣传图书馆权利以及确立原则,1940 年ALA 理事会建立了智识自由委员会(the Intellectual Freedom Committee,IFC)。IFC是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法案》,由ALA 理事会通过,为保障图书馆用户、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员的权利而建立起来的。当发生触及知识自由以及审查问题等的事务时,IFC 将与ALA 其他部门和工作人员开展紧密合作[10]。1944 年,IFC 主席卡诺夫斯基(Leon Carnovsky)在向ALA 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只有极少数的干扰图书馆员选书的事件得到报道,这可能意味着没有事件发生,也可能意味着图书馆员并不在意这些干扰的报道,甚至可能意味着图书馆员在图书选择政策上相当谨慎,在可能遇到干扰之前就规避了事件的发生[11]。这个报告内容暗指ALA 应该重视图书馆选书的标准和立场。同年,约翰·卡尔森(John Roy Carlson)的《内幕》(Under Cover),和莉莉安·史密斯(Lillian Smith)的《奇异的果实》(Strange Fruit),都因有悖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而被列为禁书。其中,《内幕》描述了20 世纪30 年代末40 年代初美国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情况,《奇异的果实》描述了分别属于黑人和白人两个种族恋人之间的爱情。面对1944 年的禁书风波,IFC 主席卡诺夫斯基提议修订《图书馆权利法案》的第一条款,最终得到通过。1944 年版本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图书馆不应仅仅因为一部分人的不赞同而移除或禁止描述确切事实(factually correct)的图书。”[12]1948 年,在IFC 主席博宁豪森(David K. Berninghausen)的提议下,ALA 理事会通过了对《法案》的修订。
1950 年,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扩大以及新媒体的出现,ALA 理事会面临新的问题。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公共图书馆(Peoria Public Library)因为提供《边界》 (Boundary Lines)、《手足情》 (Brotherhood of Man)和《苏联人》(Peoples of the USSR)三部电影予以流通,遭到伊利诺伊州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Peoria American Legion)的反对,并向图书馆施压,要求移除这些馆藏。由于《法案》的条款只针对图书和其他读物,并未明确包括非纸质资源,因此,一些图书馆员认为《法案》仅适用于纸质文献,而对非纸质文献的审查制度采取漠视态度[13]。有见及此,ALA 在1951 年仲冬会议上补充了对法案适用范围的说明:“《图书馆权利法案》应适用于图书馆收藏或使用的所有供交流的资料和媒体。”[14]
1961 年,ALA 对读者自由平等地使用图书馆的权利作了明确声明:图书馆不得因读者的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观点而拒绝为其服务。1965 年,ALA 在华盛顿仲冬会议前的一次针对知识自由的预备会议上,集中讨论了“拥有充分事实根据、高可信度的(sound factual authority)图书或者其他读物不应因其党义或者教义的不同被宣布禁止或被剔除”这一条款。与会者对该条款的批评源于一个真实案例:伊利诺伊州贝尔维尔(Belleville)的一位天主教图书馆员拒绝将新教徒的出版物《教会与国家》(Church and State)列入馆藏,并且援引了《图书馆权利法案》的这一条款作为他的正当理由[15]。此事例说明条教中“拥有充分事实根据、高可信度的(sound factual authority)”这一表述而且也容易被滥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图书馆的馆藏作了不必要的限制。根据该会议讨论的结果,ALA 在1967 年对《法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
1980 年修订的《法案》在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文字表述上的精简和调整,重点仍强调对馆藏选择的平等中立,对个人平等使用图书馆服务的权利予以保护,以及公众使用会议室的平等原则。1996 年《法案》的内容沿用了1980 年的版本,重申应取消对年龄的限制和歧视。
《法案》是一份指导美国图书馆服务的基本原则声明[16]。在实际工作中,还需要有明确的操作指引来解决具体细节问题。因此,IFC 起草并获ALA 理事会批准,颁布了一系列对《法案》的阐释、Q&A 等文件,并陆续对阐释文件予以修订。
2.3 美国《图书馆权利法案》修订内容分析
《法案》自1939 年6 月19 日由ALA 理事会通过最初版本,随后历经了1944 年10 月14 日、1948 年6 月18 日、1961 年2 月2 日、1967 年6 月27 日、1980 年1 月23 日,以及1996 年1 月23 日的6 次修订。每次修订无不是伴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针对图书馆实际工作中对法案原则的存疑,是图书馆界为读者争取平等权利的积极响应。其中,1948 年和1967 年的版本修改幅度较大。
1948 年《法案》的修订情况:(1)卷首语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理事会重申其信念,以下基本政策应该成为全部图书馆服务之指导”。这一修订简化了制定法案的目的,明确其为适用于全部图书馆服务的政策,使之具有广泛而普遍的指导意义。(2)第一条款修订为:“作为图书馆服务的职责所在,挑选的图书和其他读物应基于社区中所有民众的兴趣、信息和启迪教化,任何资料不可因为作者种族、国籍、政治或宗教观点不同而遭排斥。”与1939 年相比,一方面强调图书馆在馆藏选择上负有责任,应该予以重视;另一方面也指出图书馆在这方面应该具有主动性。文字上删除了之前“源于公共资金的资助”的字句,使该法案的原则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强调资源获取与选择的平等与公正,并确立选书的原则是基于所在社区的“全体民众(all people)”的兴趣、资讯和启迪教化。(3)第二条款中,特别提出“拥有充分事实根据、高可信度的(sound factual authority)图书或者其他读物不应因其党义或者教义的不同而被宣布禁止或被剔除”,这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偏见所做出的修订。(4)第三条款针对挑战图书馆平等精神的社会现象,特别提出了“由道德、政治见解的志愿仲裁者或者将建立美国主义强制概念的组织所强烈要求和实施的图书审查制度,必然受到来自图书馆的挑战。”这是首次在《法案》 中明确提到“审查制度(censorship)”,表明图书馆反对审查制度的态度,也表明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坚持思想自由传播的立场。(5)新增第四条款,提出图书馆应该联合各种可能团结的力量,以抵抗外界对思想自由交流和表达的限制,强调图书馆应该捍卫自由的思想交流和充分的思想表达[17]。
1967 年《法案》的修订情况:首先,第二条款删除了1948 年版本提到的“拥有充分事实根据、高可信度的(sound factual authority)图书或者其他读物”这一表述,文字上更为简洁,避免出现因不必要的表述而引起的滥用。同时,将原来的“图书和其他读物(books and other reading matter)”更改为“图书和其他图书馆资料(books and other library materials)”,扩大了馆藏载体的范围,延伸至图书馆全部馆藏资料;其次,精简第四条款,扩大可合作对象,共同抵制任何限制思想自由传播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删除了第四条款中的“美国人的传统和传承”(the tradition and heritage of Americans),避免流露民族主义情绪;最后,第五条款新增了“年龄(Age)”“社会(Social)”两点,列入不得歧视的声明中[18]。
2.4 美国《图书馆权利法案》历次修订特点
(1)文字表述精简化。在针对收藏选择资源应平等公正的第二条款内容中,1939 年提出“应该公正而充分地选择各种体现不同观点的资料”。1944 年特别提出不可剔除“描述确切事实(factually correct)的图书”。1948 年采用“拥有充分事实根据、高可信度的(sound factual authority)的图书或其他读物”的表述。1967 年删除了这一描述,避免出现可能的滥用。这个修订过程一方面体现了ALA 能够及时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相应的政策规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用下定义的方式无法囊括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图书馆学家阿什海姆(Lester Asheim)针对选书原则,提出“在选书时,我们试着明确资料入藏的各种理由;但其实,在审查制度下,你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可以剔除它”[19]。文字的精简显示了《法案》修订的成熟。
(2)文字去情绪化。《法案》的卷首语修订了两次。1948 年的第一次修订,删除了“因为世界上许多地区逐渐偏执于限制自由言论,并以审查制度影响着少数族群和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权利”的表述,1980 年的第二次修订则明确“所有图书馆都是信息和思想的论坛”。此外,在第三条款针对审查制度的立场和态度上,1948 年增加了关于审查团体的描述,但在1967 年的修订中又删除了这些文字。这种处理避免了政策在文字表述上的情绪化。
(3)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社会上出现禁书风波的时候,《法案》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图书馆应持有的立场和观点。在面对关于个人平等使用图书馆的讨论时,1961 年新增了第五条款:“个人使用图书馆的权利,不得因为其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观点而遭拒绝或褫夺。”这一补充条款将图书馆服务对象扩大到所有人,包括了少数族群、残疾人和被监禁的人,种族、宗教、国籍或是政治观点都不应该成为个人使用图书馆的限制。1967 年在这一条款中新增了“年龄(Age)”“社会(Social)”两点。1996 年再次重申不可因年龄而令读者的图书馆使用权受到限制。可见随着未成年人使用图书馆的服务不断受到重视,《法案》也相应地做出了指引。
(4)《法案》 精神贯彻始终。虽然《法案》历经多次修改,但其平等、自由的精神始终如一:第一,平等、自由使用图书馆的权利。尽管社会上存在禁书风波等压力,ALA 还是坚持图书馆应平等、公正地选择馆藏资源,并呼吁图书馆应挑战任何审查的压力。第二,强调图书馆选择馆藏的主动性。始终重视图书馆应基于其服务的社区全体民众的兴趣、资讯需求和实现启迪教化的目的来进行馆藏选择。这是图书馆服务的职责所在。第三,随着平等观念的发展,不断扩大个人使用图书馆的平等权利。从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观点,至社会观点、出身、年龄等各方面坚持图书馆所应持有的平等原则和立场。
(5)《法案》的可扩容性。《法案》作为政策指引,确实无法包罗万有。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有细致而明确的操作指引解决在图书馆服务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法案》 的阐释、Q&A 等文件,在指导图书馆实际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最早于1951 年7 月颁布的《标注与等级划分系统》(Labeling and Rating Systems)[20],到最近于2010 年新增的《在狱人士的阅读权利》(Prisoners Right to Read)[21],IFC 至今已经颁布了22 条《法案》的阐释。这些阐释随着图书馆界新问题的出现,不断得到修订和补充。
3 结语
从《图书馆权利法案》的历次修订,可以看到美国图书馆协会对图书馆服务的平等、自由、公正、开放等原则不断重申和细化说明。其修订的次数越多,补充的解释文件越细致,说明美国图书馆政策正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随着《法案》历史演变的推进,每个时期都为下一次修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法案》也不断得到完善:从实践中形成指导理论,进而用理论解决现实出现的问题,再次为理论的修订积累素材。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促进了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成熟。
[1]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M]. 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229.
[2] John Kukla,ed.,The Bill of Right:A Lively Heritage[M]. Va. : Richmond,1987:6.
[3] Robert Allen Rutland. The Birth of the Bill of Rights:1776- 1791[M].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1:36.
[4] 张友伦. 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问题[J]. 历史研究,1996 (2):118- 132.
[5] 程焕文. 图书馆权利的来由[J]. 图书馆论坛,2009(6):30- 36.
[6] Louise S. Robbins, Rosalee McReynolds. The librarian spies:Philip and Mary Jane Keeney and Cold War espionage [M]. Westport,Connecticut: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09:4.
[7] Judith F. Krug, James A. Harvey. A history of 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s [J]. American Libraries, 1972(3):80.
[8] [9] Marci Lingo. Forbidden Fruit: the Banning of the Grapes of Wrath in the Kern County Free Library [J].Libraries& Culture,2003 (4):351- 377.
[10]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 Intellectual Freedom Committee (IFC) [EB/OL]. [2013- 09- 09]. http:/ /www. ala. org/ groups/ committees/ ala/ ala- if.
[11] Ruth E. Hammond , Donald Kenneth Campbell,Russell J. Schunk, et al. The Administration of Libraries[J]. ALA Bulletin,1945 (10):389- 394.
[12] Judith F. Krug, James A. Harvey. A History of 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s [J]. American Libraries, 1972(1):80- 82.
[13] David K. Berninghausen. Film Censorship [J]. ALA Bulletin,1950 (11):447- 448.
[14] News Roundup — 1951 Midwinter Meeting [J]. ALA Bulletin,1951 (3):93- 99.
[15] Ervin J. Gaines. Intellectural Freedom [J]. ALA Bulletin,1965 (9):785- 786.
[16] 程焕文. 图书馆权利的界定[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 (2):38- 45.
[17]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Library Bill of Rights [J].ALA Bulletin,1948 (7):285.
[18] Office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Intellectual Freedom Manual [M]. 2nd ed.Chicago: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1983:14.
[19] Beverly Goldberg,Judith F. Krug. On the line for the First Amendment [J]. American Libraries,1995 (8):774- 778.
[20] ALA Council,Labeling and Rating Systems [EB/OL].[2013- 09- 09]. http:/ /www.ala.org/ advocacy/ intfreedom/librarybill/ interpretations/ labelingrating.
[21] ALACouncil,PrisonersRight to Read [EB/OL]. [2013- 09- 09]. http:/ /www.ala.org/ advocacy/ intfreedom/librarybill/ interpretations/ prisonersrighto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