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
2014-02-12走走
走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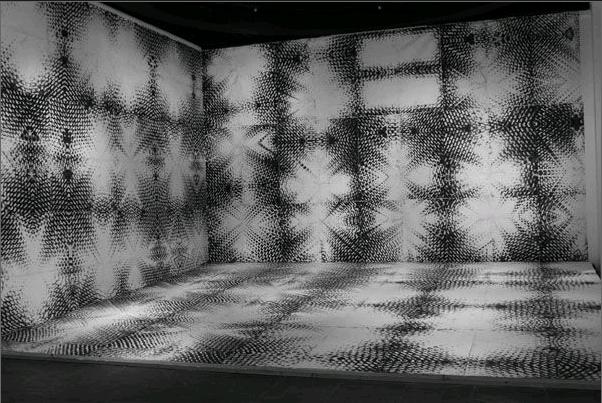
离开贡院西街后,她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早上去的时候,她坐的是公共汽车,那会儿她心里想着,那份半个世纪前的爱该有多浪漫。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东西了。要是她知道,这次出行将改变她的整个生活,她也许会立即跳下车的。
可那时,她根本就没想到该回家,她凝视着那些摇摇晃晃掠过的店铺,想着自己身上那种相信真爱的纯真也许将再次萌生,脸上就隐隐约约有了笑意。
现在,她只想快点到家,把窗帘都拉上,睡一觉。但那张脸,毫无笑意的脸,总是出现在她眼前,挥之不去。
她一进家门,就在傍晚的暗淡光线下看见了那幅全家福巨像。客厅中的两扇门打开,就是全家福。照片上那个唯一的男孩,此刻正在宽敞的屋子里来回踱步。他穿了件旧毛衣,脚踩在拖鞋里,手指间夹着根快烧完了的香烟。他一见到她,就像是见到面熟陌生的朋友似的,向前走了一步,却又迟迟疑疑地站住不动了。
在从窗户映进来的余晖下,他不断打量着她,她却看着巨像上那张毫无笑意的脸。
“那是一段很糟糕的日子,”他退到椅子边坐下,“所有老朋友都离开你,连见面能说个‘你好的朋友都找不着。你可能要去最偏远、最贫穷、最落后的小地方。那时候,你心里慢慢开始有了点怨气,很快你就知道,那是唯一的办法,根本就不允许有其他的办法,你知道你内心的黑暗开始造反了。你只是想抓住属于你的生活。真的,很多妻子带着孩子离开,所有人相互出卖,都只是为了这个。”
“那真的是一段很糟糕的日子,”他继续说下去,“混蛋们得势,而我们失宠。一切都从你手上夺走,你一下子掉进最黏最稠的那个泥潭。在那儿你是没法抗争的,你越用力,就会在那泥潭里陷得越深。”
但她记得的,只是他在八十年代写过的那些回忆性散文,那些文章让他们全家重新名声大振。他出版第一本散文专辑时她才二十三岁,正是黄金年代。虽然从全家福上,那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身上,她一点也没感觉到天生的著名作家气质,但她想,她一定会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的。她和他的血液里,都有来自一个著名作家的天分和勤奋啊。每次演出著名作家写的那些话剧时,她都是坐在第一排的观众。每次演出结束时,听着人们热烈的鼓掌声,她就会骄傲地抬起头,含着热泪望向舞台,那在黑暗中缓缓合拢的幕布。
三十多年来,他频频出现在电视或报纸上,最近则是网络上,回忆那位著名作家。他回忆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幸福生活,他公布了很多照片,他努力写文章,调入作家协会,他谈论自己的日常生活,对各种话题提出观点,想证明自己配得上做那个著名作家唯一的儿子。拍照时他拿着作家的文集某卷本,摆出各种姿势。他参加各种展览的开幕式,不太重要的文艺会议。只要有记者提问,他都愿意侃侃而谈,就作家的教育观、阅读观、写作观、爱国主义观等问题发表见解。
“就算那是一段很糟糕的日子,你也很快走出来了。”她低声咕哝了一句。
“那年你才三岁,我先是被停了职,整天无所事事地在单位里坐着,后来开始写检讨,写到麻木,写得胳膊和手,连动一动的念头都没有。每天早上起来,一点都不想把自己好好收拾干净。从上到下,一粒粒扣上那些扣子时,要用上全身的力气。大部分时候,我一天都不说一句话。”
“今天是他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第一天。我告诉过你我要去看看,你为什么不阻止我?在那里,看到那些材料,我惊呆了。我经历过的那些失败、背叛,在他的遭遇面前,显得多么不值一提。”
他低下头,不再看她。过了很久,他站起来,从桌上拿起烟,披上他挂在椅背上的夹克衫,“我们去那里转转吧。”
他们坐上出租车。车开了很久,才开到一个厂区前。她看着他靠近门卫,给门卫递了支烟,低声说了几句后转身向她招手。
厂区的南侧是地铁车辆段,北侧是刚刚修复的转河。空荡荡的厂区里,似乎只有他俩在走动。
“这里从前是片湖水,再往前,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荡。据说这片水域源自元朝,是什刹海在城墙外的一部分。五八年春天对这片芦苇荡进行改造时,我还在列宁格勒读书呢。唯一见过这片湖水的那一次,就是那年夏天的那个早上。要是没发生那事儿,这湖水,还真是美丽。”
“美丽的东西,不是应该带给人一种生活的乐趣、爱的愿望吗?”
他没有接她的话,他只是说,“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她真的闭上了眼,于是,呈∞字形的湖水在她眼前荡漾了起来。湖的东边是苗圃、花坛、游人长椅、码头。湖的西边是荷塘、稻田、灌木林。湖上架着一座三十米长的木拱桥。湖心是一座孤岛,岛上种着柳树。
“那年初夏,湖里先是出现了许多大红、墨黑的金鱼,然后是字画、瓷器、三枪牌自行车,再往后,就漂上来了一些死人。又过了两年,为了修建战备工程,这湖成了渣土填埋场。一车车土石滚进湖里,水泥构件朝天空竖着。再后来,湖被彻底填平,建成了地铁修理总厂。”
她睁开眼。远处,地铁车辆正从黑暗的地下驶出地面。
“他穿得干干净净,独自来到这里。这里是他觉得,这个城市最美的地方。他在湖边坐了整整一天,在树下,听着鸟雀鸣叫,几乎没动过。看到天开始擦黑,他会不会有些伤感?黄昏,总是会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忧伤。最后,夜深了,除了黑鸦鸦的柳树外,什么都看不清了,湖边什么人都没有了,他步入湖水自尽。作为一个著名作家,他死得体体面面,却没给你们留下任何字,你觉得是为什么?”
他摇摇头,抽出一支烟来点上,“我知道今天你看到的那些材料让你很悲伤,我那时候还年轻,我相信那样做,是为了未来,要是我知道……从那时开始,我的整个世界就塌了。”
“我是坐在一个角落里翻阅那些东西的,我好像本能地就看到了那些。”她没法告诉他,那些秀丽的书法字,对她有多大的触动。她也说不清楚,她一共读到过多少遍,那个签名。
“那份材料,一笔一划,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拿起笔来,就像个第一次做作业的小学生似的。我是在单位里写的,还没写完的时候,我感觉有人坐到了我面前,我抬起头,愣住了。他平静地看着我,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痛苦。那一瞬间,我的内心充满了犯罪感。‘爸爸,我轻轻喊道,‘我这就撕掉。但他突然在我眼前消失了,我不安地转头,门好好锁着,屋子里空无一人。过了很久,我才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上交了那份和他划清界限的材料以后,我双手捂住脸,哭了一会儿。但我是如此害怕,既没有哭出声来,也没有流下眼泪。”
他说完,看到她沉默不语,就盯着她的眼睛说道,“如果当年的那一切在今天重现,我真的希望,你也像我那么做。”
“爸爸,”她侧了侧身子,他的目光让她很不舒服,“我看到的,不是你说的那些。”
两人之间静了许久,就在这段沉寂里,她想到了那张沉静安详的脸,“和我说说奶奶和爷爷的故事吧,”见他一脸的诧异,她解释道,“我记得小时候,奶奶总是会长时间地看着爷爷的照片发呆。他们相爱吗?”最后那五个字,她像是在说悄悄话似的,把声音压得低低的。
“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母亲。一次我生病,她一边看着我掉泪,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她爱父亲,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很幸福。”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带着种安慰她的语气补充道,“她应该爱他的,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爱花,在你小时候住过的小院里种过一百多种花花草草,他走后,她一直把它们照顾得很好。她以前和我说过,她最喜欢那座小院了,对她来说,他在院子里浇花,小院的烟囱里往外冒着烟,那就是幸福。”
她听着,一些已经遗忘的图景浮现在脑海里。一个夏天的早晨,父亲似乎打算和奶奶一起出门去一个什么地方,最终父亲一个人走了,她还在他的身后跟了几步路。她长大了一点,一次一连吃了好几个柿子,之后肚子疼了好几天,因为她不知道不该喝凉白开。那座小院里有两棵柿子树,每年秋天,树上坠满沉甸甸的柿子,发出橙色的光,很是温馨。她的眼前满是那橙色的光,她甚至感受到了它散发出来的温暖,但光越来越强烈了,让她焦躁不安起来。这和她眼下面临的另一种痛苦的煎熬很相似。她想起来,从她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天起,她就很害怕这段感情,就是因为害怕失去时的这种痛苦。她已经害怕了二十年。今年,他们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儿子离家后,一天早晨,丈夫提出了离婚。
那时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进了卧室,先是躺到了床上,不过很快她又爬了起来,因为听到了丈夫锁门的声音。她起床的速度太快,导致了体位性低血压,眼前一片漆黑。她跌坐回床上等了一会儿,感觉到血液重新正常流动了,才走到窗边,开始向下张望起来。一辆黑色的奥迪A6驶来,停下,她看见丈夫上了车,车子并没有马上发动,也许丈夫也在隔着玻璃望着她吧。车终于动了,离开了她的视线。她的胃开始灼痛起来,痛一直扩散到了整个胸腔,让她难以呼吸。
此后的每一天晚上,她听着楼道里的声响归于寂静,想象着丈夫正在干什么。到后来,她痛得连想象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她站在窗后,把目光投向外面黑幽幽的车道,看看有没有什么奥迪A6停下。他不会回来了。她拉上窗帘,从窗户那儿一直退到床边,仰面倒了下去。她想自己这一生真是失败,她将作为一个不幸的女人,在孤独中死去。
有天晚上,她随手打开电视,竟然看见了丈夫被采访的镜头。身为大学校长,丈夫正侃侃而谈对创意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采访结束,她换一个台,主持人正在讲解一部俄罗斯电影全片开头的那个长镜头,“导演拍摄了一棵没有一片叶子的树,从清晨一直到太阳升起,预示着什么也不做苦苦等待,是没有春天的……”
她一度认为,这是上天给自己的一个暗示。但在最终寄出那些匿名信之前,她犹豫了。
她决定去一次东城区市档案馆。这一年,距她的爷爷,那位著名作家去世,四十六年;离她的奶奶去世,十一年。是个阴天,还刮着大风。她想这城市怎么像自己内心一样,那么阴,那么暗。她记得自己睁大眼睛,听着奶奶讲述她长长的逃难寻夫过程。那一年,她一个人雇了几个车夫,带了十件大行李,三个孩子,乘着夜色悄悄离开北平,先是坐火车到了安徽,又离开火车向西进入河南,夹在灾民队伍里一路向西,穿越整个河南省,走了五十多天,一直走到重庆,和丈夫团聚。每次听,她都会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似的对奶奶说道:“您太了不起了!”于是,老人的眼眶禁不住湿润起来,走到那幅全家福前,用手抚摸一下,那张毫无笑意的脸。
她想亲眼看看,那些家人口中,证明患难情缘的情书。既然它们能在几十年前,让一对男女彼此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许那些文字也会让自己重新充满爱的能量。
她一到那里,就贪婪地翻阅起来。她甚至看到了著名作家中学时代的习作,但她没找到她真正想看到的东西,她急了,她可是为了它们才来这里的。就在这时,她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字体。
如果这是一个长镜头,那么,镜头先是从很远的地方照出一条胡同,然后慢慢拉近,再往后就出现了一个三进小院,一进门是一座灰色砖影壁,接下来看到的就是第二道门了,一座五彩木影壁,镜头再近一些,是一个秀丽的“福”字。绕过木影壁,院子豁然眼前。(她在这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两棵大柿子树,从俯拍的这个角度看,它们尤其枝繁叶茂。院子里挂着刚洗完的衣服,屋檐,墙壁,慢慢看到了一间窗户。镜头从窗外慢慢拍到里面那些家具、摆设、书、画,以及坐在床前正写着什么的女人。镜头推到笔尖,她看清了女人笔下的字……
“我好像就站在那儿,站在她的身后。我看着她正在写字的手,就像是在看着我自己的手一样。”
那些类似日记一样的揭发信,完全可以充当著名作家的工作日志,比如今天写了多少字,写的是什么,给哪里写的,写给谁,见了多少客人,都有谁,说了些什么,等等等等。一日之内诸多事情,一、二、三、四、五,分头叙述,总到十以上。也有为其开脱辩解的,细心的人一定可以猜得出来,写下这些的女人,是个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
当她看到这些时,她哆嗦了起来。
“原来我的身体里有这样的基因,”她说道,“在她写下那些的时候,他在这里,一个人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天。”
“伤害了他,毁灭了他的,并不是我们,而是不幸本身。……那年头,我们大家都太害怕了。”
“在那个小院里,大家都选择忽视,他的孤独。”
“你以为她没有注意到吗?她早就知道,但她应该怎么做?她要是愿意,就不会把他们拆开了。在她辛苦持家,照顾他病重的母亲时,他却和另一个女人一起在另一个城市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惜的是,有五年时间,她一点儿也不知情。她还一直期待着他能来找她呢。后来告诉她的,是他的朋友,当然是出于好心。于是她带着我们上了路,但他还是不肯来见我们,他说自己病了,需要住在医院里,因为另一个女人也病了,他们就在医院里躲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另一个女人主动离开为止。此后,有一段时间,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他还犹豫过,要不要两人一起离开……他对很多朋友说起过,说人的一生只会有一个爱人……”
她听着听着,抱紧了自己的肩膀,头有点晕,但也许只是因为站立得太久了。她真想躺下来,蜷成一团。
一个男人,要是老想着另一个女人,在他写作时,看书时,坐在树下等待夜晚来临时,甚至在他和这一个女人说话时,那另一个,总是忽地出现在他眼前,会是怎样的感觉呢。而这一个,为了忘记这一切,每天准备着家里人要吃的饭菜,心不在焉地听着大家谈论文学,感叹世事……
现在,她能感觉到,身体里,那个不幸女人的存在。她避开他的目光,扭过头朝厂区出口望去,路灯已经亮了,但那些细细的弯着的杆子在她看来,像是一个个格外忧郁因此格外沉默的女人。
“我们都是可怜的人……”
“人是为了自己以为想要的东西而生活的,”他又点起一根烟,他长时间地轻轻按着她的肩膀,夜幕像罩子一样落下,两人衣角的轮廓也开始模糊起来。
“但是,相信我,父亲优秀的血脉每天都在我们身体里流动不息,”他用一种神秘的语气骄傲地对她说道,“别放在心上了。来,让我们回家,闭上眼睛,睡一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