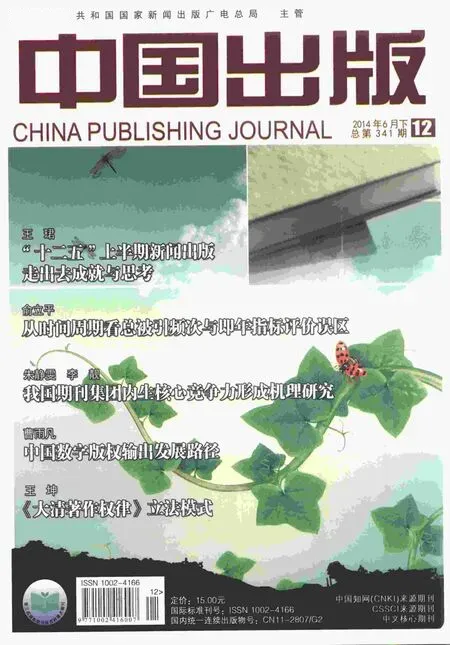鲁迅对俄苏文学作品译介成就概述*
2014-02-04武玉明廉亚健
文/武玉明 廉亚健
*本文系2013年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课题项目阶段性成果(J13SY70),2013年度山东省社科联项目阶段性成果(13-ZC-WH-14)
鲁迅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字数都接近300万,数量相当。冯雪峰评价说“鲁迅的工作时间,以他一生中用在著作方面的时间来说,一半以上用于介绍外国文学和学术性的著作上,其余一半用于创作上。”[1]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与他在文学翻译上的丰硕成果密不可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鲁迅一生中翻译最多的是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字数大约142万字,占据全部译作的近2/3。他翻译过的99位外国作家作品中,俄苏作家共有37位。在他的著作和翻译作品中所涉及的377位外国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中,俄苏就占101位。由此可见俄苏文学在鲁迅翻译事业中所占的分量。
一、鲁迅青睐俄苏文学的缘由和译介目的
关于鲁迅与俄苏文学的渊源,罗果夫说过:“从一九零七年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为止,这位现代中国的伟大作家,对于研究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兴趣,是一天一天的增加的。”[2]鲁迅对俄国文化和文学的评价一直很高:“我觉得俄国文化比其他外洋文化都要丰富”,“中俄两国间好像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经验好像有一种共同的关系”,“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外国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3]
鲁迅对俄苏文学的情有独钟,是由于当时中国和俄国的社会状况有相似之处,而且中国民众和俄国民众一样,都有“国民的劣根性”,俄国的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深刻解剖、讽刺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兴趣。另外,俄国文学反映的黑暗现实贴近中国现实,“从类似的俄国的人民的生存境遇中看到世界上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明白了这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4]俄罗斯文学的同情弱者、反抗强者的人道主义使鲁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说过,“与其看薄伽丘、雨果的书,不如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们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5]鲁迅对俄国文学和作家感到格外亲近,并把俄国文学看作导师和朋友。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始终关注人生,显示出“为人生”的鲜明特点,鲁迅的文学主张也是为人生的艺术,两者不谋而合。而俄国文学自普希金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与鲁迅倡导新文学反映现实、揭露黑暗的要求相契合。因此鲁迅特别推崇高尔基、果戈理、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钦佩他们揭露国民丑陋性的勇气,并且呕心沥血地将他们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以此达到改造国民性、改良人生、改造社会的大目的。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正值国民革命战争时期,苏联文学反映人民的被压迫和反抗的斗争,给正在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奋勇向前的力量。鲁迅认为苏联文学表现出“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希望通过苏联文学的译介为革命者运送思想的“军火”,以振奋民众的精神。
二、鲁迅对俄苏文学的译介阶段及特点
在从事俄苏文学译介的众多翻译家中,鲁迅是最热忱、最执著、也是最艰苦的译者。根据历史的维度,鲁迅对俄苏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07~1917) 晚清及民国初期
1907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开手的第一篇文学论文就是《摩罗诗力说》,介绍了世界各国著名的反抗诗人,重点介绍了摩罗宗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等人,表现了他们争天抗俗、反封建反侵略的勇气和斗志。鲁迅十分推崇和敬仰这种摩罗精神,就像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一样,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运输了精神食粮,鼓舞了革命者的士气。
鲁迅对外国文学的译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目的是通过介绍和翻译外国作品,来启蒙国民意识、改进国民精神,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寻找出路。1907~1908年他与周作人开始合作翻译域外小说,希望“别求新生于异邦”。他在小说的序言中第一次阐明了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的主旨和意义:翻译外国作品的动机是以文学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翻译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这些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唤醒国民的精神,振奋民众的革命热情,促使国民进步。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和迎尔询的短篇小说都收录进了《域外小说集》,因为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残忍、黑暗、哭诉、寻找……他后来的小说写作,大多还是受了俄国人的影响,安德烈夫、伽尔询、阿尔志跋绥夫都使他产生感动”。[6]尽管《域外小说集》当时只卖出去20多本,但它的问世却为被压迫民族作家作品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从此,鲁迅与俄国文学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果戈理、高尔基等一大批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通过鲁迅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俄国文学在中国文坛盛行一时,产生了深远影响。
2.第二阶段(1919~1926)五四运动及20年代
伴随着磅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俄罗斯文学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中国传播开来。充满人文情怀和社会变革思索的俄国文学,呼应当时中国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探寻中国出路的精神需求。鲁迅把翻译作为救世的精神武器,以启蒙国民精神、唤醒国人奋进。
1921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绥惠略夫是个孤独的社会反抗者,他热爱民众,想要拯救他们,却不被群众所理解,愤而走向极端,仇视群众,向他们开枪。鲁迅选择这部作品翻译,一是他喜欢作家的现实主义风格,二是对于孤独的革命者不被群众理解的悲剧非常感慨。之后又翻译了他的三篇作品:短篇小说《幸福》《医生》和散文《巴什更之死》。鲁迅是第一个将阿尔志跋绥夫作品介绍到中国的人,阿尔志跋绥夫也是鲁迅翻译作品数量最多、评价频率最高的俄国作家。原因是他作品的内容符合鲁迅的“口味”,而且两人的文风和个性有相近之处,都爱憎分明、敢说敢做,两人的语言都很冷峻、入木三分。
鲁迅的翻译题材众多,除了小说、散文、戏剧、杂文,还有童话等。1926年他翻译了他喜爱的俄国盲人诗人爱罗先坷的童话作品《桃色的云》和《爱罗先坷童话集》,爱罗先坷并不是世界上知名的诗人,在1921年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之后,才引起鲁迅关注。由于爱罗先坷的童话表现出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因此,鲁迅热情地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希望读者能从他的童话中看到童心的美,把梦幻变成现实。
3.第三阶段(1927~1936)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极大关注,“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呼声日益升高。鲁迅认为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里,具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因此大量把苏维埃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他称自己翻译的文艺著作和文学作品都是“战斗的作品”,把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这些文学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向前的精神,引领大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鲁迅翻译了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主要描写俄国在十月革命大风暴中,人们对革命泾渭分明的态度。鲁迅曾高度评价说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描写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并称之为“新文学的大炬火”“一部纪念碑的小说”。该书描写了1919年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在远东南乌苏里边区,由主人公莱奋生领导的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浴血奋战,最后只剩19人,仍然坚持突围的故事。这部富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著作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斗志,同时也给当时中国的革命作家深刻的启示。1930年《毁灭》的译介是鲁迅为奋进中的革命者偷运思想的“军火”的最好佐证。
1931年鲁迅编订了《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和下册,名为《竖琴》和《一天的工作》。1935年他翻译了苏联小说家勒·班台莱耶夫的儿童小说《表》,该书讲述了一个有劣迹的流浪儿在教养院里成长为一个爱学习和劳动的好孩子,最后归还自己偷的金表的故事,反映了社会环境和劳动对人的精神境界的影响。鲁迅的译本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重印次数最多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之一。
在俄苏作家中,鲁迅很推崇高尔基。1934~1935年他翻译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书中的16个故事揭示了俄罗斯国民的丑陋性。鲁迅评价高尔基“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与病情。”契诃夫是鲁迅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收录了《假病人》《暴躁人》等八个短篇,既诙谐幽默,又具有讽刺性,让人笑过后感到沉重和悲哀,鲁迅用“含泪的微笑”形容这种讽刺文学,翻译时准确、深刻地体现了喜剧性和悲剧性融于一体的“契诃夫式的幽默”。
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被鲁迅称为“俄国写实派的开山主师”。他的长篇代表作《死魂灵》对鲁迅影响最大。《死魂灵》是一部史诗般的鸿篇巨制,描写了俄罗斯民众的苦难,大胆揭露了国民丑陋的本质。1935~1936年鲁迅耗尽心血,坚持带病翻译这部巨著,可惜没译完就去世了。《死魂灵》是鲁迅用生命完成的代表其最高成就的译作,堪称其翻译生涯的绝唱。
另外,鲁迅在介绍俄国文艺作品的同时,还注重俄国文艺理论的研究,他认识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指导革命文学的重要意义,于是1929年之后他陆续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及《文艺与批评》等俄苏文艺理论著作,促进了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鲁迅还翻译了苏联的文艺政策,如《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关于文艺领域上党的政策》等。鲁迅通过把这些国外的先进理论输入国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
三、结语
“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始于翻译,也是以翻译告终的”。[7]鲁迅从1907年开始写《摩罗诗力说》起,一直到1936年逝世前翻译《死魂灵》为止,30余年他不遗余力地译介俄苏文学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俄文学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俄苏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值得后人敬仰和深入研究。
[1]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43
[2]罗果夫编.鲁迅论俄罗斯文学[M].时代出版社,1949:25
[3]张梦阳.鲁迅与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史概述//社科院编《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22
[4][5][6]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366,452,114
[7]戈宝权.鲁迅——杰出的翻译家[J].翻译通讯,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