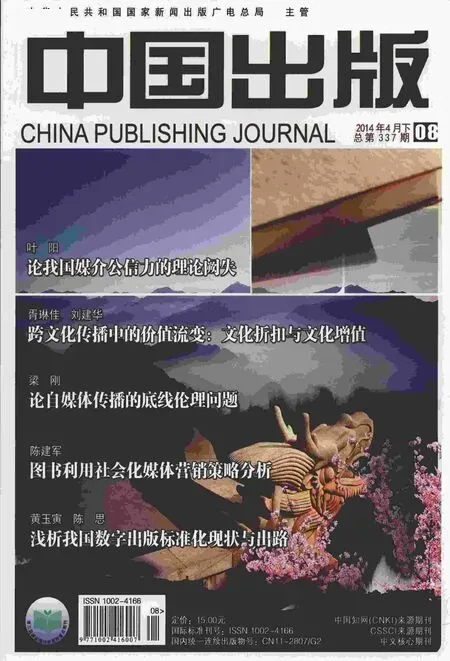论自媒体传播的底线伦理问题*
2014-02-04文/梁刚
文/梁 刚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网络文化背景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创新研究”(12YJC710037)、北邮社科基金项目[2012BS06]及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成果。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提出媒介“三分法”: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简单说来,互联网诞生前的一切媒介都是旧媒介;新媒介指互联网上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代媒介;新新媒介则指滥觞于20世纪末、兴盛于21世纪的互联网上第二代媒介。近年来以博客、微博等为典型代表的自媒体无疑属于莱文森所说的新新媒介,其巨大影响力和传播力冲击并改变了既有媒介格局,渐成新兴舆论场域。与此同时,自媒体伦理失范现象频发,甚至跌穿社会公序良俗底线。因此,维护自媒体良性和谐传播秩序,探讨自媒体传播的底线伦理问题,具有现实紧迫性。
一、两个重要概念的界定
一是自媒体。美国著名硅谷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在《自媒体: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一书中提出并阐明自媒体概念,认为“20世纪的大众媒体结构,转变成某种更有草根意味和深化民主的东西。……通讯网络本身就是人人发声的媒体”。自媒体,有学者译为草根媒体,这不无不可,但更确切的理解可能是Web2.0时代的新兴公民媒体。在丹·吉尔默看来,“我们不能再将新闻视为由大型组织机构控制的商品。身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不能再忍受有限的选择。”非职业新闻传播者的兴起,有助于让沉默的大众发出声音,从而激发了“真正资讯充足的公民观念的复兴”。[1]这就是说,自媒体打通了公共传播与私人传播、专业领域与业余领域之间的鸿沟。它所催生的传播革命“已经普遍地将‘权力’从媒体转移到了受众。在这个层面上受众有了更多的媒介选择,而且能够更主动地使用媒介。”[2]如果说与传统大众媒介相对应的是原子化的中心控制性大众社会,那么与自媒体对应的则是开放性和多元化的公民社会。从信息传播模式上说,信息交流实现从居高临下的训示到交谈与协商模式重新定向。不妨这样说,Web2.0时代的自媒体传播标志着互联网理念的一次升级换代,从原来的自上而下、由少数资源控制者主导的互联网体系,转变为由广大公民用户集体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
二是底线伦理。“底线伦理”是上世纪90年代由著名学者何怀宏提出、阐发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伦理学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圣贤伦理或高蹈道德,底线伦理强调的是基准道德水平。用何怀宏的话说,“底线伦理即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雨果说,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为人的常轨……你可以做不到舍己为人,但你不能损人利己;你可以不是圣贤,但你应该认同道义和人道。你攀升不到道德最高境界, 但道德最低下限必须坚守,那是人类最后屏障!”[3]显然,底线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和很大程度的重合,但是底线伦理还包含制度伦理或制度正义的特殊内涵。也就是说,底线伦理不仅涉及个人道德义务问题,而且涉及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其实,底线伦理正是以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选择为尺度的。规则面前没有例外,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底线伦理是一种属于公民社会的温和的道德义务论。底线伦理一方面告别高调的“君子国”式的道德乌托邦,另一方面也坚决拒斥一切“逃票者”或特殊公民。
二、自媒体传播底线伦理的核心价值
底线伦理把道德裁决的能力赋予给每个个体公民,对每一个公民充分信任,公民既有主张个人权利、实现自我利益的充分自由,也有服从社会良俗、履行公共责任的基本义务。正如梁启超所言:“义务与权利对待者,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4]自由(权利)和责任(义务)构成自媒体传播底线伦理的核心价值。
1.自由
自由具有复意性。一个基本意思相当于英文中的Freedom,它指的是一种自由的状态, 即摆脱某种羁绊或束缚后所获得的自由解放状态;另一个基本意思则相当于英文中Liberty,是可度量的作为权利表达或呈现的自由,因而也是能够明确界定的。新世纪以来勃兴的自媒体无疑极大解放了民众的传播理念、传播方式和传播行为。丹·吉尔默不无兴奋地指出:“新闻由普通民众生产出来,他们想发言、想自我表现;新闻不再只由‘正式’的新闻机构提供——传统上,新闻机构才是决定历史最初面貌的发言人。这一次,为历史添上新色彩的执笔人,却有部分是传统的阅听大众。这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互联网上有新兴的出版工具。……我们见证了新闻的未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未来新闻的一部分。”自媒体的高度开放性、透明性和可分享性,决定了它作为最新中介,已当之无愧成为社会信息的公布栏和社会意愿的发声筒,成为个体吸纳与整合社会能量的接收器,同时也是个体能量放大为社会能量的转换器。这样就带来一个颇为严峻的问题。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作为主体,同时也相互作为对象” 的世界,没有一个人能使自己永远处在主体的位置。那么,如何处理个体非职业自媒体传播者之间可能的“自由”的冲撞呢?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坚定捍卫者,但同时他又主张对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在罗尔斯看来,不加限制的自由是必然要发生冲突的。他由此提出:第一,对自由的限制的标准要用平等补充自由,即自由是平等的自由,人人都有自由的权利;第二,对自由进行限制的最终目的只能是维护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说,对自由的限制,就是使自由变得平等。在自媒体传播活动中,把关者和审核人是缺失的环节,从而带来极强的用户自我赋权功能,给予公众参与者空前的传播自由。有学者谓之当代媒介的“民众化转向”。立足于自媒体传播的底线伦理和媒介良序运行,应当更加强调这种具有明确边界的权利意义上“平等的自由”,而不是一味肯定作为“革命”或“解放”意义上的抽象自由。
2.责任
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规范理论早就指出,大众传媒应该是自由却又自我约束的。这一点显然也应同样适用于新兴的自媒体。微博等自媒体必须承担公共责任、履行公共义务。每当微博“大V”们发布一条微博,便会有大量受众阅听,加上网友的互相转发,微博“大V”在无形中已成为社会舆论的发动机。据统计,目前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中,10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1.9万个,百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3300个,千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200个。一些微博大V倾向于认为,在以商业运作为基础的现代媒介中,公共利益是什么和什么能吸引公众眼球是合二为一的东西,这是有失偏颇和危险的。事实上,“表达自由一直包括抑制表达的自由”,“没有公认的道德义务就没有精神权利。如果发布者是一个撒谎者或是一个激起仇恨和猜疑的不诚实的煽风点火者,那么他的要求就是没有基础的。……他已经利用他的自由来破坏他的自由。”[5]这就是说,表达自由必须融入责任义务要素,两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基于微博特别是名人微博的传播具有马太效应的影响力,微博主们应当时时提醒自己恪守底线责任伦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深刻提出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区分。简单地说,意图伦理以意图的好坏作为善恶的标准,只要动机是好的,即使办了坏事也是可以原谅的;责任伦理则注重效果,认为只讲意图而不顾效果是不负责任的。比较而言,现代社会伦理更加倾向于责任伦理,即不能因为行为的良善初衷而免除道德和法律责任。有学者明确认为,“网络伦理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是很有见地的。[6]在此意义上,拥有千万粉丝的姚晨所发一则微博就很值得称道:“昨儿愤慨之下,差点转发救小悦悦的陈贤妹被辞退的新闻,但脑子里瞬间闪念:消息来源准确吗?观望一下再发不迟。果然,今日又看见澄清的新闻,陈大姐没被辞退、也没被房东赶走。感慨之余庆幸:第一,不管怎样,好人没遭恶报,这再好不过。第二,这仨月饰演记者,俺都锻炼成记者思维了,入戏啊! (2011-12-27 09:51)”姚晨的“愤慨”和“差点转发”是出于道德义愤,所幸未被“意图伦理”谬误绑架,而是三思后行的“记者思维”即“责任伦理”思维占了上风。在Web2.0时代“病毒式”信息扩散活动中,社会舆论风险系数倍增,亟待提升并强化全体传播活动参与者的责任意识,把传播自由与公共责任的匹配和对应,置放在自媒体底线伦理价值结构的中心性位置。
三、坚守自媒体传播的底线道德原则
底线道德原则,是指构成一种伦理规范体系中最具普遍性和共识意味的基本准则。在道德实践中,它作为道德判断的根本依据、道德选择和评价的最后标准起作用。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拟的,都需要一种基本的道德共识才能维系和良性发展。在自媒体传播过程中,每个人兼任信息的提供者、使用者和消费者,既是用户又是把关人。每一主体都处于与自我、他人、群体的复杂关系之中。借鉴罗尔斯“重叠的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观点,从平台管理者、运行者到亿万普通用户都应共同遵循并维护以下底线道德准则。
1.诚信原则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伦理思想把诚信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以至于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无信。“民无信不立”的格言尤其体现了诚信道德的精神基石意义。在自媒体传播模式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在整个传播活动中扮演基础性底层结构角色,信息沿着社会关系网络流动,而相互信任正是人际关系系统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要素。例如,微博传播就是一种基于“关注”和“被关注”的信任链,高度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才能完成。
在网络媒介进入Web2.0时代的背景下,丹·吉尔默指出:“媒体集团享有高额毛利。有太多例子显示出,严肃的新闻以及公众信赖感都陆续被牺牲。这些让新闻业出现破洞,而新兴的记者正在填补这个缺口,尤其是平民记者。”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公民记者或草根发布者的出现并不会自动兑现信息真实性的新闻伦理准则,恰恰相反,网络流言或虚假信息等不时搅动起舆论漩涡,极大挫伤了自媒体传播的公信力。因此,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诚信原则不仅是一种个人美德伦理,更是一种社会规范伦理;既要充分重视诚信作为个人人格美德的内在自律力量,更要注重有效建立诚信作为社会公共伦理底线的外在普遍性约束机制。事实上,现代信用伦理对个人人格信用的要求更多地诉诸社会组织化、制度化的制约上。新浪微博平台构建的用户信用积分机制就颇具可操作性。每个微博主的初始信用积分均为80分,上限为100分;按照分数高低,微博用户信用分将分成4个等级,超过90分为高信用,60分以下为低信用。如果账号存在违规行为,将被扣除一定的信用积分;信用积分低于60分,用户的相关页面将显示“低信用”图标,积分为零则将被删除账号。在普遍推广这一做法基础上,各网站还可考虑设立统一数据格式、可信息共享的“谣言粉碎机”和“钓鱼网站曝光台”等。当各方面条件成熟时,还可进而打造全国性网站辟谣联盟,让诚信成为传播者进入自媒体空间的“通行证”。
2.无害原则
从比较伦理学角度来看,从来没有这样的社会:它的道德准则不包含不伤害他人的禁令。这里所说的无害或不伤害原则,就是指作为一种独立个体的人之间的互不侵犯、互不侵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英国哲学家密尔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由有权利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御。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之所以能够使用一种权力反对其意志又不失为正当,唯一目的只能是防止伤害到他人”,因为安全是人类最强烈的需要,“所有人都把它看做是一切利益中最重要的方面,缺少了它,没有人能够生存”。[7]就自媒体伦理问题来讲,无害原则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自媒体传播是一种基于社交关系的大众传播。一条信息经过意见领袖的转发、评论,会立即形成信息传播的爆发式增长点,出现“几何级放大效应”。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阳教授曾用软件对250个大V的微博进行分析——选择了四个常用骂人词语,最终搜索出脏话微博6246条,脏话率大于千分之三点八,明显高于一般网友。[8]语言污染继而导致话语暴力乃至现实肢体冲突,催生了网络骂战,“大V约架”等公共事件。
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网络人肉搜索触碰公民合法权益底线,尤其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底线的社会伦理风险及其危害。在这方面,“丁锦昊事件”可谓一起典型案例。2013年5月24日,网友@空游无依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条关于埃及3500年前文物被中国游客刻上“丁锦昊到此一游”的微博。该条微博随即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被迅速转发超过8万次,评论近2万条。接下来,该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网友@蜡笔小球“人肉”出肇事者可能是曾就读于南京某小学13岁中学生丁锦昊;25日,丁锦昊母亲出面道歉;26日,丁锦昊曾就读的南京某小学网站被黑。数千年前的文物被涂鸦固然令人痛惜,但接下来成人自媒体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更值得反思。例如有网友痛骂其素质低劣,“给祖国丢脸”,甚至声称要“清除民族败类”。对海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公开讨论或谴责无可厚非,但这种过于激烈的言辞很容易在让人获得某种道德优越感的同时对当事人造成精神创伤和权利伤害。事实上,如果一定要有人对此事件负责的话,首先是丁锦昊的监护人即父母;其次,当时的陪同导游因未尽劝止义务亦难辞其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这场关于中国人海外旅行不文明行为的网络讨论显然不应造成对一个年仅13岁少年名誉权和隐私权的双重侵害。所有自媒体传播者必须明确认识到: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换言之,法律构成底线伦理的底线。
3.公正原则
这里所说的公正原则,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在某些制度中,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人之间做出任何任意的区分时,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9]也就是说,每一具备公民资格的个体都没有等级贵贱之别,都享受完备性的道德主体身份。“每个人都被看做一个,而不是更多”,用社会制度的眼光来看,没有哪一个人比别人享有更多的分量。
公正原则就是要求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成员,没有歧视,也没有偏爱。对于自媒体传播而言,这也就意味着微博大V和网络名人必须同样接受社会传播制度及基本伦理规范的约束,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网络共同体中的特殊成员。有学者敏锐发现:“微博上意见领袖与公众间的来往是双向的、直接的,而这种双向的互动又是不平等的。以某些意见领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个“意见部落”,真的能实现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对话吗?显然是不能的。”[10]这一对于微博舆论领袖教主化、民粹化倾向的担心绝非杞人之忧,而是客观看到“围观就是力量”的正反两面,提请关注网络自媒体社会动员的负面效应。越是“音量大”的网络名人,越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这也是社会公正伦理提出的起码传播规范和道德要求。
公正原则作为一种社会德性,它还要求公平地分配权益和义务,把个人应享有的和应承担的分配给个人,使人人各得其所。在这个意义上,“正义就是均衡、相称,也就是有原则或者有法律、持之以贯,而不是随意安排”。[11]对于自媒体传播秩序的治理而言,相关管理机构和司法部门也应遵循行政伦理和法治伦理,严格依据传播逾矩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损害程度来定责处罚,坚决杜绝执法偏差。凡不是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以春风化雨的批评教育为主;误传谣言造成一定不良后果的,公开道歉并删帖;在传播活动中明显损害他人名誉权的,承担民事责任;对已被证明是虚假信息的仍反复传播、炒作甚至加工、夸大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无疑是公正原则“纠正”的正义或“矫正”的正义的具体体现。
[1]Dan Gillmor.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Reilly Media, Inc, 2006
[2]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3]肖英.生命的原则——访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N].中国青年报,1998-12-09
[4]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5]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刘大椿等.网络伦理的若干视点[J].教学与研究,2003(7)
[7]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8]范承刚等.大V近黄昏?[N].南方周末,2013-9-12
[9]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0]许纪霖.微博、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的转移 [N].组织人事报,2011-4-28 .
[11]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