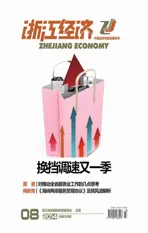为实实在在的努力“点赞”
——记Y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
2014-02-04刘亭
刘亭
城中村最大的问题,是国有和集体两种公有制产权的落差。问题倒逼政府变革:对模糊的集体产权进行彻底私有化,拿土地城市化的级差地租增值收益对农民的私有产权进行国有化“赎买”
笔者有幸,应邀参与了一个咨询团队的实地调研,主题是关于城中村改造和相应新社区建设的。去看的Y市的做法,总称谓之“城乡新社区建设”,其实质是政府在切合城乡发展实际的基础之上,“按照价值置换方式,实行多村集中联建,采用高层公寓加产业用房、商业用房、商务楼宇、货币等多种形式置换,推动农村向社区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地方上的同志要听我们“远来的和尚”念经,我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大致讲了三条不成熟的意见:
第一,这是一次触及实质的产权制度变革。城中村最大的问题,是国有和集体两种公有制产权的落差。当然,这集体产权,也不过就是一种不上不下、不伦不类的私有产权罢了——说实在的,又有哪个农民个体,会把自己承包和居住的农村土地视为公有财产(说共有财产起码还准确一些)?城中村的前身,是地地道道的农村。然而,在城市“怪兽”的疯狂扩张和政府的征地拆迁之下,耕作的农地或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都是些矮小破旧的农舍或“空间换地”的“碉楼”,在那里固守着姓“集”的宅基地在苟延残喘,成为城市的“贫民窟”和“烂疮疤”。先头城市政府还可以花钱征迁,但精明狡黠的农民和急于求成的官员博弈,总是官员们败下阵来,这也预示着招数的边际效益递减和政府的“黔驴技穷”。正是问题的倒逼,终于使政府想到了彻底的变革——对模糊的集体产权进行彻底的私有化(量化到个人),然后拿土地城市化的级差地租增值收益,对农民的私有产权进行国有化的“赎买”(置换为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国有土地70年使用权)。至于农民其他的和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也通过将集体经济改组为产权明晰的股份合作经济,股权从此与农民的身份和户籍脱钩,由此全面完成了土地的“变性”和人口的“改户”。
第二,这是一场农民自愿参与的社会变迁。城市化说到底,并非只是一场以财富增值为指向的纯经济的建设活动。其本源的涵义,更倾向于是一场以素质提升为目标的人口社会变迁。亿万以农为生的社会群体,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并主动改变自己的就业和工作方式的同时,在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上,也彻底融入了现代的城市文明。总书记在多次场合说过,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这句话恰当地批评了某些地方“造城运动”的拔苗助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的恰恰是一个脱节于工业化并被人为严重阻滞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理解总书记讲话的精髓,恐怕更要着眼于对过往那些早该城市化的人口进行“补课”,助其顺畅地实现城市化,而不是倒行逆施,继续让他们固化在“非驴非马、亦城亦乡”的所谓“农村土地”之上。农民为什么会“自愿”,因为他们认同了参与城市化的损益补偿。Y市经过周密调查和严格测算,开出来的价码是1∶5,即“以合法住宅建筑占地面积为基数(每户最高不超过140平方米),按1∶5确定置换权益面积,其中3/5为高层公寓面积(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下同),2/5为产业用房面积(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下同)。”加上彻底市民化后其他配套的房产入市交易、过渡安置补助和参与者奖励、城镇居民社保和股份合作资产权益政策“同步落地”,那他们的自愿,自然会是由衷的。由此,城中村改造这一继计划生育之后新凸显的“天大难事”,也就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了。
第三,这是一步落实三中全会全深改《决定》的实际行动。记得《决定》出来之前,社会普遍担心有何“干货”和“实货”。全文一发,此派言论一概噤声,转而变为质疑究竟有几个百分点的落实。总书记虽大声疾呼“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并重申顶层设计和实践创新一个不可或缺,但囿于既得利益和探索风险,还是有很多地方和官员会选择“唯上唯书”的明哲保身。在改革无需大话、只求担当的时刻,我们亲眼见到了这样坚定而清醒的践行,实在是感慨万千:“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列宁同志说得多么好啊!在决定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这一轮全深改中,不正需要这样“真的猛士”“铁肩担道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