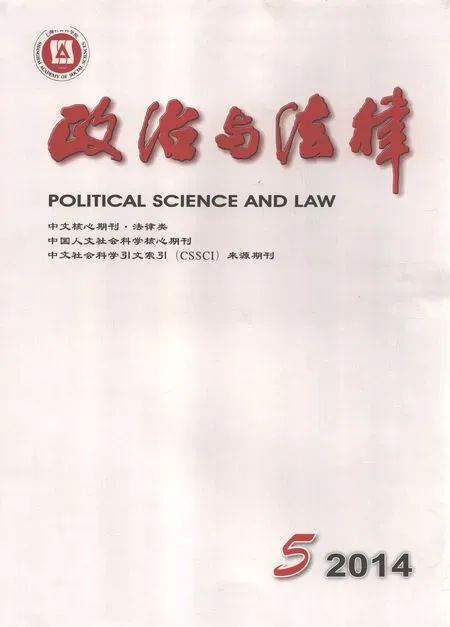过失犯的危险犯:以中德立法比较为视角
2014-02-03陈兴良
陈兴良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过失犯的危险犯:以中德立法比较为视角
陈兴良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过失犯的危险犯是过失论中较少涉及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较为疑难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过失犯的危险犯的存立有着较大的分歧。德国刑法中,存在着过失犯的危险犯的立法例,对比中德刑法的规定,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过失犯的危险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过失犯的危险犯应当具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且以故意犯的危险犯为立法前提,因此,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过失犯的危险犯。这种立法状况,和我国所特有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二元处罚体制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为了给行政处罚预留空间,我国刑法将那些发生了法益侵害结果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才规定为犯罪,对于那些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或者情节较轻的行为一般都予以行政处罚,在这种情况下,过失危险行为一般都只是行政处罚的对象,而不能进入刑事立法的视野。
过失犯的危险犯;过失犯的具体危险犯;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
过失犯的危险犯这一概念,是两种犯罪分类相交的产物。一种犯罪分类是以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为标准的分类:故意犯与过失犯。另外一种犯罪分类是以是否发生法益侵害的实际结果为标准的分类:实害犯与危险犯。以上两种分类形成的组合,就产生了以下四个概念:故意犯的实害犯与过失犯的实害犯、故意犯的危险犯与过失犯的危险犯。在刑法理论上,故意犯的实害犯与故意犯的危险犯这两个概念并不存在争议。而过失犯的实害犯这个概念则需要进一步厘清:过失犯的实害犯也就是过失犯的结果犯。对于过失犯来说,并不处罚未遂,都是在发生了实害结果以后才受刑事处罚。因此,过失犯的实害犯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过失犯在没有发生实害结果的情况下,当然不能按照未遂处罚;那么,是否可以按照危险犯进行处罚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中外刑法理论上都存在争议。在我国,随着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对于醉酒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展开了讨论,这一讨论直接涉及过失犯的危险犯问题。尤其是在我国风险刑法理论的语境中,更是为过失犯的危险犯提供了知识背景。为此,有必要对过失犯的危险犯进行深入研究,以此提升刑法教义学的水平。
一、《德国刑法典》过失危险犯规定的探析
过失犯的危险犯,又称为过失危险犯,是一个与故意犯的危险犯或者故意危险犯相对应的概念。例如我国学者认为,故意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故意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既遂标志的犯罪。而过失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过失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①参见舒洪水:《危险犯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第74页。在此,论者所定义的过失危险犯是一种危险状态犯,即所谓过失犯的具体危险犯,似乎并未包括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那么,是否存在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德国刑法理论上,是肯定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的,而且在《德国刑法典》中也有关于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规定。罗克辛教授指出:“当人们使抽象危险性犯罪的刑事可罚性取决于上面提到的‘没有结果的过失’时,这个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根据现行法律实现了。”②[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下文笔者还将论及《德国刑法典》中关于过失犯的危险犯的具体规定,可以印证罗克辛教授的论述。因此,合乎逻辑地说,过失犯的危险犯既包括过失犯的具体危险犯,又包括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过失犯的具体危险犯是指以造成一定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过失犯。而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是指以实施一定的危险行为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过失犯。如果说,过失犯的具体危险犯是一种结果危险还属于客体危险,那么,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就是一种行为危险。对此,有德国学者论及过失犯的危险犯中的双重的危险概念时指出:“对过失危险犯的理解必须制定双重的危险概念而变得更加困难。一方面违反注意义务要求,根据有观察力的观察者的判断,行为对受保护的法益带来了危险,另一方面犯罪结果恰恰在于特定的行为客体因违反注意义务而受到危害。这两个危险概念的区别在于,行为的危险性是根据是否会影响受保护的法益而抽象地加以评判的,而行为客体的危险是以是否属于危险行为的有效范围而具体地加以认定的。”③[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00页。因此,在过失危险犯的情况下,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之间是存在明显区分的,一如故意犯的危险犯。
过失犯的危险犯是与过失犯的结果犯相对应的,因此,上述犯罪分类是从结果犯与危险犯的分类中引申出来的一对范畴。德国学者罗克辛将犯罪分为两类:侵害性犯罪和危险性犯罪。这里的侵害性犯罪就是结果犯或者实害犯,而这里的危险性犯罪就是危险犯或者行为犯。罗克辛教授指出:“根据行为构成的行为客体是受到损害或者说在整体上有危险,人们可以在侵害性犯罪和危险性犯罪之间做出区分。大多数行为构成都是侵害性犯罪。在这种犯罪中,行为的客体在构成行为既遂地存在时就必须真实地受到损害,例如,杀人犯罪(第211条以下),身体伤害犯罪(第223条以下),毁坏财产犯罪(第303条),等等。相反,危险性犯罪仅仅表现为一种或轻或重的对行为客体的强烈威胁。在这里,最重要的区别是具体的和抽象的危险性犯罪的区别。”④同前注②,克劳斯·罗克辛书,第221-222页。在刑法典所规定的犯罪中,绝大多数犯罪都是所谓侵害性的犯罪,包括结果犯或者实害犯。此类犯罪,其构成要件要素是齐全的,包括了行为、客体、结果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侵害性犯罪的情况下,存在着实际的法益侵害结果,在构成要件上采取的是结果性的归责。因此,侵害性犯罪是一种典型的犯罪形态。与之不同,危险性犯罪并不存在行为对于客体的实际损害结果,而只是存在着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当然,这种危险性可以分为具体的危险性和抽象的危险性。因此,危险性犯罪也可以相应地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在危险性犯罪的情况下,因为不存在实际的法益侵害结果,在构成要件上就不是采取结果性的归责,而是基于行为自身危险性的归责。在危险性犯罪的立法例中,罗克辛教授列举了《德国刑法典》关于放火罪的规定。
放火罪是各国刑法中通常规定的犯罪,属于公共危险罪,我国刑法称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我国刑法对放火罪规定比较简单,只是规定了故意犯的实害犯、故意犯的具体危险犯和过失犯,即过失犯的结果犯。尤其是,我国刑法中的放火罪侵害的客体包括人身侵害和财产侵害,因此在放火罪的构成要件中包含了侵害人身的犯罪与毁坏财产的犯罪。但《德国刑法典》对放火罪的规定则较为复杂,设置了各种类型的罪名。《德国刑法典》第306条规定的是放火罪的基本犯;第306条a规定的是严重的放火,即放火罪的加重犯;第306条b规定的是特别严重的放火,即放火罪的特别加重犯;第306条c规定的是带有死亡结果的放火,即放火罪的结果加重犯;第306条d规定的是过失的放火,即放火罪的过失结果犯;第306条e规定的是积极悔过的放火;第306条f规定的是火灾危险的引起,即放火罪的危险犯,包括故意犯的危险犯和过失犯的危险犯。在以上规定中,涉及过失犯的规定包括以下三个条款。
其一,放火罪的结果加重犯,即带有死亡结果的放火。《德国刑法典》第306条c规定:“如果行为人通过第306条至第306条b规定的放火至少轻率地造成他人死亡的,那么,处终身自由刑或者不低于十年的自由刑。”
在这一规定中,放火这一基本行为过失地造成了他人死亡的后果:行为人对于放火是故意的,但是,对于死亡结果则是过失的。因此,属于放火罪的结果加重犯。
其二,放火罪的过失结果犯,即过失的放火。《德国刑法典》第306条d规定:“(1)行为人在第306条第1款或者第306条a第1款的情形中过失地行动或者在第306条a第2款的情形中过失地造成危险,处三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2)行为人在第306条a第2款的情形中过失地行动和过失地造成危险的,处三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
在这一规定中,虽然在法条中存在着造成危险之类的表述,使人误以为是对于过失犯的危险犯的规定,但该法条是以《德国刑法典》第306条第1款、第306条a第1款和第2款为前提的。而第306条第1款是放火烧毁财产的犯罪,即放火罪的故意犯的结果犯;第306条a第1款是有人居住的场所,也是故意犯的结果犯;第306条a第2款是对第306条第1款规定的放火烧毁财产犯罪的加重犯,其加重条件是因此造成他人健康损害的危险。就这一规定的内容而言,是对于财产的故意犯的结果犯与对于他人健康的故意犯的危险犯的竞合。因此,除了第306条a第2款中存在竞合性的危险犯的内容以外,其他犯罪都是结果犯,即以发生财产烧毁的实际损害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因此,《德国刑法典》第306条d规定的放火罪,是过失犯的结果犯。
其三,放火罪的危险犯,即火灾危险的引起。《德国刑法典》第306条f规定:“(1)行为人使他人的①易燃的工厂或者设备;②农业或者喂养经济的其中存放着其产品的设备或者工厂;③森林、草原火灾沼泽地或者;④已经耕种的田地或者农业经济的存放在田地上的易燃的产品,通过抽烟、通过明火或者火源、通过丢扔燃烧着的或者闪烁着的物体或者以其他方式处于火灾危险之中的,处三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2)同样处罚,如果行为人使第1款第1项至第4项所标明的某一物品处于火灾之中和因此给他人的身体或者生命或者具有重要价值的物品造成危险。(3)行为人在第1款的情形中过失地行动的或者在第2款的情形中过失地造成危险的,处一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
在这一规定中,放火行为并不需要发生实害结果,而只要求造成引起火灾的危险,因此属于危险犯,对此确定无疑。从以上三款法条规定来看,第1款是对财产烧毁的放火罪之故意犯的危险犯的规定,这是一种具体危险犯。第2款是对他人身体或者生命造成危险的放火罪之故意犯的危险犯的规定,这是一种抽象危险犯。第3款是过失犯的危险犯的规定。那么,这里的过失犯的危险犯究竟是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抑或既包括具体危险犯又包括抽象危险犯?对此,值得进一步辨析。
危险犯可以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危险犯的所谓危险是一种具体危险,德国学者指出:“法律对具体危险犯(konkrete fährdungsdelikte)的规定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考虑之上,即某个违反规范的举止对受保护的客体有可能(kännen)造成危险和当罚,一旦(sonfern)该危险性在案件中具体(konkren)出现。危险性的出现,在这里是构成要件标志(Tatbestandmerkmal)。如要处罚,需由法官特别认定。”⑤[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因此,具体危险犯的危险是一种危险的结果或者状态,需要法官加以认定。在犯罪的构造上,具体危险犯与侵害性犯罪是相同的,甚至也被认为是结果犯。只不过在实害犯中,这种结果是一种实际的损害结果。而在具体危险犯中,这种结果是一种可以预期的损害结果,即危险结果,也可以说是结果发生的危险。例如罗克辛教授指出:“这种具体的危险性犯罪是结果犯罪,这就是说,它与前面讨论的侵害性犯罪,基本上不是通过不同的归责标准来加以区别的,而是通过在一种侵害性结果的位置上出现了各种行为构成的危险结果来加以区别的。因此,与在侵害性犯罪中一样,一种在恰当的、不许可的侵害性风险意义上的具体‘结果性危险’,就必须首先被创设出来。”⑥同前注②,克劳斯·罗克辛书,第275页。根据罗克辛教授的观点,具体危险犯的具体危险本身就是一种结果,需要法官根据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危险犯的构造与结果犯是相同的,都是“行为+结果”。只不过,在结果犯的情况下,这种结果表现为实际损害;在具体危险犯的情况下,这种结果表现为危险状态。笔者曾经将具体危险犯归之为行为犯,因为我国刑法对具体危险犯的表述是:“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从逻辑上理解,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就是法律规定的一定犯罪结果没有发生,又怎么能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果呢?⑦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这里主要还是涉及对结果的理解。如果把这里的结果理解为构成要件的结果,在具体危险犯的情况下,这种构成要件的结果并没有发生,当然可以将其归之于行为犯。但是,如果把这里的结果理解为法益受到的威胁,则这种结果就是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如此理解,则可以把危险状态本身作为一种结果,因而将具体危险犯归入结果犯。
然而,抽象危险犯的所谓危险是一种抽象危险,德国学者指出:“抽象危险犯(abstrakte Ge f ährdungsdelikte)则是建立在法律的这个认识之上,即一定的举止方式普遍(generell)在对受保护的客体形成危险(gefährlich)。行为的危险性在这里不是(nicht)构成要件标志,而只是法律规定的存在理由(Grund für die Existenz der Vorschrift),法官对此通常不必去审查危险性在个案中是否已经出现或者并未出现。”⑧同前注⑤,约翰内斯·韦塞尔斯书,第14页。因此,抽象危险犯的危险是一种立法推定的危险,并不需要法官具体查明。在这个意义上,抽象危险犯不是结果犯而是行为犯,即只要实施一定的构成要件行为即可构成犯罪。由此可见,在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区分的。根据以上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定义,《德国刑法典》第306条f所规定的过失犯的危险犯,既包括过失犯的具体危险犯,又包括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由此对应于故意犯的具体危险犯和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对于财产烧毁的放火罪来说,要求对于财产烧毁的结果具有危险,这是一种具体危险。但对他人身体或者生命损害的放火罪来说,并不要求存在具体危险,因此是一种抽象的危险犯。对于《德国刑法典》第306条f所规定的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罗克辛教授指出:“抽象的危险性犯罪,是指依照典型的危险的举止行为被作为犯罪而处于刑罚之下,不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出现一种危险的结果。这就是说,防止具体的危险和侵害,仅仅是立法的动机,而不是使这种具体的危险和侵害的存在成为行为构成的条件。因此,放火烧毁房屋所产生的损害财产结果为第306条所包含,另外,因为立法者想到放火能够产生的对自然人生命造成的危险,又在306条中作为重罪对其规定了特别严厉刑罚的威胁。但是,在具体案件中不存在对生命的威胁时,这个条文的原文文字也已经得到了满足。”⑨同前注②,克劳斯·罗克辛书,第278页。因此,对于放火威胁自然人的生命的犯罪而言,这是一种抽象的危险犯,并不需要对他人生命产生具体的危险。
二、我国刑法是否存在过失危险犯的辨析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过失犯的危险犯问题,同样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当然也与我国刑法是否规定过失犯的危险犯这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并未规定过失犯的危险犯,因此,也就不可能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对过失犯的危险犯进行研究。而是基于过失犯的增加这一现实,从立法论角度提出了是否应当将过失行为犯罪化,即设立过失犯的危险犯问题。对此,我国学者存在着不同观点。笔者曾经将这种不同的规定概括为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过失行为仅有造成某种损害的可能性,不宜规定为犯罪。但是,对那些主观恶性比较重,损害结果虽未发生,但发生的可能性极大,且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巨大的严重过失行为,可考虑在分则中特别规定为危险状态构成的过失犯罪。从实际情况看,这类犯罪应该主要出现在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犯罪中。”⑩王伊端、王晨:《晚近过失犯罪发展趋势研究》,载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论者在此提出的设立过失危险犯,是指具体的过失危险犯,并且认为应该对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设立过失危险犯。否定说则认为:“否定犯罪过失的结果责任是不合适的。危害结果是限制过失责任范围的客观尺度。脱离这一标准,便会无限制的扩大犯罪过失的范围。在业务活动过程中,行为人违反任何一项注意义务(主要是规章制度)都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如果对这种行为处以刑罚,无异于刑罚惩罚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而且,这种立法的效果不好,加重了业务人员的心理负担,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⑪⑪姜伟:《罪过心理的立法构想》,载《廉政建设与刑法功能》,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由此可见,否定说主要是从刑法谦抑的角度否定过失的危险犯。同时,也考虑了设立过失危险犯的社会效果。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讨论,表明我国学者对于过失犯的危险犯问题的关注。在当时,笔者是赞同否定说的,并且主要是从恪守过失犯的结果无价值的角度进行了论证,指出:“在刑法理论上,危险犯就是指法律规定不以发生某种实际危害结果为要件,而是具有发生这种结果的危险为要件的犯罪。危险犯通常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由于它不要求犯罪结果,因此必须是该行为本身就具有足够危害的,是所谓行为无价值。而过失犯历来都是结果犯,以发生的危害结果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是所谓结果无价值。在没有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就没有过失犯罪可言,因此,我们认为,过失不存在设立危险构成的可能性。”①同前注⑦,陈兴良书,第191页。应该说,当时对于过失危险犯的讨论都还是较为粗浅的,并未涉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因此,在过失危险犯问题上,笔者的观点也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的。尤其是在尚不了解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关于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的情况下,这种对于在刑法中是否应当设立过失危险犯的探讨,缺乏较为宽阔的视野,难免失之局囿。
在1997年我国刑法修改以后,对于过失危险犯的关注视角开始从立法论向解释论转变,即围绕着我国刑法的具体罪名,对于我国刑法是否存在过失危险犯展开讨论。尤其是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以后,在醉酒驾驶构成的危险驾驶罪的讨论中,也涉及过失危险犯的问题。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国学者主要围绕以下三个罪名对过失危险犯进行研讨。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我国《刑法》第330条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二)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四)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我国刑法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定,除了法条所列举的四种具体行为以外,还规定了以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为该罪成立的条件。这里的传播是指实害结果,而传播严重危险是指具体危险。因此,以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情形,属于实害犯。以传播严重危险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情形,则属于危险犯,确切地说,是具体危险犯。对此,并无争议。问题在于: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果该罪属于故意犯罪,则本罪是故意犯的危险犯。如果该罪属于过失犯罪,则该罪是过失犯的危险犯。因此,该罪是否属于过失犯的危险犯取决于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
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是过失,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肯定其为过失犯的危险犯。②参见刘仁文:《过失危险犯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将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认定为过失的主要理由在于:行为人对于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虽然可能是故意,但对于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这一结果是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因此属于过失犯。③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第五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3页。由此可见,我国学者是根据行为故意、结果过失这一逻辑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归之于过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是根据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认定为故意,而是根据对于传播严重危险的主观心理态度认定为过失呢?这里涉及传播严重危险这一要素在构成要件中的体系性地位问题。对此,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引入客观超过要素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论证该罪属于故意犯。张明楷教授指出:“将本罪确定为过失犯罪,缺乏‘法律有规定’的前提,只能确定为故意犯罪,但宜将‘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视为本罪的客观超过要素,既不需要行为人明知该结果的发生(但要求有认识的可能性),也不需要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其发生。”①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85页。在此,张明楷教授否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法律没有规定。因为我国《刑法》第15条第2款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刑法》第330条所列举的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显系故意,而并没有规定该罪是过失。在这种情况下,该罪应当认定为是故意犯罪。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并没有充分的法理根据。过失犯可以分为纯正的过失犯与不纯正的过失犯:前者是指只能由过失构成而不可能由故意构成的犯罪,后者是指既可以由过失构成又可以由故意构成的犯罪。刑法关于“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主要适用于不纯正的过失犯而并不适用于纯正的过失犯。因为在不纯正的过失犯罪中,同一种行为,故意与过失都可以构成犯罪。因此,在法律没有规定过失犯罪的情况下,只能处罚故意而不能处罚过失。而纯正的过失犯只能由过失构成不能由故意构成,因此无需法律规定,也应当负刑事责任。就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而言,如果构成犯罪,则是纯正的过失犯。对于纯正的过失犯,并不需要法律规定也能构成犯罪。例如我国刑法中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就是如此,因此,以缺乏法律规定为根据否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过失犯,理由并不充分。至于客观超过要素的见解,笔者认为还是具有独特性的。但这只是排除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认识,而肯定对其的认识可能性,以此认定该罪属于故意犯。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能否认定为故意犯,根本问题还是在于行为人是否可能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持希望或者放任的主观心理。过失说认为,行为人虽然对于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是故意的,但对于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则不可能是故意,而只能是过失。但这一说法的根据并不明确。对该罪持故意说的学者则认为该罪属于明知故犯,主观方面应该是故意。例如黎宏教授指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违反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具有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希望或者放任该种结果的发生。因为,从本罪的实行行为来看,多半是明知故犯,说行为人在行为时对自己可能引起的后果没有认识,是难以想象的。”②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854页,注【98】。对于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属于故意,笔者是赞同的。在笔者看来,在该罪中,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与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之间应当具有因果关系,即在客观上,行为人不仅必须实施了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例如,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等,而且,这一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还必须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不可否认,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直接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因此,在客观上我国刑法对于该罪的入罪设置了极为严格的条件。不仅如此,而且在主观上行为人要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具有认识,如果没有这种认识,该罪也不能成立。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330条所列举的四种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是该罪的实行行为,而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则是该罪的构成要件结果,行为人对其应当认识。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相对于情节严重,是区分犯罪行为与行政处罚行为的界限。事实上,《刑法》第330条所规定的四种行为,在《传染病防治法》第73条中都有明文规定,对于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可以处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第330条将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从而在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之间划出了明确的法律界限。因此,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体现的是刑事政策的精神。从法条内容本身理解,将该罪认定为故意犯,更能够限缩刑罚范围。基于这一分析,笔者认为该罪属于故意犯,由此可以否定过失犯的危险犯。
(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我国《刑法》第332条规定:“违反国家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具有相似于前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范构造,也是以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我国学者指出:“行为人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行为具有高度的危险性,一旦这一危险转化为具体的危害结果时,后果将会极其严重。因此,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考虑,《刑法》第332条将本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是指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行为造成了传播的后果。换言之,行为人的行为使他人感染上了检疫传染病。这在刑法理论上被称为实害犯。‘有传播严重危险’,则是指虽然尚未实际造成检疫传染病的传播,但具有造成检疫传染病传播的较大的现实可能性。这在刑法理论上称为危险犯。”①同前注⑭,王作富书,第1351页。以上对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立法规定的描述是正确的,因此,该罪是否属于过失犯的危险犯就在于主观罪过形式是否过失。我国学者正是在肯定该罪是过失犯的基础上,认为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的危险犯立法例。②参见前注⑬,刘仁文书,第26页。
关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罪过形式,在我国刑法学界也是存在争议的,即故意说与过失说的争论,当然也还存在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的观点。该罪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主要取决于对故意与过失的界定。我国学者在论证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属于过失时指出:“根据刑法理论,故意和过失都是针对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而言的,本罪中行为人对‘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是不希望发生的,因此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③同前注⑭,王作富书,第1352页。这一论述是以行为人不希望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发生作为其逻辑演绎起点的。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确实存在这种不希望的主观心理态度,当然不能构成该罪。但不能由此得出结果,行为人可以构成过失犯。根据刑法第332条之规定,只有在行为人对于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具有希望或者放任的主观心理态度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该罪。因此,该罪属于故意犯,而不能构成过失犯的危险犯。
(三)危险驾驶罪
危险驾驶罪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设立的一个罪名,其中,笔者重点讨论醉酒驾车构成的危险驾驶罪。我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竟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危险驾驶罪,包括了两种行为:一是追逐竞驶,二是醉酒驾驶。其中,更为引人注意的是醉酒驾驶构成的危险驾驶罪。在《刑法修正案(八)》设立危险驾驶罪之前,我国刑法只规定了交通肇事罪,这是一个过失犯罪,以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作为犯罪成立条件,属于过失犯的结果犯。对于交通肇事罪来说,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既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过失的。但对于肇事结果,都是过失的。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中,事实上包含了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但酒后驾驶机动车,即使达到醉酒程度驾驶机动车,只要没有发生肇事结果,都不构成犯罪。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条件之一。例如,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了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六种情节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在这六种情节中,就包括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由此可见,醉酒驾驶行为的入罪具有明显的对于肇事后果的依赖性。但《刑法修正案(八)》设立危险驾驶罪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观: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可以独立入罪,而不再依赖于肇事后果。因此,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的入罪是典型的刑法处罚的前置,体现了刑法对公共安全的特殊保护。
从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规定来看,醉酒驾车构成的危险驾驶罪是危险犯,而且是抽象危险犯。因为只要实施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即使没有发生肇事后果也构成犯罪,因此是危险犯。这种危险不是具体危险,而是抽象危险。因此,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我国学者指出:“抽象危险犯的危险在于该种危险尚无具体危及的对象、尚未达到具体危险,距离实害结果则更是相对较远,在这个意义上,将抽象危险犯的危险归为行为的危险而将具体危险犯的危险归为结果的危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以如此逻辑来看我国的危险驾驶罪,在行为性质上应当属于抽象的危险犯。”①刘军:《危险驾驶罪的法理辨析——兼论刑法法益保护的前期化》,《法律科学》2012年第5期。在我国刑法中,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最初是设立了具体危险犯。例如《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规定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分别设立了实害犯和危险犯。其中,危险犯以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作为标志。这里的危险犯不仅是故意犯的危险犯,而且是具体危险犯,而《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则属于抽象危险犯。
那么,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的抽象危险犯呢还是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争议。这里主要涉及如何界定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问题,即: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②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这里的故意表现为:明知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会危及公共安全而实施该行为。对于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的观点,冯军教授持反对意见,其从《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范目的出发,论证了危险驾驶罪属于过失犯。根据冯军教授的观点,《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范目的不是防止行为人通过醉酒驾驶行为来故意地维护公共安全;也就是说,它针对的情形是:行为人故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并且故意通过醉酒驾驶行为来引起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范目的在于弥补在交通违反行为与交通肇事罪之间所承载的处罚漏洞。因此,应当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解释为过失的抽象危险犯。③参见冯军:《论〈刑法〉第133条之1的规范目的及其适用》,《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冯军教授采用规范目的的分析方法是值得赞许的,尽管笔者并不赞同其结论。冯军教授的意思是:醉酒驾驶型的危险驾驶行为虽然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危险犯,但完全可以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害犯)的未遂犯。因此,根据既有的刑法规定完全能够处罚作为故意犯的抽象危险犯的醉酒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在此并不存在着处罚漏洞。只有在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肇事罪之间才存在处罚漏洞,因而有必要设立作为过失犯的抽象危险犯的醉酒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笔者认为,刑法已有规定并不能成为否定新设罪名的理由。更何况,将醉酒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理解为故意犯,并不能认定为《刑法》第114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危险犯)的未遂犯。正如张明楷教授指出:“如果行为人仅具有造成抽象危险的故意,而不具有刑法第114条要求的造成具体危险的故意,就不可能成立刑法第114条的未遂犯。”尤其是张明楷教授论及:“冯文主张危险驾驶罪属于过失的抽象危险犯的观点,不仅没有实现刑法的规范目的,没有填补所谓相关的漏洞。反而导致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受处罚,而故意的抽象危险犯没有相应的可以适用的法条的矛盾局面。”①张明楷:《危险驾驶罪的基本问题——与冯军教授商榷》,《政法论坛》2012年第6期。事实上,过失的抽象危险犯的设立是以故意的抽象危险犯为前提的。例如《德国刑法典》第316条对交通中的酩酊做了以下规定:其一,行为人在交通中(第315条至第315d条)驾驶交通工具,尽管他由于饮用酒精饮料或者其他醉人的药物而不能安全地驾驶交通工具的,处一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如果该行为没有在第315条a或者第315条c中被用刑罚加以威吓的话。其二,也根据第1款予以处罚,如果行为人过失地实施该行为。
以上《德国刑法典》关于醉酒驾驶罪的规定,可以分为两款:第1款是故意犯的抽象危险犯,第2款是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因此,将我国刑法中的危险驾驶罪解释为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可能会使故意的抽象危险犯丧失处罚根据。而且,将我国刑法中的危险驾驶罪解释为过失的抽象危险犯,还可能会扩张刑罚惩罚的范围。因为,如果将我国刑法中的危险驾驶罪理解为故意的抽象危险犯,则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于过失的抽象危险犯不得处罚。但将我国刑法中的危险驾驶罪解释为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则不仅使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故意的抽象危险犯无法处罚,而且使不应当受到处罚的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受到处罚。
三、过失危险犯的法理考察
基于以上论述,对于过失犯的危险犯,在《德国刑法典》中有处罚性的明文规定,因此德国刑法学界围绕着其立法的正当性对过失犯的危险犯展开了刑法教义学的讨论。但在我国刑法中,对过失犯的危险犯并无规定,因此我国刑法学界应当讨论的主要还是在刑法中是否应当设立过失犯的危险犯的问题。
过失犯在一般情况下,都是过失结果犯。德国学者在论及过失结果犯的不法构成要件时,指出:“过失行为的不法性的确定,是根据它的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Erfolgs-und Handlungsunwert)。在过失结果犯的范围内,组成不法构成要件之基础的,是三个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连接的特征:结果造成(Erfolgsverursachung)、违反客观上所要求的谨慎义务(Verletzung der objektiven sorgfaltspflicht)和由于举止的缺陷所造成之结果(Erfolg)的根据谨慎规范所指向的保护目的而客观上的可归责性(objektive Zurechenbarkeit)。”②同前注⑤,约翰内斯·韦塞尔斯书,第392页。因此,在过失结果犯的情况下,实行的是结果归责的原则。尤其是,过失的实行行为本身具有较为强烈的规范性特征,它像故意犯那样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定型性。在这种情况下,过失犯的结果就成为过失犯构成的根本标识,对于过失犯的归责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刑法典》关于过失犯的危险犯的规定,完全不同于过失结果犯,德国学者称为“没有造成结果的过失”。这种所谓没有造成结果的过失,其实就是一种过失的未遂。但在刑法理论上,从来都认为过失犯不存在未遂或者过失犯的未遂不处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关于过失犯的危险犯的处罚性规定,实际上是过失犯的未遂不处罚原则的一种例外或者突破,反映了刑法对于过失犯处罚范围的扩张。例如,德国学者在论及没有造成结果的过失时指出:“如果过失行为人虽然违反了注意义务实现了行为不法,但还没有产生消极的结果,即结果不法不存在,就存在着与故意犯罪未遂相当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行为大多不受处罚。”①[德]冈特·斯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418页。故意犯的未遂之所以受处罚、过失犯的未遂之所以不受处罚,主要就在于行为人的意志决定:故意犯存在着对于构成要件结果的意志决定,结果之所以没有发生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但在过失犯的情况下,并不存在行为人对于构成要件结果的意志决定,因此不能适用故意犯未遂处罚根据的法理。
在我国刑法学界否定过失危险犯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过失犯是结果犯,而危险犯,无论是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则不存在这种结果,因此,没有结果的过失是不能成立的。我国《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这一过失概念显然是以结果为本位的,我国学者由此得出过失犯只能是结果犯的结论,指出:“客观上发生了严重危害结果,是构成过失犯罪的客观条件。只有实际上发生了严重的危害结果,才能赋予行为人的行为以犯罪的性质,也才能体现出行为人主观过失的严重性。如果实际上没有发生危害结果,或者发生的危害结果不严重,那么,即使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也不构成过失犯罪。”②侯国云:《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4页。这一论述把我国《刑法》第15条关于犯罪过失概念中的“危害社会结果”理解为构成要件结果,因此没有这种结果过失犯罪就不能成立,从而排斥了过失犯的危险犯。我国学者在论及过失行为与过失结果在过失犯的构成要件中的功能时指出:“在过失犯罪的场合,行为人对构成犯罪的事实缺乏认识,即使有可能性之认识,但也不希望其发生或轻信能避免其发生,也就是说,行为的结果不是他特定的目的,因此,过失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和危害性,不受法律上否定之评价。故通称过失犯罪为‘非行为犯’。但是,过失犯罪的结果对社会却是有害的,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也就是说,当过失行为还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实指严重的危害后果)时,其行为本身不具有犯罪的性质,但当过失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时,其行为就构成了犯罪。可见,过失犯罪具有浓厚的实质犯色彩,故又称过失犯罪为‘结果犯’(实质犯),意即无实害即无过失犯罪。”③同上注,侯国云书,第85-86页。由此可见,在我国刑法的语境中容纳过失犯的危险犯,需要对我国《刑法》第15条关于过失犯罪的概念性规定进行合理的解读,否则难以在我国刑法中肯定过失犯的危险犯。
其实,这个问题在故意犯中也同样存在着。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一故意犯罪中的故意,也是结果本位的。那么,在故意犯中如何能够容纳危险犯呢?因为,危险犯也是结果缺失的,在故意犯的危险犯的情况下,如何满足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国学者提出了结果本位主义的故意概念与行为本位主义的故意概念,指出:“在结果本位主义的刑法体系中,危害结果既然是意欲的对象,自然也是认识的对象,并且认识内容实际上需要以危害结果为核心。相应地,凡是指向结果或者影响结果出现的因素都会被认为属于故意的认识内容或明知的范围。而在行为本位主义的刑法体系中,故意的认识对象则以行为为核心。据此,只有与行为相关且直接影响行为违法性的因素才属于认识的内容。”④劳东燕:《犯罪故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在此,论者是从理论上分析故意认识内容的,但从刑法教义学角度来说,我国《刑法》第14条以及第15条之规定的“结果”到底是指什么,这个问题恰恰是最为关键的。如果把这里的结果理解为构成要件结果,即对行为客体的作用或者影响,则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只能是结果犯的故意,只有对结果具有认识时才有可能成立故意。同样,我国刑法中的过失也只能是结果犯。反之,如果把这里的结果理解为法益侵害性,也就是上述学者所称的(实质)违法性;那么,当这种法益侵害体现为实害时,当然要求对结果有认识。当这种法益侵害体现为危险时,要求对行为的危险性的认识。由此,可以将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分为结果犯的故意与行为犯或者危险犯的故意。基于这一逻辑,我国刑法中过失犯罪概念中的结果,也应当做以上理解,即在过失犯的结果犯的情况下,行为人所要求预见或者已经预见的是实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在过失犯的危险犯的情况下,行为人所要求预见的是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如此,则可以在我国刑法关于犯罪过失的语境中,容纳过失犯的危险犯。
在过失犯是否可以成立危险犯的争议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失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危害性,是否应当作为犯罪处理。否定说的理由是过失行为的危害性取决于结果:如果发生了法益侵害结果,则过失行为具有危害性;如果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则过失行为不具有危害性。因此,在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情况下,不能成立过失犯的危险犯。这一观点涉及危险犯的处罚根据问题。在实害犯,即侵害性犯罪中,法益侵害结果已经发生,因此,可以根据法益理论为其刑事处罚的正当性提供根据。但在危险犯的情况下,法益侵害结果没有发生,其刑事处罚根据如何进行论证呢?关于这个问题,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还是存在差别的。就具体危险犯而言,虽然法益侵害结果没有发生,但具有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表现为结果性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说,具体危险犯仍然属于结果犯,只不过其结果不是实害,而是危险状态。对此,德国学者许乃曼提出规范的危险性结果理论加以说明。该理论认为,具体的危险存在于侵害性结果偶然地没有发生的场合。这种偶然性不是确定为在自然科学上无法说明的理由,而是确定为一种人们不能相信会出现的情形。①参见前注②,克劳斯·罗克辛书,第277页。但抽象危险犯与此有所不同,不仅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而且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只是一种行为性危险。对此,德国学者霍恩和布雷姆提供了客观上的违反谨慎性的解释径路,而许乃曼则修改为主观上的违反谨慎性。②参见前注②,克劳斯·罗克辛书,第279页。无论是客观上的违反谨慎性还是主观上的违反谨慎性,都以防止危险发生作为最终目标,同时也为过失犯的危险犯创造了空间,即,过失性的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危险发生与故意性的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避免结果发生一样,都是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行为。因此,不仅存在故意犯的危险犯,而且也存在过失犯的危险犯。
过失犯的危险犯对于危险的发生具有过失,其在客观上与故意犯的危险犯相同,只是主观罪过形式不同而已。就故意犯的危险犯与过失犯的危险犯而言,故意犯的危险犯在处罚上要重于过失犯的危险犯,因此,只有在处罚故意犯的危险犯的前提下,才能处罚过失犯的危险犯。例如,《德国刑法典》就是这样规定的。我国刑法对于醉酒型的危险驾驶罪,对于醉酒驾驶行为会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是明知的,因此属于故意犯的危险犯。就此而言,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过失危险犯的处罚性规定。换言之,在我国刑法中,只有明知醉酒驾驶行为会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仍然驾驶的,才构成犯罪。如果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饮用了含有酒精的饮料,没有认识到自己处于醉酒状态而驾驶的,尽管对于客观上造成的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具有过失,也不能认定为危险驾驶罪。
我国刑法,即使是在1997年修订以后,结果本位的立法特征还是较为明显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一般都要求发生一定的危害结果或者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因此,我国刑法中的行为犯或者危险犯的立法规定是较为例外的。这种立法状况,笔者认为与我国所特有的二元处罚体制具有密切关联。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着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二元处罚体制。在行政处罚中,又可以分为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和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除此以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还存在着劳动教养,它介乎于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直到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决议,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刑法中,为了给行政处罚留下空间,除了性质严重的行为以外,其他行为都根据情节分别予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即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刑事处罚;情节轻微或者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行政处罚。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只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刑法典中的重罪和部分轻罪。因此,我国刑法中只有极少数故意犯的危险犯,没有过失犯的危险犯。对于这些危险行为,一般都按照行政违法行为予以处罚。而在其他国家,行政机关,甚至警察机关都没有处罚权,一切涉及对公民财产和人身的处罚都必须经过司法程序。因此,即使是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危险犯,需要处罚也必须以刑法规定为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刑法典中存在较多的危险犯,包括过失犯的危险犯的规定,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了。
即使在其他国家,过失犯也存在一个从过失结果犯到过失危险犯的演进过程,其社会背景是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风险源的增加,所谓风险社会的到来。德国学者许乃曼教授曾经提出“从过失犯罪向危险犯的演进”的命题,指出:“从公平和威慑效果的角度来看,传统的过失犯罪的概念都有欠缺,因为某一不谨慎的、极端危险的行为是否会造成损害后果,纯粹是偶然事件。只要行为人相信如果因为其行为的后果没有危害性而不会受到处罚,那么对行为人可能实施的处罚的威慑和预防效果就会大大削弱。对造成了严重损害后果的轻微过失犯罪行为处以重罚,而对造成轻微损害后果的重大过失犯罪不予处罚,都是错误的和不公平的。因此,所有欧洲国家对立法都已经摈弃了传统的过失犯罪的概念,现在都转而采纳了危险犯罪的概念。”①[德]许乃曼:《传统过失刑事责任观念在当代社会中的弊病——新的趋势与展望》,王秀梅译,《法学家》2001年第3期。这里所谓传统的过失犯罪的概念,就是指只有发生危害后果才处罚的结果犯的过失犯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危险犯就成为过失犯的立法发展趋势。例如《德国刑法典》就极为细致地规定了过失犯的危险犯,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规定。过失犯从结果犯向危险犯的立法发展趋势,反映了在科技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危险源的增加,刑法功能从事后的惩治向事前的预防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刑法的预防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我国目前主要是在从风险社会理论中引申出来的风险刑法的框架内论证过失犯的危险犯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是1986年提出的,正如罗克辛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学者普里特维茨在1993年出版的关于《刑法与风险》的著作,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对风险刑法问题进行研究。②参见前注②,克劳斯·罗克辛书,第19页。《德国刑法典》关于过失危险犯的立法则出现在1975年,可见立法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只能说,风险刑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为过失危险犯的立法提供了理论论证。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过失危险犯的规定,这是讨论的一个面向。如前所述,笔者个人并不认为我国刑法存在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但是,在逻辑上是否存在以及在刑法中是否应当设置过失危险犯,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笔者曾经认为,所谓过失危险犯实际上是过失犯的故意行为的犯罪化。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成立的是故意的抽象危险犯。③参见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例如,交通违章行为,就像醉酒驾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故意的,当刑法中只有交通肇事罪的时候,只有发生肇事结果才能构成过失犯的结果犯。没有发生这种肇事结果,故意的交通违章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但将故意的交通违章行为,例如醉酒驾驶规定为犯罪以后,就成为故意犯的危险犯。但是,能否得出结论说,根本就不存在过失犯的危险犯呢?现在看来,尚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故意的交通违章行为以外,还存在过失的交通违章行为,当刑法规定在没有发生肇事结果的情况下,过失的交通违章行为也构成犯罪的时候,就属于所谓过失犯的危险犯。但是,过失犯的危险犯既然是与故意犯的危险犯相对应的不纯正的过失犯,应当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并且,必然以刑法规定了相对应的故意犯的危险犯为前提。
从我国刑法来看,结果本位的倾向还是极为强烈的,在晚近的立法中,出现了向行为本位演变的某些迹象。类似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立法例。此外,我国《刑法》第338条从过失犯的结果犯的环境污染重大责任事故罪修改为故意犯的危险犯的环境污染罪,也是最佳例证。笔者认为,这些规定只是表明我国刑法中出现了某些故意犯的危险犯,但还没有出现过失犯的危险犯。在我国目前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双重制裁体制下,没有发生实害结果的过失行为,仍然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还没有达到刑事处罚的程度。
(责任编辑:杜小丽)
D F611
A
1005-9512(2014)05-0002-14
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兴发岩梅讲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