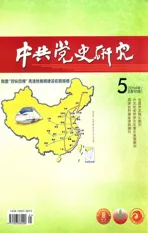民团、农民武装与陕甘边红军的建立及影响
2014-02-03黄正林
黄正林 温 艳
(本文作者 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西安 710062;温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陕西理工学院教授汉中 72300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中共党人在陕西、甘肃交界地区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在第二次反“围剿”之后,与陕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因而成为中共中央和南方各路红军的落脚点。在近些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中,陕甘边根据地史研究颇受重视,也取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①如李仲立、曲涛:《陇东老区政权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陇东老区红军史》是研究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比较重要的著作);刘凤阁:《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探源》,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党史论文集》,2001年印行;曲涛:《红色足迹——陇东老区重大事件述评》,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李东朗: 《简论陈家坡会议》, 《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3期等;这基本可以代表陕甘边历史当前的研究水平。。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从“革命史”的角度考察陕甘边的历史,缺乏对相关历史事件文献的挖掘与求证,对许多问题的讨论价值判断大于实际判断,把复杂的历史问题一并归为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缺乏对复杂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考察。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化,一方面,对如何研究革命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范式,主张将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相互联接和互动为切点,“将为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从而实现中共历史研究的突破”①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方面,对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就中共苏维埃时期历史研究而言,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提供了理论基础与范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主要利用当下能够看到的文献,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地区社会生态入手,对陕甘边红军建立过程中收编民团、农民武装以及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陕甘边界地区的民团与农民武装
陕甘边界民团与农民武装的形成,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政治与自然生态有直接的关系。民国建立后,在地方军阀的统治下,陕甘乡村政治生态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军阀为了扩充地盘和实力“不停地打仗,无情地吮吸农民的膏脂,税收高到最大限度”②〔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14页。。农民不仅要承担传统的田赋和正税,且还要承担日益繁杂的田赋附加和各种捐税。陕西各种捐税即达30余种,如特征产业税、民团费、房捐、车马费、青苗费、契税附加、省银行股本捐 (银行的股本,随时征收,但征而不还)、省府库捐、畜税、屠税、牙税、杂税、斗捐、秤捐、预征田赋 (每年两三次不等)、教育费附加、建设费附加、借征房租、登记费 (不登记则房屋和田地充公)、烟亩费、烟亩附加、指烟借款 (无论种烟与否都得交纳)、车捐 (乡村马车与人力车出入城内)、军队维持费、剿匪费、子弹费、侦探费、修械费、花捐 (明暗娼妓纳捐才能接客)、烟灯捐、赌捐,此外还有催款费及省府派往各县催款人员的招待费等,如时人所言“自民国成立以来,苛捐杂税,巧立名目,五花八门,光怪陆离”③何挺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 《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据统计,与陕北相邻的甘肃庆阳县1906年始征百货统捐,税率不过5%。民国以后改为百货征收局,1914年开征包裹税;1926年开征皮毛、公买商畜、药材、驼捐、庆环烟酒、董志牲畜税;1927年兼征卷烟特捐税;1928年兼征屠宰、散茶税;1929年兼征大布统捐、印花分销等,征收的税种达20余种④张精义:《庆阳县志》卷6《财赋志·税捐》,1931年修。。除各种捐税外,居民还要负担驻军或过往军队的各种粮饷,如庆阳县每年承担随粮丁摊派的军款达48000元,镇原达6万元,超过丁粮的3倍,正宁负担有军部提粮、借粮、军款3项,每年达29100元⑤王智:《廿一年甘肃民众负担概算》,《拓荒》第2卷第1期,1934年3月。。随着大量摊款接踵而至,“遂产生大批提款委员会,车骑四出,鸡犬皆惊,每区有摊派至数千元不等,每县有摊派至数万元不等”⑥孙左齐:《中国田赋问题》,新生命书局,1935年,第258—259页。。军阀造成的政治混乱,大量的粮食被搜刮去养活军队,导致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农民的贫困。
就在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1928年至1930年西北发生了大旱灾,陕甘地区成为重灾区,各地产生了大量的灾民。如庆阳县遭灾待赈的难民有62000余人,占全县人口的71%,⑦《甘肃省庆阳县民国十七年灾情一览表》,手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藏。宁县灾民达8.7万余人⑧《甘肃省宁县民国十七年灾情一览表》,手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藏。。1929年灾情继续扩大,甘肃居民无粮无种者达80%⑨季啸风、沈友益主编: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4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4页。。陕西泾阳、三原、耀县、富平、蒲城、大荔6县“无衣无食灾民共达四十万”⑩浪波:《西北灾情的实况及其救济的方策》,《西北》1930年第11期。。据1929年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估计,饥荒造成陕西250万人死亡,几乎占全省人口的1/3,另有50万人逃荒到其他省份⑪〔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4页。。旱灾把陕甘地区农民推上了生存的绝路。大部分地方“富户变为贫户,家贫者流于乞丐”①《甘肃省宁县民国十七年灾情一览表》,手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藏。;环县“年富力强者或逃走邻县,或乞丐度日,或佣工以苟全性命”,②《甘肃省环县民国十七年灾情一览表》,手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藏。合水县“年壮之人,欲苦力佣工以觅食,到处无活可做”③《甘肃省合水县民国十七年灾情一览表》,手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藏。。定边、靖边居民生活无法维持,而以树皮、草根为食,但“此种物品,亦因天气亢旱,无从获得。面黄肌瘦,甚至身肿殒命于道旁街市者,触目皆是,人兽相食,骇人听闻”。④季啸风、沈友益主编: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43册,第511、521页。大旱灾使陕甘农民生活雪上加霜。
由于乡村政治与自然生态的恶化,陕甘农民生活艰难到了不能忍受的边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农民面对最要紧的问题包括饥饿、战争和土匪的破坏、长期恶化的债务、租佃增多、离乡城居地主的出现、沉重的税收和土壤的干燥。这些情况促使农村秩序破坏,满足不了人们生存的最低需要”。⑤〔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3页。因此,有的农民铤而走险,被逼走上了与官府对抗的道路,有的则放弃家园上山投靠“山大王”落草为寇。从民国建立到30年代,陕甘地区民变此起彼伏。1915年8月,宁县北区农民5000余人围攻县城,“反对新税,归交农具”⑥宁县志编辑委员会: 《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0—401页。;环县民团团总利用农民对赋税的不满,杀死新任县长李祎,发动起义⑦蔡屏藩:《陕西革命先烈事略》,台北1962年印行,第113页。;陕西蓝田农民因不堪苛捐杂税,包围县城进行“交农抗税”斗争⑧政协蓝田县委员会: 《讨袁期间蓝田县的一次“交农”运动》,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第112—114页。。1924年4月,合水县3000多名农民包围县城;次年宁县平子镇发生民变,进行抗税斗争⑨陶继尧、沈满:《合水农民的一次抗税斗争》,《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0—133页;魏绍武:《张兆钾盘踞陇东》,《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3页。。1926年6月,周至农民举行反对军阀吴新田暴动⑩政协周至县委员会:《盩厔农民反抗吴新田的武装斗争》,《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3年印行,第84—91页。。1928年至1930年西北大旱灾把陕甘民众推到了生死边缘,陕甘地区随着灾民的增多,无依无靠的灾民或加入民团,或落草为寇。据统计,1931年前后,位于子午岭山麓的正宁县有民团10余股,合水县有民团20余股⑪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4卷《军事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庆阳县以北部子午岭深山的南梁为中心,活动着许多饥民武装,每股少则10多人,多则几十人⑫华池县志编纂委员会:《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06页。。子长县形成了四大民团,即北区的折可达民团、东区黄天锡民团、西区李丕成民团、南区宋应昌民团,团总均为当地大地主⑬子长县志编纂委员会:《子长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5页。。20世纪30年代初,清涧县较大的民团白秀珍、张云、惠树藩、拓守清、李成善、黄维汉、白瑞珠、邱树楷等8支民团⑭清涧县志编纂委员会:《清涧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0页。。为反对官府与军阀勒索,仅落草在黄龙山地区的农民武装就有十余股之多,如河南贫民樊老二 (钟秀)、河南难民马永旺、郭宝珊以及本地贾德功、梁占奎、杨谋子、李志英等⑮刘在时: 《黄龙山区“山大王”去向记 (1912—1938)》, 《黄龙文史资料》第2辑,1990年2月,第157—162页。。这些民团、农民武装成为灾民的归宿,如陈珪璋势力大增的主要原因是饥民“蜂附其部以求食活命”,时称“跟陈珪璋吃大户”。宁县四乡几乎村村有人投奔陈氏,甚至是整村投靠,如良平傅家、贾家两庄跟陈吃大户的农民有“贾一连、傅一团”之称。⑯宁县志编辑委员会:《宁县志》,第411页。
30年代初,随着土匪的增多,一些地方农民自发组成民团,试图保护一方平安。如宁县有上五社民团、中五社民团、北八社民团、东三社民团等,每个民团都有一个群众举荐的团头。这种民团无事人各在家中,一旦有事,几个团头商量后,击鼓为号,就会把民团集中起来。①《李志合1984年5月20日谈农民自发斗争》,刘凤阁、任愚公主编: 《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这些民团又被地方军阀看中,成为扩充实力的目标。如陇东军阀谭世霖为扩充实力,给活动在庆阳各村镇的民团“××营”的番号,“一律归他管辖”②《黄金贵谈太白收枪》,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30—331页。。不仅使这些民团有了“合法”的外衣,也可以从地方军阀那里获得一些弹药和给养补充。
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学者马克·塞尔登说:陕甘交界的黄土高原“远离省内主要权力中心,长久以来成为武装流寇的理想之地”③〔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11—12页。。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团、农民武装是占据陕甘乡村社会的核心力量,中共陕甘边政权和红军的建立,既利用了这里沟壑纵横的地理环境,也利用了在这里兴起的民团与农民武装。
二、民团、农民武装与陕甘边红军的建立
关于民团与农民武装,毛泽东指出:“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页。在中共建军初期,就比较重视对民团和农民武装的改造。1927年9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针对改造农民武装问题指出:“土匪原来是破产的农民,被乡村封建阶级不断的经济压迫,不得已才上山的。只要运用得当,他们的确是贫农的好朋友,是农村阶级斗争中别动的生力军。应择其可以引上革命途径的诚恳的与之联络。”⑤中央档案馆等: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甲2,1992年1月印行,第198页。1929年6月,中共中央要求陕西省委“加紧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灾民都投入土匪中去,党要深入群众中去,获得群众,使之变成农村的武装”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刘志丹在建立陕甘边红军的过程中也指出:“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⑦《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7页。因此,争取民团和农民武装是中共创建军队时的主要策略,也是陕甘红军创建过程中的主要方式。
1929年四五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红石峡召开会议,指出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即白色的(兵运)、灰色的 (改造土匪)、红色的 (建立革命武装)。会议决定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打入国民军队进行兵运工作。⑧《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22页。刘志丹在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期间 (1928年秋至1930年秋),动员大批中共党团员和外围青年,打入陕北高自清、杨庚午,甘肃谭世麟,宁夏苏雨生等地方民团部队中,进行兵运活动。1930年春,苏雨生投靠杨虎城,刘志丹、谢子长离开了苏雨生。在此前后,谢子长、刘林圃、习仲勋等分别发动了靖远兵变、乾县兵变、两当兵变等,先后都失败了。习仲勋在总结两当兵变失败原因时指出:“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⑨中共陕西省委、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经过多次兵运失败后,刘志丹等人把建立军队的重点放在收编地方军阀、民团及农民武装方面。
1929年秋,刘志丹、王子宜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合法取得了保安县 (今志丹)民团的领导权,⑩《刘志丹纪念文集》,第248页。马克·塞尔登对这件事情做了十分有趣的描述:“刘志丹在王子宜和曹力如的支持下着手军事问题,寻求在他的家乡控制民团。刘的当地人事关系,使他可以直接和县长谈话。精心策划的谈判之后,通过游说当地学生,获得大户地主人家的支持被证明是关键性的。刘志丹变成了民团司令,曹力如成为副司令。” 〔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45页。在以后的多次军事活动中都是以保安县民团为骨干力量。1930年春,刘志丹离开苏雨生部后,“准备在甘肃民团队伍中搞点势力”。①《马锡五1959年4月23日谈刘志丹的革命活动》,《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06页。刘志丹把目标盯在陇东民团谭世麟和由民团发展起来的地方军阀陈珪璋部。当时,谭世麟任陇东民团司令,急于扩大实力。刘志丹的黄埔军校出身深得谭世麟青睐,刘志丹利用这层关系与谭进行谈判,谭给刘志丹以补充第2团的名分,谢子长任团长。部队由自己组建,谢子长从杨庚午拉出来的周维琪1个营,靖边张廷芝民团1个营,刘志丹控制的保安民团1个营②《姜兆莹1985年9月9日谈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 (上),第320页。。不久发生三道川事件③1930年夏季,刚刚组建起来的陇东民团补充团驻在庆阳北部三道川,张廷芝设计收缴了周维琪营的枪,又袭击了刘志丹营,以保安县民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武装在这次事件中遭受巨大损失。,刘志丹利用谭世麟民团发展队伍的计划受挫。
三道川事件后,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打着陇东民团谭世麟骑兵第6营的旗号,以到合水县太白镇补充粮草为名,从保安县民团中抽调了几名骨干,收缴了陇东民团第24营的枪,打死营长黄毓麟,获得了50余支枪和10余匹骡马,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收枪活动,为组建南梁游击队奠定了基础④最近几年的研究中,把这次行动称之“太白起义”,甚至称是“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在陇东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其实,这就是一次收枪行动。第一,这次行动没有任何政治纲领,就是利用谭世麟骑兵第6营的名义,获得黄毓麟的信任,收缴了该营的枪支与马匹,收枪之后也没有打出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旗号,故不具备起义的特质。第二,黄毓麟民团并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只是在动乱年代成立的地方民团,被谭世麟委以陇东民团第24营番号。故打死黄毓麟,收缴该营枪支,根本谈不上是“打响陇东地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1930年前后,活动在陕甘边界的农民武装主要有赵连璧 (即赵二娃)、杨培盛、贾生财和唐清山等。赵连璧与刘志丹是姑表亲戚,年幼丧父母,在刘家当雇工11年,后被张廷芝民团拉去,逃跑后又在陈珪璋部下当兵,搞了几支枪回家要与刘志丹一起干。刘志丹让他到合水太白一带活动。赵连璧的胆子大,枪法好,有活动能力,南梁一带土匪、民团“都归他管”。⑤《王世泰同志在边区历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5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1986年5月印行,第110页。杨培盛、同守孝两人是米脂人,以贩皮货为生。杨培盛在皮货遭到民团抢劫后,与同守孝组织了一支100余人的武装,活动在庆阳南梁、二将川一带。⑥《杨培盛1985年8月谈南梁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38页。贾生财是横山人,逃荒到合水县蒿咀铺,先在陇东民团当兵,先后任班长、排长,后来自己拉起了四五十人的民团,一直与刘志丹保持着联系。唐清山原籍河南,逃荒到西华池附近,组织的饥民武装活动在合水瓦岗川一带。⑦《张占荣1985年4月11日谈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27—328页。这几股农民武装的领导人与刘志丹关系密切,刘屡次派他们出去搞武装,故“每当志丹的武装活动失败后,还有赵二娃等的武装可以依靠,于是很快地就又搞起来了”⑧《马锡五1959年4月28日谈刘志丹的革命活动》,《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10页。。
1931年初,刘志丹聚拢的民团与农民武装被谢牛打散后,赵二娃、杨培盛、贾生财等再次回到陕甘交界地区活动,又发展起来了。其中赵连璧、同守孝有200余人,杨培盛有几十人,贾生财利用社会关系在合水东区搞到民团团总的合法名义,驻在蒿咀铺。⑨《刘景范1983年5月16日谈陕甘边早期革命武装斗争》,《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14页。刘志丹在合水脱险后,先到贾生财民团,后又到赵连璧部队,接着又到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的驻地。在这里通知赵连璧等旧部前来汇合,并进行了整编,将全部人马编为3个大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别担任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全部人马大约有400人,300多条枪。这支由民团、农民武装组成的队伍是南梁游击队最基本的力量。
活动在陕北的“土客队”(保护鸦片贸易的武装)也加入到中共领导的队伍中来。1931年9月,原来活动在山西吕梁山区的晋西游击 队30余人,在黄子文等人带领下渡过黄河,到达陕北。10月,在安定 (今子长)县北区遇到从山西来到陕北杨琪、师储杰等的“土客队”,因阎红彦、白锡林曾在“土客”中做过工作。①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山西革命回忆录》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因此,杨、师要求与晋西游击队一同活动,在接受了约法三章 (一是听从队委领导;二是不抢穷人东西;三是不强奸妇女)后,与晋西游击队合并行动,共约300余人,师储杰任大队长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31—132页。。10月底,师储杰大队到南梁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共计有700余人。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和立足的问题,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本想挂靠在陈珪璋部,但陈表示冷淡,“没搞得成”,③《马锡五1959年4月28日谈刘志丹的革命活动》,《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 (上),第310页。另据刘景范讲述,1931年11月,谢子长与高岗从平凉来到南梁,谢子长与陈珪璋进行了谈判,把部队编为陈部第11旅,谢当旅长,刘当副旅长,部队编为两个团,1团长师储杰,2团长刘志丹兼任,并派马云泽到平凉办理编制与军服事项。当时,接到中共陕西省的指示,独立建立武装,决定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参见《刘景范1983年5月16日谈陕甘边早期革命武装斗争》,《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15页。又据吴岱峰回忆,是“刘志丹当时在自称陇东绥靖司令的陈珪璋部补了个十一旅旅长的名义。这时,陈珪璋派刘宝莹 (系陈珪璋某旅副旅长)来南梁找刘志丹,企图收编南梁一带的武装。刘志丹利用这个机会,派马云泽为他的代表,到甘肃平凉与陈珪璋交涉,并借机要些服装,以解决部队的过冬问题”。参见吴岱峰:《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和发展》,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22页。这件事究竟是谢子长的建议还是刘志丹的想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就活动在陕甘交界地区,以打土豪保障部队给养。以这支队伍为基础,1932年1月,在甘肃宁县柴桥子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
红26军建立后,不仅面临着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的威胁,也面临着活动在陕甘边界地区民团和农民武装的威胁。因此争取和改变周边民团、农民武装是红26军的主要政策。争取黄龙山农民武装郭宝珊部可称典范。郭宝珊原籍河南南乐,逃难到陕西洛川县落户,由于受到官府和豪强欺凌,1931年2月,拉了一些贫民投靠黄龙山土匪梁占魁、贾德功,被封为营长,“但与贾、梁貌合神离,自成系统”。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等率部打韩城时,黄龙的“山大王”也参加了战斗,这时郭宝珊已经了解到红军是打富济贫的,刘志丹专为穷人做事,就产生了与刘“交朋友的念头”。④黄罗武口述,张俊祥整理:《从“土匪”到司令》,《黄龙文史资料》第1辑,第29页。郭宝珊认为“红军是打富济贫,反对苛捐杂税,杀贪官污吏,和我的想法一致,思想上有向往之意”,于是他的队伍自立为“义勇军”⑤郭宝珊:《我的起义经过》,《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610页。。他让部属仿效红军只打“大户”“财东”,决不允许损害贫苦百姓⑥王世泰:《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斗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357页。。他也同情红军,同年6月红军南下失败后,一些红军战士、伤员返回照金,郭宝珊不但没有为难,而且给予了方便。次年春,贾德功民团小头目魏八娃带领100余人到甘泉、富县一带抢劫,被红26军3团缴械,刘志丹给他们讲了红军的政策,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家。魏八娃返回黄龙山后,大肆宣传刘志丹“够朋友,讲义气”,对郭宝珊影响很深。⑦杨茂堂:《回忆西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613页。1934年农历六月初,刘志丹、王世泰派黄罗武去黄龙山与郭宝珊接触,希望他能够与红26军合作⑧黄罗武口述,张俊祥整理:《从“土匪”到司令》,《黄龙文史资料》第1辑,第25—43页。。当时,郭宝珊也想投靠国民党军队,“当正牌军官”,对红军的收编举棋不定。是年秋,杨虎城部冯钦哉第24师“围剿”黄龙山,郭宝珊撤离黄龙山。当郭到达合水时,刘志丹派马锡五送去了慰问品和3匹马。⑨郭宝珊:《我的起义经过》,《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610—611页。10月20日夜郭宝珊到达庆阳北部,宣布参加红军,其部被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郭宝珊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土匪也投靠了红军。⑩《马佩勋谈西北抗日义勇军》,《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79页。
除了郭宝珊外,陕甘边红军还收编了一些小股民团和农民武装。1933年9月,宁县农民何炳在平子镇杀了县政府催粮官及团丁后,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打富济贫,被红军收编后,组建了陕甘边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指挥部第4支队,①《李德禄、罗金财、刘永康谈平子游击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1986年印行,第220页。次年夏编入红26军第1团。1933年7月,中共耀县县委组织农民群众,收缴了北区赵连璧民团的枪,遣散了民团,组成了耀县游击队,有百余人,旋即编入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3支队,同年11月编入红26军第3团。②张邦英:《照金根据地及耀县武装斗争情况回忆》,《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 (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85页;耀县志编纂委员会:《耀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310页。宁县平子镇在抗捐抗税中建立的农民武装有六七十人,1933年11月,枪杀当地地主赵新玉兄弟后,投奔红军,编为陕甘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宁县第三支队③刘永培:《回忆红军游击队宁县第三支队》,《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第838—845页。。同年10月至1934年春节,红军先后缴了南梁寨子刘团头、阎洼李家沟门赵福奎、东华池张世弟、林锦庙马建有、庆阳城壕川王洼子地主武装、义正川高台寨子高团总、洛河川旦八寨子曹俊章等民团枪④刘约三:《西北红军的创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第809页。。春节前后,刘志丹率红军突袭耀县,在路途收编了黄龙山土匪杨谋子部五六十人⑤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第717页。。夏季,中共地下党栾新春、贺吉祥等打入子长县折可达民团,并使其民团一部分哗变,组建了红军游击队第8支队;秋季,地下党员李广生、苗海水等人将该民团所剩40余人全部拉出,编入红军陕北独立1团3连;12月,打入黄天锡民团内部的红军封德俊组织哗变,打死黄天锡及其儿子,率团兵投奔红军,编入陕北独立1团⑥强铁牛:《子长国共军队及战斗概况》,《子长文史资料》第2辑,1990年8月,第71—72页。。这些民团、农民武装的收编或缴枪,不仅解决了部队装备的问题,也壮大了红军队伍。
刘志丹是把活动在陕甘交界处一些民团和农民武装引向革命的关键人物,因他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熟知陕甘交界地区的社会情况与民风,知道如何同地方政府与军阀、民间会社(如哥老会)和民团、土匪打交道,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维系着这支部队。如《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也说:刘“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⑦范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第118页。有两件事情能说明刘志丹在这方面的能力,第一件事情是1931年初,在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刘志丹利用他与哥老会的关系⑧为了使陕甘边红军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刘志丹和一些哥老会大爷交了朋友,哥老会的人见了刘志丹都称“刘大爷”,见面也行哥老会的拜见礼。参见张策:《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为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五十周年而作》,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1986年印行,第19页。,派马锡五 (哥老会的行衣大爷)联系到当地哥老会大爷罗连城,送给罗200两大烟土,罗帮助刘志丹队伍购买了许多子弹、大米、白面,⑨《刘景范1983年5月16日谈陕甘边早期革命武装斗争》,《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13页。不仅使处于危险中的弱小队伍转危为安,而且与其建立了“互不侵犯”的统战关系。第二件事情是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部队来源复杂,既有阎红彦、杨重远等从山西带来的晋西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又有杨琪和师储杰等土客武装,还有一些刘志丹收编的民团、农民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商议,决定采用“拜把子”⑩在陕甘边红军初创时期,“拜把子”是维系部队关系和建立红军武装的方式之一。1930年5月,刘志丹在陈珪璋暂编13师做兵运工作时,就与陈珪璋、谢子长、刘宝堂等18人结为异姓兄弟,刘志丹起草了《结盟誓词》:“我兄弟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如有中途背叛者,天诛地灭。此誓。”参见《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页。又如阎红彦曾与靖边土匪头子张廷芝也“结拜过金兰兄弟”。参见王子宜:《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 《刘志丹纪念文集》,第250页。的旧形式来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按照年龄排列了“八大兄弟”,即师储杰、杨琪、杨仲远、谢子长、刘宝堂、刘志丹、马云泽、阎红彦。①马云泽:《创建陕甘革命武装的回忆》,《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628页。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比较管用而且可行的策略。
总之,中共在陕甘边领导的最早的游击队就是由活动在南梁的民团、农民武装和活动在陕北的“土客队”组成的;红26军建立后,先后收编了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以及一些小股农民武装。这些民团、农民武装是组成陕甘边红军最基本的力量。1934年11月7日,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日子,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此时陕甘边红26军拥有4个正规团1000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②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50页。
三、对陕甘边红军的影响
在陕甘边红军初创和壮大的过程中,兵源主要是民团、农民武装,部队的成分十分复杂。据对红26军调查,在部队的成分中工人占5%,雇工占50%,贫农占20%至30%,其他占20%,“因为部队工人成分很少,所以农民意识特别浓厚”③《红26军1934年6月20日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262页。。这支队伍人员五花八门,思想也不一致,有想真正跟着干革命的,有想发财的,“也有借这个摊子哭他的恓惶”的④《姜兆莹1985年9月9日谈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24页。。这支以收编民团、农民武装组成的部队,面临着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是部队的纪律问题。个别原来民团和农民武装的头目,有吃、喝、嫖、赌、抽、抢的习气,对红军的纪律、宗旨和政策不了解,故纪律成为这支队伍的要害问题。二是红军给养的问题。陕甘边红军初建过程中,给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获取,一个是在没有打出红军旗号前,为了获得粮饷和装备,数次与陈珪璋谈判,求其收编;一个是通过打土豪的办法获得补给,但初建的游击队与红军对土豪的标准不甚了了,多次发生见财物就抢的情况。
因此,在红军初建时期,部队屡屡发生违反纪律甚至抢劫、杀害民众的事件。1931年腊月初,刚刚会师不久的部队路过宁县盘客任家堡子时,遇到当地民众的抵抗,还没有等到部队领导下命令,士兵就一窝蜂似地攻入了堡子,“结果打、砸、抢了个一塌糊涂。堡子里的男人打死打伤不少,女人被强奸,大姑娘吓得用煤烟子把脸抹得黑黑的”⑤马佩勋:《深切怀念子长同志》,《子长文史资料》第2辑,第142—143页;又据张占荣回忆,在这次行动中一支队杀了荏掌堡子 (任家堡子)里的21名群众,高岗对此事进行追查,是一支队战士郭立本带头干的。参见《张占荣1985年4月11日谈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29页。。部队驻陕甘交界的新堡、柴桥子、三嘉原期间,第2支队不断发生夜间外出抢劫事件,商店、脚户、客商、粮食、布匹、骡马等“什么都往回拿”,甚至“不分贫富见财就抢,见妇女就强奸,群众怨声载道,旬邑县地方党也有反映”⑥李维钧:《战斗中成长的陕甘游击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90—491页。。腊月二十四日,为了解决部队粮食问题,派人出去打土豪,赵连璧在打土豪的过程中抢了永和集,“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来了”,还拉了100多头毛驴回来,群众找部队领导反映:“赵连璧抢了他们的毛驴,见谁的拉谁的”⑦《张占荣1985年4月11日谈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 (上),第329页;雷恩钧: 《从晋西游击队到西北反帝同盟军回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86页。。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也不时发生抢劫事件。1932年7月,在陕甘边界遭到“围剿”后,游击队到了陕北“将群众吃的一扫而光”,所过路途,“群众望风远逃”,“百姓骂为土匪”⑧《高岗1932年11月29日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给陕西省委的报告》, 《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213页。。在陕北,从黄龙山收编来的农民武装纪律也比较差,“每住一个地方,杀猪、宰羊,扰得百姓不得安宁”⑨《王四海1986年11月6日谈保安游击队、红二团》,《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74页。。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早期游击队有传统农民起义和绿林习气①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完全发生在陕甘边游击队身上,在鄂豫皖红军建立的早期,“存在相当多诱奸甚至强奸妇女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发生在很多高级干部身上”。参见张永:《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正如马克·塞尔登所言:“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游击队与陕北山里众多反叛和秘密社会小团体,不仅仅在不满军阀和地主权势上一致,特别是在较早年月,他们经常从事绿林好汉行动——劫富济贫。他们的突袭策略和撤返山区与其他反叛团体并无二致。”②〔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50页。这种与民团和农民武装“并无二致”的做法,把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推到了最尴尬的地步,并且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游击队两位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与谢子长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与分歧。争执与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上。第一个核心问题是要不要打红旗。根据阎红彦的说法,刘志丹主张不打红旗,理由是“当时条件不成熟,时机未到,自身力量还小,公开打红旗会引来敌人的进攻……利用军阀名义,发展自己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了再打红旗”。谢子长主张打红旗,理由是“采取这种依靠民团、土匪武装,在军队中搞上层活动的方法,党的武装始终是搞不起来的”,并认为当时有成立红军的条件,“坚决主张公开打红旗,用鲜明的旗帜,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争论中,支持谢子长意见的是少数,支持刘志丹意见占多数。③阎红彦:《关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缴刘志丹的枪的关系与事实经过》 (1963年12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434/13/12/73。因此,1932年1月,这支部队改名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完全是他们自己干的,并不是根据省委指示”。为什么叫反帝同盟军?陕西省委给中共中央的解释是:“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阶级,到处充满乱抢乱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恐怕在群众中信仰倒地。”④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2月15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 (一),1992年印行,第16页。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整顿这支部队的纪律。刘志丹、谢子长都认识到新组建的队伍需要整顿,但分歧在于如何整顿。刘志丹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谢子长主张“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⑤《刘景范1983年5月16日谈陕甘边早期革命武装斗争》,《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16页。。关于打不打红旗、如何改造部队的问题上,在与刘志丹谈不拢的情况下,发生了刘志丹部下赵二娃抢劫群众的恶性事件。为了解决部队纪律问题,谢子长召开了中共党员组成的队委会,未让刘志丹参加。会议认为:“刘志丹部则多是本地人,土匪、民团、哥老会、大烟鬼较多,到处拉票抢人,纪律很坏,虽然有几个党员 (如魏佑民、刘约三等),但都没有实际权力,加上志丹同志坚决不同意打红旗,对这个部队,一点把握都没有。因此就决定先解决刘志丹部赵二娃、杨培胜 [盛]等人的枪。”如何来解决刘志丹领导的第二支队?会议研究决定:“在驻地三嘉原,以集合部队出发为名,出发前由总指挥谢子长讲话,讲话结束后立即缴刘志丹部的枪,并规定对志丹同志不能出问题,只打死赵二娃一人,其他不动。”⑥阎红彦:《关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缴刘志丹的枪的关系与事实经过》 (1963年12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434/13/12/73。这是一次由谢子长主持召开的解决刘志丹第2支队的秘密会议,因布置严密,刘志丹等毫无察觉。由于收编来的民团、农民武装屡屡发生抢劫事件,引发了打不打红旗与如何改造部队的问题,两位主要领导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1932年2月6日,发生了三嘉原事件,谢子长缴了刘志丹第2支队的枪。⑦黄正林:《1935年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肃反问题考论》,《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
第二,影响了中共陕西省委、中共北方局对刘志丹和陕甘边红军的评判。三嘉原缴枪事件发生后,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刘志丹的“第二支队纯系土匪集合而成……时常防备其哗变偷走,而各大队土匪都占绝大多数,在第二大队有洋烟灯八十余架,这些即可证明成分的好坏”;第2支队“时常外出抢人,奸淫妇女,与土匪毫无分别”①《陕甘游击队材料之六 (二月十二日至三月二十日)》,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 (一),第118—119页。。在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把西北反帝同盟军第2支队完全定位为土匪,因此肯定了这次缴枪行动。即便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在各种场合也认为这是一支由土匪组成的队伍,批评之声不绝于耳。1932年6月,中共北方局召开会议,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在会议上讲:刘志丹部都是土匪, “刘是同志,黄浦 [埔]学生,渭华暴动时任过总指挥,军事委员会主席,陕北特委书记,以后和党无形脱离关系”。三嘉原缴枪后成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除在旬邑吸收了很少数的一部分农民以外,大部分还是老土匪,直到现在土匪还占二分之一以上”。②《陕西代表杜励君在北方会议上的报告——关于陕甘游击队产生、“四二六”罢课与党的策略、白军兵变、士兵工作、省委及各地的工作概况等》(1932年6月2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 (一),第200—202页。9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批评游击队的严重错误与弱点时,指出“干部的提拔不是从可靠的工农分子与共产党员而是纯粹军事作战上的老土匪”③《陕西省委关于边区军事计划——粉碎敌人对陕甘边的四次“围剿”》(193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收文时间),《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 (二),1992年印行,第59页。。因此,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坚决的立刻撤换现在游击队中的土匪流氓、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指挥员。对于现在游击队中的土匪成分,应该毫不迟疑淘汰出去。”④《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 (1932年8月25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 (一),第444页。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看来,这支队伍充其量是一支得到群众赞扬的“好土匪”而已⑤《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 (1932年1月20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 (一),第3页。。
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后,并没有改变中共陕西省委对红26军的“坏印象”。红26军大多数成员来源于原西北反帝同盟军和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些人“出身”不好,不能执行党的路线,多次要求中共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到红26军工作。就在红26军成立之初,“因为励君 (即杜衡)对军事不懂,团长 (即王世泰)对领导也没办法,整个形成了志丹参谋长个人意见,所以建议省委很快的派遣政治军事人才到部队来”。⑥《金理科给省委的报告 (第一号)——关于红二十六军及边区工作概况》(1933年□月2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1—3月,1992年印行,第143页。1933年3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央提出“最好派三个得力军政干部来,做政委、团长与参谋长”⑦《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改造省委与红二十六军干部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33年3月23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188页。。尽管刘志丹留在部队中,但陕西省委认为他不适合做上述三个职务。刘志丹在红军和民团、农民武装中有很高的威信,所以在渭北开展工作时,收编了当地一些农民武装为地方游击队。⑧《渭北特派员拓夫关于渭北党的工作情况给省委的报告》(1933年2月6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1—3月,第185页。但受到中共陕西省委的指责,认为“用改编土匪的办法代替了在斗争基础上组织游击队工作。当时在游击队指挥部下有十几个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是怎样 (的)东西呢?都用[是]游击队用委任状改编的土匪,不论什么人来一报名,于是就给他一张委任状,编为多少多少支队,因此,虽在名义上有几十队,但有很些[多]指挥部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土匪部队利用我们的红旗到处随意勒索群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群众谓之‘假红军’”。⑨《陕西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1933年11月25日(收文时间),《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1992年印行,第244页。这些成为中共上级机关评判陕甘边红军时抹不去的阴影。
1934年6月,中共驻北方代表对以刘志丹为核心的红26军领导集体并不满意,认为红42师有两个最严重的问题:一是“现在干部能力最差,一般同志政治水平低”;二是“脱离省委领导与地方党没有联系”,因此“要求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来加强红四十二师的领导”①《中共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关于红二十六军情况向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汇报》(1934年6月20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23页。。同年7月,陕甘边与陕北党政军在南梁阎洼子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的信中指责红26军是“右倾机会主义” “逃跑主义”“梢山主义” “枪杆子万能”,有“浓厚的土匪色彩”②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6页;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74页。。会后不久,谢子长写信给中央驻北方代表,一方面指责“四十二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一方面“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四十二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二十六军的办法”③《谢子长致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 (1934年9月5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32—233页。。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批评红26军的游击队是“招兵买马拉土匪流氓”建立起来的,陕甘边特委执行富农路线,“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和一贯右倾”等④郭洪涛:《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1934年8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412/13/23/24。。1935年1月,陕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再次指责红26军执行的是“土匪路线”,“不能正确地站在劳苦群众利益上开展群众斗争,吸收最好的劳苦群众参加,所以征收的战斗员许多是流亡 [氓]分子,经常把枪扛上跑了”⑤《陕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政治经济、群众斗争及游击队情形、党团组织等问题》 (1935年1月24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第444页。。上海临时中央认为刘志丹“思想很右”,于是7月至8月间,中共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聂洪钧到陕甘边根据地,解决陕甘苏区“右派反革命问题”⑥聂洪钧:《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革命史资料》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第112页;朱理治:《往事回忆》,《朱理治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43页。。由此可以看出,在陕甘边红军和苏维埃建立的过程中,由于与上级和中共中央沟通存在问题,加之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主体是在改编和吸收了大量的民团、农民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成长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违纪乃至抢劫事件,严重影响了上级领导对刘志丹和红26军的评判。
综合上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陕甘大旱灾,迫使一些无法生存的农民或组织民团自保,或落草为寇以谋生计。陕甘边苏区红军创始人刘志丹等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特殊身分,收编了部分民团和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陕甘边苏区初创时期红军游击队和红26军的主要兵源。但是这些收编来的民团和农民武装在最初的革命活动中,出现了违反红军纪律的行为,犹如斯诺所言:“从我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证据来看,似乎没有疑问,在陕西头一两年的斗争中,对官僚、税吏、地主的杀戮是过分的。武装起来的农民长期积压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就到处打家劫舍,扣在他们的山寨里勒索赎金。”⑦〔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 《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正因为这样,红军创始人和红26军被上级领导机关误判,常常受到指责。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来到陕北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北方局乃至中央几乎都把刘志丹和他的团队看做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最后派代表亲自到陕甘边和红26军来解决刘志丹等人存在的问题,肃反的发生也就成历史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