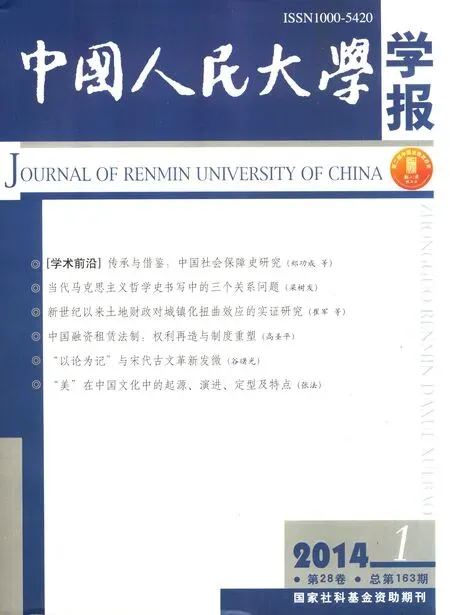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的三个关系问题
2014-01-24梁树发
梁树发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的三个关系问题
梁树发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书写中遇到了以下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客观历史事实和“哲学事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非主流思潮及“相关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对这三个关系的正确处理不仅是提高著作质量的要求,而且是一个哲学史观问题。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和“理论实践”构成哲学发展的“背后故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要讲好这个故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应该写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问题,引发对思想史类著作书写的方法论的思考,即如何处理主流思想与其发展的“相关因素”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两种表现形式,能否正确对待和解读、阐释存在于国家主导思想体系中的以间接形式表现的哲学思想,是对哲学家们的一种挑战和期待。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问题;意义;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既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也反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特点。要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水平,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的质量,就必须处理好这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下三个问题:客观历史事实和“哲学事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非主流思潮及“相关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一、哲学的“背后故事”与哲学思想发展的关系
一些西方学者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化了,这种简化表现在哲学原理和哲学史两个方面。西方学者的批评有它的片面性,也包含某种意识形态因素,但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教材的编写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合理的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简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的编写,都有适当简化的要求,但是,简化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一部通史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编写,由于有内容全面的要求,因而不能有过多的简化。编写中一些细节不被或未被纳入著作内容,往往不是简化的结果,而是这些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无关紧要,或者没有发生实际影响。简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的编写,简化是必要的,但是,简化什么和简化到什么程度,要服从著作、教材的结构和内容的需要,不能任意简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著作、教材的编写,以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构的完整性为前提,不能发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重要理论的遗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编写中,一定的内容被舍弃和简化后,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理论内容、基本过程和基本线索不仅更加清晰,而且不发生重要遗漏和断裂,以反映和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完整面貌。当然,在实际编写过程中,由于对问题的理解和对文本的掌握情况,遗漏总会有的,但这不是刻意简化的结果。一般说来,遗漏是非目的性的行为,简化则是目的性的和自觉的行为。
简化的确有个适当与不适当的问题。造成不适当简化的原因,除文献掌握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哲学史观问题。哲学史是一定的概念、范畴、观点、思想形成、演变的历史,它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但它不脱离历史并且总是形成于和表现于历史之中,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任何一种哲学概念、范畴、观点、思想的形成都能够从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中找到根据。而作为历史事实的首先是存在于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客观历史形势,是以世界性的和根本性的历史形势为内容的时代,是一切进步阶级和广大群众的伟大实践。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几个特点时,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认为“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20世纪初的俄国,“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1](P279)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特点和经验的以上论述告诉我们,要理解和发现一定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定主题(即被提到首要地位的那一方面)和一定概念、范畴、观点和理论的形成,就必须考察作为其根据和根本条件的客观历史形势(它通过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具体方面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行动的条件和实际任务。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不能认为我们不了解或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去分析决定一定概念、范畴、观点、理论形成的背后的事实。但是,又不能不承认我们不大善于做这种分析和说明,不大善于从一定的哲学思想与事实的联系中说明一定哲学思想的产生。在已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历史事实往往只是形式化地被作为理论、思想形成的一般背景放置在理论、思想陈述的前面,而缺乏事实与理论的有机连接。这里存在的简化,可能不是对事实本身的简化,而是分析环节上的简化,是书写者思想懒惰或认识能力低下的表现。
作为哲学形成和发展基础的不仅有客观的历史事实,还有哲学生活或“理论实践”方面的事实。本文把这一方面的事实称为“哲学事件”。“哲学事件”是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各种大的活动,如在重大哲学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围绕重大哲学问题举行的重要会议、对重要哲学思潮开展的有组织的批判、重要著作的出版和重要学术组织的建立等。这些事件、活动由哲学问题引起,有哲学家的广泛参与,对一定时期或长远时期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或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定背景,当然也是其发展的一定条件,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不能没有这些事件、过程的陪伴。它同样是我们理解一定哲学思想如何得以形成、发展的线索。客观的历史事实和“哲学事件”共同构成一定哲学思想或一定时期的哲学发展的“背后故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以及教学都要讲好这个“背后故事”,即讲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每一崭新观点、思想产生的“背后故事”。只有讲好这个故事,才能够讲好一定的哲学,才能够理解一定的哲学。我们要讲好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情况,不能不联系我国这一时期发生的哲学上的“三次大讨论”,即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性质问题的讨论、过渡时期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同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相联系的“哲学事件”还有: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2](P289-306);毛泽东在读到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63年第1期上的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文章后,于1964年8月18日—24日先后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在北京同参加科学讨论会的坂田昌一和各国科学家、同周培源和于光远谈“物质无限可分”和“关于人的认识问题”[3](P389-394);毛泽东在看到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稿和贺龙副总理的批语后,于1965年1月12日所做的批示,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而要讲好“文化大革命”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不能不谈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大讨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讲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这些“背后故事”,是讲好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这个大故事的前提。
问题不只在于要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背后故事”,还在于如何讲好这个“背后故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思想史,要求从历史的事实中发现、发掘思想,要求从事实、事件的连续中把思想的连续揭示出来。不能从事实、事件的联系和连续中发现和揭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的另一种弊病。这个情况在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阐述中和关于我国一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阐述中,表现得比较突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常常被淹没在苏联发生的几次“哲学事件”①“两次哲学论战”(20世纪20年代“辩证法派”与“机械论派”的论战、米丁为首的“正统派”与德波林学派的论战)和“三次哲学大反思”(第一次是1947年6月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的全苏哲学讨论会,第二次是苏共20大前后哲学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第三次是1987年4月“哲学与生活”讨论会)。参见李尚德:《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118~126页、148~18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中。而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哲学发展,也往往满足于对几次“哲学事件”的阐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题或主导线索没有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哲学事件”可能引领了哲学的一定发展方向,也在其中深化了对某一哲学问题的认识,但是,全面的哲学发展不可能仅限于几次“哲学事件”,“哲学事件”之外的哲学的日常发展是整个哲学发展的基本过程。在关注“哲学事件”的同时也能够深入到对哲学的日常发展过程的研究中,才是对哲学发展全过程的和全面的研究,才可能避免重要哲学思想发展的遗漏,才能防止哲学思想发展链条的断裂。就苏联哲学研究而言,如能深入到苏联哲学的日常发展中,我们将有可能对苏联哲学的总的发展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国内有学者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对苏联“哲学事件”做了详细考察之外,还从社会哲学、科学哲学、经济哲学、语言哲学、人的哲学等方面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4]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而是一部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门著作。
二、非主流思潮及相关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写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引起的。有学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出发,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要写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国内出版的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著作使用“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其中包含“西方马克思主义”)列入著作的附录。[5]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都过于简单化,因此,以此为理由而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之外的做法是欠妥当的。这里,我们暂且不去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先假定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探讨在这种认识前提下它是否应该写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问题。我们说,尽管在性质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但只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相关,它就应当被写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是记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发展的著作,它的一个基本过程,也是它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同一切错误思潮的斗争,包括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斗争”,当然只是一种概括的或简单的说法,就其过程来说,它包含研究、对话、批判等具体环节。理想的结果是把包括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内的一切错误思潮消灭掉,但思想、理论的东西与实体性的东西和制度性的东西不一样,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被彻底消除的,客观上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同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长期并存的过程和时期。所以,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生存环境”,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活中的常态和存在与发展的方式。斗争对斗争的双方都会产生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积极的结果是从对方获得对自己发展有益的资源,获得激励自己发展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真理同谬误的斗争看做真理发展的规律,看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6](P230-231)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就应该反映马克思主义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过程,揭示它在同一切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看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相关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相关因素”,也是应该写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书写不能回避的因素。假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所怀疑,那么试想,我们今天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如果在内容上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个著作、教材会是什么样子?它不可能是一部反映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客观过程的著作、教材,当然它也不会是受读者欢迎的著作、教材。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呈现的是一种苏联哲学(即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足鼎立”的态势。“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探讨,核心内容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是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现状而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批判性反思。它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又称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不同的思路、范式、话语甚至结论(其中可能包含许多错误),它也始终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发中保持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它往往是批评性的,并包含误解和攻击的成分)。正是这种对话、交流和相互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因此,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现实表现与意义,使它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起构成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完整画面。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画面就不够完整,就不能完全地和客观地说明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能完全说明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后,苏联哲学终结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①“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与那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宽泛地理解为全部当代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研究区别开来而提出的概念。所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本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创始于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它是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这一特定时段的西欧激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参见王雨辰:《加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观念与方法》,载《河北学刊》,2009(4);梁树发、于乐军:《关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载《理论视野》,2010(8)。也终结了,但是,具有与其相同或相异理论倾向和传统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还在,独立的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象还存在。假若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应换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教材不能够将其纳入其中的简单逻辑,罔顾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那么,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岂不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花独放”?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谈到事件、人物、思想、流派在著作中的“写入”,其意义可能有以下方面:第一,不分事件、人物、思想、流派的性质,只看其历史影响,在著作(与历史同义)中“记上一笔”。第二,具有价值选择和褒贬意味,“写入”著作意味着对一定事件、人物、思想和流派的肯定。第三,通常意义上的“内容包含”。没有特别的价值选择和主观意图,写入与不写入仅仅取决于内容的需要,即取决于客观历史和理论历史阐述的需要。以上所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被写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主张,是第一种和第三种意义上的,绕开了对它的性质与意义的价值评价。我们无论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做马克思主义的(它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支流甚至异端),还是看做非马克思主义的,它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相关因素”,并且是值得“记上一笔”的相关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就没有内容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不能完全地和客观地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问题的思考,也使我们遇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相关因素”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除了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和基本规律外,还有其他一些“规律性现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规律与这个过程中的主要现象和基本现象相联系,它们是前面提到过的客观历史形势和由此决定的无产阶级的行动任务,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及其影响下的理论斗争,是科学文化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能力,以及对理论生活具有直接影响的国家意识形态管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相关因素”的“规律性现象”,是对主要现象和基本现象的补充,是一种“副现象”。它们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马克思主义与方法的关系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诞辰和逝世周年纪念性话语,等等。这些带有哲学意义的规律性现象要不要或者可以不可以写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呢?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目的在于发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规律出发,它们是应该写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或者说,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中,发现和能够读到这些规律性现象。因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中的事实。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书写中的被吸收,可能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更具有可读性、更有色彩,并且更为可信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是我们以往的研究没有发现的,也可能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编写所忽略了的。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哲学家们以标准的(或专业性的)哲学语言、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在有关著作和活动中直接显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一种是以非哲学的语言、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中,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间接显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以该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需要通过哲学家的解读、阐释与发挥而得以呈现。
不能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表现形式与它的两种形态混淆起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形态分别指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表现形式是指其中每一形态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它们中的每一形态都有两种具体的哲学表现形式,这两种表现形式按其表现的直接性与间接性而划分。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语言、思维方式和文本的表面性质来判断一种思想是否为哲学,而忽略或否认在一般理论体系中或在非直接的哲学文本或活动背后深藏的哲学思想。这当然是对哲学表现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表现在文本方面认为:只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才算得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而《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哥达纲领批判》等则不算他们的哲学著作;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只有《实践论》、《矛盾论》才是哲学著作,而《反对本本主义》、《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则不能被视为哲学著作。就文本形式和叙述形式而言,似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能被看做是哲学,而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看做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能被看做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当代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哲学表现或履行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形式与现实,特别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具有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品质,颠覆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形式的传统认识,从而使哲学家们不得不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来,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来。放弃以往那种关于哲学表现形式的单一性的认识已成为必然。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确不直接是哲学或表现为哲学,不是直接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说它们不是哲学。就其内容和具有的意义而言,它们当然是哲学,是一种以非哲学的形式表现的哲学,是蕴含在或深藏于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是需要通过哲学家的解读、阐释与发挥而得以理解和呈现的哲学。这种解读、阐释与发挥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表现形式,可能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的和常态性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国家主导思想体系功能的发挥,一般是与作为国家主导思想体系总体即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融入这个总体中的。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和性质上具有的与政治的关联性。要认识这个总体中的哲学并将它呈现出来,需要哲学家的解读、阐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种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哲学的常规的表现形式,是所谓以哲学的存在和表现形式而存在和表现的哲学,就形式而言,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无特殊性可言。这就是作为学科和专业而存在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和性质上具有的与学术的关联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表现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它们是一种哲学形态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各有所长,因而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并且这种互补性不只在于它们的形式方面,而且在于它们的内容方面。存在于国家主导思想体系中的、间接显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更接近于社会生活现实,并且在哲学创新方面往往有突出表现,因而一方面对于那种作为一种学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在内容上不断补充和丰富以直接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表现形式的关系问题相联系的,是与这两种形式相关的两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队伍的关系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以两种表现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在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一般没有本文所说的以两种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只有所谓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在书写形式上往往表现为对哲学家个人的哲学的阐释,即哲学家个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与记述。但在我们书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中,则少见或几乎见不到我们的哲学家们的“个人的”哲学,特别是在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个人的”哲学。所以,我们书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部分,几乎是无主体的哲学。我们的有鲜明个性和特色的哲学家个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往往见不到。而作为哲学家个人(他们一般是已经不在世的)的哲学思想出现的又往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主导思想体系的解释和阐述。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教材中较为多见的是国家主导思想体系的哲学,但是,就是这一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书写得也不够好。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似乎不大善于、有的甚至不太情愿做这种解释、阐述和发挥的工作。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和教材的编写,一方面,在充分反映国家主导思想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成就的同时,不要忽视或遮蔽我们的职业哲学家们,特别是现世的职业哲学家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的哲学家们也要积极地参与(至少不要有意规避)和善于解释、阐述和发挥主导思想体系中的哲学思想,在两种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联系和统一中书写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 《列宁选集》,3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李尚德:《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 杨春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孙伯鍨、侯惠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下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李 理)
The Three Relationship Issue Concerning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
LIANG Shu-f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we've encountered three pressing problems as follow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philosophical events”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mainstream thoughts,the“correlate factors”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anifestations of China's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Handling them properly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orks,but also an issue of historical outlook of philosophy.“The stories behind”,constituted by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theoretical practices”,should be told efficiently by the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The question whether“Western Marxism”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brings about a rethink on how to write intellectual history,namely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stream thoughts and the parallel“correlate factors”.There're two manifestation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and it is a challenge as well as an expectation for philosophers to properly handle,interpret and expla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state-dominated ideological system but represented in an indirect way.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writing;problems;meanings;methods
梁树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