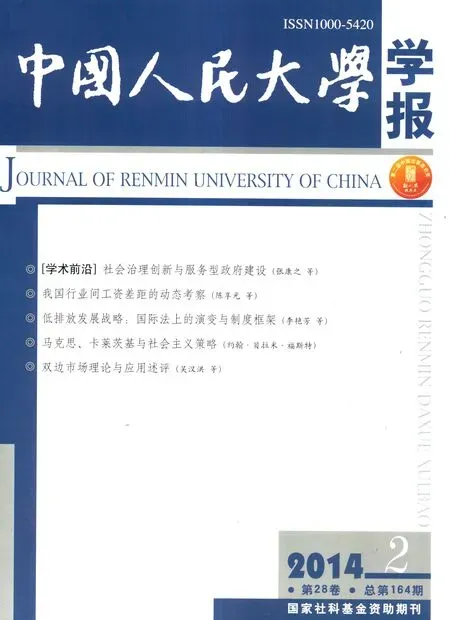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观研究
2014-01-24张冰
张 冰
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观研究
张 冰
近30年来,艺术终结命题引起知识界热烈讨论,作为最早提出此命题的黑格尔便进入了当代视野。客观而言,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观是其哲学体系的自然推衍,但从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伊始,就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主要围绕着它的涵义是否是指艺术的死亡来展开。克罗齐是目前主张从死亡的角度来解释黑格尔这一观点的代表,而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则持异议,从而成为倡导非死亡论的代表。鲍桑葵的意义在于,他转变了在黑格尔那里这一命题仅仅是其哲学体系的逻辑推衍的状态,将它变成了对艺术命运的预测。这恰与当下艺术终结命题的讨论遇合,为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进入当下提供契机和依据。在当代视野中,学者们的争论与交锋,也丰富和拓宽了黑格尔的这一命题,加入了当代意义指向。
黑格尔;艺术的终结;绝对精神;克罗齐;鲍桑葵
近30年来,艺术的终结命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热烈讨论,并于21世纪初传入中国,迅速引起学界关注。知识界常常将其学术渊源回溯到19世纪的黑格尔。然而,国内学界对黑格尔这一命题的关注一直不充分。目前为止,只有薛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第一章中对此做过详细分析。但由于那时艺术的终结命题在西方刚刚引起讨论,因此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而薛著的讨论也还停留在黑格尔本人的思想体系中,其论述依据主要是黑格尔的《美学》,既没有将这种讨论有意识地带入到当时的知识语境,也没有从更广阔的知识链条中去审视黑格尔这一思想的历史价值。进入21世纪后,艺术终结命题开始在国内广受关注,很多学者在讨论时也会自然地提到黑格尔,但此时出现另一种弊端:即不加论证地将黑格尔思想与当下的艺术终结命题混为一谈。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国内关于艺术终结命题的讨论,与黑格尔真正阐述的观点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知识界的这种模糊对于我们无论是对黑格尔的理解,还是对当下正在讨论的艺术终结来说,都是无益的。因此,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回到黑格尔,探讨他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围绕这一命题所产生的聚讼,从今天的艺术终结的视野来审视它的价值和意义。
一、黑格尔艺术终结命题的生成
对黑格尔艺术终结命题的考察,首先需要回到他对艺术的思索。可以这样说,黑格尔对艺术有着超凡的鉴赏力。翻开他的《美学》,其中对很多艺术作品精当而深邃的评析,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是那些作品的典范性阐释。甚而这部理论性极强的哲学著作,也被世人看作是艺术批评和艺术史著作,有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他是现代艺术史之父[1](P282)。黑格尔本人也对艺术特别关注,戏院、博物馆是他经常光顾流连的地方。而有趣的是,在他并不漫长的人生中,对艺术的分析差不多只是出现在他思想后期的著作中。虽然出版于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提到“艺术”,但此时他对艺术基本上还谈不到哲学意义上的关注,艺术被放在宗教下面来考察,与现代艺术观念关系不大。1817年,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出版,在其中的第三部分“精神哲学”中,他将艺术单独列了出来,作为绝对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来阐述。由于这部分在全书占据的篇幅很小,只是从556节到563节,因此还是一个纲要性的描述。这些思想后来在1828—1830年的美学讲演,即我们后来熟悉的《美学》中得到了充分展开。我们对他艺术思想分析的主要依据正是这两种著作。
黑格尔对艺术的思考是以他整个哲学体系为基石的。根据法国哲学家科耶夫的分析[2],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曾经发生过一些变化。最初他的设计是以精神现象学为其整个哲学的导论,以逻辑学统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彼此间是一种平行结构关系。但最终在体现他整个哲学框架的《哲学全书》中,他的哲学体系衍变成了有着先后顺序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在这一有着时间顺序的完备体系中,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平行结构被打破,精神现象学也不再是整个体系的导论,而成为精神哲学中“主观精神”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一体系的前后变化中,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处于宗教之下,作为宗教一部分的艺术被单独提取出来,与宗教、哲学并立,成为绝对精神的三种表现形式之一。而对艺术的理解,也由《精神现象学》中广义上的“艺术”转变为严格被划归为“美的艺术”的现代艺术概念。这种理解上的变化为我们讨论他的艺术哲学提供了可靠基础。
《精神哲学》共分为三个部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艺术作为绝对精神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它承接着第二个部分即客观精神。这种位置也就意味着它自身存在着自然外化的部分,借此与客观精神相对接;同时它还以绝对精神为内核,从而进入到后者的领域,成为绝对精神家族中的一员。这种特殊位置的设定揭示了艺术在精神哲学中的桥梁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黑格尔对艺术思考的路向。从下文的分析中也能够发现,黑格尔正是从这种桥梁性思路来开始自己对艺术的阐释的。
在《精神哲学》的第三部分,黑格尔指出:
“当绝对这个意识第一次有其形状时,它的直接性就在艺术中产生出有限性因素。也就是说,一方面,绝对意识分解成普通的外在存在的作品,以及分解成产生这一作品的主体,这个主体沉思和崇拜作品。但是,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具体的沉思,是绝对精神作为理想的含蓄的心理图画,在这一理想中,或在这主体精神产生的具体形状中,它的自然直接性,只是理念的一种符号,为表达理念而为充满活力的精神所改变,以至于这形状显示理念,并只显示它:这就是美的形式或形状。”[3](P169)
这段话差不多包含了黑格尔对艺术的基本定位,也是他后来在美学讲演中展开自己的艺术哲学思想的种子。
首先,在黑格尔看来,艺术是绝对精神开始展示自身的第一种形式,是绝对精神第一次有了形状时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这种理解一方面使绝对精神有了定在,成为我们可以捕捉的事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决定了艺术的特质,使之成为一种有形体的存在。而又由于形体本身并不是绝对精神的本质构成,因此艺术虽然属于绝对精神,但却被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可以直观的形体,另一部分则是内容,即落实为绝对精神的理念。这种二合一成为黑格尔所理解的艺术的本质。在《美学》中,黑格尔更是明确地将这种二合一的艺术本质描绘成,“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4](P47)这种水乳交融的状态。
其次,这段话还透露出,黑格尔实际上更强调从形式和直观性的角度来理解艺术的特殊规定性。由于有形体,因此直接性是艺术的突出特征,这种特征使之能够诉诸于人的感官,并被直观。再者,这种直接性还包含了艺术是一种形式的意味,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只是理念的符号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理念贯穿于整个世界的发展,绝对精神又贯穿于艺术、宗教和哲学,因此,虽然理念和绝对精神作为艺术的内核,支配了艺术的存在和发展,但它们毕竟不是艺术所独有的东西。所以,最能够体现出艺术质的规定性的东西是其形式,是艺术的形式性特征使之与宗教、哲学分别开来。
再次,黑格尔在本段的第一句话中就指出,绝对精神在第一次有其形体时,有限性也就出现了。在他的哲学中,有限是与无限相对的范畴,是无限的否定物。而无限又是理念发展的终极目标,有限是无限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扬弃的对立面,是理念发展的局限性的体现。具体落实在黑格尔的这段论述中,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绝对精神还处在朦胧状态和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主观性本质上。因此根据黑格尔辩证法,它必须经历外化来思考自身这一特定的阶段,又因为理念的本质是主观的、自由的,所以它必然要回到自身。而这带来的结果是,借助外化来认识自我的阶段只是处于绝对精神和理念认识自我的途中,终将被后者的进一步发展所超越。
实际上,在这段话中,黑格尔对绝对精神的这种有限性的强调,其实质强调的是:从绝对精神的发展辩证法来看,艺术出现伊始,就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它的有形体方面。在前文中我们指出,艺术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的形式,这一点使之与同属于绝对精神的宗教和哲学区别开来,确立自身的独特性。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它终有一天会被超越的宿命。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感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吊诡:具体的形象一方面是艺术质的规定性,是其之所以为艺术的依据;另一方面,从绝对精神的发展辩证法来看,具体的形象又是艺术作为绝对精神的致命伤,是其必然被更高级的绝对精神形式所超越的这一不可逃避的宿命的根源。
在黑格尔的这种设定中,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艺术如果被超越,那么实现超越的绝对精神又将走向何方?被绝对精神发展所超越的艺术生存状态如何?这都是黑格尔应该回答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黑格尔回答说,艺术将被宗教所超越。“当形状和知识的直接性和感性特质被废弃的时候,上帝,就其内容而言,就是自然和精神的基本而真实的精神。然而从形式来看,他首先呈现给意识的是一种心理表象。一方面,这些半图画式的表象赋予其诸内容要素以独立的存在,使它们互为假定,成为前后相继的现象;它还使它们的关系成为依据有限的反思范畴的一系列事件。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有限表象的形式也将会在对一个精神的信仰中和对虔敬的奉献中被克服和弃置。”[5](P176177)这段对宗教的描述中,黑格尔指出了艺术与宗教的区别和联系,同时还指出了宗教也终将被绝对精神所抛弃的命运。艺术与宗教的区别性特质主要在于艺术的感性和直接性。此外二者的内容也有差别。尽管都是绝对精神,但宗教的内容是上帝。这个上帝是绝对精神发展到宗教阶段的具体体现者,它与绝对精神“同出而异名”。宗教的表现形式是一种表象。黑格尔特地对此表象做了限定,即“心理的”表象。这种界定意味着,与艺术外在的、感性的形式不同,宗教阶段的绝对精神(上帝)虽然也涉及到“形”、“象”,借用它们来表现自身,但是这种“形”、“象”是心理的,即主观的、内在的,因此,与艺术不同,宗教已经是绝对精神“向内转”的阶段了。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联系,即二者都没有完全地抛弃“形”和“象”来思考和认识绝对精神。这一点构成了艺术与宗教之间的关联,使前者合理地向后者过渡。查尔斯·泰勒在解释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表象(vorstellung)是一种更加内在的意识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表象(vorstellung)内在化了在艺术中以感性形式得到具体化的东西。”[6](P657)他的这种表达也是在强调宗教所指代的绝对精神是更为内在化的这一事实。但黑格尔又认为,宗教并不是理念发展的终点和顶点,因为在宗教阶段,理念仍然需要借助上帝形象来思考自己,虽然这一形象是内在化的,但这种内在化是具体的个别性和主体性的东西,仍然需要借助“形”来思考,而不是普遍的、内在的思维自身的自反思、自认识。而后者正是黑格尔所理解的哲学的特质。当绝对精神实现用自身来思考自身,思维既是其思考的中介,又是它自己的时候,哲学就取代宗教而成为了绝对精神的表现形式,同时精神的历史也就行进到自己的终点。
关于第二个问题,黑格尔说:“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7](P14)这段话中所传达出的信息引起后世学者旷日持久的聚讼,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给予专门分析。在这里我想着重分析的是黑格尔对他所处时代的艺术存在状况的定位。他认为,艺术的辉煌时代是古希腊时期;艺术的黄金时代是中世纪晚期,即文艺复兴时期。换句话说,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艺术正当其时,与精神的发展同步。在那一段时间,艺术体现着时代精神,履行着精神的最高职责,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在黑格尔所生活的时代,由于“偏重理性的文化迫使”人们“无论在意志方面还是判断方面,都仅仅抓住一些普泛观点,来应付个别情境”[8](P13),这也就意味着,黑格尔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定位为哲学的时代,是以抽象的、以普遍性、主观性为特征的思维来思考精神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的主导精神是哲学。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黑格尔指出,艺术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已经被“引入歧途”。这是因为,第一,“真实对感性的东西”“不再那样亲善”[9](P13),不再崇拜和沉思作品;第二,艺术家受到周围理性氛围的影响,把过多的抽象思想放到了作品里面,这带来了艺术的理论化倾向。很显然,这种倾向与黑格尔本人所规定的艺术的感性本质是抵牾的。
当黑格尔从他的哲学构建出发,指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艺术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不再具有崇高地位,不再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尤其是在《美学》第一卷的结尾,他明确提出,艺术的最后一种类型,浪漫型艺术解体时,有关艺术的终结的话题便由此产生了。
二、黑格尔艺术的终结命题引发的聚讼
当黑格尔在美学讲演中,根据自己的哲学辩证法,推导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哲学作为主导精神的时代,艺术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并进而宣布艺术终结了的时候,他应该没有想到,将约100年后,这一观点居然引起后学旷日持久的争论。
对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命题,从文献研究的情况来看,在19世纪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出版于1885年的英文版《黑格尔美学》,是黑格尔美学讲演的一个节选本,并带有导读。在导读中,翻译者仅仅提到黑格尔对艺术的未来有些沮丧,但实际上他并不重视这个命题,在他所选择的《美学》原文中,没有后世学者经常提到的那些有关艺术终结的段落,他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黑格尔对艺术美与自然美、艺术与科学之间关系等观点上[10]。但当历史又向前行进了100年,1985年,彼特·维斯(Beat Wyss)在其著作《黑格尔的艺术史和现代性批判》中,思路的构建则完全不同。在第一部分,他把黑格尔论述的三种艺术类型即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对应于艺术的清晨、正午和夜晚;在第二部分,他以关键词来组织行文,提举的四个关键词分别为:衰退(degeneration)、衰落(decline)、中心的失去(loss of the centre)和堕落(decadence)[11]。这实际上表明,他基本上是以当下语境中的艺术终结命题的指向为纲来结构全书的。除维斯外,其他作者也都把黑格尔的这一命题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关注。例如泰勒,在其著名的研究黑格尔思想的著作《黑格尔》中有关艺术思想的讨论,对艺术终结命题的解释也是其兴趣点之一。这种变化表明,在黑格尔去世后的100多年以后,随着艺术发生的巨大变化,迫使学界从前人那里寻找资源,从而发现了黑格尔,并将他的这一命题发掘出来,用于解释当代艺术状况。然而,在这种发掘的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对他的这一命题的争议,进而构成一段耐人寻味的学术史。简单说来说,这一争议的核心就是黑格尔艺术的终结到底是否意味着艺术的死亡。
当寻找这一聚讼的滥觞时我们发现,早在克罗齐的著作中,争议就出现了。在1902年出版的《美学原理》中,克罗齐写道:“人们有时从艺术与哲学、宗教鼎立这个看法推出艺术的不朽,因为艺术和她的姊妹都属于绝对心灵的范围。有时人们认为宗教是可朽的,可以化为哲学,因此又宣告了艺术的可朽,甚至已死或临死。”[12](P76)克罗齐在此例举了两种对艺术的看法:一种是以谢林为代表的浪漫派观点,即认为艺术是哲学的极致,是哲学的最高表现;一种是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艺术将被哲学所取代。他对这两种观点都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艺术是心灵的表现,本身并不存在线性的发展问题。因此他接着说:“这问题对于我们没有意义,因为艺术的功能既是心灵的一个必要阶段,问艺术是否被消灭,犹如问感受和理智能否消灭,是一样的无稽。”[13](P76)但是,抛开他本人的知识立场,我们发现,他对黑格尔终结命题的理解,是认为黑格尔主张艺术的可朽,他用的语词是“已死”和“临死”,这代表了整个黑格尔艺术终结命题聚讼中的一派观点,即认为黑格尔主张的是艺术的死亡,相应地,克罗齐也就成为这一派最早提出者。后世很多学者都持与此类似的观点,认为黑格尔主张艺术的死亡,他对艺术的前途是悲观的。例如朱光潜在《美学》一书的注释中说:黑格尔“对于近代资产阶级文艺的评价是不高的,对它的前途也是悲观的”[14](P240)。弗雷德里克·拜泽尔(Frederick Beiser)也认为,黑格尔的《美学》是对艺术的攻击,他认为艺术没有未来。拜泽尔还把自己对黑格尔美学这一部分的讨论命名为“艺术之死”(Death of Art)[15](P298)。
鲍桑葵是较早对克罗齐式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回应者,从而成为否定将这一命题理解成艺术之死的代表人物。在他看来,克罗齐误译了黑格尔的“Auflosung”(终结)一词。他说:“克罗齐反复口头引证的‘艺术之死’这一句子,并没有出现在黑格尔600多页的《美学》中,我确信它也没有出现在他的其他著作的任何地方。这可以表明术语‘Auflosung’被误译了。”[16](P197)鲍桑葵是典型的黑格尔主义的信徒。在《美学史》的“结束语”中,他重点讨论了艺术的前途。由于这部分的论述黑格尔主义色彩非常浓重,我们既可以将其看作是他本人对艺术未来的思考,也可以看作是他对黑格尔的艺术的终结命题的理解和阐释。在这部分中,他明确提出艺术的终结是一种门类艺术的终结,是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艺术的消亡。他说:“首先有必要睁开我们的眼睛,去看一看各门艺术目前的情况,去调查一下在各门艺术中哪些是生气勃勃的,哪些门类在目前条件下是死亡了的,或者处于生机停顿的状态。”[17](P371)并且鲍桑葵还指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占据主流的艺术门类是长篇小说。他说:“近代生活条件在许多方面都十分不利于各门造型艺术。长篇小说(或者说市民叙事诗)则特别适合于近代生活条件。”[18](P372)无论这种观点合理与否,他都是对黑格尔《美学》的一种补充说明,并且也证实了,无论是他所理解的黑格尔的观点,还是他本人所持的观点,艺术的终结都不是指艺术的死亡。与鲍桑葵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也很多。例如海德格尔在谈到黑格尔的艺术终结命题时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新的艺术品和艺术运动的兴起,黑格尔从来没有否定这种可能性”[19](P80)。
从克罗齐到鲍桑葵,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克罗齐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只是从其自身哲学体系出发而已,其中并没有包含对艺术未来指向的思考;但鲍桑葵则不同,他以“艺术的前途”名篇,就已经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仅仅是出于自身哲学体系的推演而出现的终结命题,已经被鲍桑葵转换成对艺术未来的关心了。这种转换恰好与最近几十年有关艺术终结命题的争论遇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有关这一命题的争论,正是对艺术命运和未来的担忧。而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有关黑格尔的艺术终结命题的争论仍在持续。知识界试图在通过对他思想的争论来释放当代的心理焦虑,毕竟在目前,艺术的发展和确定性都成为了一个问题,这让艺术哲学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然而在这种热闹的争论中,我们还是引用薛华先生的话来澄清一个问题:“其实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学说和悲观主义没有内在联系,正如它和乐观主义没有内在联系一样,因为它在体系上讲的是另外一种东西”[20](P28)。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艺术终结命题仅仅是其哲学体系的自然推衍,与艺术的命运无关,当然也谈不到他本人对艺术或悲观或乐观的态度。因此,最近几十年有关黑格尔这一命题的争论,仅仅是借前人之思想,发今人之幽情而已。当下的艺术终结命题与黑格尔本人思想并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接近。
三、当代视野中的黑格尔艺术终结观
即便如此,黑格尔的艺术终结命题还是被带入到当下的讨论视野中来了。这带来了它的当代性,即学者们从今天的艺术终结视野中发掘出了黑格尔思想中更多的内涵,为当下的讨论提供理论支撑,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黑格尔的思想,扩容了他的艺术终结命题。上文中我曾经指出,黑格尔在自己的体系中,推导出艺术逐渐走向理论化,并进而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这构成了对艺术终结命题的最基本理解。除此以外,在当代语境下,黑格尔的这一命题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有意义的指向思考。
首先,黑格尔指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不利于艺术的发展的。这一观点在上一部分中,我已经从他哲学体系的宏大叙事出发做出了解释。即在一个理性化时代,时代旨趣是不利于艺术固有的感性本质的发展和生存的,因为这一时代的人们更需要的是哲学。除了这种理解之外,实际上,在《美学》的第一卷,黑格尔还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虽然这种解释也结合着理念和绝对精神的发展,但他把这种理念的体现者具体地落实在当时整个社会的“教育、科学、宗教乃至于财政、司法、家庭生活以及其他类似现象的‘情况’”[21](P220)等等,用他自己的术语来说,就是“一般的世界情况”上,从而将他的艺术观念带入到一个在我们看来更广阔的天地中来分析,即从艺术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艺术的存在状态。
借助于文学作品,黑格尔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古希腊时期做了比较,从而指出市民社会实际上与艺术的存在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他是通过引入“艺术理想”这一概念来完成自己的分析的。所谓的艺术理想,“就是统一,不仅是形式的外在的统一,而且是内容本身固有的统一,这种本身统一是有实体性的自由自在的状态”[22](P220)。黑格尔赋予了这个概念很多的哲学信念,其中特别突出的便是他对“独立自足性”的理解。根据他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说的独立自足性,是指“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23](P221)。而所谓的个性,或者说主体性是指某个具体的人,所谓的普遍性并不仅仅是指抽象,还指一般世界状况,只不过他的哲学中的一般世界状况最终并不是完全落实在具体的社会生活,而是落实在类似于正义、公正、道德等观念上。在黑格尔看来,普遍性与实体如果没有获得定在,那么就还没有获得主体性,因而不是独立自足的,而个性若未以普遍性为其意蕴,则也构不成独立自足,因此二者的交融才是独立自足的完整理解。
为了进一步澄清自己的观点,黑格尔对古希腊时代的艺术与他所处时代的艺术进行了比较,指出这两个时代具体体现理想的性格方面的质的区别。“英雄时代的个人也很少和他所隶属于那个伦理的社会整体分割开来,他意识到自己与那整体处于实体性的统一。我们现代人却不然,我们根据现时流行的观念,把自己看作有私人目的和关系的私人,和上述整体的目的分割开来。”[24](P231)黑格尔用英雄时代来指称古希腊时期。在这一阶段,性格是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或者说独立自足性就在于人物性格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例如阿克琉斯,他虽然与阿伽门农之间是君臣关系,但他是自由的,完全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行为。这种统一还表现在人物性格的所有行为都需要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立法上。例如俄狄浦斯,当他了解到自己犯了弑父娶母的罪行时,选择是自己惩罚自己。但是到了现代,这种统一完全被打破,普遍性成为人物性格外在的东西,而个体意味着私人,二者已经分离。在现代,人不再是自己为自己立法,而是外在的法律、道德对人进行评判。这些都表明,人不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
黑格尔的这些想法,试图解释的是市民社会与古希腊时代的区别,也许还试图用这种方式捍卫他所崇拜的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的赞美。但在这些想法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黑格尔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指出,现代人和现代艺术都已经必然地处于分裂之中。对于现代人来说,普遍性处于具体的人之外,不再与人合二为一,因此人处于分裂状态。艺术同样如此。当艺术理想是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时,现代社会所能够提供给艺术的却是分裂,它必然地与艺术的本性发生冲突,因此,在现代,艺术不可能再达到理想。理想只能是过去的事了。这是对艺术的终结的另外一种发人深省的理解。
其次,黑格尔的整个艺术观念,从今天的艺术终结立场来审视的话,会发现他解释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美与艺术联姻所存在的困境,同时也暗示出了二者关系解体的可能性。现代艺术观念诞生于18世纪中期。当法国学者巴图将音乐、诗歌、绘画、舞蹈和雕塑等放到一起,为它们冠之以一个共同的名称“美的艺术”时,他为它们能够组成一个家族找到的理由就是,它们都是对美的模仿。对于美是什么,学界至今并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但一般来说,有几个主要特征则是大家公认的,如美是感性的,形象的,具有直观性等。而把美和艺术联系在一起,似乎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很少被人从学理上质疑的一种组合——艺术自然是美的集中体现。但是,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尤其是以杜尚为代表的先锋艺术,强烈抨击将美和艺术看作一体的做法,身体力行地倡导二者的分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先锋艺术逐渐得到知识界的承认,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艺术殿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与艺术的分离被世人所接受。尽管这种分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有很多环节需要解释,但这并不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们的重点在于,艺术的终结这一命题构成中,美与艺术的分离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而黑格尔美学较早地预示出了这种趋势。
再回到黑格尔的宏大哲学体系。在他看来,艺术的本质是理念,它通过形象,即感性直观来显现理念,试图达到对理念自我的认识。感性和形象都是18世纪以来对美理解的题中之义。这一观点似乎可以转换成另一种说辞,即艺术是通过美来显现理念。但是,艺术的本质毕竟是理念,理念终将超越感性的束缚,走向更高的阶段,而对于艺术本身来说,它也终将超越感性,走向另外的方向,例如更为哲学化的道路。也就是说,美与艺术浑然一体的情形只是艺术发展某阶段的状态,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联系。黑格尔的美学为二者关系的可能松绑提供了学理基础。可以说,这也是到了20世纪,黑格尔的艺术哲学能够明确地参与美学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熟悉20世纪的艺术史,就能够发现,先锋艺术正是走在当初黑格尔所规定的路上——放弃艺术的感性特质,剥离艺术与美的关系,将艺术转变成一种思考。
再次,在黑格尔的论述中,还暗示出了艺术终结的另外一种指向,即门类艺术的终结。在他那里,他把作为复数的艺术进行了内部排序,依据是它们所体现出的理念的发展程度。从大的方面来看,他把艺术分成了三个阶段,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这三个阶段意味着理念在不断地向更高阶段发展,因此,当理念发展到古典型时,象征型艺术便终结了。同理,当艺术发展到浪漫型时,古典型艺术也便终结了。从小的方面,即从艺术的内部构成来看,黑格尔将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歌等,排成一个依据理念发展程度而成的序列。他说:“建筑,外在的艺术;雕刻,客观的艺术;绘画,音乐和诗,主体的艺术。”[25](P108)从他的这种描述可以知道,建筑是外在于理念,还没有被理念所渗透的艺术。雕刻则是在建筑物中,将神灌注于无生命的物质堆。从绘画始,艺术开始脱离物质。而到了诗歌,艺术则完全从感性因素中解脱出来,隶属于观念。从这个排列顺序来看,在巴图那里被并列的艺术门类具有了时间性,因而出现被更为主观性的艺术门类所取代的情形。例如,当理念发展到雕刻阶段时,建筑就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成为最高职责的承担者,用黑格尔的话说,就会成为过去的事。而从我们今天艺术终结的立场来看,这也就意味着某种艺术门类的终结。
第四,在黑格尔那里,还有着另外一种艺术的终结的指向,那便是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的《艺术史的终结?》一书中,他把黑格尔看作是艺术史书写模式终结的标志性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从艺术史终结的立场来审视黑格尔思想的合理性。在前文中,我们也曾经指出,很多学者把黑格尔看作是现代艺术史之父。他的《美学》三大卷,从古印度、埃及的建筑讲起,一直讨论到19世纪。可以说,这部著作完全可以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审视。黑格尔认为,艺术发展到浪漫型艺术时,就走向了终结。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理解他的这一观点:即在艺术时代,艺术是最高精神的承担者,根据理念在其内部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艺术史;但是当理念发展到宗教阶段,艺术不再承担着最高职能,这个时候,艺术史的书写必然要转换方式:一种艺术史的终结,伴随着另一种艺术史书写范式的开启。
艺术的终结命题在新世纪初被迅速引入国内,吸引学界长时间关注。但在众声喧哗中,很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人们似乎更愿意仅仅从字面意义去理解这一命题的内涵,从死亡的角度轻蔑地将其作为奇闻怪谈或者胡言乱语。但是,让我们回到黑格尔,回到这个最初提出这一命题的哲学家,通过对其基本观点、围绕着他的艺术终结命题所引发的争论,以及他的这一命题中可能有的意义指向的当代性的阐发和梳理,我们能够更为清楚地意识到,这并不是有关艺术死亡的判决,而或者是从理论出发的哲学推衍,是对艺术现实的深深关切。因此,澄清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会使我们在面对这一命题时,少些意气用事,多些冷静思索。
[1][15] Frederick Beiser.Hegel.London:Routledge,2005.
[2]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5] Hegel.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London:Oxford,1894.
[4][7][8][9][14][21][22][23][24][25]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载《朱光潜全集》,第1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6]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0] John Steinfort Kendey.Hegel's Aesthetics.Chicago:S.C.Griggs and Company,1885.
[11] Beat Wyss.Hegel's Art History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2][13] 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16]Massimo Iiritano.“Death or Dissolution?Corce and Bosanquet on the‘Auflosung der Kunst’”.Bradley Studies.Volume 7.Issue 2,Autumn 2001.
[17][18] 鲍桑葵:《美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9] Martin Heidegger.Poetry,Language,Thought.New Yok:Harper and Row,1971.
[20] 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A Study on Hegel's the End of Art
ZHANG B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In his famous Aesthetics-Lectures on Fine Art,Hegel suggested that art would end.Philosophers after Hegel regarded his view as the origin of the thesis of“the end of art”.This thesis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over the last 30 years in the academia,and Hegel's view is reexamined again.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parts.The first part talks about the end of art in Hegel's philosophy.In the second part which analyses the debates about Hegel's thesis of the end of art,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debates originated from Croce and Basanquet in early 20thcentury.Croce held that what Hegel claimed is the death of art.Whereas Basanquet thought Croce misunderstood Hegel,thus giving rise to a new perspective of looking into the thesis,that is,about the future of art.This new direction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sis under recent discussion.Hence Hegel's opinion entered into a new context and received new interpretation,which is the task of the third part of this paper.
Hegel;The thesis of“the end of art”;Absolute spirit;Croce;Basanquet
张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 张 静)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艺术终结的旅行——从西方到中国”(11XZW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