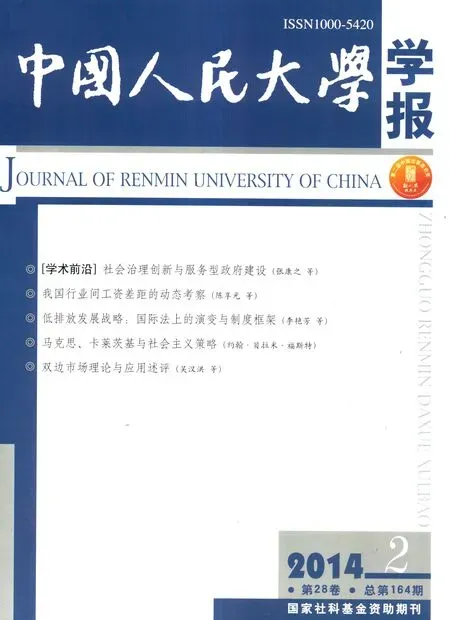共时的“商讨”
——格林布拉特与文学史写作的另一种维度
2014-01-24陈倩
陈 倩
共时的“商讨”
——格林布拉特与文学史写作的另一种维度
陈 倩
在“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下,怎样写作文学史以及写作怎样的文学史成为新历史主义在深化期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培根起,文学史撰述便已向“学术史”靠近,倾向于以历史的方法处理文学和文化事件,从而“文学”成为“史”的定语。格林布拉特从“文化诗学”出发,在澄清人们对培根文学史观的误读基础上,结合雷蒙·威廉斯、海登·怀特、蒙特洛斯、格尔兹等人的相关论说,提出“文学”与“历史”形成一个平等的、共时性的“商讨”场域。他试图证明文学史并非只是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和评判,其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现象。由此,“文化诗学”不仅强调“历史的文本化”,且进一步关注“文学史写作方式的文本化”。国内外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讨论新历史主义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它的诸种文本策略以及跨学科视角,却忽略了它对“文学史”本身的述说及其动因。深入考察该问题对于全面理解文学史观的当代转型有重要意义,它亦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维度。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文学史;共时性;商讨
20世纪80年代,在新左派运动、各种形式主义文论和文化人类学等催生下,新历史主义蓬勃发展。格林布拉特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人,他提出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口号以及基于大量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现象而总结出的一系列文本策略,如“逸闻主义”(Anecdotalism)、“改编式模仿”(Appropriative Mimesis)、“商讨网络”(Network of negotiation)、“自我塑铸”(Self-fashioning)也成为新历史主义勾连“历史”与“文本”的重要途径。
然而,在格林布拉特逐渐被学界关注的同时,他的一篇文章《什么是文学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以往的格林布拉特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文化诗学”对旧历史主义及其他理论的颠覆;新历史主义的各种具体策略;“文化诗学”的跨学科视野。相对而言,《什么是文学史?》在格林布拉特的诸多文章中理论性较强、论述最为抽象,且着眼于一个元命题,与其一贯从具体文本入手阐发思想的写作风格不太相似,容易被忽略。国内对此基本止于简单译介,国外虽有针对它的书评,但大多都是关注此文与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关联,对它的写作动机、对话背景和重要性并没有分析透彻。①此类代表作如Carolyn Porter.“History and Literature:After the New Historicism”.New Literary History.Vol.21.No. 2.1990(Winter,):253-272;John E.Toews.“Stories of Difference and Identity:New Historicism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Vol. 84.No.2.New Historicism,1992(Summer):193-211.
事实上,笔者认为此文是格林布拉特讨论“历史”与“文学”(文本)关系的关键,也是新历史主义提出十多年后,发展到成熟阶段进行自我反思和深化的重要结点。值得关注的是,几乎与新历史主义的发展同步,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热议“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在诸多“重写”的设想中,不乏对新材料、新体例、新思路的探讨。然而,由于对“文学”与“史”关系的辨析不够明晰,文学史写作及文学研究似乎始终难以摆脱传统的窠臼。或许,格林布拉特的反思能为我们“重写文学史”提供一种可能的维度。
一、被误读的培根与“文化诗学”的敞开
在《什么是文学史?》的开篇,格林布拉特开宗明义提出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到应该更新的时候了。雷蒙·威廉斯注意到,在整个中世纪及其前后一千多年里,“文学”与“审美”无关,只是“识文断字”的代名词,它甚至被广泛运用于法律文书中。[1](P466)直至18世纪,“文学”的范围才缩小为与想象和虚构有关的审美形式,这期间起重要作用的是培根的文学史观。
格林布拉特强调,多年以来,人们对培根文学史观的理解侧重于他提倡建立“不受文学和书本知识阻碍”的学术史,从而文学史向学术研究靠近。培根注意收集材料,呼吁“记述重要作家、流派、研究机构”等等,并坚持以“因果律”来判定哪些材料易于和适于学术研究。他宣称应该以历史的方法处理文学和文化事件,尽量不要掺入研究者的个人判断。尽管培根的观点也曾受到争议,但它在后世成为主流:经典文本仿佛传达出每个时代固定的精神;文学史写作提倡所谓“科学”而排斥审美判断;对文本的阐释被认为是评论家而非文学史家的任务。格林布拉特认为,以往学者从这个维度去理解培根的文学史观,从而把文学史和审美趣味区别开来,把学术看作文化的进步和救赎,“文学”逐渐成为“历史”的附庸和定语成分,“文学”在文学史中实际上已经消失了。[2](P472-475)
不难看出,不满于传统“文学史”观是新历史主义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展开批判的逻辑起点。[3](P6)格林布拉特发现,人们很大程度上误读了培根。培根亦曾意识到,如果仅按因果律和学术法则撰写文学史,那么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文学史,因为文学史始终不应脱离对经典文本语言、风格等审美形式的品鉴,这些才是文学的根本。培根强调在历史与学术的表达之外存在某种精神体验,格林布拉特认为这种“精神”实际上是隐喻,只有清楚这一点,“文化诗学”才不会沦为没有“诗学”的“文化”。[4](P476-478)以往文学史家选择性地理解培根,才造成文学史写作只重历史既成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可能性和敞开性。培根最感兴趣的恰恰是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东西,两者的碰撞是文学史应该揭示的对象。
在重读培根的基础上,格林布拉特明确提出,“历史”与“文学”是处于同一场域的“共时性”文本,文学并非历史的修饰语,它们具有极强的“互文性”,两者是循环的过程而非限定。[5](P481)这种思路威廉斯也论述过,他认为艺术作品与历史并不是相互证实,而是持续地相互塑造。[6](P396)格林布拉特称这种相互塑造为“世界与话语之间的商讨”。至此,“文学史”由一个定名结构变成了并列结构,格林布拉特在只重审美形式与只重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文学研究之外开辟了第三条路。
循着格林布拉特的思路,新历史主义的学者们纷纷重新定位文学史。蒙特洛斯指出:“文学的历史就是聚焦的文化语码,并使文学和社会彼此互动的历史。”[7](P393)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等多篇论文中也提到:“对历史文本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偶然事件的创造性与话语性阐释可被认为具有情境主义的诗学品质。”[8](P296)帕特森、伽勒尔、多利莫尔、维勒也都强调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十分相似,“历史转向并不要求文学批评重新转向传统社会事件史和作家生活史,而力图在共时性的历史文本中恢复历史性的文化发展轨迹。”[9](P10)
“文化诗学”最大的实践对象是文艺复兴的文本,这种选择并非偶然。因为文艺复兴是文学内涵最早出现分化的时期,也是文学史的敞开期。长期以来,“古典研究”占据西方文学史写作的核心。到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仍集中于圣经研究。但是中世纪末期至文艺复兴,传统“文学”观却出现一个极大的敞开空间。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出现许多不被以往接受的诸多新型“文学”形式和题材,比如“城市文学”的繁荣。巴赫金在对拉伯雷的研究中,提出文艺复兴艺术的一系列新特征,包括“广场化”、“狂欢”、“脱冕”、“降格”等。文学史描述的对象也发生巨变:从上层精英文本转向下层民间文化,从“大历史”转向“小历史”、从“单线视角”转向“复线叙述”。新历史主义正是从文艺复兴找到了最初的理论灵感。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中,除了培根,对格林布拉特影响至深的还有蒙田。蒙田的写作本身就是对“文学”概念的全新尝试。他主张通过描绘日常生活、社会习俗、个人心理等文化现象来塑成“历史”。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界限,“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和“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是并置的。文艺复兴研究以其丰富的可能性,成为“文化诗学”敞开的最初场域。
首先,传统文学史考察作家作品时常将其与“客观”的人物和事件建立对应的关联,而新历史主义则对文本提供不同的解读渠道,展现多元的文学史。比如《文艺复兴人物瓦尔特·罗利爵士》分析了罗利创作的深层动因。他是著名航海家和诗人,曾在美洲建立第一块殖民地,并镇压了爱尔兰叛乱。因为与伊丽莎白一世产生了恋情,罗利获得垄断羊毛出口、锡矿开采等特权,也得罪了不少贵族。女王去世后,罗利被判处死刑,行刑前在伦敦塔被关了13年。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正是在被关押期间完成的。[10](P79-116)在格林布拉特不无想象的诠解中,创作成为罗利排解苦闷、回忆过往及幻想另一种生活的方式。通过这段被人忽略的逸闻,格林布拉特试图说明“文学”与“历史”始终处于互动中,文学史写作存在多种维度。
其次,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对象往往停留在“经典”,新历史主义认为“经典”是不断变化的,它把文学史指涉的“文本”范畴扩大到文化人类学“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现象。[11](P52)在《神奇的领地:新大陆之谜》中,格林布拉特强调文学史写作并非一成不变,它不断受新的文化类型甚至外来因子的影响,只有“深描”才能获得文学史嬗变的深层机制。[12](P99)格林布拉特十分认同格尔兹的“文化阐释”方法,格尔兹的理论预设是文本与其语境享有平等地位,“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探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13](P3-17)由此,文学史不再是对狭隘经典的被动记录,而成为一个参与文化形塑的主动因素。
最后,新历史主义既强调文学史中的政治、身份、流通等现实因素,又试图超越习俗与理性,寻求审美解放。比如传统文学史大多认为《哈姆雷特》以丹麦的故事讽喻了中世纪的英国。格林布拉特却强调此作是作者的心理写照。1596年,莎士比亚的儿子哈姆雷特夭亡,他的妻子和父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按天主教风俗要为孩子做弥撒。但当时英格兰已实行新教,为亡者祈祷是非法活动,而且新时代的气息也与天主教传统格格不入。所以莎士比亚始终矛盾着,最后也没如家人所愿。[14](P56-79)格林布拉特以独特视角再现了这段文学史公案,即莎士比亚为此写了一部关于儿子努力让父亲的灵魂得到安慰,又不违背人文主义反对蒙昧的戏剧。尽管这种推演有过度诠释之嫌,但可见文学史是多种元素寻求对话与协商的。
二、文学史观的当代转型
当“文化诗学”已在欧美学界有相当影响之际,格林布拉特再来讨论《什么是文学史?》颇具深意,与其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语境下出现的新问题、理论潮流的思考密不可分。
最直接的动因或许是新历史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尽管对历史的写作方式、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有较鲜明的阐述,但如何处理文学史这一介于创作、评论、学术的交叉领域和元命题,其态度始终暧昧。新历史主义的前十年,忙着以颠覆的姿态同传统史学观和其他理论划清界限,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格林布拉特才认识到“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性,开始实际主持《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编撰和修订工作(艾布拉姆斯仍为挂名主编)。《选集》隔几年出一版,在第五版问世时的1986年,正好是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等理论兴起之时,1993年第六版的面貌就明显有所不同:一些非“经典”的作家作品和非“主流”的文学形式(如书信、日记)被收纳进来,评价标准也与过去产生极大区别。而自2000年出版的第七版开始,格林布拉特大胆改革,他的加入使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渗入权威学界。比如,第七版增加了“贺拉斯组画”等跨学科元素,使文学史叙述不再单一,关联性更强。[15]编排体例上也以“专题”为线索,扩大了文学疆界,即如上文所提将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现象全纳入到文学考察中来。再比如,第八版在“奴役与自由”的专题中,新增了洛克、休谟等人的哲学文本;而在“女性”专题中甚至添入伊丽莎白一世、苏格兰玛丽女王等人的书信、演讲和诗歌,以便从不同的视角和身份使女性作品形成对话和“协商”,从而改变了传统文学史呈现出的女性文学面貌。[16]
可见,针对新历史主义兴起后,如何写作文学史这一重要元命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格林布拉特通过“诺顿文学选集”的编撰做出了自己的反思和尝试,《什么是文学史?》正生成于这样的语境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经历了话语和方法的转变,为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史观提供了契机。
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从实证式的社会历史批评到各种形式主义文论再到解构主义的几次转折,评论界出现日益严重的非历史倾向,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被忽视,重新讨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从历史的语境中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意义的呼声也逐渐强烈起来。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力图使文学批评具有现实维度的努力受到尊重,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主张重新开辟文学研究的历史途径。而新历史主义同样作为这种主张的回应和具体实践,逐渐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批评运动。
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著名演讲中指出,各种话语通过“流通”而进行“商讨”,构成当代审美实践的核心。“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纯清的火焰。相反,文艺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是一番谈判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17](P14)格林布拉特进一步强调,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复杂性既不能仅用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新马克思观来概括,也不能完全用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来分析。前者认为现存话语中有关“私人”与“公共”、“诗学”与“政治”、“个人”与“历史”的区分都是虚假的,希望取消话语领域的划分,从无产阶级的未来中重新获得一种整体性;而后者则认为资本主义本质就是垄断式的独白话语,主张向所有的“同一性”宣战。这两种观念都是单一的理论设定,抹杀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丰富性。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既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能共处其中,也不会产生一切话语都截然孤立的机制。[18](P7-13)新批评拒绝单纯从传记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观察文学,但是,流行的解构批评又面临文本意义延宕、价值虚无、所指取消的“无家可归”的困境。新历史主义赞同解构批评对文本开放性的追求,却抵制其无限消解的主张,转而提出解构与建构并重的“文化诗学”观。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文化诗学”而言,“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摆动,从而相互依存与转化,两者中无一具有绝对优越的地位,因为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话语、文本或叙述。传统历史观把文学看成隐喻和象征的体系,而历史是客观、实在的领域,新历史主义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一点。因此,“文学史”观在当代也发生了重要转型。以往的文学史写作是将有限的经典作品按照历史发展的秩序整理出一条对应的发展脉络,故而重心落在“史”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逐渐转变为“文学”与“史”的互释,即同样注重从文学的角度、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描画历史。
文学史观的此种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似乎可以证实当代文化的一系列关键转向。比如传统的文学史以“史”为经线,不免会是宏大叙事的,而新的文学史观更偏于个人化的审美感受;传统的文学史是单线的叙述,新的文学史观则呈现出复线结构;传统文学史遵循历史的必然律,新的文学史观则在诸多纷乱的话语中充满可然性;文学史反映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经典作品,而渗入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回到《什么是文学史?》,格林布拉特最后总结,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将“文学”与其当下文化语境分隔开,因此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只存在现实的“文化书写”。人们对培根的片面误解使文学史写作日益科学化而非诗学化,而“诗学化”既是对传统经典的逸出,也是对经典的复兴;既是对文学史的超越,也是向它的回归。[19](P479-481)
三、“重写文学史”:一种可能的维度
上文已述,《诺顿文学选集》的修订反映了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西方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尝试。英国批评家柯莫德在《关注的形式》(1985年)中亦曾对以“经典”诠释为中心的传统文学史写作提出质疑:“虽然很难看到学术机构,包括招生机构,可以抛弃经典而正常运行,但捍卫经典再也不能由中心体制的力量来进行,也不能由必修课来延续。”[20](P3)美国学者布鲁姆同样针对传统文学史过于学术化和意识形态化,指出“许多同行避开了审美领域,其中一些人至少在当初还有体验审美价值的能力。审美语境中的遗忘是具有毁灭性的……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或顶多视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的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1](P15)可见,无论是经典评价机制的改革还是文学史的日益“文本化”与“诗学化”,当代西方学界已不满于过去新批评或历史主义的做法,试图探求文学史写作的多元维度。
几乎与西方对文学史的反思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国理论界也开始了“重写文学史”的努力。刚刚经历文革后的反思期,中国的文学史写作也希望摆脱政治话语、物质与阶级论的主导,返回审美本身,从“大”过渡到“纯”。[22](P110)在范式转换的基础上,采取了很多新策略。以外国文学史的写作为例,1918年周作人所著《欧洲文学史》可视为我国外国文学史的最早代表,它奠定了以体裁和时代分期为主线进行叙述的模式,但介绍得相当简单。杨周翰等人主编,主要由北大和社科院诸位专家编写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964年和1979年,它基本沿用了周作人的思路,但增加了新的题材,并且加重了19世纪文学的分量,将研究时段延续到20世纪,对作家作品评介得更为细致。20世纪80年代之后,“重写文学史”成为自觉,出现更多试图突破传统文学史的作品。比如1985年朱维之等人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和1987年出版的陈惇等人主编的《外国文学》,均加入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和过去忽略的内容,注意博采众长,使文学史写作更向学术研究靠近。由郑克鲁主编、20世纪90年代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注重点面结合及经典作品的具体分析,相比以往文学史更深入、细致,并且在体例上也形成时代——文类——作家——作品的层级结构,显得更有条理。王忠祥、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1999年)具有创见性地评述了很多被学界忽略的作家作品,比如印度《五卷书》、《百喻经》,希伯来《塔木德》等;突破以往将东西方文学史分开论述的体例,将古代“双希”、印度、埃及、巴比伦、日本等文学并置论述,体现了一种比较视野下文学史观念的革新。
经过诸多学者的不懈探索,我国的外国文学史写作可谓“渐入佳境”。然而,和西方学界所面临的困境类似,这些“重写文学史”的努力仍大多集中于三个方向:其一,在材料选取、“经典”判定和时段划分等方面的改革。其二,在写作体例、题材分类等方面的新尝试。其三,文学观念之争,即以文本和审美为中心,还是以社会背景和相关文化现象为中心。换言之,这些“重写”的文学史极少真正触及文学史写作方式本身,终难从根本上改变“文学”与“史”的关系,总有雷同之感;大多仍以“历史”的方法处理文学,而非从“文学”的角度结构历史,从而无法真正摆脱传统文学史局限于学术史的巢臼。
由此,《什么是文学史?》或许能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维度为我们重新审视和写作文学史提供一种可能的维度:“(文学史写作)将语言塑造的各个领域作为潜在书写对象,拒绝在某种书写形式和另外一种之间假设固定的和先验的界限……意识到所有文学创造力都涉及社会能量的复杂交换和协商过程。”[23](P469)
可见,“文化诗学”不仅强调“历史的文本化”,且进一步关注“文学史写作方式的文本化”。具体而言,“文化诗学”不仅注重“文学”或“历史”材料的展现和判定,而且将此二者的关系及其可能涉及的所有“文化现象”都作为文学史写作的对象,并试图在它们之间建立复杂的、共时“协商”的关联;在以历史为背景描绘文学的同时,也注意以文学的形式书写历史;将文学史写作的方法、视角、观念、故事逻辑甚至读者参与均呈现出来,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元叙述”。在当代形式美学和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之时,文学史本身的“文本化”和“诗学化”或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结语
以讨论人们对培根文学史观的误解为起点,格林布拉特突出了文学史写作的“文化诗学”特征。他强调在当代日益复杂的语境下,尤其是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使得传统宏大结构的“文学史”分化成无数个体化的审美体验和阐释,“文学史”的写作方法也由此必须得以重新定位,即“文学”与“历史”并非传统的定名关系,“文学”并非“史”的附庸,文学史考察的对象也不能再局限于所谓的经典文本,“文学”与“史”应该被放置到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它们是处于一个互文场域的共时性的“商讨”主体。文学史并非只是对文学现象的简单概括和评判,它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学(诗学)现象。
笔者认为,“文化诗学”提出十多年后,已在欧美学界有相当影响之际,格林布拉特再来讨论《什么是文学史?》是有深意的。一方面,虽然“文化诗学”试图将文化的所有层面均纳入隐喻体系,从而促成人类生活的诗学转向,但文学史写作本身几百年来却一直被视为学术活动而非诗学现象。换言之,此前的“文化诗学”强调了“历史现象的文本化”,却忽略了“文学史”写作自身的“文本化”,如果不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新历史主义无法真正跳脱出以史为基点的框架。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普遍不满于传统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开始热议应当如何写作文学史以及写作怎样的文学史,格林布拉特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是文学史?》是新历史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反思和深化之作,在格林布拉特的理论谱系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它应被视为新历史主义讨论“文学”与“历史”关系的关键。格林布拉特提出这一重要“元命题”对于我们更深入理解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以及文学史观的当代转型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内写作新文学史的探索或将有一定启发。
[1][2][4][5][19][23] Stephen Greenblatt.“What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Critical Inquiry.Vol. 23.No.3,1997(Spring).
[3] Louis Montrose.“Renaissanc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Subject of History”.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1986(1).
[6][7] Louis Montrose.“New Historicism”.Redrawing the Boundarie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
[8] Hayden White.“New Historicism:A Comment”.In 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London:Routledge,1989.
[9] 王进:《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批评理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10] Jürgen Pieters.Critical Self-fashioning:Stephen Greenblatt and 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Peter Lang,1999.
[11] 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 Stephen Greenblatt.Marvelous Possessions: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1.
[13]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
[14] 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15][16] Abrams,M.H.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New York:Norton,2006.
[17][18] 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0][21] 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12。
[22] 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责任编辑 张 静)
Synchronic“Negotiation”——StephenGreenblatt and Another Dimension of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CHEN Qi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In the context of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how to write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what kind of literary history should be written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rns for New Historicism.From Bacon,the western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had approached to“academic history”,thus making“literature”the mere attribution of“history”.Stephen Greenblatt clarified the common misreading on Bacon's idea according to his“Cultural Poetics”and combined with related discussion of Raymond Williams,Hayden White,Louise Montrose,Clifford Geertz etc.,proposed that“literature”and“history”are in an equal and synchronic field of negotiation.In other words,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s not only a kind of summary or evaluation of literature,but also a kind of literary narration.Most of previous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concentrated on the subversion and texts strategy of New Historicism but ignored its discussion and discourse background of“the literary history”.Deeper study on this problem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of literary concept,which would be another possible dimension of“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Stephen Greenblatt;New Historicisms;History of Literature Synchronicity Negotiation
陈倩: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