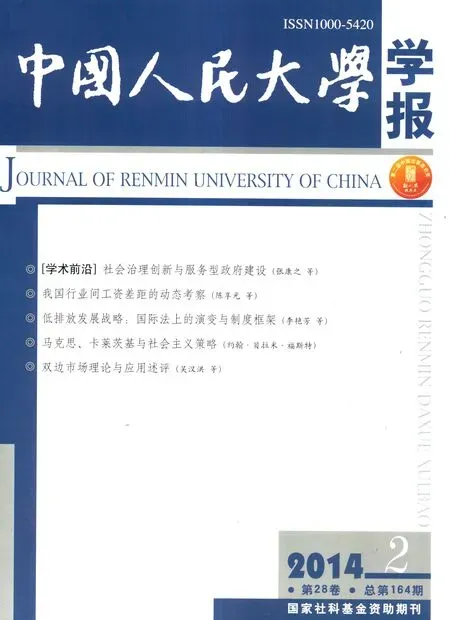儒家“仁”德与他者的痛
——“道德冷漠”问题救治的道德哲学之思
2014-01-24陈继红
陈继红
儒家“仁”德与他者的痛
——“道德冷漠”问题救治的道德哲学之思
陈继红
儒家“仁”德为当下“道德冷漠”问题的救治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具言之,“仁者爱人”确证了“己”对他者的责任,并基于一种“道德主体间关系”指明了此种责任与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体关联性,由此而激发“旁观者”的责任自觉;“为仁由己”喻示了“以德性指引规则”的律令,引导人们重新返回到人本身去思考行为之目的,由此而克服“以规则取代良知”的道德冷漠现象;“三达德”之德性构成昭示了人己两利的实现之途,引导人们在承担对他者责任的同时充分尊重“己”之合理的外部利益需求,由此而消解抑制主体施救于人之意愿的致因。上述资源唯有在“仁”德的现代转化中才能以恰当的方式得以应用。
儒家“仁”德;“道德冷漠”;“仁者爱人”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界关于“道德冷漠”问题讨论的热度渐呈上升趋势,学者们从伦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救治方案。究其实质,这些方案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型:一是外部制度或规则的完善;二是内在德性的培养。显然,前一种方案占据了上风。但是,制度或规则的力量固然有效,却难以避免这样的困境:我们有的是规则、法律和道德体系,却仍然缺乏有道德的善良人。制度或规则的实现无法离开内在德性的支持,如此,从道德哲学的视域思考个体应当成就的内在德性,或许是救治“道德冷漠”问题根本途径。
齐格蒙·鲍曼引用怀贞鲍姆的观点提出了“道德冷漠”问题的应对之策:“至少要出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不同于我们已知的其他任何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超过中介行动以及人的自我在功能上的简化等社会造成的障碍。”[1](P286)在这里,所谓“道德规范”的着重点并非是外在于人的规则,而是与内在于人的德性相关。它的内涵与鲍曼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即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应无条件地承担起自身的道德责任。在中国社会,鲍曼所向往的这种德性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灵魂——那就是儒家的“仁”德。本文意图从多种向度发掘儒家“仁”德中所蕴含的救治中国社会“道德冷漠”问题的有益资源,使“对他者的责任”在人的德性构成中得以充分扩展。
一、“仁者爱人”:“对他者的责任”之确证
“道德冷漠”问题最为典型的表征是旁观者现象。梁启超曾经对旁观者作了刻骨的描述:“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2](P69)百年后的中国,旁观者并没有因梁启超的痛斥而消失,从集体围观他者落水而不愿施救的看客,到“小悦悦”事件中的18名路人,旁观者成为公共生活中持续发生的道德冷漠事件的主角,并以一种强劲的节奏击打着我们的良知,使我们不能不对此作出必要的回应。
鲍曼认为:“所谓旁观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人需要帮助时,他并没有积极地行动起来。”[3](P210)如果说这个解释仅是对表象的描述,那么梁启超的界说可谓直击本质:“旁观者,放弃责任之谓也。”[4](P69)综而论之,所谓旁观者,就是放弃对与“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共场域中的他者应该无条件承担的责任之人。那么,“己”对他者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此种责任的依据又是什么?法学家们希望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解答这两个问题,却难免遭受正当性与可行性的质疑。究其实质,“己”对他者的责任无法从外在的强制力中获得自觉践履的动力,这种自觉的动力应当主要源自于主体内在的德性追求。那么,何种德性能够促发此种自觉呢?儒家“仁”德中关于“仁者爱人”的思考,或许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人己关系构造的基点,引导我们同情他者的痛苦并主动承担对他者的责任。
“仁者爱人”是儒家关于“仁”之内涵的解答,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己”对他者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这个命题表明,作为一种内在于人的德性,“仁”具体地表现为“爱人”这种道德责任,其中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亲亲”,即对亲人的爱;二是“爱类”,即对公共场域中的陌生人——他者的爱。这两层内涵之间的关联只在一个“爱”字,所谓“爱”,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即“惠”,意味着“分财于人”、“恩惠利人”等具体的助人行为。①参见《孟子·滕文公上》:“分财于人谓之惠”。包咸注《论语·里仁》“小人怀惠”章曰:“惠,恩惠。”参见阮元:《十三经注疏》,247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此种“爱”在面对不同的施与对象时具有不同的含义:就“亲亲”而论,具体表现为以“礼”为指导的亲人之间的关心与爱护,如“孝”、“悌”、“友”等等;就“爱类”而论,则表现为对他者的苦难给予无差别的同情与救助。以儒家的观点,这两种“爱”不但在施行次序上存在着先后之别,应当遵循“孝悌为本”或“亲亲而仁民”的路向;而且在程度上亦存在厚薄之分,应当严守“仁者,亲亲为大”所标示的分界。但是,儒家虽然以“亲亲”作为“爱”之起始与重点,但始终坚持以“爱类”作为“爱人”的最终指向,并以“博施济众”式的“爱类”行为作为“爱人”的最高境界。最为重要的是,“爱类”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为儒家所重视,不但韩愈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宋明儒亦以“天地万物一体为仁”为“爱类”立论。近代以降,“爱类”更是取代“亲亲”转而成为“爱人”的中心,如康有为所言:“能爱类者谓之仁,不爱类者谓之不仁。”[5](P81)如此,“仁者爱人”昭示了以“亲亲”与“爱类”这两种责任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责任结构,“己”对于他者的责任在其中得以阐明。
在以宗法等级结构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中,儒家对“亲亲”的认同并不难理解。耐人寻味的是,在公共场域的偶然情境中发生的“爱类”何以可能?或者说,儒家为何要将一种貌似与宗法血缘无干的责任纳入“爱人”之中呢?这个答案只能在儒家关于“仁”的另一种解释——“仁者人也”中寻找。
所谓“仁者人也”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以“仁”之德性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视人为一种道德主体的存在,即朱子所言“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6](P367)其二,明确了人己关系中的交互性责任。注家们皆以“相人偶”为此句作注,如郑玄认为:“人也,读作相人耦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7](P1629)这就是说,“仁”是在人己关系中的展开,作为道德主体而存在的人,“己”与他者在人格上具有平等性,因而应该“以待人之道来相互对待”。[8]综合这两层含义,“仁者人也”喻示着人己关系是一种交互性的道德主体间关系,存在着一种交互性的责任,其前提是对人作为道德主体存在的认同与肯定。
由此可知,作为此种交互性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爱类”的背后隐含着儒家对“人”作为一种道德存在之主体的承认与尊重。易言之,否认或放弃此种责任,便等同于放弃了人之为人的特性。这就使“爱类”获得了具有说服力的理据。但是,仅仅从人的存在方式说明责任的来源,依然不能指向问题的根源。孟子于是将“仁”落实到“人心”上,在“尽性知天”中将人的道德性存在追溯为“天道”,而朱子更是将作为“人心”之“仁”上升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人的道德性存在成为“天理”。于是,“爱类”——“己”对他者的责任便获得了神秘的形而上依据,从而被提升为一种无条件的自然责任。
在儒家那里,“爱类”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重在强调“已”对他者的责任,以他者道德主体性的实现为动机,而不要求他者或社会的对等回报。《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耿宁认为,孟子此处所言“恻隐”是因为“它对另外一个人而言是危险的,我们是为他者担心害怕,我们倾向于做某种不是针对自己,而是针对那另外一个人而言的危险处境”。[9]确实,在孟子看来,对即将入井之孺子的“不忍人之心”或“恻隐之心”,既非契约式的义务使然(孺子与我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亦排除了任何功利的计算(非内交于孺子之父母、非要誉于乡党朋友),更无自保的倾向(非恶其声而然),而是源于一种内生的驱动力:对“己”与他者同为道德主体的认可。因此,“爱类”排除了任何外在的功利计较,充分强调了“己”对作为平等主体的他者无条件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孟子与莱维纳斯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
同时,“爱类”亦表明了“己”与他者之间是一种“道德主体间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昭示了“他者”与“己”的一体关联性。荀子在“仁者使人爱己”、“仁者爱人”、“仁者自爱”这三个命题的比较中,排除了“仁者爱人”中“自爱”的成分。①参见《荀子·子道》中的相关阐述。郝大维、安乐哲亦据此认为这个命题“有自我抹杀的印象”。[10](P122-123)应该说,这种理解是有一定误差的。就“爱类”而论,儒家虽然着力于指向他者道德主体性的实现,但是这个目标是以对人己之间的道德主体性关系的认肯与追求为基础的。孟子所言对孺子的恻隐之心中应当隐含了这样一种心理发生机制:只有在“己”之道德自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生发对作为同类之他者的“自然恻隐”②朱熹认为:“合下制这‘仁’字,才是那伤害底事,便自然恻隐。”参见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282页, 2007。;并且,也只有在实现“己”之存在价值的意向下,“己”对他者的责任才可能排除外在的功利计较。王阳明在解读“孺子入井”时也说:“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11](P1066)这是以“一体为仁”阐明了上述孟子隐含的思路。如此,“己”对他者的责任实际上成为“己”之道德主体挺立——“成己”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他者’奠定了我作为主体的伦理本质”。[12](P11)
“仁者爱人”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理解旁观者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旁观者的道德认知中,由于缺乏一种“类”本质的自觉——对人之道德存在方式的认肯,因而将“己”与他者视为原子式的个体,否认了二者作为“类”的同质性与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承担对他者的责任与“己”之价值实现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于是便产生了如“责任分散”等诸多功利的计较。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从德性养成入手,将“仁者爱人”的内涵灌注到人的心灵中,在人己之间确立一种道德主体间关系,使人们充分认识“己”对他者的责任与“己”之自我实现(“成己”)的一体相关性,同情他者的痛苦并施行救助的行为。
二、“为仁由己”:德性对规则的指引
在当下中国,另一种“道德冷漠”的蔓延令我们触目惊心,如拒治无钱病人的冷漠医生、为追逐新闻而偷拍自杀场景的冷漠记者、制造“毒奶粉”、“毒胶囊”等无良企业中的冷漠员工等等。作为同一类型“道德冷漠”事件中的主角,他们的行为呈现出共同的特征:以组织规则取代个人良知,以此克服对他人悲惨命运的动物性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责任指向发生了转移,“我对他者的责任”必须屈从于“我对组织的责任”。在鲍曼看来,这种屈从意味着要“消除个人自己的独立特性和牺牲个人自己的利益”[13](P29),即放弃个体内在的德性追求,或者说,德性“被减化为单数的德性,这个德性就是一种服从道德规则的性向”。[14](P111)
这一问题的致因与现代规则伦理饱受争议的“短板”不无关联。正如麦金太尔所指出的,现代规则伦理视规则为“社会生活的首要概念”,而“美德的正当性取决于规则和原则的某种在先的正当性”。[15](P133-134)这种只注重规则的单边主义以如何解决利益冲突为中心,忽视了“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之目的性诉求,因而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种冷漠的工具理性。而现代人却将之奉为圭臬,因而陷入了“以组织规则取代个人良知”的误区。按照麦金太尔的观点,似乎应该回到亚里士多那里寻找美德资源;我们则认为,儒家“仁”德中蕴含着更为有效的应对“道德冷漠”问题的理论资源。
如前所述,“仁者爱人”中已然包含了“成己”的目标,但仅仅是确证了这一目标的应然性与潜在性,而并没有指明从“偶然所是的人”向“可能所是的人”转化的实现方式。如果缺少这一环节,那么人们虽然在对“成己”目标的认肯中拥有了自觉承担对他者责任的意愿,但是这种意愿很可能在功利的计较中屈从于外在的压力而放弃。儒家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于是在“为仁由己”中接续了“仁者爱人”没有完成的任务。
孔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句话明确地指明了“成己”的实现方式:以内在德性指引行为规则,实现二者的内外统一。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其中的逻辑及其意义?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仁”所指在何?其中的答案可以从“仁”的意义结构中寻找。所谓“为仁”之“仁”,并非仅仅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德性”,更非规则伦理意义上的“规则”,而是如陈来所指是一种“德行”。①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七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论语〉的德行伦理体系》,载《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所谓“德行”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前述之天命于人的内在德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之存在方式的表达;其二,指外在之行为。儒家认为,“仁”之德性只有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中才能真正实现,即所谓“力行近乎仁”(《中庸》)。在这个层面上,“仁”为人的行为设定了“应该”或“不应该”的具体规定,因此亦具有了“规则”的意蕴。芬格莱特认为,“仁”这种力量必须从行为者散发出来,因此,不应当将我们的注意力指向人的“内在”方面,而是要指向他的行为。[16](P55)这显然是从行为层面限定了“仁”的意义结构。如果认同这种理解,那就意味着承认“仁”是规则伦理意义上的外部利益冲突的产物,其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如此,“为仁”便将成为一种机械的遵守规则的过程。而在这个意义上,“为仁”只能说是“由人”——对外部强制力的屈从,而“由己”——“主体自身力量的体现”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②杨国荣将“由己”释为“主体自身力量的体现”,本文对此有所参照。参见杨国荣:《善的历程》,2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芬格莱特也承认:“它是人类(当他们成为真正的人时)的一种力量,它指向人类并影响人类。”[17](P55)这就表明,所谓“外在”的行为并不能摆脱人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仁”的意义结构中,内在之“德”居于主导地位,决定了外在之“行”(规则)的目标与内容;同时,内在之“德”又必须以外在之“行”作为表现形式。由此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为仁”始终是以“成己”——“己”之道德主体性的挺立作为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内在的德性追求指引并决定着外在的行为规则,德性与规则是内在统一而非外在对峙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仁由己”的内在逻辑。
由是,“为仁由己”的灵魂在于“以德性引导规则”的律令,这一律令完全来自于人性的要求,内含着康德式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意蕴。在此律令的指导下,人们能够在功利与“成己”的较量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如果说孔子在“由己”与“由人”之分中已经含蓄地表达了这种较量,那么他关于“安仁”与“利仁”的辨析则使这层隐约的意涵浮出了水面。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作为具有外在相似性的道德实践活动,当自我实现与外部利益之间具有一致性时,“安仁”和“利仁”的辨识度并不高。但是,当这种一致性被打破时,二者的根本差异就会浮现出来:“安仁”者“安其仁而无适不然”[18](P69),不会屈从于外部的压力而放弃德性追求;“利仁”者则屈从于外部利益的要求而放弃“仁”之践行。究其实质,二者的分界点在于对“为仁”之理解方式的差异:“安仁”以其为一个德性指引规则的过程,“利仁”则以其为规则决定德性的过程。皇侃与程树德皆认为“利仁”为“智”而非“仁”,应该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①皇侃认为:“利仁者其见行仁者若于彼我皆利,则己行之,若于我有损,则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程树德也认为:“无所为而为之谓之安仁,若有所为而为之,是利之也,故止可谓之智,而不可谓之仁。”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228~2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安仁”与“利仁”之分进一步阐明了“为仁由己”所表达的“以德性指引规则”的意义世界:“成己”始终是外在行为的目标指向,当这一目标诉求与外部利益发生冲突时,主体应该坚持以强大的内在力量拒斥外部规则对内在目标的挤压。只有这样,“仁”德才能真正实现。
在儒家那里,“以德性引导规则”的决定性力量并不直接来源于神秘的“天命”,而是诉诸人的自由意志。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里包含着如下的逻辑进路:“人”之自觉→自由意志作用→“仁”之获得。分而述之,“仁远乎哉”是一个理论前提,此即“仁者人也”的另一种表述,表达了主体对人之存在方式的自觉。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我欲仁”的观点,将“仁”的获得归因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易言之,“我欲仁”是一个主体自由选择、自由决定的过程,这种“自由”的主导力量并不在于诸如社会制度、组织规则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是来源于“我”内心的呼唤——由对“仁远乎哉”的认同而产生的理性自觉。在此种自由意志的作用下,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充分显扬,而“以德性引导规则”因之成为可能。由是,“天命”的、内在于人的“爱人”之责任便可以冲破种种外在的阻隔而由潜在的意愿变为现实的行动,“仁”得以真正实现——“斯仁至矣”。而作为“爱人”的一项重要内容,“己”对他者的责任便不可能因为外部规则的压力而被无奈地弃置。如此,“仁者爱人”便由意愿转化为行为。
由上述可知,“以规则取代良知”的道德冷漠现象意味着“成己”目标的迷失,这种迷失使得人的自由意志为外在的强制力所操纵,行为的动力不再是人性的自觉,而是理性计算下的利益角逐。在这个意义上,人不再成为目的本身,而是沦落为逐利的工具。而“为仁由己”的意义正在于引导人们重新返回到人独有的存在方式去思考道德行为的意义,使人们通过主体自由意志的显扬,遵循“以德性指引规则”的律令而行动,以此排除外在力量的侵扰,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规定。由于道德行为的内生性,道德冷漠带来的另一种精神困扰——外在行为与自我价值的分裂问题亦迎刃而解。
我们不能否认麦金太尔的思考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但是,他也面临一个难题:在规则以系统而严密的姿态存在的现代社会,以德性伦理取代规则伦理能否成为现实?然而,在儒家那里,这一难题却并不存在。“为仁由己”始终贯穿着西方古典德性伦理意义上的“好人”之目的诉求,在这一点上,儒家和麦金太尔是一致的。但是,“以德性指引规则”并没有宣告规则的消亡,而是给予了其恰当的定位:退居于德性之后而作用。所不同的是,儒家并不认为两者是一种并行关系,而是一种“指引”与“被指引”的关系,这在儒家关于社会规则——“仁政”的思考中更为明显。①《孟子·公孙丑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表明孟子是以主体德性的实现为目标指引社会规则的制定。因此,相对于麦金太尔而言,“为仁由己”是一个更加温和、也更加适应“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
三、“三达德”:人己两利的实现之途
助人行为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自我牺牲,如时间、财产、健康等外部利益,这种自我牺牲甚至会达到一种极端状态,如生命的付出;也有可能会招致一种恶的结果,如彭宇案、许云鹤案等折射出的助人者“好心不得好报”、“好心反得恶报”的道德悖论。如此则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助人行为是以排斥“己”之外部利益为前提的。这种理解极大地干扰或抑制了主体施救于人的意愿,因而成为诸如“扶不起的老人”等道德冷漠现象的致因。
此种致因固然与制度设计的缺陷有着重要的关联,但是,从主体的道德能力来看,确有可究之因。从种种陷入被“反咬一口”之困境的案例来看,主要根源当然在于被救者的道德水平或社会制度的缺陷等问题,但施救者道德能力的缺乏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此,我们不但应当承认诸如完善“见义勇为”奖惩规则等外部制度的重要作用,同时亦不能忽略完善主体德性构成的独特价值。
关于后一种向度,儒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他们看来,助人行为仅仅依靠“仁”德是无法实现的,还要辅之以“智”与“勇”这两种德性,在此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己”与他者的利益皆能得以保障。在孔子那里,此三种德性作为君子德性构成的三大要件而被正式提出。孔子的主要论述如下: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在上述德性次序中,存在着“仁”与“知”(智)的先后差异。朱子认为此种差异在于阐述角度的不同:“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此诚而明,明而诚也。”[19](P985)这就是说,从德性构成上看,应该是“仁”、“智”、“勇”之渐次展开,“仁”在其中居于首要地位,同时,“仁”的实现又必须获得“智”与“勇”的扶持。
这种意味首先体现在“仁”、“智”之辨中。在先秦儒家那里,对“知”的理解有三个层次:一是“知人”,即经由对人的能力、品格的明辨而形成的政治智慧;二是“成物”,即对万事万物内在规律的把握;三是“是非之心”,即通过知识的掌握而形成的理性推断、分辨能力。在上述不同的理解中,第三种解释具有贯通之义。这一点在《白虎通·性情》中得以阐明:“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朱子亦认为:“知是一个分辨不乱之意。”[20](P984)在儒家那里,“智”与“仁”同为天命的、根植于人性的德性,并与“仁”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仁”对于“智”的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孔子认为,“仁”是“智”之实现的保障条件。②参见《论语·卫灵公》:“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中庸》则认为德性的完成是一个由“仁”及“智”、由内而外的自然发展过程。③参见《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另一方面,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孔子亦指出了“智”对于“仁”的扶持作用,并由此以“人己两利”作为实施助人行为的合理限度。《论语·雍也》中有一段话: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在这里,宰我设置了一个情境:“井有仁焉”——有人陷落于井,而且这个人是与“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他者。宰我的问题是:一个已经具备仁德的人,是否应该自投井中救人?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其一,在此场景下,仁者是否应该承担救助他者的责任?其二,此种救助行为能否排除自我的利益需求——譬如生命?第一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孔子以“可逝”与“可欺”表明了救助义务的必然性,这与前述“仁者爱人”、“为仁由己”的立场是一致的。关于第二个问题,孔子则以“不可陷”、“不可罔”表明了“智”的考量对于自我利益保障的意义。在此种情景下,所谓“智”的作用包含了如下之理性推断、分辨过程:(1)对“井有仁焉”之真伪的判断。在孔子看来,这个过程是“可欺”的,并非关键所在。(2)对自身能力的判断及后果的预期。孔子之所以不赞成自陷以救人,因为这种行为超出了自身能力的许可范围。虽然其动机是善的,但结果却是恶的:不但不能实现对他者的责任,亦无法保护“己欲”。(3)对救助方案的选择。对于落井之人,孔子既认为有必救的义务,又不赞成自陷以救人,那么,他的方案是什么呢?朱子阐明了孔子隐含的意思:“盖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从之于井,则不复能救之矣。”[21](P91)这就是说,应当结合实际情境与自身的实际能力,选择人己两利的救助方案。由是,在孔子看来,助人行为首先发端于“仁”——施救的意愿与行为,必须以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作为代价;同时,此种自我牺牲必须是在“智”之作用下的考量,在积极承担对他者责任的同时,应当充分保护“己”之合理利益需求。因此,以“智”作为“仁”之必要补充,是人己两利的实现之途。
在类似的“孺子入井”的情境中,孟子虽然没有明言“智”的意义,但是应该有类似孔子的考量。此种推论基于如下两点:其一,孟子认为,“己”对他者的责任应该以对自身能力的确认为前提,这其中已然包含了“智”的判断。孟子举了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挟太山以超北海”,二是“为长者折枝”。①参见《孟子·梁惠王上》的相关论述。他认为,前者已然超出了“己”之能力范围,后者则在“己”之能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这正是践履对他者责任的立足点。此种理性判断显然是“智”的作用过程。孟子虽是在喻示“仁政”的可能性,但是,所谓“仁政”是从乍见“入井孺子”的“不忍人之心”推出来的,因此,“智”当然也要参与日常的助人行为。其二,孟子明确地指出了“智”对于“仁”的认知与守固作用。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在孔孟的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概括了“智”之于“仁”的辅佐作用:“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在上述“井有仁焉”的情境中,作为“三达德”之一的“勇”的价值何在?在儒家那里,“仁”、“智”双彰被视为理想人格的全部内容,而“勇”德似乎被排除在外了。实际上,儒家不但以“勇”为“仁”、“智”实现后的自然结果,而且看到了“勇”对于二者实现的独特价值。所谓“勇”,即孔子所言的“不惧”,是指一种面对死亡与危险的无畏的态度以及果敢的决断能力。孔子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勇”在三达德中的意义,这个任务是由宋儒来完成的。朱子认为:“有仁、知而后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盖虽曰‘仁能守之’,只有这勇方能守得到头,方能接得去。若无这勇,则虽有仁、知,少间亦恐会放倒了。所以《中庸》说‘仁、智、勇三者’。勇,本是个没要紧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则做不到头,半途而废。”[22](P985)如此,“勇”对于“仁”与“智”的意义得到了系统的阐明。联系上述“井有仁焉”的情境,“勇”在其中应有参与。在“智”之作用的最后步骤——救助方案的选择之后,应该是作为“着力去做”的“勇”之出场——实施方案。如果缺少了这个“末后工夫”,那么“智”的选择只能停留在心理思考的层面,而“仁”——对他者的救助意愿则成为空想。不但如此,“仁”中所包含的“行”之意蕴,亦当是在“勇”的推动下实现的。由是,儒家不但以“智”弥补了“仁”之缺陷,更以“勇”作为“仁”与“智”之实现的着力处。如此,在“三达德”兼备的状况下,对他者的救助便成为一种无可疑虑的责任。
就现代社会的助人行为而言,倡导“三达德”的意义在于:在实施助人行为的过程中,施救者应当充分运用“智”的判断,即对自身的行为能力的认知与救助方案的选择。如此,我们才能在实现他者主体性价值的同时充分尊重“己”之主体性需求,在合理的限度内牺牲自己的利益,一般来说,这个限度即“己”的合理性利益需求——如生命、名誉、成就等。当然,这个标准可以根据主体不同的道德追求而有所变化,舍身救人是英雄主义式的崇高追求,人己两利是普通人的合理限度,人己俱损则是应该避免的限度。其中,“人己两利”又可以根据自我牺牲程度的不同区分出不同的境界(这是一个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此外,“智”的判断亦需要“勇”——具体行动的推助,使心理层面的选择方案成为现实的行为。当前,我们提倡“见义勇为”与“见义智为”的结合,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才能得以解释。综而言之,在“仁”之“爱人”、“智”之“理性”、“勇”之“行动”的共同作用下,主体施救于人的意愿才能最大程度地得以释放,助人行为亦才能获得公允。
四、“仁”德的现代转化及其困境
从主体德性构成的角度言,儒家“仁”德确实为“道德冷漠”问题的救治开出了一剂良方。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儒家“仁”德是以“亲亲而仁民”为践行路向的,认为“爱类”必然是从“亲亲”中推衍出来,以“亲亲”为自然之基。在这种路向下,“爱”在“礼”所规定的等差次序下由亲人推至他者,以至于“爱类”之“爱”是非常稀薄的。不能否认的是,儒家的这种思考与传统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相适应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然而,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儒家“仁”德所依赖的等差之爱的根基已然不复存在。随着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张,对“爱类”的需要甚至已经超过了“亲亲”。因之,儒家“仁”德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只有在现代转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恰当的方式汲取儒家“仁”德中的“爱类”资源。
在“仁”德的现代转化过程中,面临着一个与我们的讨论主题相关的理论困境:是否应当割断“爱类”与“亲亲”之间的联系?易言之,是否应当将“爱类”的根基依然落实到“亲亲”上?之所以称为“困境”,是因为正反两面的答案皆面临着反向的诘问。
近代以降,一些学者断然否定了“亲亲”外推为“爱类”的可能性。其中,一种路向是间接的否定,如谭嗣同提出了“仁—通—平等”的伦理原则,将“仁者爱人”解释为资产阶级的平等关系,并充分肯定了墨家“兼爱”的价值。孙中山则以“博爱”释“仁”,而他所谓之“博爱”,是以“为人类谋幸福”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博爱。[23](P510)以上观点以“兼爱”或“博爱”取代了“仁爱”,间接地否定了“推”的思路。另一种路向是直接的否定,认为“爱类”是无法从“亲亲”中推出来的。如韦政通认为:“以己为中心的推爱,无论在事实上或理想上都跳不出差序的格局。”[24](P13)何怀宏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并不是说爱人可以从自爱中逻辑地推演出来,因为这里根本推不过去,或者推过去也是只有越来越稀薄一途。”[25](P111)按照上述思路,“仁”德的现代转化必然是以否定“亲亲”外推的路向为前提。但是,如果否定了“亲亲”,那么,如何解释“爱”之情感的自然根基、使“爱类”得到人们的心理认同?进而言之,否定了“亲亲”的根基性意义,如何成就“善良的人”?而没有了“善良的人”,“道德冷漠”救治的根本性出路就被堵塞了。
与以上观点针锋相对的是,一些学者充分肯定了由“亲亲”外推至“爱类”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如贺麟认为,普爱是先平实地从等差之爱着手,推广推充,是善推其等差之爱的结果。[26](P61-62)罗哲海也认为,亲人之爱“可能是一种发展过程上的前提,因为家庭乃是人们首要履行道德的地方,而后才能逐渐扩大范围……在家庭中自然培养起来的爱,终将成为对待外人的模式,但决不会以舍弃父母为代价。”[27](P164)杨国荣则指出:“在孔子那里,以孝弟为本与肯定仁道原则的普遍性,并不存在内在的紧张,毋宁说,前者乃是后者的逻辑前提。”[28](P16)按照上述思路,“仁”德的现代转化应该肯定儒家“外推”的基本路向,继续将“爱类”的根基落实到“亲亲”上。但是,如果依然肯定“亲亲”的根基性意义,那么,如何使“爱类”走出人情差等的窠臼、适应公共空间日益扩展的需要?事实上,已经有批评意见指出,儒家“仁”德所展现的等差之爱正是“道德冷漠”问题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
也许,我们可以有调和性的第三种思路。可以肯定的是,“仁”德的现代转化并非意味着离开其传统内涵的支持而另起炉灶,而应是在其基础上的更新与改造。在此前提下,我们的思路是:在肯定由“亲亲”而“爱类”之外推的基本路向下,充分扩展“爱类”在“仁”德中的比重。关于前一点的理据在于:其一,从恻隐之心的生发机制来看,“亲亲”是“爱类”的自然根基。如孟子所言,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在其感发之时,必然是以“亲亲”作为其根本的基础,“亲其兄之子”必然胜于“亲其邻之子”,此正是人情之自然感发机制。①参见《孟子·滕文公上》夷子与孟子的论辨。如果否认了这一点,必然会陷入墨家以“兼爱”为标志的功利主义的泥淖。如是,“爱类”便由一种内生性的责任而变异为外生性的责任——对规则的服从,由此必将导致前述之“以规则取代德性”的“道德冷漠”现象。其二,从个体德性养成来看,“爱类”的养成离不开“亲亲”的内在支持。梁启超认为:“就析义而言,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由是,“公德者,私德之外推也”。[29](P119)作为公德的“爱类”养成的核心是“爱”之情感的培育,而其基点正是作为私德的“亲亲”——父母子女之爱的培育。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爱父母子女的人如何成为“善良的人”?而缺乏一颗善良的心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出对他者的爱?
在肯定外推路向的同时,我们亦应认识到,唯有充分扩展“爱类”在“仁”德中的比重,才能使其与现代社会的结构形态相适应。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特征使得以职业或社会交往为中心的公共场域成为人们越来越依赖的生活共同体,而家庭(家族)共同体的中心地位已经退居其后。在此种情状下,我们需要重新解释“外推”的内涵。所谓“外推”,并不意味着“爱”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稀薄,而是意指将“爱”的关注点从家庭生活转向公共生活,在自身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自觉承担对他者的责任。至于“亲亲”与“爱类”之间的比例构成,则取决于主体自身的能力与道德追求。
这一思路是一条“中间道路”,汲取了前两种思路的优势,并力图解答它们面临的诘问。但是,它也面临着一个问题:“仁”德中所包含的“仁者爱人”、“为仁由己”、“三达德”等思想资源与作为公民道德的“乐于助人”等规范如何衔接?无论是张岱年式的“循旧名作新名”的思路②参见张岱年:《试论新时代的道德规范建设》,载《道德与文明》,1992(3)。,还是方克立提出的以传统文化作为“支援意识”的方案③参见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载《红旗文稿》,2009(1)。,对于发掘儒家“仁”德救治当前的“道德冷漠”问题皆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1][13]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4] 梁启超:《呵旁观者文》,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5] 康有为:《大同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18][2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7]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3。
[8] 白奚:《“仁”与“相人偶”——对“仁”字的构形及其原初意义的再考察》,载《哲学研究》,2003(7)。
[9] 耿宁:《孟子、斯密与胡塞尔论同情与良知》,载《世界哲学》,2011(1)。
[10] 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 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
[14] 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5] 麦金太尔:《追随美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16][17] 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9][20][22] 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7。
[2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 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5] 何怀宏:《良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6]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7] 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28] 杨国荣:《善的历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9] 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
The Confucian“Benevolence”and the Agonies of Others——The Moral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the Redemption of“Morality Indifference”
CHEN Ji-hong
(School of Maxism,Hohai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8)
The Confucian“Benevolence”has provided us useful sources to solve“morality indifference”. Specifically,“The Benevolence Loving Others“clearly contains the responsibility of“oneself”to“others”.On one hand,it has pointed 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responsibility and self-re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relations among moral subjects”;on the other hand,it can arouse the responsibility of“others”.“Practicing Benevolence depending on oneself”symbolizes the aspect“from morality to rule”,guiding people to return to thinking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human so as to overcome moral indifference caused by the situation of“conscience replaced by rules”.The“Three Virtues”direct the way to realize both one's own benefits and that of“others”,thus elimina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restraining one's own needs.The afore-mentioned resources can only be properly appli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the theory of Confucian Benevolence.And a“third way”can be found to avoid the theory dilemma thus caused.
Confucian;Morality Indifference;The Benevolence Loving Others
陈继红:法学博士,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京210098)
(责任编辑 李 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研究”(12&ZD09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现代转化”(2013B13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