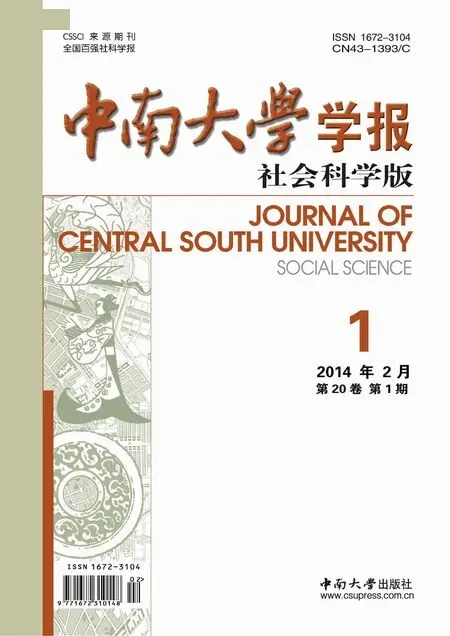现代性的救赎
——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2014-01-23步蓬勃韩秋红
步蓬勃,韩秋红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现代性的救赎
——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步蓬勃,韩秋红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哈贝马斯;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现代性;救赎
“现代性”的危机,肇始于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现代性谋划,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所导致的人的伦理、价值、精神等方面的现代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和异化,。启蒙思想家认为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他们各自的逻辑发展,不仅可以自动地提高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而且可以不断地超越自身、完善自我。然而现实的伦理事业并未如启蒙思想家谋划的那样顺利发展,科学、道德和艺术与生活世界的分裂,造成约束力普遍缺失,道德相对主义滋生蔓延开来,现代社会危机重重。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种伦理危机,虽然肇始于伟大的启蒙现代性谋划,但危机的根源并非在于现代性和谋划本身,而是在于生活世界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出现偏差。谋划本身并未完成,谋划仍需继续,于是哈贝马斯重拾“交往理性”,为冲出启蒙思想家们“乌托邦”式的现代性伦理谋划所造成的重重困境,走上了现代性的救赎之路。
一、现代性的谋划
哈贝马斯说:“就现代性语言而言,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1](1)“由启蒙哲学家们在十八世纪精心阐述的现代性规划,是一种遵循其内在逻辑坚持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与自主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个规划旨在把每个领域的认知潜能解放出来,使之从令人费解的宗教形式中摆脱出来。”[2]启蒙思想家用理性取代传统经验和上帝权威,认为理性作为人的本质才是人的行为的根据和基础,并将理性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理性作为至上原则可以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通过理性不但可以为自然而且也能为道德立法,理性不仅是认知的最高根据,也是道德的最高根据。启蒙思想家还强调个体在道德生活实践中的作用,认为道德的社会是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社会风尚可以通过个人理性自觉加以提升;现实社会中的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人的理性的积极作用来消除;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可以通过理性个体的自治与理性管理的他治的伦理谋划得以规范。
这个完美的谋划图景涉及科学、道德、艺术三个领域,表现为认知-工具、道德-实践、审美-表现三个理性结构,关注对真理、正义、审美的追求。如果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真理、正义、审美三个层面上互动交往,在科学、道德和艺术领域相互合作,那么人们将生活在一个真、善、美的社会当中,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团结、友善、和平。科学、道德、艺术都有各自的发展方向,都有各自的内在逻辑,可以在独立的、不受约束的意义上自由发展。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怀揣着无比的热情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试图通过对人的共同生活进行理性的合理安排与设计,建构起一套能够普遍拥护和遵守的伦理规范,以达到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理想社会生活状态。
由启蒙肇始的现代性正是通过谋划达到对于现代社会的精神体验。麦金太尔认为现代性危机主要原因在于启蒙的现代性谋划的失败,哈贝马斯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启蒙的现代性谋划仅仅受到了挫折,现代性危机虽然肇始于启蒙谋划,但造成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谋划本身,因启蒙谋划是项未完成的工作,现代性的危机原因在于人们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上。“现代性这个说法一再表明了那种对可以回溯到过去的古典时期的时代意识,就是要把自己把握为,从过去向现代过渡的结果。”[3]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所谓现代性,从广义上说,就是时间上的当下性,就是把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的时间性。哈贝马斯所侧重考查的现代性不是这种广义上的现代性,而是一种文化的现代性,即人类整个文化对传统观念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与传统世界观的分裂,即表现为科学技术、道德法律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分裂。哈贝马斯认为,启蒙的现代性谋划导致了传统文化领域的分裂,正因此分裂,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的文化专家。当某些人成为某些领域的文化专家的时候,专家文化又与大众文化相分裂,由于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间制约的失衡,远离生活世界,未能在指导社会实践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因此产生现代性的危机。
二、现代性的危机
当启蒙思想家“乌托邦”式的伦理谋划付诸社会实践时,所谓的道德专家们的理性的道德标准却成了空洞的道德说教,实践中的道德行为则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目不忍睹的惨剧:环境污染、资源殆尽、宗教冲突、种族战争、制假售假、吸毒贩毒、人性冷漠、悲观焦虑、拜金享乐、信任缺失等等,像瘟疫一样广泛传播并向各个层面渗透,都展示出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与颠覆,令谋划的美丽画卷黯然失色。在哈贝马斯看来,二十世纪的道德惨剧正是现代性危机的深刻表现,现代社会的价值迷失和现代性的伦理危机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现代性的伦理谋划与整个现代性规划深深地扎根于现代性理性进步观的价值迷失之中,这种价值迷失从根本上反映了现代性价值取向对人的生存、自由和解放价值的背道而驰。“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模糊,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破坏。司法、经济、政治、教育等行政管理领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规则,已经与最初的宗旨发生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仅仅遵循技术原则。原来建筑在人与人相互协调和理解之上的生存价值在全面的外部干预和控制之下彻底丧失,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被严重侵蚀。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4]
启蒙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宗教对人们的束缚,求得人性的自由解放,因此,现代性的诞生和成长是以“上帝死了”为代价的,上帝的地位和作用潜在地被所谓的“自由”和“进步”观念所替代,从此,具有内在约束力的神圣道德法庭在人们心目中宣告解体,取而代之的则是普遍理性信念以及由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功所证明的“进步”观念。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由于神圣的领域世俗化了。世俗话语取代了神圣规范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显然启蒙做到了,然而启蒙所展现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控制自然获取生存的历史哲学,这种哲学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神话。自笛卡尔开始的现代理性主义对理性的作用推崇有加,康德认为理性不仅可以为认识奠基,也是道德的最高根据,具有至上性,理性不但是立法者,而且是审判者,一切行为都要经由理性的权威确定其合法性,黑格尔更是将理性推至顶峰成为绝对精神,到韦伯那里,理性成为衡量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准,即一种工具合理性。现代主义对工具理性的崇拜以及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导致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秩序和模式的一系列人为设计,于是理性神话代替了神圣神话。现代性谋划的实践由此导致的现代性伦理悲剧,暴露出丧失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所具有的局限性:抽象化、绝对化、凝固化的理性,割离了其与感性生命、生活世界的联系。另外,过分强调理性能力的主体哲学也暴露出其消极的一面。主体哲学人为地把世界一分为二,坚持一种方法论的唯我论,确信理性是能为主体的目的提供中介与手段的抽象能力。主体通过自我意识就可以把握一切知识和道德问题,通过征服他者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这种认知结构必然导致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自我与他者、现实与传统的对立。现代性伦理危机已经证明,一方面,主体的自我确立把人从传统权威中解放出来,释放了主体的力量;另一方面,主体自我意识的展现过程导致了传统的解体,使本来相互和解的伦理关系异化。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问题就出现在工具理性的主体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或者说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这种系统化的发展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生活世界人们的语言交往被大机器所取代,并且分工越来越专门化,使得科学、道德、艺术的商谈脱离生活世界,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被破坏,生活世界的自身再生产受到破坏,这才是启蒙的根本问题。
三、现代性的救赎
面对现代性危机,学界争议纷纷:人类究竟应该继续完成现代性的谋划,还是应该终止或超越现代性的谋划?哈贝马斯认为,应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现代性谋划。虽然现代性作为一项启蒙规划出现了危机,表现为知识与信仰相分离、系统与生活世界相冲突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但是仅凭这些,还不足以断言现代性终结了,因为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现代性尽管有其阴暗的一面,但还不足以因此而全盘否定现代性自我超越的可能。他认为理性的意义并没有穷尽,理性除体现在目的和策略行为中之外,也体现在相互理解的交往行为中,回到日常生活实践,仍然会发现理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应当继续挖掘“交往理性”的财富,围绕“交往理性”重新规划现代性,为现代性伦理继续发展谋求新的方法和动力。
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的主要贡献就是通过工具理性控制自然的力量取代过去神圣的规范进而达到整合社会的作用,然而这也是现代性问题的根本所在。启蒙崇尚工具理性精神,工具理性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出现在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或者说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这种系统化的发展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生活世界人们的语言交往被大机器所取代,科学、道德、艺术的商谈日益脱离生活世界而独立发展,彼此间的失衡导致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被破坏,生活世界的自身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这才是启蒙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恢复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要恢复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就要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用交往理性来代替以主体为中心的工具理性,所以说现代性并未完结,仍需进一步向前推进。“只有继续启蒙才能克服带来的弊病。我丝毫也不赞同一种绝对的理性批判,这种批判只能毁掉理性本身。然而,这并不是说我盲目地崇拜理性,而是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理性地审视我们所具有的理性并看到它的界限。我们不能像扔掉一件旧外套一样抛弃这种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它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肉中。现代性生活条件是我们所不能选择的——我们被抛入其中——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必然。”[5]
用交往理性来代替以主体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并不是说把工具理性剔除掉,而是将其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理性,才能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生活世界的三大功能,即文化的再生产、社会化和人的个性的形成由科学和技术、道德和法律、文学和艺术共同完成,它们分别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以及人和他自己的关系。由于启蒙所导致的文化分裂,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传统理论特别强调工具理性的重要性,文化形式间的失衡便导致了生活世界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能把科学和技术、道德和法律、文学和艺术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并且发挥更大的社会整合作用,这样既解决了由于片面强调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现代性文化价值领域科学与技术、道德与法律、文学与艺术这三种文化形式的失衡,同时在整合三者的基础上又使人类其他方面的理性能力得以释放,创造更大的文化价值。交往理性为现代性以来的科学、道德、艺术的分离重新找到一个普遍的理性基础,并把人类的现代化运动建立在这个理性的基础之上。“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的理解和相互承认中表现为一种约束力量。同时,它又明确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1](376)
哈贝马斯把审美的、道德的、认知的要素统统纳入到他的交往理性的概念中来,这既能包含启蒙的优秀成果又能面向未来解决启蒙的问题。艺术、道德和科学由分裂走向整合必须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进行并且通过语言在自由的、非强制的环境下进行。现实生活中,人们为生存控制自然,逐渐在经济交往中形成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是造成分裂的主要原因,因而整合社会首先需要批判这种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消解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的干预,使人真正成为平等参与社会规则制度制定的独立主体。这样道德、法律规范的制定在无强制的商谈中进行以致最终形成。认知的真理性、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和审美判断的真诚性重新回到日常生活领域,文化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重新获得社会整合的功能。
文化的不同领域的分裂是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标志。哈贝马斯认为,如果继续推进现代性,就必须贯彻交往理性的原则。因为,现代性造成的文化分裂,主要体现在文化专家的出现,而这些所谓的专家文化的发展使认知的真理性、道德的正当性和审美的真诚性脱离了日常生活领域,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文化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不再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科学的工具方面要素被强化,道德的和审美的方面也逐渐被染上功利色彩而渐渐失去必要的限制,因而造成现代性的危机。为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文化必须以完整性的姿态重返生活世界,使关于认知的真理性、道德的正当性和表达的真诚性重返日常生活领域,使它们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讨论的主题,才能彻底拯救生活世界的分裂,重新整合社会。在交往中,借助语言,人们在话语交流中为自己的命题提供理由,说服对方,如果理由正当并且能为对方所理解就能够被接受,那么他就实现了认知的、道德的、审美的命题中所包含的真理性的有效性要求,这样在日常交往活动中文化的三大领域:认知、道德、审美联系起来,不再彼此分离。当人们在自由平等、无强制的商谈中对一些问题达成共识的时候,文化中的这几个方面就会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这就是哈贝马斯为什么强调交往理性在解决现代性问题上的意义所在。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被理解为控制自然的有效性,即为人类在生活实践中控制自然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理性很自然地被理解为工具理性。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哲学主要也是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理解理性的。哈贝马斯反对前辈们对理性的片面性理解,认为理性应该在人类相互的非强制的交往活动中获得理解并得到解释,确切地说,理性应该体现在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理解过程中,而不是单纯体现在人类控制自然的活动中。把理性由单纯的工具理性的理解方式转换为包容工具理性的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交往理性的理解方式,打破了以往理性概念的狭隘性理解,拓展了理性的范围。哈贝马斯所设想的改变现实生活世界的交往必须付诸生活世界的实践才能检验其有效性,然而生活世界本身的某种东西倍受人们的质疑,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交往活动如何保证其无强制性以及交往活动中所提出的命题的可靠性就必然遭受质疑,人们接受命题的理由是否是理性的也遭受质疑,这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1]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2] 哈贝马斯. 现代性对后现代性[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43.
[3]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和未竟的现代性事业[M].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6: 39.
[4] 章国锋. 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113.
[5] 哈贝马斯, 哈勒. 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22-23.
Redemption of Modernity——On Habermas’ philosophical logic of paradigm shift in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BU Pengbo, HAN Qiuhong
(Politics and Law School,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China)
Facing the complex modern problems, Habermas did not negate modernity as it made science, morality, art and life-world separate according to their logical development features. He thought that the spirit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did damage to the reproduction function of life-world.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had improved in terms of the ability to control nature, it influenced and undermined social integr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as the main function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nd then let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which be accommodated in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o overcome life-world problems caused by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Enlightenment project is still an unfinished work item. Habermas’ redemption of modernity is actually a re-understanding of the“rational” which is emphasized by the ideas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it is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paradigm shift from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Haberma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modernity; redemption
B516.6
A
1672-3104(2014)01-0146-04
[编辑: 颜关明]
2013-07-08;
2014-01-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1SSXT122)
步蓬勃(1974-),男,黑龙江泰来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韩秋红(1956-),女,吉林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