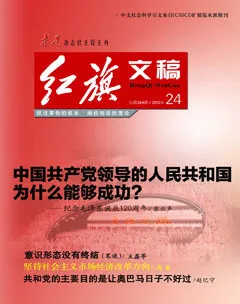文摘
2013-12-29
金冲及: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在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先说要有全局性的眼光。毛泽东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有把握地走好每一步棋。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没有这种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当机立断,正确决策,大刀阔斧地打开新的局面,而是被动地忙于应付枝枝节节的局部性事务,那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甚至会坐失良机或发生失误。再说要有敏锐的预见性。预见性,同全局性眼光分不开,要求指挥者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能够分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毛泽东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品质。总之,全局性眼光和预见性十分重要。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会有宏伟的胆识和魄力,才可以引导人们在行进中始终有明确的方向感和充分的自信心。这是毛泽东工作方法的突出特点。所以,总给人以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感觉。
(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
樊纲:制度的改进会释放出生产力来
制度和发展的基本的关系就是制度的改进能够释放出效率,改变资源配置。制度的改进会释放出生产力来,很多东西,包括资源稀缺、劳动力的能力、科技发展、创新能力等,都必须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才能使这些生产的要素、增长的要素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制度特别重要,改革特别重要的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希望这一次再能够通过制度的改进创造出一部分新的利益来,新的效率来,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只有政府的简政放权,才能有助于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新的竞争力,释放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活力。因为有新的利益格局出现,来要求来推动这个市场,来要求改革。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逐步推进的事情,所以也不要希望明天就见成果。尽管要抓紧,但是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来源:《北京日报》2013年12月9日)
石伟:全面深化改革的“变”与“不变”
所谓“改革”,在于国家治理的改变革新,着眼于治理创新之“变”;所谓“制度”,在于国家治理的建章立制,着眼于治理法度之“不变”。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之间,国家治理终将完成发展要义中的现代化转身。改革求“变”,是在国家治理的视野中“坚定不移推进体制创新”,就是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六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改革之“变”是“发展”这个重大战略判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功实践的最好诠释。改革之“变”,重在创新。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制度求“不变”,是在国家治理的视野中“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就是在体制改革中彰显制度观念。治国理念的“不变”,在于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不变,党的基本路线不变,人民利益导向不变,在宏观上保证改革方向正确,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制度不是僵化的,并不排斥改革之“变”。习总书记指出:“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此,在坚持治国理念和文本法度“不变”的同时,我们要充分注意到改革带来的制度完善和创新。
(来源:《学习时报》2013年12月9日)
王绍光:中国人更重民主实质而非形式
在国外主流的学术界、舆论界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威权体制。凡是讲到威权体制,都没有太多的“合法性”,其实我觉得更准确的翻译是“正当性”。但是,看看随机抽样的调查数据,就会得出跟判断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中国,从1990年开始,有大量全国性或地方性随机抽样调查,其中不少是外国学者抱着挑刺的态度设计的调查,但这些调查的结果显示,至少超过70%的受访对象都支持中央政府和共产党。二十多年来都是一样。现在研究中国体制“正当性”的学者,几乎已经不争议这个数据可不可靠,大家开始转而争议的是,为什么中国一个威权体制还会有这么高的正当性?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伪问题。既然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国人民如何看待“当家作主”的含义就至关重要。我的主要论点是:第一,中国人民期待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实质性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第二,中国已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出一种不同类型的民主,即代表性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第三,尽管中国政治体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基本符合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期待,使中国现在的体制在老百姓心中享有较高的正当性。中国百姓在理解民主时,更关切民主的实质意义,即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对其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而不是政治体制是否符合某些外在形式。
(来源:《环球时报》2013年12月5日)
马洪超:负面清单让政府市场各就各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这让“负面清单”这一较为专业的词汇,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了解。有了负面清单,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定位均可以更加明确。一方面,哪些领域不可以做、存在哪些限制,政府在给市场主体划出一条清晰的政策底线后,可以将精力更多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和事后监管,为企业公平公正竞争,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企业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和市场实际,作出自己的判断,不必过多考虑政策或财政支持等因素的影响。企业选择在适合的领域自由投资,必定会激发其作为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从具体操作过程来看,负面清单的制定需要政府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根据市场发展实际,科学合理地制定。清单制定后,减少了审批,政府将主要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环境等工作;至于企业间的竞争,则主要是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若触犯了法律和市场规则,政府出手治理。综合来看,这能够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关系,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来源:《经济日报》2013年12月10日)
杜学文:文艺创作要正确反映伟大时代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执着追求。在这一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目共睹,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文艺不可能回避这一伟大时代,必须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贡献积极的力量。文艺创作要在情感和形象中表达能够引领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价值观。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情感的形象表现,具有意识形态意义。文艺创作要更加密切地关注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的中国现实。中国目前的发展和进步,意义十分重大。文艺创作要表现社会的发展进步,必须掌握观察社会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文艺创作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必须加强理论引导。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在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文艺理论方面还有待提高。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0日)
[加拿大]马克·沃伦:协商民主有助于实现三类益处
协商民主的特质就在于它能产生某种协商影响力,恰恰是这种协商影响力为国家和政府的治理提供了一种内在合法性。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社会对协商影响力的需求日益增加。现代社会可以被区分为三种权力及其影响力:强制性权力、货币和团结,它们在西方社会的长期演化对西方社会的治理提出了结构性的挑战。而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三种权力及其影响力的相互作用也对中国社会提出了类似的挑战。协商民主能够有助于我们实现三类益处:一是政治功能,有助于建构一个好的政府。例如,通过公共协商,政策才能更好地回应民众的要求,由此产生一种内在的合法性;协商理性还为承认和尊重差异提供了机会。二是伦理功能,意味着协商治理的道德合法性。民主的道德合法性来自它在程序上证明了参与者的平等道德地位,确保了进入集体决策的道德理性。因而协商民主在政治共同体中产生了一种伦理的团结。三是认识论功能,协商民主力图在大众决策与专家决策之间确立恰当的平衡。协商民主通过建构正当的程序所做的决策比专家的决策更有效。协商民主是一种融合了真理、事实性和权利的,比任何其他方法更加理性的政治决策方式。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7日)
[澳大利亚]肯·泰勒:城镇化要保护传统文化与历史遗存
城镇化过程中应与文化遗产整合,尤其是那些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文化景观”的遗产。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不仅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也有经济价值。比如上海朱家角就是一个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完美融合的案例,它使朱家角和苏州河沿岸形成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意大利威尼斯同样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历史的城市景观使人们更加了解一座城市或者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人、历史建筑、文化社区等文化遗产构成了一座城市的活力和价值,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