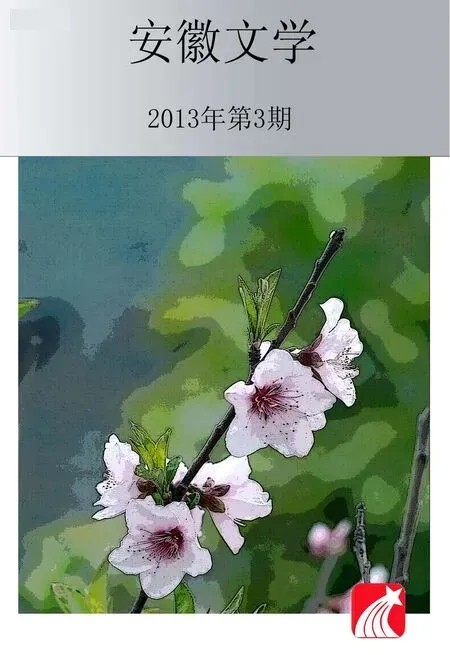莫里森小说中女性的“自我认同”、轨迹及意义
2013-12-12管丽峥
管丽峥
美国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一直关注着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心理状态特别是女性的自我意识问题。她塑造出的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女性形象的命运,反映出其对女性如何逐步增强自我意识、建构自我、认同自我的探索过程。本文首先对几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分析这几类女性如何形成一条自我认同的轨迹,通过这条轨迹来发掘出莫里森对女性自我认同过程的探索和其创作的现实意义。
一、“自我”与女性的“自我认同”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1938-)认为在现代社会自我的认同(Se1f-identity)是受到两个方面因素影响的:一个是“身体外在的‘给予’”,另一个是自我(Se1f)的反思。 在现代信息的流通十分发达的情况下,纷繁复杂的信息对个体产生的作用相互干扰,因此个体在自我认同过程中受到外界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少,而“自我的反思性”却对“身体和心理过程产生了广泛影响”,[1]个体进行的反思活动对于个体是怎样的状态和将成为什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个体的反思规划创造了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的方案”,[1]因此,“自我认同”即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而作为生活在当代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因此她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有极其丰富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既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又是主体会发生何种行为的主导。而一些女性主义者也认为:女性在进行自我认同时“应该,从一些其他的事情中,从她已经建立起来的形象和男人创造的环境中,而不是追根溯源从建立的过程中重新发掘她自己”。[2]因此,莫里森笔下的黑人女性总是在与“环境”(包括白人社会体系、白人群体和白人文化和黑人群体和黑人文化以及黑白的矛盾等构成的总的社会环境)和男性对女性的各种影响中,生发出自我意识,再逐步建构自我和认同自我。黑人女性们因为各自的处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自我认同结果,而每个女性的自我认同过程也是复杂的,而这也就给了莫里森以巨大表现、创作空间。
二、小说中具有“自我认同”意识的女性形象
(一)迷失者
莫里森作品中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正统白人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对自己种族的排斥感。她们的自我认同意识被白人文化毁灭或者被异化,成为流浪在白人文化观念中的迷失者。作者对这类形象做出鲜明的刻画是发表于1970年的 《最蓝的眼睛》(The B1uset eye)。
被毁灭的迷失者以 《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Paco1a)为代表。佩科拉是一个黑人小女孩,她在学校和社会上饱受种族歧视之苦,在家庭中又不能得到父母之爱,反而遭受排斥和强奸,最终心理扭曲、精神崩溃,幻想自己有了一双白人的蓝色眼睛。佩科拉的悲剧在于她受到的白人审美观念的影响,认为只有像是白人那样的外貌特征才是美的。说明“黑即丑”不仅是白人的审美观念所造成的审美偏见,甚至还在黑人群体中形成了对这个偏见的认同。但是白人审美观念对佩科拉造成的影响只是最直接的原因,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黑人自我认同的失败。佩科拉对自己黑人身份的厌恶感,使得她极力去夸大白人的“美”,渴望拥有白人的“蓝色眼睛”实质上是她想要摆脱自己的“黑人自我主体”,而重新拥有一个 “白人的自我主体”,这样她才能真正摆脱精神伤害,并且被社会所接纳。但是主观愿望与不可更改的现实之间产生的巨大的矛盾,使得佩科拉最终精神崩溃,其自我重构和认同的行为彻底失败。
被异化者的代表则是佩科拉的母亲布里德洛夫太太(Ms.Breed1ove)。她从乡下来到城市之后,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让她失去了对自我和黑人身份的认同感,并且认为白人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观念才是好的、对的、正常的。而对白人地位和生活状态的向往使得她最终产生了错觉,她把自己打工的白人家庭当成真实的生活,而自己的家庭生活则变成梦,“她越来越不顾及家庭、孩子和丈夫,——他们就像睡前恍惚的念头,只在一天的边缘时刻出现——只在清晨和深夜出现”。[3]生活在白人尊贵身份的庇护之下,布里德洛夫太太模糊和忽略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最终迷失在“宠物般”的生活中。布里德洛夫人虽然没有遭受精神上的彻底毁灭,但是她实质上是故意逃避真实的自我,而把自己当成白人社会中的一员来进行自我认同的。这样扭曲的、被异化了的“认同”使得她的“迷失”带有一种荒诞和悲剧的色彩。
这一类的人物形象是作者按照黑人群体中不能正视自己的黑人身份,也因此无法建立起强大的自我认同的人所塑造的“反面教材”。作者精心描述布里德洛夫太太的“宠物心态”以显示黑人想要“忘记”自我,企图融入种族偏见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白人群体的荒谬和可悲;而对佩科拉,作者则是抱着无限同情,谴责种族歧视对黑人的自我建构和认同过程所产生的强烈危害及危害的延续性,佩科拉求“皂头牧师”的虔诚和其疯癫对话中对自己“拥有”蓝色眼睛的心态令人深深被触动。
(二)反抗者
反抗者是莫里森作品中出现的具有自我觉醒的意识的人物形象,这类女性人物对自身处境看得较为清楚,有强烈的内省意识;对来自男性、白人社会压制和对黑人群体本身的弱点认识也很有深度,并且都采取了一定的行为去反抗。这类人物可以按照其行为的方式和反抗的对象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较为有力的反抗者,她们的反抗意识十分强烈,对男性和白人是对抗性的态度;另一种类型是较为无力的反抗者,她们不满白人话语中的黑人“低劣”形象,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偏见,但是对待周围环境却是一种积极融入的态度。
有力的反抗者以 《秀拉》(Su1a,1971) 中的秀拉(Su1a)为代表。秀拉是以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带有“疯魔”(demoniac)①特点的人。她能够看着母亲被火烧是因为母亲说自己不喜欢秀拉,这泯灭了她心中对母亲的依赖和对爱的信任;她能毫无任何困难就把祖母夏娃(Eva)代表的已经没有任何实质的权威推翻了,因为她对“权威”的现存性和合理性表示怀疑;她把女性朋友之间的情谊看成是“首位”的,而把与男性之间的关系看成次要的,莫里森曾经说过:“当我写秀拉的时候,我正处在一个关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印象之下,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是处在首位的。女性,你的亲密朋友,却总是第二位的。因此,女性群体的骨干不喜欢女性而更加喜欢男性,我们需要被提醒要爱女性。”[4]因此她能够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就与奈尔(Ne1)的丈夫上床。秀拉的离经叛道引起了社区内部的强大反应,她以一个“坏的榜样”成为社区人观察和改变自己的“镜子”,社区的乱伦,弃老废小的状态因为秀拉这匹“害群之马”得到改善。但是秀拉一死,社区的精神面貌又退回到从前。评论者芭芭拉(Barbara Hi11 Rigney,1938-)认为:“在莫里森的小说中,身份一直是变化的,没有脱离于社团的独自存在的自我,不论那个社团的生活是多么悲惨或者卑微,个人性格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结构中种族和性别的影响,从个人成长的最初就不可与这种影响分离。”[5]秀拉的反抗是源于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黑人群体内部建立起来的“自欺”性的道德观念,这些促使她“创造”(make)了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处处与不合理的现实、虚伪的道德作对,反过来成就了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这样的人物除了秀拉以外,《宠儿》(B1oved,1987)中的塞丝(Sethe)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被白人追踪的特殊情况下,为了不再让孩子重复奴隶的命运,她的自我意识战胜伦理观念——她亲手锯断了宠儿的脖子。
另一类反抗者的形象就以《柏油娃娃》(或译柏油孩子)(Tar Baby,1981)中的雅丹(Jadine)为代表,雅丹是白人农场主瓦莱里安(Va1erian)的黑人奴仆的侄女,在瓦莱里安的资助下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聪明漂亮,是一个德才兼备的“成功”人士,按理说这样一个既是女性又是黑人,并且出身卑微,却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真的是十分令人羡慕和感到骄傲,但是她的成功是遵照白人文化的标准而判断的,她是一个“欧化了的非裔”。[6]美国的社会活动家杜波伊斯提出过“双重意识”问题,是指少数族裔处在不同的文化世界观中产生心理冲突现象。雅丹的成功一方面是对黑人拥有同样智慧的头脑和卓越的能力的证明,是对种族偏见的有力反驳;但是另一方面,她的成功却是以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为参照,因此,这类人物虽然是具有较为客观的自我意识和微弱的反抗意识和行为,可是缺乏对黑人文化和身份的自信作为其内在的心理支撑,因此这类形象的反抗就显得较为无力,不能像秀拉那样形成对黑人社区的强烈影响。
(三)理想者
莫里森作品中还有一类女性形象,她们具有更为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实践目的,并且能够建立和确认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这类人物最终都能够形成对自我的认同,并以一种稳定的精神状态生活下去,是作者塑造得较为理想的女性人物形象。这类人物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以《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1omon,1977)中的彼拉多(Pi1ate)为代表,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形象;另一种则更加贴近现实中黑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是具有现实性的一类人物,以《慈悲》(或译《恩惠》)(A Mercy,2008)中的弗罗伦斯(F1orence)为代表。
尽管莫里森多次强调过《所罗门之歌》是一部以男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但是作为引导 “奶人”(Mi1kman)寻找祖先之根的彼拉多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女性。她出生时母亲就死了,她自己摸索着从子宫爬出来,拖着脐带和胞衣,因此成人后没有肚脐,除了生理特征异于常人以外,她还拥有能够和鬼魂沟通的能力,其他人因此把她视作不祥之物。群体的排斥使得彼拉多不再寄希望于群体的交往和庇护。她“丢掉她所学得的任何一种假想,从头开始”。[7]在摆脱掉外在社会的混乱的价值、道德观念和文化影响之后,她捕捉到了自己存在的本质,从此以一种蕴含着非洲传统文化精神的“诗意的”方式“栖居”和体悟人生,不是像自己的兄弟们那样,带着白人文化的“杂质”去寻找非洲文化之“根”,而是以维系、继承非洲文化传统的心理作为生存信念,坚定地认同自我和自我存在的意义。因此她才能引导作为寻根男性代表的“奶人”摈弃白人文化的“杂质”,实现飞翔之梦。
《慈悲》中的弗罗伦斯是17世纪一位被掠夺到美洲的非洲女奴的女儿,通过一次奴隶主之间的交易,她被换给了具有慈悲之心的白人农场主雅各布(Jcob)。弗罗伦斯认为是母亲抛弃了自己,因此对母亲怀恨在心。在失去了对母亲的依赖之后,她转而寄希望于白人农场主能够给她人身自由和黑人铁匠能够带给她爱情的幸福。因此,虽然对母亲的恨意不断刺痛着她真实的自我,可是她却仍然带着一副讨好的面具,等待白人和铁匠的“拯救”。但是,在出行寻找铁匠为女主人丽贝卡(Rebeka)治病的途中,她亲身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奴隶的黑人是怎样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歧视和排斥的,愤怒和羞耻感激发了她一直被抑制的自我意识的成长。最后黑人的拒绝使她的“希望”彻底破灭,她终于认识到“自我”的独立不能依赖于任何人的施舍,而是要通过自己对自己的肯定和认同。
莫里森在一次采访中认为彼拉多是一个“完全知道自己是谁的女人”,②肯定了彼拉多坚定的自我认同的态度,但是因为形象的魔幻性和象征性,所以彼拉多如此纯粹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只能是一种理想的代表,所以她其实是作者刻画出的黑人女性应该“成为”的理想范本。而弗罗伦斯是在遭受到一系列的心理创伤之后,终于明白自我认同对于自己会拥有什么样命运的意义,她最终得到的是自我给予的、最稳固、可靠和“永恒的”“自由”。[8]如果说彼拉多是作者认为一个女性要“成为什么”的范本的话,那么弗罗伦斯则是“怎样成为”的范本,因此较彼拉多更具有现实意义。
(四)三种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
迷失者、反抗者与理想者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
她们的联系表现为:她们进行自我认同的参照物基本相同,就是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男性权威,而在此基础上又有差异:迷失者是自我意识彻底被异质的文化或者观念吞噬的形象,她们缺乏独立和反抗意识,或者对自己产生了扭曲性的认同,或者再也无法进行自我认同。反抗者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她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或是反抗男性话语中的女性形象,或是反抗白人话语中的黑人形象。反抗意识较为强烈者往往采取极端行为,而更加显示出其自我意识的确立和主导作用,并且她们的自我认同不依赖于白人的文化价值观,最终要实现黑白的差异性;反抗意识较弱的女性虽然认同自己的黑人身份,但是同时她们的自我认同又依赖于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企图实现的是黑白的一致性;因此反抗者尽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行为,但是她们的自我认同都是不完善的。例如秀拉尽管桀骜,方式却是“自焚”式的,她能改变一时,却无力支持下去,因此作者安排她过早死亡,虽然壮美,但是如果这种自我认同的方式却没有真正给人以生存的动力,那么它仍然不算是成功的。理想者是作者塑造的理想的女性形象,相对于迷失者,她们具有强大的自我意识,因此不会放弃抗争,保持自我的独立性;相对于反抗者,她们也有反抗的行为,但是既不会向白人文化或者男性权威妥协,也不会做出极端的伤害他人的行为,她们会用各种方式保持自己的自信心和生命力,怀着希望积极生存。
三、三种女性形象“自我认同”的轨迹及意义
从莫里森的创作时间来看,这一系列具有自我认同意识的女性形象是有其轨迹的。《最蓝的眼睛》发表于1970年,其中塑造迷失者的形象出现得最早;接下来是较为激烈的反抗者形象,出现于1974年发表的小说《秀拉》中;再往后是1977年的《所罗门之歌》,带有魔幻和象征色彩的彼拉多出现;接下来是1981年的《柏油娃娃》,比较无力的反抗者雅丹出现;往后是根据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而创作的发表于1987年的《宠儿》;再往后是发表于2008年的《慈悲》,更加具有现实色彩的理想者弗罗伦斯出现。
可以看出,发表于早期作品中的人物都比较极端:佩科拉是彻底被毁灭了的,秀拉是非常出格和离经叛道的人物,彼拉多则是最早也是最不真实的“理想者”,而中、后期所塑造的形象则越来越贴近现实,即便是魔幻性十分强烈的《宠儿》,也是根据历史上女奴杀子的真实事件写成,而《慈悲》中的人物就更加接近现实中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应该说,会有这个过程是源于作者对现实的持续的深入观察和深切关注,实现于作者在及时地配合现实和自己的探索而创作的作品中,显示于作者对现实中黑人女性最终能够摆脱束缚、扭曲“自我”的枷锁,坚定认同自我的乐观精神。
首先,这条轨迹反映了作者注重创作的现实意义。从这一轨迹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始终与现实相关,莫里森十分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即便是塑造出的与现实差距较大的人物形象,也不过是取于生活,经过她的构思和创作,产生出既震撼人心,又能反映现实的作品。她不止一次说过“我个人对那些特殊的人着迷,因为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适用于普通人的特征”,[9]“我确实对出格的人感兴趣,他们是狂野的,而平常的女性可以从中得到新鲜的体验”,[10]明确地表示自己作品的现实意义和现实目的。
其次,作品中行体现的这个变化过程渗入了莫里森对女性如何逐步增强自我意识、建构自我认同的探索。作者在初期创作中倾向于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因而将产生于现实的问题做了夸大处理,以使它们更加鲜明突出;而随着应该“怎么办”的实际要求出现,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如何通过写作来表现解决问题的过程,就反映在其后期作品中。因此在早期作品中相继出现了“不要成为”的人物、“极端反抗”的人物、“理想”但是不真实的等等一系列 “不该成为什么”、“该成为什么”的形象。而究竟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就反映在其后期的小说中,也就在回答前期的问题:“怎样成为”。
再次,反映出作者对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的“自我”的成长和自我认同是充满信心的。她的作品前后跨越30年,而其中显示出的是越来越乐观的积极态度,特别是在最近的小说《慈悲》中两个年轻的女奴,弗罗伦斯和索柔(Sorrow),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精神困境说明作者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相信她们能够不断努力,摆脱套在她们身上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枷锁。
注释
①Barbara Hi11 Rigney.The Voices of Toni Morrison[M].Co1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38.
② 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M].王守仁,吴新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4.
[1](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Luce Irigaray,“Sexua1 Difference,”in Margaret Whitford,ed.,The Irigaray Reader:B1ackwe11 Pub1ishers,1991:201-202.
[3](美)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陈苏东,胡允桓,译.南海出版社,2005.
[4]Toni Morrison.“The Art of Fiction” Interviewed by E1issa Schappe11[J].The Paris Review,1993:134.
[5]Barbara Hi11 Rigney.The Voices of Toni Morrison[M].Co1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
[6]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 [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Toni Morrison.Song of So1omon [M].New York:A Sigent Book,1997.
[8]Toni Morrison.A Mercy,A1fred A[M].Knopf,New York,Tronto,2008.
[9](美)托马斯·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妮·莫里森访谈录[J].少况,译.外国文学,1994,1.
[10]Pum Houston: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issue of O,The Oprah Magazine 2009,Ju1y.http://www.oprah.com/omagazine/Toni-Morrison-on-Wr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