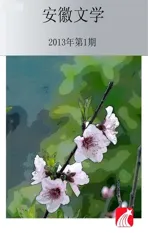试论司空图《诗品》“虚实相生”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因
2013-12-12叶嘉馨
叶嘉馨
司空图是晚唐诗人,但其最为人称道的则是在诗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著有《二十四诗品》(亦称《诗品》)传世。与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不同,司空图《诗品》不是对诗歌具体写作方法的评论,而是以四言诗的形式,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前代诗歌中出现的24种风格或境界。
本文认为,《诗品》虽寥寥千余字,却无处不体现着司空图宁静淡泊、高远清空的风骨,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虚实相生”的审美特征。拟以《雄浑》、《纤秾》两节加以说明。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诗品·雄浑》
与初唐诗人王昌龄所写边塞诗《从军行》表现出的“入目所见壮丽之景”与“由内喷薄而出的磅礴豪情”显著不同,他笔下的“雄浑之境”极少具体物象的填充,却勾勒出了一种无边无际的时空苍茫之感。
可见,在司空图眼中,雄浑不必要只靠实物去展现,而可以通过一团气韵表露无余,自有“得其真体而超然物外”之风流,扣得“环中”,可谓“不言雄浑而尽得雄浑”。在这种不拘泥于现实物境而弘扬无形潇洒之气的审美倾向下,《雄浑》从抽象中概括出具体之意,从而透视出“虚实相生”的审美特征。《纤秾》一节亦是如此。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诗品·纤秾》
“纤秾”用于形容文艺风格,意为“富丽优美的文艺风格”或“浮华的风格”。皋兰课业本曰:“此言纤秀秾华,仍有真骨,乃非俗艳。”[1]7孙连奎《诗品臆说》曰:“入手取象,觉有一篇精细秾郁文字在我意中,在我目中。”[1]8都表达了对《纤秾》的赞誉,并将司空图所描述的“纤秾”与传统意义上的“浓抹艳丽”区别开来。
不难发现,司空图反对世人将“纤秾”单纯理解为艳丽词汇的堆砌,所采用的“流水”、“深谷”、“碧桃”等意象连缀,抱着闲适清淡的眼光审视自然春光,于美而不艳之物中觅得“纤秾之感”。这里恰恰与“雄浑”相反,物境为实而心境为虚,但同样虚实相生、表里一体,令人称绝。
司空图《诗品》“虚实相生”的审美特征既有时代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本文试作粗浅的梳理。
其一,晚唐衰败的时代背景及司空图心向佛道的个人意趣促使其产生闲适淡雅的情趣,孕育了《诗品》“虚实相生”的审美特征。司空图所处的晚唐时期,藩镇割据,支零破碎的山河无法再支撑盛唐气象。司空图早年有济世之志,但在入仕后才明白国家的现状已无法改变,于是“在济世与归隐的夹缝中”[2]生存。正是因为在现实中难以寻得精神寄托,于是不免将其关注点由实转虚,借以在虚幻之中获得最后的陶醉。因此,司空图携有唐朝诗人所特有的高阔磅礴的气势,兼有黄昏时代所赋予的敏感纤柔的特质,偏爱“冲淡玄远”的风格,逐渐趋于“虚实相生”的审美特征。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司空图还在佛道思想中寻找闲适淡雅。《诗品》崇尚自然淡雅、高远清空,其中大量化用了《庄子》中的语句便是明证。其与道家思想的渊源极深,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同时,《诗品》也深受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影响。因此,“切实地分析、厘清《诗品》与(儒、佛、道)三家思想的渊源关系,对于深入把握其内在思想脉络和理论实质,有着重要的意义”。[3]
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司空图认为,诗贵含蓄,诗歌最得灵神之处即为其“味外味”、“韵外致”。他在《与极浦谈诗书》中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物外之象虽然难以把握,却是诗文的关窍。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他激赏王维、韦应物诗文,皆因其符合他所推崇的“物心二境之统一”的禅学式观点。
其二,前代诗论的发展和阶段性成果,尤其是“意境说”的发展,呼唤总结者的出现,司空图《诗品》历史性地凸显了“虚实相生”的审美特征。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针对南朝文风轻靡、北朝文尚质朴的情况,《北史·文苑传序》指出“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强调诗文不应有所偏颇。王昌龄在其《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追求形似,“情境”重视情感的生发,“意境”则是发于意念而在内心中思得,提出了“意境”这一概念。殷璠《河岳英灵集》中也倡导“意象之说”,提出应当将“风骨”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实际上是对文章的气韵作出要求。皎然《诗式》认为,诗人的情感来源于客观外物,“境胜增道情”,“言外之意境”被重视,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使意境的理论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及至司空图,他对前人所总结概括的意境概念进行了进一步推进与升华,“揭示了‘意境’的美学本质,还提出‘思与境偕’的命题,把艺术想象和意境创造联合了起来”,[4]从而凸显了“虚实相生”的审美特征。司空图认为,诗歌创作要有“象”、有“景”,而且“象”和“景”不应该仅仅止于直接性的“景”、“象”本身,而应比它本身有更深、更远的东西,这就是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一认识“和刘禹锡所说的‘境生象外’、贾岛所说的‘神游象外’、皎然所说的‘假象见意’、‘采奇于象外’等等,都是相同的”,[5]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对“意象”的认识,更以《诗品》开创性地发展了“虚实相生”的审美特征。可以说,《诗品》将“意象”的地位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他本人也因此被认为是“意象说”的集大成者。
综上所述,司空图用他对自然、冲淡、含蓄之美的喜爱,承前人之总结,提出了他较为成熟的“虚实相生”的诗文审美观念。他开启了的与前世相异的文艺评论方法,对后世文论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杨剑.司空图:在济世与归隐的夹缝中[J].安徽师大学报,1992(4).
[3]张国庆.《二十四诗品》百年研究综述[J].文学评论,2005(1).
[4]许连军.皎然《诗式》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4.
[5]敏泽.皎然的《诗式》和司空图的《诗品》[J].社会科学研究,1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