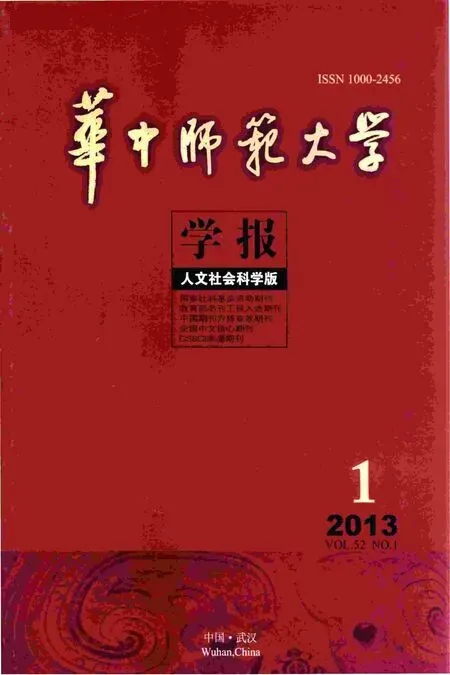社会救助的根源:对福利体制、目标与方法之差异的初步思考
2013-12-12苏黛瑞周凤华
[美]苏黛瑞 周凤华(译)
(加州大学 埃尔文分校,美国;华中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政治科学中近来比较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不同国家类型(有时也关注不同地理区域)的宏观差异,既阐述使“福利体制”①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的因素,也描述由这些因素而引起的福利体制的多样性。通常,“社会福利”或者“社会保护”被笼统地视为一种待遇,并不详细区分通常要求受益人出资的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医疗和教育补助,以及各种非出资性的社会救助。本文提出一种探索性的分类(heuristic typology),它包含三个典型的理想型,或称三种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基于各自的观念认识而形成。本文的目的是阐明观念认识对福利的影响,而不是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因素如何形塑福利。每种模式都围绕其自身的逻辑(rationale)而形成,以其福利项目服务于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式或策略,致力于各自不同的目标。本文将主要讨论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而不是更广义上的福利。
我将证明,这三种模式都受到特定时间点上国家精英和普通民众评价性思潮(stream of thinking)的影响;每一种模式也都必须解决福利政策总是会面临的问题。在特定的国家内,人们的文化信念、历史经验和国家-社会关系的遗产无疑也发挥着作用;国际通行的规范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特定国家在某一时间节点上可能比在其他节点上更多地表现出某一模式的特点;在同一时间,全球不同的社群也呈现出不同的福利模式。这些时间和地域上的差异似乎表明,在某个民族静态的文化或者不变的全球流行观念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我并不打算探讨使全球福利项目及其递送呈现不同风格的思想观念那些更深远的历史基础,我的目的是系统化地讨论、区分,并且提出不同风格的福利观念之所以存在差异的直接根源。
我首先会简要回顾学术研究中对福利政策的分类,接下来说明这三个模式,概述它们各自的逻辑或动机,各自意欲服务(或者某些情况下是隐藏的甚至默而不宣)的最终受益人;各自采用的策略类型及其目标。我也坚信,这些模式的上述每个要素都受到观念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家与其民众对彼此的看法和期望,一国当时被认为合适的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责。在此基础上,我会用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案例来揭示他们对待穷人的诸多不同立场和方法。这些案例凸显出一个事实:政体类型相同的国家,或者表面上追求相似贸易和发展路径的国家,对福利对象仍然可能采取大相径庭的立场;尽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各国在纷纷强调社会保护的同时,仍然可能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政策设计和意图。
一、文献回顾
政治科学中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主要范畴是关注国家政体类型②和制度对该国所提供的福利种类的影响③。与此相关,政体变迁,尤其是民主化和民主转型,通常被认为会诱使政客们对选民诉求做出新的回应④。
事实上,学者们一直选择民主政体作为福利研究的背景,一系列关于福利的假定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社会保护的开支水平与特定的执政党相联系(也就是说,左翼工人党提供更多开支,而右翼党派主政则提供得较少)。学者们显示,党派内部的竞争和民众通过社会运动、利益集团施压,以及选举等表达出来的需求促成了这些结果⑤。分析民主国家福利提供的学者也认为,福利政策是政治联盟机制,或者是选民内部某个“核心群体”偏好的函数⑥。
因此,考察民主国家社会保护的研究者假定,政客们全部的关切就是研究者们所谓的“选举要务”;政府提供援助是政客们受“选举要务”的驱动。这些研究强调与选举要务相关的动机。这意味着,对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理解福利或民主国家的任何政策,就是搞清楚政治候选人为赢得选票如何行动。相应的,这些研究者认为,试图获得职位的人需要通过取悦特定的社会阶层来形成联盟;研究者也考察各党派提出的用来引导选民做出选择的政策平台;他们还分析了领袖(和未来的领袖)讨好受政策影响集体,比如工会或工人运动,企业联合会或其他相关利益集团的方式⑦。
社会政策研究的另一个取向是考察更多地受经济驱动的变量对福利体系和福利计划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核心的一种解释是发展水平/阶段/模式影响着对福利体系的设计和构想⑧。有时候,国际化也被认为是影响福利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国际化要求技术上训练有素的工人,加剧了国家间竞争,促进了外国投资。在绝大多数案例中,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这两股力量都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或社会支出缩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⑨。与经济制度类型有关的另一个分析框架是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主要是基于对西欧社会的考察。然而这项研究并没有特别追问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体以何种方式促成了西欧各国福利制度之间的差异⑩。
还有另外一种更宏观的方法,考察地理上相对集中的若干国家,以找出不同地理区域在福利供给上的差异,例如东亚福利模式或者南欧、拉美和后共产主义东欧国家的福利政策风格。比如,研究地理模式的学者们断言,东亚的统治者提供社会援助通常是出于“生产主义”的偏好。也就是说,东亚的领袖们用福利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比如通过支持人力资本开发,资助或补贴教育或医疗保健。
在这一研究流派,Haggard和Kaufman强调了区分东欧、拉美和东亚各国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历史遗产、民主化、“分配联盟”的需求和力量、国家的财政能力,政治制度与政体类型,国际竞争与产业重构,竞争性统治联盟的权力,以及期望和意识形态的趋势等。然而,他们是以地理区域而不是以深入分析为原则来组织材料,因此他们提出的模式未能将上述众多因素整合为紧密而清晰的福利范式。
其他的研究主张,福利的差异性源于社会结构因素,尤其是一个社会的人口状况,或者是该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平等;有人关注政策精英在回应其所处社会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时对特定福利项目的选择,或者是反过来讨论不同的福利项目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也有研究关注特定政策领域内福利方案与规范之间的差异。还有其他分析家并不太关注福利政策的总体模式,而是关注特定的政策设计和福利项目,以及由此带来的福利分配结 果。
另外一类研究考察政治和行政分权化政策已经让设定福利项目的职责转到较低层级政府的社会。这类福利研究讨论当福利责任由地方政治家承担,而地区之间原本就存在不平等,或由此而带来新的不平等时,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分歧”。当中央政府放弃自己在福利领域的所有管理职责时,中央边陲关系的变动也可能导致地区之间的 福 利 差 异。
下文将提出一种不同于以上范式中区分出来的各种模式的新框架。这一框架意图用观念性原因来解释社会政策的创立和定型,而并不考虑政体类型、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构成或社会结构、外部影响、经济制度、管理水平、政策类型或政策结果。
为了使这一框架更具普适性,我提出的这三种模式既不考虑地理空间或国家政体类型上的差异,也不强调福利领受群体之间的差别。与此相反,它直接关注支撑福利活动的更精神层面的因素,也就是,不同地方提供援助背后的价值观和理由,以及从政策供给中获益(或意图使其获益)的行动者的类型。
二、救济模式及其目标
有三个大的逻辑支持这三种不同的救济模式或救济风格。尽管有可能这三种逻辑在某些情况下各自单独起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是多种逻辑在发挥作用。
福利项目面临的三个核心议题和问题
在考察这三个模式之前,我首先列出所有福利项目都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因为各模式在运行中对有关福利如何付费、如何对待穷人、如何选择和对待受益人等核心问题的选择各具特色。这些核心问题是,首先,福利资金的拨付是否应该设定条件(比如,该项资金只要是用于人类发展就可以,还是只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获得资助);与此相关,是普惠地提供援助,还是根据某些标准只“瞄定”某些人,也就是条件性与普惠性的问题。
其次,是否需要区分体格健全的人和不健全的人,也就是是否值得救助的问题。体格健全而嗑药、酗酒的人通常被认为不值得救助,而长期病患、残障、智力缺陷者、孤儿、寡妇、老年人则通常被认为值得救助。第三个问题是恰当的资金来源,也就是援助的资金应该来自私人组织还是公共部门。私人来源比如雇主或公司、家庭成员或志愿组织、慈善基金;而公共来源则由国家来承担。
(一)三个模式的逻辑
如何应对上述三个核心问题受三种福利模式及其背后逻辑的影响。我将这三种模式称为基于权利的援助、回应性的援助和改造/清理的援助。
第一种基于权利的逻辑假定,所有的人都享有对生存、生活、社会保护和安全的权利,并意图努力实现这些权利。当实施这种模式的时候,平等、公平和正义等价值也被重视。依据这些观念制定的政策以人为目标;也就是政策维持人的生存为最终目标,人的生存本身就是目的,而并非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第二种回应的逻辑体现在那些因回应民众声音而实施的援助项目。设计这类项目是为了应对民众表达的不满(或出于恐惧),应对不满的公民已经(或觉得可能会)提出的需求。换言之,这一模式既可能是回应性的,也可能是阻遏性的或预防性的。民众的声音可能不仅仅通过民主国家的选票表达出来,也可能通过叛乱者和示威者表现出来,特别是(但不限于)有组织的叛乱者和示威者。领袖们认识到国内秩序混乱或者其权力地位不保(在民主国家表现为赢得或保住其想要的职位),这足以让他们采用福利手段对情况予以矫正,以缓解社会张力,满足公民需求,实现其愿望,或者安抚对现状不满的民众。在这种情况下,福利方案的设计是为了政治家的利益而准备和提出的。
Piven和Cloward在阐述这种模式时指出,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在社会动荡一旦平息的几个关口,对穷人的援助也显著减少。因此,在研究三十年代中期的福利时,他们指出,“随着社会恢复稳定,这些数以百万计的长期受苦的人政治影响力减少了”。这是政治家自身利益拉动社会援助的充分证据。
第三种动机是将穷人(或者他们令人不悦的特征)从公共领域中清理出去的欲望,因为公共领袖以及大众认为他们的某些特征令人不愉快,或者与该社会及其目标不相适应。从积极的观点看,主要目标可能是改造或重塑穷人,将他们整合到适当的人群中,或者让他们能更好地在国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国家作贡献。从这一乐观的角度,接受社会援助的人可能得到教导或培养,以期得到他们的合作。他们不是像第二个模式中那样,仅仅是被安抚和令其保持安静。我将这称为改造/清理模式。
然而,这种改造的事业也可能是源于负面的观点,相应的带有负面的色彩,比如管制、约束、压迫和监视穷人,把他们从其他居民中排斥出去。在这些与排斥穷人相联系的案例中,福利政策和福利项目背后的潜台词是改进整个国家。因此,它要增进的是整个集体的利益。然而,这一整体思路背后隐含的家长式目的,不论它本质上是出于善心、抑或是为了打击或虐待穷人,常常被发现给穷人更多的是责难而不是照顾。
这三种救助模式都由各自不同的方法或策略。在看重个人的救助中,提供的福利项目可能是慈善或者应得权利(entitlements),尽管这两个概念有时候被认为相互矛盾(即便提供慈善是出于“个人应该为生活而接受援助”这一认识,慈善仍然让受助人低人一等,而且救济并不稳定。而应得权利则可能给予受助人某种程度的尊严,是普遍地授予所有合格的对象,而且是制度化的)。
当救助的目的是为政客提供收益和好处,就像回应性救助那样,提供补偿或支付福利通常会有时间和条件限制。或者,政客也可能仅仅挑选领头的抗议者给予福利,以平息民众的要求。当救助的主要愿望是提升或改进国家时,则倾向于积极、善意地对待受助人,比如,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或者为了矫正他们,给受助人提供教育和卫生投入,以形成人力资本或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与此相反,当提升国家的愿望与普遍的对穷人的负面观念同时存在时-这种观念认为,不论是缺乏教育、技能,或是身体虚弱,还是长相难看的穷人,都绝无能力为更大的社区作贡献-为了保持大集体的纯粹性或达到正常水平,重塑穷人的可能性就大大小于将这些人简单地从公众眼中清理出去的可能性,不管是通过严格的管制或纯粹的压迫。
这三大类国家(和政治领袖)的理想型目标让这三个模式各具特色,每种目标都含有支持政体和/或政治领袖在国内或/或国外合法性的意图。这些意图分别是达到普世公认的、人的权利和应得待遇的标准;实现或维持社会和谐、国内秩序和稳定;实现国家发展、经济增长、进步和现代化。这些目标影响着对待贫困公民的方式。

表一 福利供给的三个典型理想型
(二)思想观念的影响
有两种明显的思想观念/心态/评价的影响使上述三种模式各具特点。这些思想观念作用于每个模式,塑造着它们的内容、形式和发展方向。第一种是国家和贫困公民对彼此的看法和期待;另一种是社会对政府(或国家)与市场的态度,以及人们希望这两种力量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些看法和态度确实有其历史渊源和意蕴,并不是作为一块白板出现的。但是我着重强,这些概念范畴让分析家得以解释政策,解释它们带来的各方互动、引发的反应,以及它们在特定时间点出现而引发的服从行为。我认为,这些思想观念影响是国家和社会双方福利行为根源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解释着伴随及驱动双方福利行为的态度和要求。
国家和社会对穷人的不同看法,以及穷人对国家的不同期望对特定国家、特定时间所设计的福利项目类型有重要的影响。有一种看法和期望 是,穷人引人恐惧和过失归因。在这种印象中,穷人是一种威胁或者危险;他们是寄生虫,招人厌恶、他们是失败者、懒虫、骗子手、落后,道德堕落或者有社会越轨行为,不负责任。这种负面印象会影响官员们给予穷人的待遇。当类似的看法盛行时,压制、改造或者重塑穷人的政治政策就会占主导地位,以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是,当流行这种看法和期望时,国家最有可能采用上述改造/清理模式当中消极的一面来对待穷人。穷人被认为有过错、危害社会,是自己导致了自身的不幸境况。
但这些不幸的人也可能被视为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外力和事件的受害者;这种观点可能与基于权利的福利模式相联系,或者是与改造范式的积极面相协调。在这些情况下,要么采用的福利项目是基于个人有权获得社会保护和保障这一认识,要么致力于改善这些无辜者境况的政策占主导地位。
换一个角度,穷人对国家的期望是另一种观念。当思想氛围-通常归功于历史遗产-是穷人期望国家有义务照顾他们的需求;在此基础上,穷人们还能团结起来,通过提出请求、参与抗议、或者给承诺提供援助的候选人投票等方式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就可能诱使国家以补偿和福利支付做出回应。也就是,他们可能用被按照回应模式来对待。不管是穷人或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谴责政府没有照顾有需要的人,还是官员和保守的右翼评论家指责穷人是自己窘境的始作俑者,这些精神面貌、看法和期望都在调节着福利项目。
民众当中盛行的对国家和市场恰当职责的看法也可能影响这些观念和期待,或者与这些观点或期待相互交织、互为构成。比如,在工作伦理和市场规律广泛受欢迎的地方,自立和个人责任在该文化的社会标准中就会占据重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福利较少可能是基于个人权利,而更可能是对底层声音的回应或者是努力改造或清理受助人的结果。而且,很显然,民众是认为国家应该照顾那些不幸的人,还是对国家“干涉”私人和家庭事务持怀疑态度,这些精神风貌和观念也会约束一国社会保护的形式。
我将证明,这些想法、假定、观点和价值观设定了社会保护项目的基础色调、方向和活力。甚至可能,其他学者所指出的诸多因素(历史遗产与经验、国家的制度能力和宪法、财政能力和经济挑战,潜在选民的影响等等)都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而是受到人们之间流行的这些思想观念和感性认识的制约。为了说明这些观点,接下来我将列举影响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福利项目、政策和态度的那些态度和认知因素。
三、案例分析
在此我提出一些简短的现实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三种模式或模型,这些例子志在使我上面抽象地讨论的地区和国家的福利策略、目标、态度和思想变得血肉丰满。这些例子有助于阐明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点上,与三种救济根源(权利观念、声音回应、改造/清理)之一最相吻合的观念性和规范性原因。我也会解释这三种不同的立场如何影响对福利项目必须面对的三个大抉择。这三个抉择是,福利项目是附条件的还是普惠的,是否区分值得救助,筹资是依靠自私人还是公共来源。我的材料主要来自研究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印度、拉丁美洲、东欧、韩国、日本、非洲、西欧,以及美国的文献。
根据Janet Chen,“中华民国”时期(1927-1949)很多人,包括政治家都视穷人为讨厌的人、懒惰的寄生虫、行为出轨,他们应该自立。领袖们不具备个人有权从国家获得保护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允许这些不适应社会的人给大众丢脸可能有害于国家。只有让这些人通过某种方式,比如强制拘留和劳动,得以改造,正在追求进入摩登社会的市政当局才可能容许他们存身。
在这一案例中,实施的是改造/清理范式。穷人通常被逐出城市或丢进救济院。可以推测,如果穷人不能被改造,将不会被视为是公民之一员。在这里,如果提供任何福利的话,是不会给予“不值得”的人的。然而,这些人有时候也确实得到过一些慈善救济,可能是因为提供救济的私人社团认为,及时穷人也应该拥有富人所拥有的某些权利。公共福利作为一个概念尚未起到任何重要作用,而在救济院中生活的“特权”确实是以工作为条件的。
在Harriss-White对“穷人当中最穷的人”的描述中,这些人是意外事故、成瘾、天灾或健康变故,以及债台高筑的余波的受害者,他们被充满敌意的社会抛弃,与社会疏离。Harriss-White解释说,他们“(资产上)一无所有,(政治和社会地位上)一文不值,(实现个人能力上)一无所能的人。
她继续争辩说,“穷人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一类人,但社会显然希望除掉这一类人”。在论及印度和秘鲁这些可怜人的命运时,她指出,确实有一些运动试图矫正这些人或给他们赋权,但在人们认为可以牺牲的地方,也确实存在对这些人权利的剥夺。她描述了跳蚤丛生的仓库,这些早已惨不堪言的穷人被丢进去栖身。显然这些人是要作为不值得救助的人被简单地清理掉,救助的条件和资金来源问题无从谈起。
另一项对印度的研究一直追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研究中,Gooptu将对穷人的排斥与英国人对他们的一种看法联系起来-穷人不稳定、多变、四处飘荡、而且危险。在英国殖民者的印象中,所有这些因素都让穷人陷入道德败坏、社会失范的境地;在统治者的想象中,这些特点有可能使穷人酝酿政治骚乱。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情况也与此十分相似。穷人的这一形象使改造或抛弃他们似乎很有道理;究竟是改造还是抛弃则取决于救助是否附条件和是否区分值得的对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民国,此种穷人管理风格背后的推力是这样一种观念:挣扎在穷困中的人是不值得救助的废物,是整个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然而近年来印度的某些地区,以及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南非,都已经启动了直接给穷人支付现金的援助项目。Hanlon及其同事认为这种赠款是全球人权宣言之后新时代的产物,而不是国内政策设计的结果。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引入了人民有权免于贫困的理念,而在“全球南方”这一理念似乎在1990年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鉴于全球很多地区已经吸纳了这一方法,很难将它与国家特定的倾向联系起来。但有可能,所有这些国家都以一定形式接受这一点-不论其是否工作,是否“值得”,或如何花掉这笔现金,人们都有得到国家支持而生存的权利。
印度的某些邦发起了现金补贴计划,仅仅针对通常被认为“值得的穷人”,比如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此外,1995年中央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引入了一个名为“国民社会援助”的项目,当户主身故或残疾、妇女生育期间(生育期妇女是另一类“值得的”对象),贫困家庭都可以得到援助。这些支出分别划入国民养老金、家庭福利和生育补贴的范畴。但论述过这一制度的福利学者Townsend指出,尽管这一举措背后的理念和意图很好,但阻碍这一制度真正服务于穷人,尤其是不能受雇佣的穷人的主要障碍在于,政府投入不足。因为政府仅仅收取国民生产总值的8-9%作为税收。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一比例尤其的低,因为所有低收入国家在1990到2001年间的平均数是14%。
研究拉美福利的学者Segura-Ubiergo从根本上削弱了主张经济发展政策或政体类型与福利模式之间存在单一因果关系的理论。这类理论家总结西欧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用民主政体的类型和特定的贸易倾向来解释福利。西欧国家的共同经验是,民主制度伴随着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开放(因而进口国外产品的门槛很低)十分普遍,工人阶级群体和政党的压力使得从进口中受损的人能够得到补偿。
但是Segura-Ubiergo通过对1980年代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的考察发现正好相反,不是开放,而是国内保护主义推动的进口替代项目与劳工救助携手并进。除此之外,1964-1984年的巴西、1973-1984年的乌拉圭和1973-1984年的智利都不是民主政体,而阿根廷在此期间的很多年份(1966-1972,1976-1982)都是独裁专制政体。因此,既然这些国家不同于西欧国家,在讨论的时期内没有一个是持续的民主政体,似乎我们获得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可借此观察这类不同的国家给予不幸者的待遇。
Segura-Ubiergo也细分了“福利”概念,发现在这些地方(针对养老和失业的)社会保险所回应的动力不同于引起医疗和教育投入的动力。既然民主制或贸易政策都不能解释拉丁美洲的社会保护,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保护的观念以及拉美天主教国家普遍的家长式领导联系在一起的,是公平、正义的原则,以及当地社区对国家责任的看法(可能是改造模式的一个变化版本,受对国家和市场职责的态度的影响)。这种对国家责任的看法与西欧的声音回音模式有所区别。试图改造穷人并使其融入社会似乎是这一模式的特征。
然而,Segura-Ubiergo也观察到,1980年代晚期的贸易自由化废除了以前的保护主义。随着市场变得开放,很多以前惯常提供福利的大公司开始改变立场,将工人推向福利欠缺的非正式部门,尽管这时候所有这些国家都已经是民主国家。因此,与经济开放时期为了回应民众声音而扩张福利的西欧国家不同,拉丁美洲的社会福利在这种情况下下降了,提示福利与贸易和政体类型之间的标准关系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启动了附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项目,超过1亿拉美贫民已经从中受益。这些项目的原型起始于1997年的墨西哥,再一次让家长式管理和条件性与福利供给相互竞争。如果母亲送子女上学、喂养得当,定期带他们去找医生体检,家庭就可以定期地得到现金。智利、萨尔瓦多、哥斯达尼加等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现在也采用了类似的项目。尽管在某些地方,比如世界银行和中美洲开发银行,这种创新符合基于权利的救助模式,但在这三个国家,福利关照与权利之间的联系似乎比较弱,弱于改造模式下福利与集权的家长作风的倾向之间的联系。
正如Franzoni和Voorend指出的,至少在他们论及的国家中,这些项目“自上而下的政策过程都受精英与技术专家之间政治联盟的主导”,他们清楚地指出,社会要求或者“民众声音”并不是福利项目的触发器,他们写道,“社会联盟至今在整个图景中还并不重要”。类似地,他们还补充说,“CCT项目的制定更多的是贫困专家的事情,而不是草根组织或者穷人自己的事情。”
继续看后共产主义东欧国家的例子。正如Haggard和Kaufman在《发展、民主和福利国家:拉美、东亚和东欧》一书中强调的,公民们在社会主义统治下长久以来抱有的应得权利的思想遗产正是这些国家所采用的福利形式的一个突出原因-过去的记忆刺激了今天的期待。当然,作者们也论述了1990年后民主统治的巩固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
但是考虑到这三个地区在社会保护风格上的差异,Haggard和Kaufman发现,虽然每个地区到1990年代都已经实行了民主制,但在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统治之后,东欧的公民似乎已经期望政府大包大揽。这一期望正是塑造该地区后共产主义福利体系的最大影响因素。他们在书中这样表述:“在东欧,公众期望政府继续提供多种普惠的保护,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公共部门继续在社会保险和服务的筹资和提供上扮演主要角色。”因此,1990年代之后,普惠型福利和政府出资在这一地区仍然风行。因此即使民众偶尔发出声音,也是出于对政府的期望,而并不简单地是因为民主化。
另一方面,韩国和日本政府则更多地依靠私人而非公共筹资发展社会保护。因此他们对资金来源问题的反应不同于东欧或西欧,即使在某些时点上,韩国的政治体制和智利、乌拉圭和秘鲁的一样是威权统治,也和西欧一样实行开放经济。除此之外,韩国和日本尽管在社会政策上采取了相似的路径,但在这些年间采用的政体类型却并不相同。
在韩国,志愿组织和企业被赋予提供社会保护的责任。事实上,在日韩两国,社会安全网都更多的是雇主而非国家的责任。正如Kim等人辩称的,“在韩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家庭支持和职业福利弥补了国家福利的欠缺”。最低标准的生活也未被视为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目标超越了所有其他的考量。
即使在1987年国家向民主制转型后,韩国仍然继续依靠志愿团体和公司提供大部分资金和社会福利。尽管1999年创立了基于权利的援助项目,对福利的公共投入也翻倍了,但覆盖面仍然有限,得到救助的穷人只占有资格受助者的三分之一。
日本也和韩国一样,只救助“值得的”穷人的观念占主导地位,救助对象仍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因为肢体格健全的人一直未被给予福利。正如Kasza解释的,官方更多地强调的一直是通过对公司的激励体系帮助人们保住工作。这一立场也与失业者应该为自己的境况负责的思想一致。历史上,家庭支持减轻了对政府帮助穷人的需求。在Schoppa的提法中,日本政府构建了一种帮助弱势人群生存的“护航资本主义”的模式,企业被责成照顾自己的雇员而且限制裁员,同时政府通过给企业补贴和支持生产的政策来帮助企业维持经营。
在日韩这两个东亚国家,为国家利益而追求高增长的目标意味着促进生产(生产主义)的公共政策是社会保护的特征,而不是权利观念或对民众声音的回应。这一分析与 Haggard和Kaufman的观点一致--尽管东亚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险水平较低,但有些国家,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确实对教育投入很多,以此提升那些因缺乏培训而致贫的穷人的知识和技能。因此这些政府出资的福利目的是改造和提升那些不幸者,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到国家发展的宏图中,也就是与改造/重塑模式的积极方面一致。
非洲大陆的国家众多,其历史渊源各不相同,对待穷人的文化传统和规范异彩纷呈,因此很难做出归纳总结。但是2006年的一次非洲联盟会议确实提出了《利文斯顿行动呼吁》。该呼吁决定,非洲大陆上的每个国家都应该建立起社会转移项目,内容应该包括社会养老金和对脆弱儿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社会转移支付,也就是针对那些“值得的人”。然而即使这一非常有限的呼吁也并没有实现。比如,直到21世纪早期,尽管家计审查的现金福利正在向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延伸,但Townsend报道说,只有赞比亚真正在提供现金转移项目,而且仅仅提供给该项目包括的最穷的十分之一家庭。
尽管南非已经开始了建立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努力,但直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尾,社会福利仍然局限于“值得的人”,也就是老人、儿童和残疾人。此外,Hanlon及其合作者也已经发现,在较穷的国家,“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总是主张穷人至少要部分地为自己的贫困负责,因而不值得支持”。只要这种情绪蔓延,非洲很多国家提供的CCT项目将仍然只会惠及他们所称的“值得帮助的穷人”。
正如Garrett等人举出的,在西欧很多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民主政体似乎确保了一点:只要偏左翼的政府上台,民众的声音足以促使政治家做出回应,提供慷慨的福利项目。这种声音通常是以选票,有时也以工人和工会的罢工、抗议表达出来。因此,民众的需求被认为值得政府做出回应。
然而在同样是“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的美国,在这个选票以相近的方式给福利分配提供动机的国度,情况却有所不同。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断言和证明的那样,美国的社会保护和保障的权利观并未像西欧很多国家发生的那样影响到投票。比如Piven和Cloward在分析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写到,“(历史地看)美国工人阶级组织脆弱,选民代表机构有缺陷,国家结构也使得公众利益难以转变为公共政策”,这使得不满的民众更经常地转向抗议活动而不是投票,而且抗议活动在美国受到的关注也比在西欧的少。
或许这两位作者更有意义的观点是,“大多数的美国人……鄙视(福利制度)”,谴责福利机构是在“纵容骗子和偷奸耍滑的人”。在这一立场背后,是Piven和Cloward所说的公众普遍的“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保留态度”和“市场观念”-相信市场力量的作用能够自动地回报那些值得的人,淘汰技能不足和德行有亏的人。因此,二战以后,尤其是1996年的“困难家庭临时援助项目”废止了原先的“失依儿童家庭援助项目”后,原来更慷慨的原则被改变了,对体格健全而找不到工作者的支持从美国的社会保护中消失了。
美国“社会救助的根源”是什么呢?Soss,Fording和Schram的新书《约束穷人》让我们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书中宣称,美国的福利领受人“不是被视为权利的享有者,而是指导和监督的对象”。这一观点与 Wilson以及法国社会科学家Castel的看法一致,后者认为,“美国未能重视穷人的社会权利”。因此这些学者并不认为实现权利是美国社会救助的基础;相反,Soss和他的合作者暗示,美国社会救助的国家目标远非实现权利。他们写道,美国人普遍认为“需要修正穷人的行为以满足公众期望”,而改革者也“将社会秩序放到社会正义和公民顺从之上”。显然,清理/改造模式,尤其是其消极的一面在这里更适用。
书中提到的新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保守主义者的“强大联盟”也支持我的观点。这一联盟“推动的议程以秩序、约束、个人责任和有道德的国家为基础”。在他们的描述中,克林顿总统批准的《困难家庭临时救助法案》要求领受救济者必须工作,设定了领取资格的时限,规定了对违反法案者的惩罚,这些都是为了吸引憎恶福利的选民的选票,而不是那些可能领取福利者的选票。Townsend认为这种对救助憎恶是因为福利批评者认为,福利项目必须于与“美国的工作价值观和个人责任”一致。这一观点将穷人生活困窘的责任归到他们自己个人身上,十分符合我在前面论及思想观念影响时引述过的,支持由市场提供福利和穷人自己应该为其窘境负责的观点。
在此我还想补充Wilson的类似观点,他认为美国的社会保护体系是在“对贫困和福利的本质及原因的基本信念体系”上生长出来的,这一体系“主要从个人角度来界定贫困和福利的经济、社会后果”。用他的话说,这一体系“从个人角度解释贫困”,比如“个人努力或能力不够、道德败坏或工作技能低劣”,而欧洲人则本能地将结构性的、或者政府性的原因作为出现穷人的推手。为支持这一观点,Wilson提到了1990年欧洲的一项调查。在这一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将贫困追溯到社会不公、不幸或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凝聚在这两个地区相反的社会保护理念基础上的这种差异,削弱了政体类型影响福利策略的理论。
四、结论
本文认为,可以从观点、看法和道德论证这样一种角度来给福利归类,将其归为三种模式或者三个理想型:基于权利观念的福利体系;因回应声音而产生的福利项目;以及为了将某些令人不快的人或者不合适的行为从公共领域中清理出去而对他们加以排斥、改造或重塑的福利政策。
每一种模式都有特定的提供或拒绝提供福利的策略,或者说,补偿或惩罚受益人或对象的策略;在所有福利项目都必须面对的三个大问题上,每个模式都在如何应对和选择上有自己的回答。这三个问题是福利是附条件的还是普惠的,是否区分救助对象值不值得,以及筹资应该是(国家)公共来源,还是(家庭、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或志愿组织等)私人来源。我提出,这些让各个模型和决定各具特征的思想观念因素,与国家和社会对彼此的看法和期待有关,与一国社会上盛行的对国家和市场的态度有关,而不是来自政体类型或贸易和发展模式。
注释
①Jacob S.Hacker.The Divided Welfare State:The Battle over Public and Private Social Benefits in the United States.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1-12.
②“政体类型”的概念由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h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Johns Hopkins,1996.38-55)提出,主要的类型是极权型、极权型、威权型、民主型和苏丹型五大类。
③直到相当晚近,西欧民主政体的福利研究仍然是这类研究的主要内容。Isabela Mares and Matthew E.Carnes.“Soc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2(2009):96.认为,强调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两个极端漏掉了这两个典型类型中间的许多变化。
④Francis G.Castles.“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 18.2 (1995):291-313.讨论了民主转型对福利的影响;Ito Peng and Joseph Wong(“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Purpos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Politics &Society 36.1(2008):61-88)发现这种转型导致新的需求和新的福利分配形式;Ho Keun Song(“The Birth of a Welfare State in Korea:The Unfinished Symphony of Democr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3.3(2003):406)解释到,民主化放开了政治渠道,追求福利的人由此可以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⑤James M.Snyder,Jr.and Irene Yackovlev.“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s.”M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pril 2000.
⑥Mares and Carnes,op.cit.,108;Peng and Wong,op.cit.,68,70,84.
⑦这类研究的例子如Geoffrey Garrett and Peter Lange.“Political responses to interdependence:what’s‘left’for the lef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hereafter IO)45.4(1991):539-64;Evelyne Huber and John D.Stephens.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Partie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Marke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aul Pierson.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Reagan,Thatcher,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⑧例子之一是 Mares和 Carnes,(op.cit.);Peng和Wong(op.cit.)提出,社会政策的制度目的被改变以适应标志着社会政策改革三个不同时代的经济-社会目标:发展国家时代、民主改革时代以及后工业时代的目标。Martin Rhodes.“Souther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Identity,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Reform.”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1.2(1996):1,7.在第7页也提到了发展因素的影响,比如工业发展的形式和社会政治发展的模式。
⑨Peng and Wong,op.cit.See also 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O52(1998):787-824;idem.,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and idem.“Glob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round the world.”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5.4 (2001):3-29.
⑩Gosta Esping-Andersen.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这三个世界是自由主义世界,法团-保守主义世界,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每个都代表一种国家、市场和家庭结合的不同的典型类型。
○11Castles和Rhodes(同上)以南欧为例子。拉丁美洲的例子见Alex Segura-Ubierg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atin America:Globalization,Democracy,and Develop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东欧的例子见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Kaufman.Development,Democracy,and Welfare States:Latin America,East Asia,and Eastern Europ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以及Mitchell Orenstein的研究。
○13Mares and Carnes,op.cit.,94raise the issue of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social policies,while Peng and Wong,op.cit.,61speak of reforms“to meet the imperatives of flexible labor markets.”提出了社会政策的劳动力市场后果的问题,而 Peng and Wong,op.cit.,61则提到改革以“满足弹性劳动力市场的紧要需求”。
○14Mares and Carnes,op.cit.,93;Snyder and Yackov-lev在第35和36页得出这一结论,提出今后的研究应该“对“社会开支”这一大的类别进行细分。”
○15Mares and Carnes,op.cit.,94担心,对社会政策实施和设计缺少关注阻碍了对其分配效果的理解。
○16Luis Ayala.“Social Needs,Inequali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Spain:Trends and Prospects.”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4(1993):159-79;Moreno,op.cit.,156;Rhodes,op.cit.,8,20.
○19Loic Wacquant(Punishing the Poor: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指出,这意味着通过监狱来对付穷人。
○21Janet Y.Chen.Guilty of Indigence:The Urban Poor in China,1900-1953.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24Nandini Gooptu.The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3-16,420-23.
○25Joseph Hanlon, Armando Barrientos and David Hulme.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The Development Revolution from the Global South.Sterling,VA:Kumarian Press,2010.19-20.
○27See references to the work of Geoffrey Garrett in notes 7and 11,above.
○34Stephen Crowley and David Ost.Eds.Workers after Workers’States:Labo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Rowman&Littlefield,2001.
○39Leonard J.Schoppa.Race for the Exits:The Unraveling of Japan’s System of Social Protec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2,4.
○40Kasza,op.cit.,115.
○44Hanlon,op.cit.,3.
○45See notes 7and 11for Garrett references;see also Segura-Ubiergo,op.cit.,35-42.
○49William Julius Wilson.When Work Disappears: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NY:Vintage,1996.161.
○54Wilson,op.cit.,1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