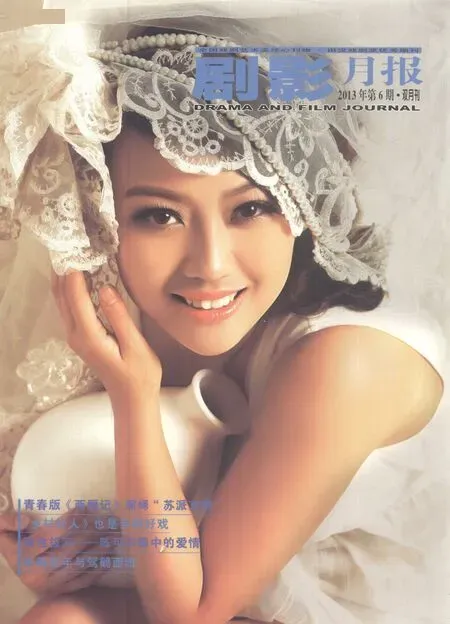我演中日版《牡丹亭》中的杜母
2013-11-21朱惠英
■朱惠英
我演中日版《牡丹亭》中的杜母
■朱惠英
昆曲中日版《牡丹亭》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与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合作打造并演出的,这是一次开拓中外合作传承文化遗产新途径的成功尝试,昆曲艺术在跨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绽放了华彩。在演出、加工、修改,再演出、再加工、再修改的过程中形成了包含《游园》、《惊梦》、《写真》、《离魂》》、《冥判》、《叫画》、《幽媾》、《重生》八折的演出版本。坂东玉三郎出演杜丽娘,作为从艺三十余年的昆曲演员我有幸参与其中饰演杜母,并且得到了剧中女儿“有妈妈的感觉”的评价,而这恰恰是我在塑造人物时期待达到的效果,我要演人物,力求做到“我就是”而不是“我去演”,这是其一;剧中杜母的戏份并不多也没有特别出彩的重头戏,甚至性格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化,如何将杜母这一人物塑造得丰满是我努力的方向,这是其二。
“至情”是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而这里的“情”,当包括人间的一切感情,不限于男女私情,老夫人对女儿的爱同样也是一种“至情”。
中日版《牡丹亭》中杜母只出现在两折戏中,第一次出场在《惊梦》一折。刚出场“夫婿坐黄堂,娇娃立绣窗”两句简单交代了自己的身份,紧接着就是“我儿哪里,原来昼眠在此,我儿醒来,为娘在此”。看到女儿昼眠,不免教训几句,从“孩儿说刺绣才罢,为何昼眠在此”的责怪,到“怎么不到学堂去看书?儿啦!花园冷清少去闲游”的训诫,明眼人都能看出,前一句是故作嗔怒状,后一句却是真心话。然后还要自我宽慰“女儿家长成了自有许多情态,且自由她,我去了。正是:婉转随儿女,辛勤做老娘”,真切表现了一位母亲对女儿的宠爱之情。第二次出场是在《离魂》一折,这一折中有着生离死别所以特别的凄凉悲切,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杜丽娘提出后园大梅树是儿心所爱,死后葬于梅树底下心愿足矣。杜母先是说“这个如何使得”,马上又说“为娘依你便了,依你便了”,作为母亲必然是要满足女儿最后的心愿的。特别是最后杜丽娘拜别母亲后,杜母的一句“儿啊”的叫喊以及用颤抖的手去触碰女儿的做法,深刻的表现了杜母的心痛悲伤之情。
这就是中日版《牡丹亭》中的杜母,我用心演绎了这一角色。回想演出的历程,从日本到北京,从上海到香港,特别是今年二月该剧首次踏上亚洲以外的国际舞台、首次以纯粹商演模式献演欧洲著名剧场,于巴黎夏特莱剧场连演七场,每天2400余张90至10欧元不等的戏票几乎被抢购一空。《世界报》、《费加罗时报》等法国媒体都对演出盛况予以报道,《解放报》记者以“此般胜景在夏特蕾怕是有一段时间难以重现了”这样的笔触来记录和评价此次演出。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凤凰卫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深度报道了此次演出。
中日两国艺术家同台演出,将代表着东方审美极致的昆曲艺术呈现给观众,共同实践昆曲的传承传播。我作为一份子身在其中与有荣焉,也愿意在以后的从艺生涯中将自己的力量贡献于昆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