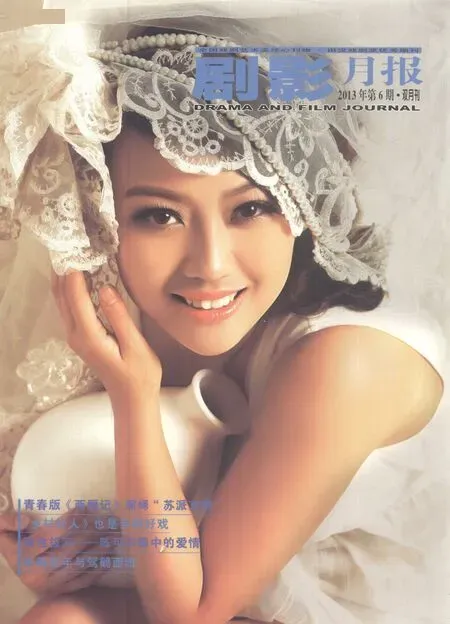漫谈话剧的音乐
2013-11-21陈学超
■陈学超
漫谈话剧的音乐
■陈学超
话剧和其他戏剧艺术一样具有两个特征:一,创作上的集体性,它以剧作者的创作——剧本为主导,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以舞台美术和音乐为辅助,以导演的创作构思为艺术处理基础。二,艺术上的综合性,实际上就是指戏剧艺术拥有丰富的表现手段,它是综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建筑等各种表现手段来塑造舞台形象的艺术。
话剧演出的综合性,使它注定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艺术。而每一次演出,则需要剧作家、演员、音乐家、舞台美术家以及舞蹈家等的集体合作,他们都在这集体劳作中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在使用道白来表演的话剧里,无论是插曲、配乐还是音响,都是演员表演艺术的辅助成分,它的价值存在于对演员塑造舞台形象的协同作用,自身的独立价值已经融入话剧价值之内。
音乐的内涵众说纷纭,但少有人能说到要害处。语言文字代替不了音乐,也说明不了音乐,如果可以,我们就不需要音乐了。余华有一本书叫《高潮》,书中列举了大量音乐家的名作名曲,但那也只是作家对于音乐和文学在叙事上的亲和性作出的梳理,他有这样一段描述:“音乐的叙述和文学的叙述有时候是如此的一致,它们都暗示了时间漫长的衰老和时间漫长的新生,暗示了空间的转瞬即逝:它们都经历了段落的开始,情感的跌宕起伏,高潮的推出和结束时的回响。音乐中的强弱和渐弱,如同文学中的浓淡之分;音乐中的和声,类似文学中多层的对话和描写;音乐中的华彩段,就像文学中富丽堂皇的排比句。一句话,它们的叙述之所以合理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在流动,就像道路的存在是为了行走。不同的是,文学的道路仿佛是在地上延续,而音乐的道路更像是在空中伸展。”从这里可以看出,音乐所表述的思想,不是因为太含糊而不能诉诸语言,相反,是因为太明确而不能化为语言。试图以文字表述音乐的思想,会有正确的地方,但同时在所有的文字中,他们又都难以正确完整地表达。
任何一种艺术形象都有特殊的存在形态,音乐通常被称为“时间艺术”,绘画雕塑则被称为“空间艺术”,而话剧则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综合艺术,只要情节允许,角色允许,时空背景允许,创作者的意念认同,那么多种元素皆可以很自然地渗进作品之中。
一般情况下,出现在影视里的音乐大多是由作家创作出歌词再由音乐家谱曲,而话剧则少有音乐家谱曲这一环节,那么音乐风格的运用就好像讲话时口音的运用,一定要综合考虑角色心理变化和剧情本身需要,时代背景等等。而不是绕着圈儿地揣测观众喜欢什么,就好比我们不宜用摇滚和HipHop让梁山伯与祝英台谈情说爱一样,除非这个音乐的选择有特别的意义存在。在开始选音乐之前,这是必需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采用这种音乐风格?我们需要一个美学上站得住脚的答案。如果没有“美学上的答案”只有“因为大众市场的考量”,那这个理由不成立。在一部话剧中,演出与观看是真人对真人,观众就在现场,所以舞台与观众的空间关系是直接的双向交流,而舞台表演是一种充满情感的表演,故事的情节设置固然重要,但其中的音乐更是起到烘托情感的作用,它更好地塑造了演员的舞台形象,也渲染了剧情。如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剧《雷雨》,就引入了巴赫音乐的“复调”语言结构,这是在曹禺1934年的原著序幕中所规定的。演出者在剧中第一次用双排键模拟管风琴的声音,以呈现曹禺当年所期望的巴赫大弥撒音乐《屋内静寂无人》。该剧还加入了九人唱诗班,合唱者以剧中人的身份带入《雷雨》的故事现场,成为强有力“雷雨之声”的一部分,成为创新《雷雨》演出文本不可替代的角色,营造出诗意和神秘气息。
为戏剧而创作的音乐,与为音乐会演奏的音乐和传统歌剧的音乐有所不同,受到与之不同的规律的制约。戏剧音乐的创作都是为了充实、支持和控制戏剧情节而设立。在歌剧中,剧情的发展和视觉的展现,都受制于音乐;在芭蕾舞剧中,音乐是作为表演的骨架和情绪衬托之用;而在话剧或电影的配乐中,音乐则主要用于宣泄情绪、塑造角色和推展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