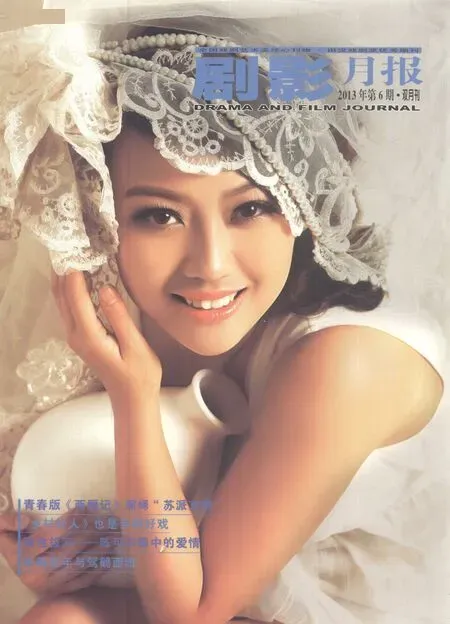《谿山琴况》对二胡演奏的一些启示
2013-11-21顾怀燕
■顾怀燕
《谿山琴况》对二胡演奏的一些启示
■顾怀燕
《谿山琴况》是明末清初虞山派琴家徐上瀛(号青山)所著的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论述古琴表演艺术理论的著作。他参照宋代崔尊度提出的说法“清丽而远,和润而远”,再将冷谦《琴声十六法》之理论扩大延伸。《琴况》全篇共二十四则,原载于《大还阁琴谱》,是对琴乐内在意境和外在风格、审美价值与标准的要求,为古琴艺术所提出的审美准则。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先把琴的技巧和审美分开,再把琴的技巧和审美揉合在一起,其意义远不只单一针对古琴表现艺术,而是对所有乐器的演奏均有极大的启迪。
所谓“琴况”,即琴之状况、意态与审美之况味、情趣。著中共写有二十四况,提纲和内涵简析如下:
(1)和——论调弦、吟揉、音意等之和(兼论本质与技巧);
(2)静——论琴音之静在于调气与练指(兼论品格修养与风格之配合);
(3)清——提出贞静宏远为琴度之内涵,并指出气候在演奏中之重要(兼论本质与技巧);
(4)远——论想象及弦外之音的意境(意境论);
(5)古——论琴音雅俗之辨(形式与风格论);
(6)澹——论琴元音之孤高岑寂(趣味论);
(7)恬——论恬之为君子之质和有德之养(趣味论);
(8)逸——论琴音之超逸实来自琴人品德之超逸(品德与修养论);
(9)雅——论琴之雅得于静远澹逸而不媚俗(风格论);
(10)丽——论琴音丽与媚之别在于古淡与妖冶(风格论):
(11)亮——论琴音之亮得自左右手所发清实的金石之响(音色论);
(12)采——论琴音之采得之于几经锻炼后指下之神气(音色论);
(13)洁——论琴音之意趣实得之于修指之严净(境界论);
(14)润——论琴音之中和温润(音色论);
(15)圆——论吟猱、按弹、乐句转折间婉转动荡无滞无碍的处理(技巧论);
(16)坚——论用指之坚必清劲和无力不觉乃可得金石之声(技巧论);
(17)宏——论琴音必中和闲雅、下指必宽裕纯朴,始能合乎古调(境界论);
(18)细——论节奏、章句转折、连指与全篇细微之处理和把握(技巧与趣味论);
(19)溜——论技巧之熟练无滞得于指之坚实灵活(技巧论);
(20)健一一论指之灵活刚健与琴中和闲雅之配合(技巧论);
(21)轻——论音之轻重变化皆不离中和之旨(音量与趣味论);
(22)重——论弹琴重抵轻出之法和情气之并兼(音量与技巧论);
(23)迟——论希声与迟趣之关系(趣味与意境论);
(24)速——论小速意趣、大速意奇之旨(技巧、趣味与意境论)。
这二十四况,其道理和器乐相通,都是由演奏的技巧谈及内心的审美。中国乐器中很少有像古琴那样具备一套完整的弹奏风格、审美准则,所以借鉴《琴况》,无疑对二胡演奏艺术也有极大的启示。
下面笔者将分别具体地谈谈“和”、“远”、“静”这三况。
“和”是诸况中的第一况,也是全篇总纲。“和”中提到三个“合”——“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
“弦与指合”,就是指法必须符合琴的客观性能,在演奏技术上,要达到演奏技巧自如运用与纯熟掌握。这一点,在二胡演奏中是重要的基础训练。我们日常所强调的各类技巧练习,在左手上,有音阶、琶音、换把等;在右手上,有各种弓法练习,如快弓、跳弓、连顿弓、连跳弓、抛弓等;还有各种训练两手配合的练习,从其他乐器移植过来的练习。概括起来说,都是为了“弦与指合”,都是在做基本功的训练,做到了“弦与指合”,演奏才能得心应手。
“指与音合”,是指音的精确性,对乐曲分析的准确性。在掌握纯熟的指法技艺基础上,使演奏的处理合乎音乐的语气、句法、章法,由此产生悦耳而富有韵味的情感音调,要做到每个音、每个乐句乃至全曲必须节奏清楚、层次分明,而不是只把音符奏出就万事大吉了。每一部作品都有其自身的不同的音乐形象和意境,我们在处理乐曲时要做的是找出内在的情感关联,选择一种最贴切的表现手法——包括对轻重缓急的处理,对乐段结构织体的把握,对乐曲创作背景的了解——然后再现作者的意图,用手指表达出音乐的作品的内容。
至于“音与意合”,徐上瀛认为:“音从意转。意先乎音,音随乎意,将众妙归焉”。的确,艺术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意境,必须驾驭与技巧紧密结合的“音”;而“音”又必须服从“意”,表达“意”,这样才能引人入胜。《琴况》认为“音”必须讲求形式的美,做到“迂回曲折,疏而实密;抑扬起伏,断而复联,”使“音”的精义与“意”的深微相一致。但《琴况》并未停留于此,它进而还强调了“得之弦外者”的重要性。它认为有了弦外之音,包括想象、风格等等,才能使艺术家的表演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与山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暑可变也,虚堂凝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其无尽藏,不可思议”。这才是“音”与“意”的真正统一,也是演奏者们最终要达到的审美境界。
就二胡演奏者来说,对音乐风格、意境的把握除了需要演奏者有娴熟的技巧来表达,更需要有各种知识的积累和情感的体验,在自身包括感知、想象、联想、意向在内的审美情感得到一种新的组合。对于多年来一直在专业院校受到训练的学生们,前面提到的两种“合”大多都能比较优秀地完成,但是在“音与意合”这个问题上似乎还有所欠缺。徐上瀛所谓“弦外之音”便要去弦外寻,比如说戏曲音乐、民间音乐、传统乐曲、各地民歌、西方音乐,还有各类艺术形式,如绘画、文学,甚至历史、人文都能对演奏有不可估量的帮助。演奏者在音乐的深度上和其它知识的广度上都应有良好的积累。一旦有意识地注意这些方面的积累,对周边的事物保持着良好的兴趣和观察力,并且在演奏中合理地加以运用,那么无疑,他在这一辈演奏者中便是崭露头角的。
关于意境,徐上瀛在“远”这一况中有重点的论述。“求于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也。”中国艺术,如绘画、诗词、音乐、舞蹈都讲求“意境”,并以此为最高的审美准则。
意境一词最早来自王国维《人间词话》,他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落第二手。”“意”即:艺术家主观情感的流露;“境”即:外在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的反映、再现。这种情境相融的境界蕴涵着无穷之味和不尽之意,使人回味。意境所强调的是一种无限和深微的精神境界。要到达所谓的“意境”就跟做学问一样,王国维引用了三句诗,提出三种境界。第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二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意境的追求是曲折、艰难、漫长而永无止境的。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创造音色,塑造形象”是密不可分的。
“静”这一况中说好的音色应该“如爇妙香者,含其烟而吐雾;涤玠茗者,荡其浊而泻其清”,“急而不乱,多而不繁”,“雪其躁气,释其竞心”,“声厉则知指躁,声粗则知指浊,声希则知指静”。包括后面的“丽”、“亮”、“采”、“洁”、“润”、“圆”、“坚”等况中都提到音色的训练和标准。
每首乐曲都有自己的艺术形象,它需要一种别于其它的音色来塑造。正因为有不同的形象,乐曲便有了在演奏中的不同音色。比如刘天华的《病中吟》,音乐形象是压抑而苦闷的,运用的音色就不能是明亮而热情的,应该是灰蒙蒙的调子。就象一个演员要演一场失去亲人的哭戏,不会穿得红红火火,不会戴得珠光宝气一样。音乐也应当有颜色,这样才合成了“音色”这个词。画家用颜料,我们用声音。在现代的很多大型作品中,音乐形象呈现出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趋势。在一首乐曲里,至少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形象,表现了更强烈的矛盾对比。这就需要演奏者的“音色库”里有丰富的色彩,并能准确熟练地运用它们,从而塑造出典型鲜明的艺术形象。比如说金复载《春江水暖》第一乐章,应当用清新流畅的绿色基调的音色。可是主题音调有多次在不同调上的出现,这就应当在绿色的基础上添加别的色彩,使主题的每次出现都有新意。D大调是乐曲主调G大调的属调,所以这一段应该较主调更为明亮,色彩应灿烂些。而尾声时主题在下属方向的C大调出现,那么音色就相对要柔和一些,有着晚霞温暖的妩媚。这样处理音色的变化会使得乐曲的层次更为分明。
二十四况中有许多都是对立统一的。比如“宏”和“细”,“轻”和“重”,“迟”和“速”,这些对举就像春夏秋冬、日夜交替一样,互相包含,组合起来,使乐曲跌宕起伏,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儒道佛的哲学思想对《琴况》的影响。
《老子》“有无相生……声音相和”,“淡兮其无味”的观点使徐上瀛崇尚“淡和”的审美观,于是有了提纲挈领的“和”况。“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声淡则益有味”皆出于此。孔子也认为“和”合乎中庸之道。周敦颐援道入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吸收、融合,提出“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的“淡和”说,从而使“淡和”成为儒、道两家尊崇的音乐审美观。《老子》说“大音希声”,徐上瀛在“和”况中也提到“太音希声,古道难复”,他从演奏美学角度对“希声”有详尽的描写,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徐上瀛此处对“希声”的解释是建立在有声之乐的基础上,和老、庄本意不同。它代表了绝大多数琴论的观点,古代琴论中的“希声”之“希”多为稀疏之意,即指“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曲为节稀声不多”的有声之乐,而《老子》“大音希声”之“希”是“听之不闻名曰希”之意,指无声之乐。徐上瀛发展了“大音希声”对古琴美学的积极影响,人们以此追求“淡而会心”的含蓄之美,要求创造音乐的深远意境,追求音乐的弦外韵味。
庄子“得意而忘言”的思想又是“远”况中弦外之音的出处。陶渊明也说过:“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认为弹琴就是为了求得弦外的意趣。此后的琴论也都重视音、意之关系,以心手俱忘、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为其最终目标,并从创作、演奏、欣赏等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体现出对弦外之音、音外之意的追求。
道家主张自然之美,自由为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认为音乐可以自由表达感情的思想,积极地影响着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李贽继承、发展了庄子“法天贵真”、反对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提出“琴者,心也”的思想,这是道家古琴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它认为音乐是一种自由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艺术,其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的各种感情的观点,是对道家“法天贵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儒家礼教思想的突破。“恬”况中的“兴到而不自纵,气到而不自豪,情到而不自扰,意到而不自浓”,体现了儒家中庸之道的积极影响。
徐上瀛晚年曾寄居僧舍,所以佛教思想对他也有较大的影响。《琴况》里提到“调气”、“绝去尘嚣”、“遗世独立”、都来源于佛教思想。在“洁”况中,徐上瀛将佛教的净观贯穿于手指的修炼始终,强调由心净始,经过指净,达到音净,并提出“音愈希,则意趣愈永”的审美观。在这里,徐上瀛再次提到了“希”,强调了有声音乐中“淡和”的风格,发展成为儒、道、佛合一的音乐审美观。儒、道、佛三家尽管从各自教义出发,对音乐的功用、目的等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音乐的审美上总体特征基本一致,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对音乐的深远的影响。
这里提到的关于儒、道、佛哲学思想对《琴况》的积极影响,在二胡演奏审美上也同样适用。哲学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停留在明清时期的古琴演奏上,对整个中国当代甚至以后的音乐乃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吸收中国哲学的积极因素,使它作用于我们的世界观,并用自己的乐器合理地表达出来——这才是我们肩负的重任。
(上海音乐学院)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吴钊:《徐上瀛与〈谿山琴况〉》
叶明媚:《古琴音乐艺术》
苗建华:《古琴美学思想中的道家思想》
苗建华:《古琴美学思想中的佛家思想》
炎樱:《由〈谿山琴况〉联想到钢琴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