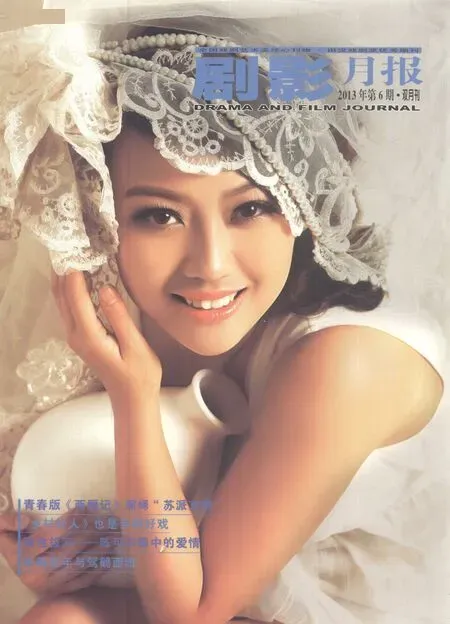中国动画艺术创作浅析
2013-11-21陶亚菲
■陶亚菲
动画在当今中国是一个既流行又时髦的新兴产业,在美国和日本动漫产业的成功示范效应下,其发展的势头很快,据统计,2012年我国的动画产量已达到了惊人的22万分钟,但是,高产并没有带来高质量和高效益,很多因为质量太差而无法播放,即使播放的也是看者寥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很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对动画的认识和理解总体上还停留在直观粗浅、简单模仿的层面上,具体表现在:学校在动画专业教育中大多侧重在漫画或者插画的技能技法培养上。诚然绘画技术在动画制作中的地位的确很重要,但它仅仅是动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种现象在一些新设动画专业的学校中尤为突出;还有一些业内人士把动画归入传统影视艺术范畴,认为动画只是影视的延伸,殊不知动画是一种全新的视听艺术形式,有其自身的艺术特点和表现形式;还有一些人把动画仅仅看成是个商品,在他们看来动画只是一个挣快钱的行业,只要选一个题材,编个剧本,找几个画手,就可以制作出一个动画产品,就可以挣钱了。由此种种导致了当前中国的动画创作问题重重:受众群体单一,画面简单枯燥,故事情节幼稚低俗,原创能力不足等等。面对问题,国内动画业界人士也做了很多努力,不论是自身产业的调整和完善,还是向外技术的借鉴和模仿,似乎都无法改变现状,中国动画仿佛陷入了魔咒。
其实,中国的动画起步并不晚,之所以在当今纷乱的时空中失去了专心和独立发展的自我,是因为动画业界心态的浮躁和对动画艺术创作真谛的认识理解偏差所致,当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和了解动画的本质特征时,就急于创作,并希望作品可以立刻得到物质回报。其结果必然是“拔苗助长”“欲速不达”。对待艺术,宗白华先生曾说:“要研究一种学术,最初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学术的根本观念完全明白,没有丝毫含糊,然后才能讲到那些高深的理论,微妙的学说。”所以面对当前我国动画创作的困境,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安住内心,回归源头,以一种恭敬治学的态度,通过解构和分析现有的动画形式来重新认识和研究动画艺术的本质,从而找到走出动画创作困境的途径,实现我国动画艺术创作的回归
动画生存的时代是被喻为“信息爆炸”的时代,在世界性的各种文化信息碰撞和融合大背景下,以往那种传统逻辑实证(经验)主义分析或模式化,统一性观念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渐渐失效,动画艺术或多或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多样性、异质性的时代烙印。因此,笔者认为动画艺术创作的突破应体现在“多元化”和“突现性”的分解和重构上,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文主义思想来认识动画,发展动画,动画创新需要一种新的思考和实践模式。因此,我们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对动画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
一.动画是对时空纬度的解构和重构
动画是一种对某一题材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动态的再创造的视听艺术形式。它运用有意识的逐格分解与逐格还原的表达方式赋予无生命物体于生命力,这是一个重构素材与异质化物质的过程。重组时空是动画运动的根本,也是它的生命源泉。而操作起来,那其实只需要运用一个很基础的物理常识:时间、空间,距离、速度的关系,但却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世界’一词是指人存在于其中的物的环境——一个与有用之物相联系的包围性区域。我之所以把有用物作为一个领域提出来,是因为从来没有这样东西作为一个有用物而存在的。任何一个有用物的存在总是属于一个有用物的整体。”动画时空的重组正是这个后现代主义现象的体现。从事动画制作的人都知道运动的绘制技术就是靠控制运动的时间和空间距离的相对比值来塑造不同的个性或情绪的技术。早在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动画师Grim Natwick就总结:动画就是时间和空间。比如要区分一个胖子的“世界”和一个瘦子“世界”,以走路来体现,胖子的步伐慢一些,所以胖子在单位时间里经过的空间距离比瘦子要短;再比如要区分一个欢乐的“世界”和一个低沉的“世界”,欢快的世界中人的运动单位时间里经过的空间距离比在低沉的世界中要长。动画时空构建是解构性的,抛弃了封闭的文化和科学的内涵,任何地区的人和事或者仅仅是想象的人和事,都可以在动画中同时为那个构建的“世界”服务,比如《冰河世纪》三维技术直接引领人们回到冰河时期,《海贼王》的世界则很明显的反应出多元文化的想象和重组,《麦兜》的时空里,则是一群动物和人一起生活工作,动物和人有同样的烦恼和快乐……而这一切都在于人的掌握之中,它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认识,不论是局部的人物角色,或者整体的时空背景,在动画中任何可以服务构建的时空组合都是合理的,它创造的是一个虚拟的不受约束的精神艺术世界。
二.动画是对艺术门类的解构和重构
动画包含了众多的艺术门类,它有绘画元素,但不仅仅只是绘画,它有戏剧元素,但又不同于戏剧,它有音乐元素,但音乐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它集绘画、漫画、电影、数字媒体、摄影、音乐、文学等众多艺术门类为一体。可以发现,动画的出现和发展并非无缘无故,它似乎在解释从“分裂走向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而这也适用于艺术领域,那些分裂的艺术门类走向一种大同的融合,从而衍生出全新的动画艺术。然而动画的综合性既是显而易见的,但又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也正是因为误解,导致了当今我国动画作品的参差不齐,杂乱无章,成效甚微的局面。我们虽然已经了解到动画包含了很多艺术门类,但却从未完整深入的分析过它们的融合性问题,这样的情况对于学习或者从事动画创作的人而言并不乐观,那些纷乱的艺门类就好像无边无际又深不见底的太平洋,让人不知所措。众多艺术学科间的“裂缝”导致了一种无奈的“拼凑组合”,即不同艺术观念的整合并没有在各个艺术学科间达成思想观念上的统一,因此产生的只能是目前中国很多动画常见的弊病,比如:场景和人物风格的不统一;过于的强调美术画面效果;动画配音与画面不同步等。其实,对于动画的综合性而言,最重要的应该在于“合”,它是一个分解再重组的艺术创作过程,是把那些独立的艺术门类变成构成动画的艺术元素而加以融合的过程,因此,对动画的认识不应该停留在其中任何一个单个艺术门类的认知方式上,那是不完整的。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日本的动画,日本的动画之所以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很多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的动画在各个组成部分的表达上达成了思想上的共识,对一部叫做《虫师》的动画片的采访可以证实这个共识的重要性。《虫师》描述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虽然那不真实的存在,但是它的制作人员们却让那个世界从银幕里延伸出来,仿佛那个”虫师”的世界就是真实的。“它不是阐述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不全是喜剧收场,也不只是描绘角色,也不一味地增加设定,它感觉似乎是真真切切的在与人对话。”导演长滨博史如是说。音乐总监增田俊郎说:每一集都是不同的故事,每一集都要营造一个不同的气氛,这样可以用音乐不经意间融入人物心情,让故事情节延展开来。美术总监脇威志也有统一的看法:他认为《虫师》的出发点是他整体的世界观,以此为基础,每一集虽然不同,但是大的基调是不变的,然后让画风去适应每个故事的情节,季节。其配音也是如此,配音演员一遍一遍的试音,以找到最适合人物角色的表演方式。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真正成功的动画并不存在艺术学科边界的藩篱,也并不强调其中某一个部分,更不是各个艺术门类的随便堆积。如果我们还执着于其中的某一基础的艺术元素的话,那么就说明对于动画王国,我们还是一个听不懂他们的语言的外国人。就像英语单词对于一个不懂英语的人来说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字母。我们需要摒弃传统艺术的界定,动画的综合其实是对于传统的超越,以寻求一个全新的起点。
三.动画是对小微信息的解构和重构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理解,把一个动画片拆分,按时间可以拆分为很多个一秒钟的定格画面,而对于同一秒的画面内,画面中的每个部分又可以拆分为一个个单独的一秒钟。为何这么拆分,因为被拆分出来的部分都包含不同的信息,一直到这个信息不能再被拆分为止。所以一个完整的动画作品可以是说是一个无数信息的集合,它们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却统一在一个大的文化主背景之下,换句话说,这个整个动画作品就是每个基础单元的文化信息构建的。因此,动画永远都带着制作者自身的文化特点,即使是制作异国文化题材的动画,也依然如此。就像日本人通常围绕他们的“物哀幽玄”的传统认识来制作动画,而美国人则围绕“自由平等”的民族梦想来制作动画。这种信息是细微的,它从开始制作到完成,渗入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单位信息,重构出新的个体化的动画艺术的风格。比如简单的走路原动画,日式的幅度很小,带着日本人本土的严谨内敛的精神风貌,而美式的幅度则很大,常常带有夸张和变型,美国自由开放的性格跃然纸上,这种文化特色从下笔的一瞬间就被确定下来。正如美国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在《实践的冲撞》中写的:“人类力量和物质力量都是难以束缚、未被驯化的。然而,跟随人类目标和意图之后的研究似乎并非如此难以驾驭。他们显得已经部分地被驯化,已处在就犯于他们所处文化的那种状态中。”日本动画和美国动画建构了两个有组织有规模的动画网络,在传到中国后,这个法则和规律似乎成了中国动画必须遵从约束性的东西,而中国按这个默认的规则去创作动画就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真实的文化信息被排除在外,这也产生了虚假文化信息与真实文化需求的阻抗和矛盾。因此,中国希望拥有中国风格的动画首先应该观察分析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细节特点,而非机械的模仿他人,不论是故事,画面,音乐等等形式的安排上,还是动画创作的实际方法上,中国不可以再拘泥与国外那些成功案例的经验。旅德华人艺术家王小慧讲过:艺术中,真实比美更重要。这种真实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艺术形式的真实,更大部分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创作方法的真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带入中国的文化信息,真正地解决目前中国大部分动画缺乏创新的问题,形成真正中国特色的动画。
动画作为当今时代的产物,它反映了社会发展多元化,开放性的趋势,而中国动画在发展中产生的阻抗和困境也引发人们再次解放思想。虽然文艺复兴以来,所崇尚的人类的力量可以无限制地把握、控制和统摄事物的人文主义不再适用动画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其人文主义思潮带来的科技文化进步的思想观念革新的重要性依然可以被证明,因此,在中国动画领域中去寻求一种思想模式的突破和转变显得极为必要和紧迫。而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带着后人文主义的多样性、异质性杂存,利于各领域间应平等互用,以及更能体现当代社会特征的思想方式已经悄然出现在艺术设计领域的最前沿。香港著名设计师叶锦添曾提出过一个未来发展的模型——神思陌路。神思是一种信息连接管道,陌路就是未知。日本设计师原研哉也有类似的理念:将信息未知化是一种新的信息形式。这种新的视角对于中国动画也可以是一种借鉴和启发,它可以引导我们重新理解动画创作方法,革新思想以超越过去的范式经验,从种种的传统艺术门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种种的国外动画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勇敢而明确地走出中国动画创作的道路。只有当我们已然克服了作为经验和理论的思想认识控制时,创意就会真正被交付于我们。
(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安德鲁·皮克林 《实践的冲撞》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6-1
威廉姆斯《原动画基础教程:动画人的生存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1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5-1
叶锦添《神思陌路》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2-1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