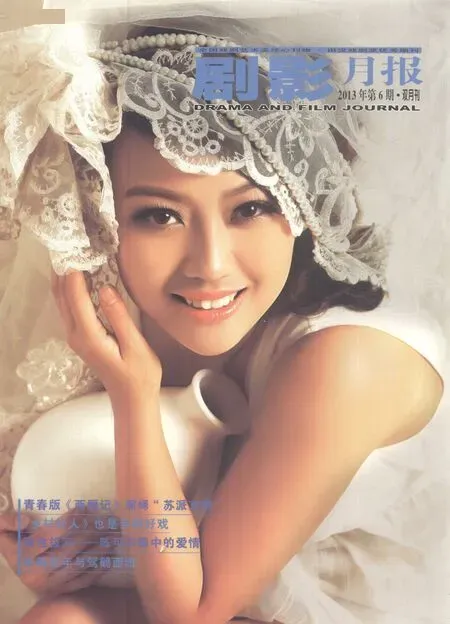风铃的回响
——话剧《天堂的风铃》随想
2013-11-21潘光宇
■潘光宇
风铃的回响
——话剧《天堂的风铃》随想
■潘光宇
南通艺术剧院话剧团排演的话剧《天堂的风铃》在江苏省各高校热演,受到莘莘学子的热捧。在当下“娱乐至上、票房第一”的演艺“怪圈”中,出现这样一部人生命题的话剧,值得我们击节称道。话剧是舶来品,她遵循的是世界文学艺术创作的美学规律,是“写人生”的艺术,欣赏话剧,需要足够的文学、哲学、社会学的思维能力和人生的感悟能力,绝非一般娱乐所能替代。大学学子与话剧的共鸣,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回响。
话剧《天堂的风铃》剧情并不复杂,甚至只用一句话便可以说清楚。但是,我们看话剧不能仅仅看故事,而是要看引起这个故事发生、发展的那个主人公带有社会典型意义的心理过程,从人性欲望与行为动作的无限冲突中感受艺术形象的魅力,并在我们的心里产生共鸣。这就是话剧的魅力。
谭小月,是话剧《天堂的风铃》中的女主人公。
谭小月,我们似曾相识,仿佛是自家儿女,又像是邻家女孩。
她任性、狭隘、不相信人间会有无私的大爱,甚至用阴暗的心理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她费尽心机只想出国留学,将同一导师的研究生男友看成了“敌人”;导师的关爱在她的心里变成了居心叵测;因出国不成而诬陷男友,想自杀却刺伤了自己的导师周明教授……
话剧《天堂的风铃》事件的“个别性”产生了陌生化效果,吸引我们要把戏看下去,而人物的“典型性”又让我们产生了心理上的共鸣,感到震惊。剧中的“这一个”谭小月,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产生谭小月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从而让我们觉醒,让我们关注,去关注更多的谭小月,去消除更多“谭小月们”的阴暗心理,让他们健康地成长起来。
戏剧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话剧《天堂的风铃》全部情节是谭小月的性格催生的,但是,更让我感到十分震惊的是那个贯穿全剧看似是一个技术性人物的“小杨记者”。一篇题目叫做《天堂的风铃》的文章,因为“女研究生刺伤了自己的导师”的内容很刺激,因为文中的周明教授的“宽容与大爱”被写得太完美,她不相信今天会有这样宽容而完美的人,从而展开了贯穿全剧的“新闻调查”。这是剧作家精心设计的一个人物,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谭小月们”的典型意义。这不是又一个谭小月吗?如果说,谭小月之所以如此任性、狭隘、不相信任何人,是因为父亲当年的过错和家庭贫寒而遭受屈辱,在她的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膨胀了她出国留学的人性欲望,那么,这个小杨记者“追求刺激,不顾别人的感受”和“不信任心理”又从何而来?这是不是一代青年的典型心理?令人深思。
话剧的人生命题,是话剧的本体特征,从英国的莎士比亚到挪威的易卜生,再到美国的戏剧大师奥尼尔以及中国老舍、曹禺的经典话剧,哪一部不是以深刻的人生命题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反观,话剧一旦进入娱乐状态,进入商业竞争,话剧将不复存在。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戏,因为过于商业化而消亡;美国话剧也在十九世纪初因为过于商业化而濒临绝境,是奥尼尔时代非营利的实验性的小剧场话剧从根本上拯救了美国话剧。即使是今日美国的百老汇戏剧,仍然是以非营利的戏剧培养出来的观众,作为消费群体的。因为,话剧一旦进入娱乐状态,进入商业竞争,便会陷入追求感官刺激的“恶俗表演”,从而失去话剧的“人生命题”,最终走向消亡。这是中外戏剧史已经作出明证的。
话剧《天堂的风铃》不是娱乐,当然也不是教科书。话剧是艺术,是审美,是高雅而严肃的诗体文学,是庄严而崇高的舞台艺术;话剧是人的精神仪式,是人的灵魂表述。我还特别欣赏话剧《天堂的风铃》所具有的现代形式美感:叙述与再现的美妙结合,流动着一个庄严而崇高的“诗魂”。
全剧从小杨记者对《天堂的风铃》一文进行“新闻调查”,到谭小月登上飞机出国留学,只有两天时间。随着小杨记者一个又一个的疑问,谭小月的思想和言行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地再现在观众面前,两天的时间里再现了两年的时空,叙述的作用和张力架设了一个个悬念,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而再现的过程和细节又是那样的震撼人心,让观众逐渐进入谭小月的内心世界。这种层层设疑、层层剥笋的戏剧结构加入了叙述体成分,舍弃了芜杂的戏剧性交代与铺陈,大大扩张了人物的心理空间,让我们非常深入地捕捉到了人物的灵魂。也许,我们还不太习惯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恰恰是现代话剧结构的独特魅力,企图让人物的灵魂与观众直接对话,并且产生心灵的共鸣。
话剧《天堂的风铃》博得学子的阵阵掌声,那掌声便是共鸣,是回响,是台上的谭小月与台下的“谭小月们”的共鸣,是一代青年关于人生命题的共鸣,更是一种生命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