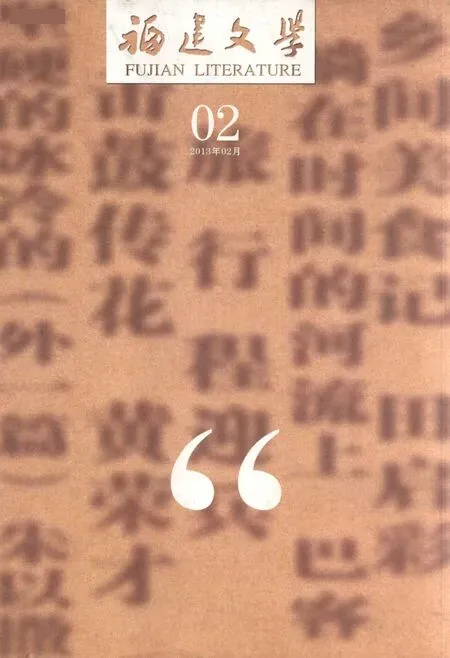乡间美食记
2013-11-16田启彩
□田启彩
凉 粉
深秋的地里,花生,玉米,芝麻,大豆,它们都不在了。只有红薯孤零零地呆在那儿。它在等待着。我们也在等待着。
霜降之后,踏着深秋的晨露,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拉着平车,全家人去地里刨红薯。这是最后一次的秋收工作,虽然工作量不大,但要显得隆重。
红薯,在农人心目中占着重要位置,它不但可以在粮食缺少的年代充饥,还可以在粮食宽裕的时候做成各种吃食。凉粉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我的最爱。
红薯拉回家后,把长得好的,大的,齐整的,没有伤疤的,都归拢到一块儿去。这些是要下窖贮存的。在漫长的日子里,慢慢地吃。把长得孬的,小的,少皮没毛,疤疤拉拉的,也归拢到一块儿去。这些残次品,一部分用擦床擦成片,晒干了,贮存起来。等来年春天,窖里的红薯吃完了,或者烂完了,这些晒干的红薯片,可以煮到玉米粥里去,是干粮的替代品。
剩下的一部分就要用清水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它们用平车拉去“弹”了。弹是方言的说法,是粉碎的意思。弹完的红薯,变成了一车泥状物,被母亲拉了回来。
红薯弹好之后,就是淋芡了。淋也是方言的叫法,是滤的意思。淋芡的工作是需要全家齐上阵的。两口大水缸是早就准备好了的,缸里的水是我们一大清早从压井里压出来的。淋芡的布兜是昨天下午就向邻居借好了的。父亲找了一根大粗棍,架在两把大椅子上,这是挂芡兜用的。大大的红琉璃盆也放好在了椅子中间。
母亲和父亲,或者是和哥哥,分别站在芡兜的两边,负责淋芡。我负责往里面舀弹好的红薯渣。两个弟弟负责往里面续水。
淋芡不但是力气活,还需要技巧。两个人要不停地用手抓住芡兜上下左右来回抖擞,而且动作要保持协调,力度要一致。这样红薯渣里的芡可以过滤得迅速而干净。这个工种等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也可以胜任了。
淋芡不是一次就能淋好的。要反复地淋,这样淋出来的芡才好。整个淋芡工作大约需要三四个小时。收拾好之后就到了做晚饭时间。
暮气笼罩下,淋好的芡都安安静静地呆在芡兜里,它们要在深秋的院子里放置一夜。一夜的时间,水就可以控完了,芡也可以成形了,上大下小的一大坨。它的边缘还会印上布兜的褶皱。颜色是灰灰的,摸上去滑溜溜的。
淋好了的芡有三种用途。一大部分仍要拉去做成粉条,在漫长的日子里当副菜吃。一小部分晒干了,保存起来,做咸汤或者做菜时用。另外的一小部分就可以打凉粉了。这是我们最期待的。
打凉粉是在淋好芡的当天晚上进行的,操作过程很简单,烧上一大地锅开水,把湿的芡倒进去,不停地搅,不停地搅,等它们变成了暗青色,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着热泡。熟透了,就成了。打好的凉粉还要晾一夜,冷却一下。不能放在地锅里晾,要把它们盛出来。碗里,盆里,都盛满了等待冷却的凉粉。
到明天早上,它们就会变成真正的凉粉了。从碗里倒出它们来,它们就成了碗的形状;从盆里倒出它们来,它们就成了盆的形状。看上去,是透明的暗青色。摸上去,凉凉的,很有弹性。你用指头弹它一下,它的身子就立刻颤悠起来,在那里来回晃荡。
凉粉,一般有两种做法:热炒和凉调。这两种做法都很简单。凉调就是凉拌,把凉粉切成方块或者长条,然后捣蒜。蒜捣好之后,加入盐,醋,酱油,香油。后来有了味精,就又加上味精。醋一定要多放,而酱油一定要少放。把这些调料直接倒入切好的凉粉里,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凉调的凉粉最大的特点就是爽口,在夏天的时候吃是非常惬意的。
炒凉粉就是把切成方块的凉粉,用热油翻炒。最好的调味料就是蒜苗和瓜豆,炒出来的凉粉,那香味馋得人直流口水。而我最爱吃的是炒凉粉里面的那些碎末和焦黄的锅巴。那是炒凉粉里的精华。
饸烙条
饸饹条在古代被称之为“河漏”。据说是河南某些地区的特色面食,主产地在郏县,获嘉也有。或者现在还有。我却是长大之后再也没见过。
饸饹条原来是用荞麦面或高粱面,后来改用面粉做,这几种我都没吃过。我小时候倒是吃过一种用红薯面做的饸饹条,至今念念不忘。
之所以用红薯面,大约是那时候面粉缺乏的缘故。先是把红薯面蒸成馍,趁热,就可以直接压饸饹条了。压饸饹条要用专门的工具,叫饸饹床。我小时候见过的饸饹床是木制的,一个直径十五公分左右的圆桶,底端是铁片,像筛子一样,分布着筷子粗细的圆孔。圆桶上面支着一个和它大小相对应的木槌,连着一个长的手柄。用的时候像压井,放入蒸熟的红薯面馍,一压一压就出来细长的面条,就是饸饹条了。因为面是熟的,压出来的饸饹条可以直接吃。我们就端着碗在下面等,等饸饹条下到碗里,热气腾腾的,拌上调制好的蒜汁,呼噜呼噜,一会儿就吃光了。于是又端着碗到饸饹床下面等……
红薯面饸饹条真是好吃。可是记忆里也并没有吃过几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天中午,母亲去别人家借了饸饹床,放在堂屋中间,为我们做饸饹条吃。记得自己端着碗在接压下来的饸饹条。褐色的面条冒着热气,红薯的香甜,配以酸辣的蒜汁,想着想着就要流口水了。
臭豆,瓜豆
在种黄豆的年代,每年家里都要腌臭豆。秋天里新收的黄豆,放到来年六月里,晴日悠长的时候,煮熟了,盛放到一个大簸箩里,给它们做一个厚厚的麦秸窝,捂着,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臭味就出来了。掀开麦秸看,当初黄灿灿水灵灵的豆子,都长了一身绿的黑的毛。拿到太阳底下晒,晒到崩崩硬的程度,用手一拨弄,一层黑绿的烟荡上来,臭豆的整道工序就完成了。
臭豆有两种吃法。一种是泡臭豆。平时没有新鲜蔬菜可吃的时候,从瓦盆里抓出一些臭豆来,放进碗里,开水冲烫,一会儿的工夫就泡软了,然后放些盐,香油,春天的时候菜地里有蒜苗郁郁葱葱,掐一些下来,切碎了放进泡好的臭豆里,那真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香。
另外一种是要进行再加工的。等到七月里,地里西瓜吃得差不多了,留一些出来,打碎了瓜皮,把西瓜瓤掏出来放进一只腌菜的小缸里,然后放进晒干的臭豆,放进一些花椒叶,放盐,用一块干净的塑料布扎紧缸口,大约十天左右就可以吃了。这种西瓜和臭豆腌制的酱,我们称之为瓜豆。瓜豆可以直接当酱吃,也可以炒着吃,蘸馍,香。最喜欢的一种吃法是,用油烹了洋葱,放上鸡蛋,再加上瓜豆酱,当卤,吃捞面。是我百吃不厌的。
在蔬菜缺乏的年代,瓜豆是可以当菜吃的。尤其是青黄不接的春天,一碗瓜豆,就可以支撑到夏天。
蒸 菜
蒸菜是最受乡间主妇们青睐的一道菜肴。因为它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做法简单,经济实惠。而且,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拿来蒸的。
初春二月,柳絮生成,正娇嫩着。挎了篮子去村外找棵柳树捋一些回家,清水淘洗,拌上黄白相掺的面,盐,花椒面,葱花姜末,上笼蒸,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蒸菜的香味就从锅里溢出来了,略带点苦味的柳絮的清香。
清明节前后榆树上会长出一串串淡绿色的榆钱。它也是可以捋来蒸的。榆钱蒸菜是一种淡淡的甜香。我们家中间堂屋靠着西山墙长着一棵硕大的榆树,每年春天都累累的榆钱,蒸着当菜吃的只是够得着的很少部分,满树的青绿色的榆钱,年年都是漫天作雪飞了。
四月份槐花开遍乡间,吃起蒸菜来就更方便,往往从一棵树下过,偶一抬头,便看见树上已是一片狼藉,那是刚刚被捋槐花的洗劫了。不知哪家中午的灶上会飘出槐花蒸菜的浓香。
槐花除了做蒸菜,还可以晒干,做馅包包子。干槐花既保留了槐花的余香,又比鲜槐花劲道,有嚼头。包子可以做成纯槐花馅的,或者辅以韭菜肉馅,都非常好吃。晒干的槐花容易保存,冬天的时候泡发了用来蒸包子,一口咬下去,就会有一股久违的春天气息自唇齿间弥漫开来。
不单单是这些树上天生的野味,就是平时自己种的菜也是可以拿来蒸的。夏天六七月份,菜地里的豆角多得吃不完,长老了,颜色苍黄,皮质松软,不宜炒和凉拌,就只有做蒸菜了。豆角做的蒸菜外皮劲道,豆子绵软,拌上蒜汁,很是美味。
后来还吃过马齿苋,芹菜叶,茼蒿等做的蒸菜,味道都好。吃上一盆热乎乎的蒸菜,再喝上一碗小米稀饭或者玉米粥,这种生活简朴而又滋味十足。是一辈子也过不腻的。
野菜香
当我们在初春的麦地里四处撒欢挖野菜的时候,并不认识后来声名遐迩的荠菜。我们只认识面条稞,把它挖回家可以放进清汤面条里调色,以增食欲。
春天闹菜荒的时节,有人甚至捋了初生的杨树叶子来吃,用水焯了,依然难掩苦涩之味。小孩子好奇心重,明知道不好吃,却羡慕别人家吃杨叶,央求母亲也弄来吃。未果。母亲对这种不入流的野菜是怀着深恶痛绝之心的,大概跟以前啃树皮吃树叶的苦难经历有关。
油菜的嫩芽也可以吃的,至于怎么吃,因为我家没有吃过,并不清楚。秋天的嫩红薯梗掐了来,切短了,焯水,放醋,蒜汁,凉拌,倒是非常爽口。
夏天生的马齿苋在乡下还有一种称呼:马西菜。它除了做蒸菜,还有一种更好吃的做法。用白面蒸成菜窝窝,切成片,拌上调制好的蒜汁。劲道中带着脆滑,在我们家中是一道很受青睐的主食兼主菜。
还有一种叫猪毛菜的野菜,也是夏日里极爽口的一款凉菜。它们喜欢生长在松软的黄沙冈上,尤喜树林里的阴凉之处。刚长出来的猪毛菜,密密麻麻地直立着,像一根根翠绿色的猪毛,它的名字也由此得来。此时的猪毛菜是最鲜嫩的,薅回家去,把白细的长根切掉,淘洗干净,焯了水,用调制好的蒜汁拌了,摆上饭桌,一霎时便风卷残云,不见了踪影。
所有的野菜都适合甚至必须用蒜汁调制,蒜汁的香辣,还有醋的酸味,可以有效遮蔽野菜本身的苦涩之气,提升野菜本身的清鲜之味。它们二者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绝配。
小时候沙冈上长着大片的树林。对于我们来说,它既是游乐园,也是采摘园。初秋时节,一场清雨过后,许多树木下面会拱出一簇簇鲜嫩的小蘑菇,憨态可掬。运气好的话,会挖小半篮子。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交给母亲处置。
清炒的野蘑菇,鲜香爽口,是一道平时难得一吃的美味。而母亲做的蘑菇炖鸡,则是天下一绝。尤其是鸡汤,黄灿灿的,那才是真正的鸡汤。鸡是家养的老母鸡,过了下蛋的年龄,才舍得杀来吃。母亲做蘑菇炖鸡,一定是要放花生米的,那花生米吃起来也有一股香浓的鸡肉味。人多,肚子空,一只鸡的肉根本不够吃。鸡肉吃完了之后,我们就拿花生米当鸡肉来解馋。
那时候还住老院子,黄泥砌就的院墙。院墙外一棵没有主干的石榴树,七枝八杈的,年年开花,结果,还负责训练我们的爬树技能。我们一家人坐在石榴树身边吃母亲做的野蘑菇炖鸡。那时候母亲还年轻,我们都只是十来岁的少年。而鸡汤的香气一直缭绕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