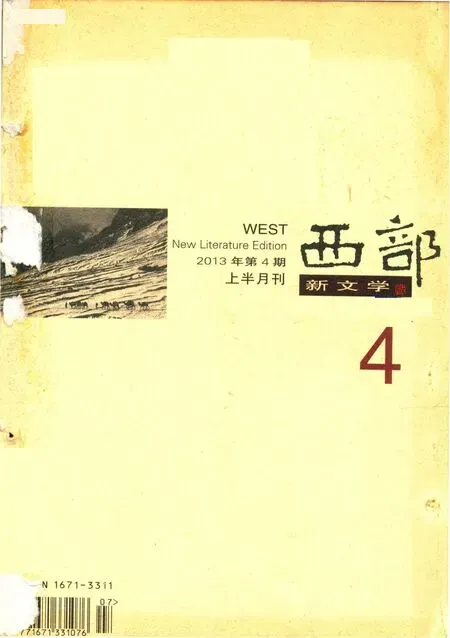雪一样的普米人
2013-11-15鲁若迪基普米族
鲁若迪基(普米族)
小凉山很小
小凉山很小
只有我的眼睛那么大
我闭上眼
它就天黑了
小凉山很小
只有我的声音那么大
刚好可以翻过山
应答母亲的呼唤
小凉山很小
只有针眼那么大
我的诗常常穿过它
缝补一件件母亲的衣裳
小凉山很小
只有我的拇指那么大
在外的时候
我总是把它竖在别人的眼前
女山
雪后
那些山脉
宛如刚出浴的女人
温柔地躺在
泸沽湖畔
月光下
她们妩媚而多情
高耸着乳房
仿佛天空
就是她们喂大的孩子
无法吹散的伤悲
日子的尾巴
拂不净所有的尘埃
总有一些
落在记忆的沟壑
屋檐下的父母
越来越矮了
想到他们最终
将矮于泥土
大风也无法吹散
我内心的伤悲
1958年
1958年
一个美丽的少女
躺在我父亲身边
然而,这个健壮如牛的男人
却因饥饿
无力看她一眼……
多年后
他对伙伴讲起这件事
还耿耿于怀
说那真是个狗日的年代
不用计划生育
木耳
是木头
是木头长出的耳朵
木头的耳朵
它听到了什么
当它被人活活扯下
木头是不是暗叫了一声
我们把它煮熟
放进嘴里的一刹那
只一声脆响
我们仿佛咬了自己的耳朵
那一刻
我们木了
光棍村
乡长说这个村缺水
饭也吃不饱
妇女都外出打工了
是个光棍村
有七八五十六个光棍
县长戏说请他与寡妇村联系一下
然后拍板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
水引来了
温饱问题自然解决了
可是,那些外出打工的妇女
还是没有回来
听说有几个在春节回了趟家
又把在家的小妹带走了
雪邦山上的雪
我看到了雪
看到了雪邦山上的雪
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映照着我内心的洁白
想到雪一样的普米人
我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多少年
多少雪落雪邦山
无人知晓的白呵
我的亲人们
在山下劳作
偶尔看到山上的雪
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
这时,木里的雪在唱
九龙的雪在飘
小凉山的雪在舞
还有很多的雪
无声地落在大地的角落
静静地白着
泸沽湖畔的庄稼
这些庄稼
越来越远离粮食
它们在湖边越长越高
高于灶塘
高于我们的嘴
日子的牙齿
很难咬动它们
作为风景的一部分
它们在风中的哆嗦
只有年迈的老人能感受
只有他们知道
在没有旅游之前
那些庄稼
在他们眼里
有时比泸沽湖还美
干净的树
一片叶
缓缓飘落
一只鸟要把它衔回树上
叶子落尽
鸟飞绝
最后剩下树
干净地站着
我从树旁走过
一阵风
那些落叶
开始在四周飞舞
要长回我的身上
沙漠
泥土被榨干后
成了这个模样
烈日下暴晒
被风驱赶着走
没有呻吟哭泣
它们的火
藏在地心里
有一天
会烧尽这个世界
夜读
这个夜晚多么宁静
月光洒满庭院
有人翻山越岭
要去寻找
一个在梦里出现过的美人
他已翻过九十九座山了
还有更多的山簇拥着
横亘在面前
他已趟过七十七条河了
还有更多的河聚集着
咆哮而来
我久久没有合上书
怕一旦合上
就像巫师
给他们关上了
最后一道门
月亮
父亲在茶马古道
曾丢失过一匹马
他从日出找到日落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匹马
天色已晚
他独自走在山路上
大山深处不时传来
树枝断裂的声音
狼的哀嚎
震颤着夜鸟的翅膀
想到自己的马
说不定有什么不测
他心里充满了悲伤
这时,他禁不住抬起头来——
一个巨大的灯泡挂在天上
给他照明
心里突然有了感恩
——每次父亲讲到这里
就陷入了沉默
我看到他眼里泛起微澜
那匹丢失的马
在微澜里与狼搏斗着
不停地昂起
血淋淋的头
神的模样
小时候听说过
无数山神的名字
可怎么也想象不出
他们什么模样
每天清晨,父亲洗完脸
就开始烧香敬神——
果流斯布炯
阿达贡森格嘎
日果落帕石窝
宜底嘎琼嘎
木多瓦擦
噶佐噶呆……
无数个山神的名字
河流一样
从父亲口里流出来
浇灌着我梦幻的世界
袅袅香火里
我睁大眼睛
希望能看到山神显灵
可是,总是落空
问父亲“果流斯布炯”是什么
他说“果流”是我们村庄
“斯布炯”是护佑我们的山神
我们第一个要从他开始敬奉……
如今,在遥远的地方
每次默念到“果流斯布炯”
眼前就会浮现出
父母慈祥的面容
无声的倾诉
我见过沙
见过被金沙江水
淘洗过无数次的沙
最终变成了一粒粒黄金
我还见过风沙
见过有人披着它
在迎亲队伍到来之前
裹走了新娘
可是,我没有见过沙漠
没有见过那么多沙
相聚在一起是如此的静
它们交流的方式
如此独特
让我想到星与星的对话
水与水的交融
坐在沙包上
看塔里木河蜿蜒
一群水鸟紧贴河面飞翔
罗布人恬静的村庄
被游人吵醒
胡杨林金黄的叶子后面
谁的红纱巾一闪
勾起了我的思念
就让我变成一粒沙吧
好对你无声地倾诉
好似一阵吹过故乡的风
那一年登泰山
就要登顶的一刻
一阵风呼叫着吹来
它像从很远的地方赶来
还叫着我的名字
顺手摸了下我的头
帽子就被摘去了
顺手摸了下我的耳朵
有些话就被掏走了
顺手摸了下我的脸
一层皮被撕下了
顺手牵了下我的衣角
就长出了翅膀
它吹过身旁的松树
松树弯下了腰
吹过前面那座庙
我听到了呼啸声
那声音如此亲切熟悉
多像一阵吹过故乡的风啊
我像一座老屋
在那一刹
被吹得七零八落
泪水纷纷扬扬
心里的一扇窗
瞬间被吹开了
久久不停地晃荡
种苦荞的人
小凉山上
苦荞是最普遍的作物
那些种苦荞的人
最初的时候
把一片片林子伐倒
用一把火烧了
随便挖几锄后
就撒上了苦荞
第一粒苦荞成熟的时候
布谷鸟品尝后飞走了
种苦荞的人燃起火把
用一只鸡在荞地边转转
默默祈祷上苍的恩典
他们用独特的方式
庆贺一个节日的到来
让一粒粒饱满的荞粒
在铺开的披毡上欢快滚动
虽然满坡的苦荞
最终只有几小箩筐荞粒
然而,他们不说一句话
把荞粒酿成美酒
磨成白金一样的面
收藏在柜子里
平日紧咬牙巴
煮一罐盐茶
啃几个洋芋
亲朋好友来的时候
才拿出珍藏的美酒
宰了羯羊,烙上荞饼
整个村狂欢
仿佛日子就只有那么一天
看着种苦荞的人
醉倒在荞秸秆上
我忧伤的诗
在铅灰的云层里飘荡
一茬茬的苦荞啊
一茬茬的人
多少茬的苦荞
才能养活多少茬的人啊
叹息声里
种苦荞的人
默默地咬了一口荞饼
不急于吃下去
而是默默地嚼着
好像他嚼着的不是荞饼
而是从太阳上掰下的
一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