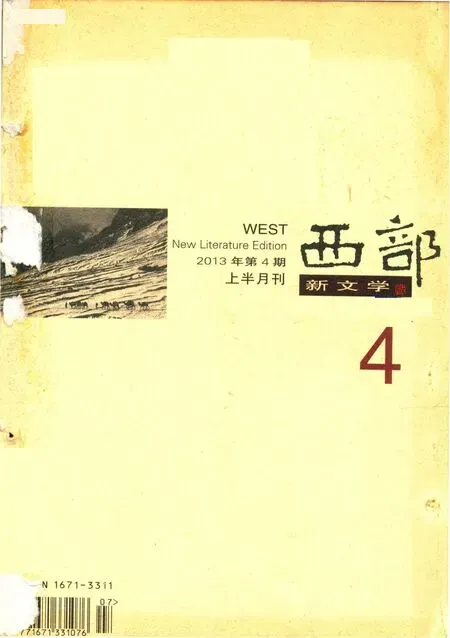最温柔的挚友
2013-11-15董夏青青
董夏青青
阿山在世的时候,我当他是家门口的一棵老树,哪会有出了门再见不到的一天?还曾想,我要是死了,阿山一定是帮着抬棺材的一个。没想到他走在我前头,由我来写下这篇悼文。
他是我一生中可能遇见的,最温柔的挚友。
第一次见他,听他说自己叫“阿三”,于是我“阿三、阿三”地叫了很久,每回他都笑呵呵地答应,直到有一天在他工作的地方玩,听见他朋友叫他“阿山”,这才知道一直喊错了他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不提醒我改过来,他很不好意思,笑眯眯地说,名字就是个代号,何况自己也不重要,叫错了有什么要紧。
聊天时,他很少大声发表见解,或者用侃侃而谈的语气给人提意见。多数时候,他总是微笑,有礼貌地注视着说话的人。在他这笑容里,能看到与年龄不符的羞怯和单纯,一种生来便与人交好的善意。而同时,这笑容里还有某种不可名状的警惕与忧虑,使他的脸无论何时看来,既亲近又疏远。
三年时间里,我和阿山每回见面、写信,聊的都是有关写作和信仰的事。听上去矫情,然而事实如此。我不知道他具体的家庭情况,不了解他某时是否有喜欢的女孩,也不清楚他喜欢吃什么。我们自从认识,就像是亲人,跨过了相互交换个人基本信息的阶段,直接进入了彼此最迫切渴望有人作伴的小世界——言说的世界。
我们每隔一段日子,便长聊一番,先说说各自最近练笔的大致内容,之后聊自己想写的人、想讲的好故事。他曾和我说,他想写他在酒店工作时的一位师傅,这位师傅的老婆几年前离家打工,至今音讯全无。他带着三岁的女儿,除了工作、喝酒,空闲时喜欢翻翻萧红的书。讲到师傅和一些日子不大如意的朋友的时候,阿山总会表现出难得的激动,他说虽然这些人在痛苦中艰难度日,但不似外人想的,人在贫穷中就只会麻木、堕落、无知,他们的心是有感知力的,受苦受难的人们能通过文字获得解脱和安慰。
何止萧红,卡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别尔……一切承受了生命之痛的作者,都成了阿山视之为生之奥秘的启示者。通过这些历经苦难的困窘的人,阿山不断思索——文字的美在何处生发、文字为人世何种样貌的生命提供庇佑、信仰能否解脱狭隘利己的文字私欲、无名者的尊严如何被文字准确表述、命运无名高地之上的痛苦和忧愁是否能经由文字排遣和展现……
现在想来,通信抑或交谈,都像在履行一个仪式,力图严谨地使用词语,坦诚说出内心对所见、所闻的忧虑不安和痛苦,不必担心他人误解、嘲笑。
阿山常说,感觉自己是寄居于现世的不明星球来客。他有这样的感觉,不只因为经济条件对人交往领域的自然划分,还因为他的心充满一般人所不能感知和理解的圣徒般的博爱和坚忍。这种无法探究其来源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使他和他的文字具有了强大的感召力,也使他承受着常人毋须担负的重压。
两天前看到一段话,作者在写到 “文革”之后一代人的精神状况时说:“人与人之间的幻想破灭的后果也不相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中国所谓 ‘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愤世嫉俗、工作中的消极被动和缺乏创造性以及不断增加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渴望。”“文革”已过去三十余年,而在我们生活的此时,许多人无论其出身、现况如何,都情愿将自己归入这“失落的一代”。
失落的人们面对现实,眼见爱与善的体质这般贫弱——思想不敌公文,灵魂拗不过权力,理性败给横欲,审慎的智慧斗不过无畏的无知,时常败下阵来,自甘闭着眼横活。细想阿山,他日夜在酒店的电工班工作,按月拿着一千多元的工资,背在身上的蓝色卡其布挎包,还是从酒店某间客房门口的垃圾袋里翻出来的,他却从未急于表达出于一己之私的愤懑、不安——让情绪暴力干扰理性、以激愤的宣泄取代悲悯,代替最严厉的自我审视。当然,阿山也恼怒、也怨恨,他只恨自己避重就轻的狭隘和懒惰,恨自己时常无力书写那横梗在心头的他人的痛苦。他一生安于表达和思考,从不失落。
写,是为了讲述,替自己,也替熟悉或者不知名的他们,公开地讲述。为了不让承受痛苦的人心在不明不白中销声匿迹,为了不让充满诓骗、大话、毁谤、荒唐和蛮横语气的话语围捕无辜的替罪者,为了不让谎言公然成为浇筑在现实之上的真理。
还记得读完福柯,与阿山讨论何为“底层”,最终俩人讲到,也许底层不单指缺少经济支撑的物质意义上的穷人,它还有一层含义,即是话语不及之处——那里的人放弃表述或者被迫缄默,因为其不会使用表述的工具,只能任由机构和部门制成表格、数据,任自大的学者在常规想象中横加定义与概述。而作者,其责任便是用一种与之对抗的语言说话——
前人将可以继承使用的言辞、语句和讲述故事的传统以及话语记录的仪式感 “借贷”给后世的作者,让其在这些言说方式面前,仔细寻找最洁净的,尚未被陈词滥调所戕害的,尚未被惯性思维所拖累的语词。之后,他们便步入无人知晓的道路,相信自己在从事最伟大的事业——言说,为自己,为他人,力图呈示这个在历史上确凿存在过的时代真实的精神状况,在与那冰冷陈述和虚伪言词做抗争之时,力求以美的文字恢复人的尊严、思考和情感的火光,使活着的人们找到与死者的亲缘关系。
“好累,太累了。”阿山不止一次地对我说。
能不累么?
若一位作者抱定这样的心念,如是对待文字,他必定是自卑、胆怯、不好活的。因为生活本身太沉重,因为爱惜和珍视语言的力量而不敢贸然与唐突,甚至因为无力贴切地讲述他人的痛苦而自责。阿山不懈怠地观看,不敢丝毫放松地写,希望借由文字刷洗,洗净自己和他人残缺的个性、困窘的生计、粗劣的灵魂、卑微的智慧、尖敏的痛感,直至最后在九华山出家,决心以洁净的生命投入到对宇宙生灵的爱中。
经过了这样的挣扎和磨砺,他的心已遍是刻痕。
刻痕岂是人人都有的神明的奖励?
一位基督信徒说:如果没有伤痛,你哪里会有能力呢?正是你的伤痛,你微弱的声音才能被人倾听。即便是天使们也无法劝动尘世中人们那苦恼而又愚钝的心,但一个在生命路上曾如此破碎过的人却可以,想要成就爱的人必要承受伤痛。
说得多好啊。阿山,经由宗教,在经文的诵读声中,你懂得了神明不是靠神迹,而是经由自己身体的伤痕治愈了人心。
对阿山的离世,我只能写出如上不是悼念的悼念,算作对自己和有的人不愿正视、不敢承担的信念的再确定。
还能如何?我至今仍不相信今生再不能与他见面,不能再和他说上一会儿话。我相信他此时还在山上劳作、读书和诵经,如此一来,怎能写出一篇像模像样的悼文!
阿山,别走太远。愿你安宁、自在,盼你偶尔来我身边,小坐片刻,如往日一般,将那个世界里我未曾谋面的无名者的生活,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