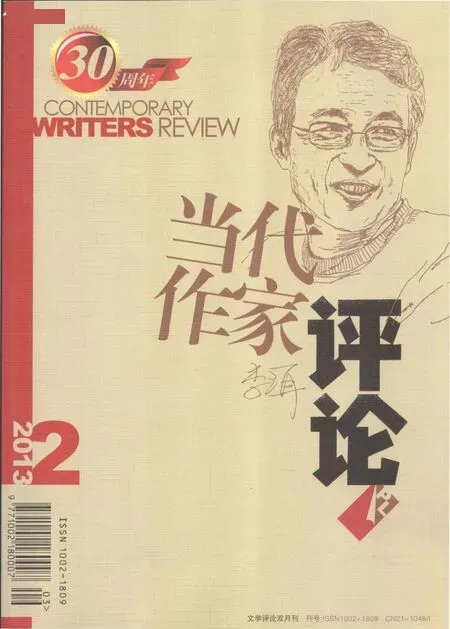文论下载
2013-11-14徐怀中,贾平凹
“尽管他作品描写的只是自己故乡那个小村庄”(《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徐怀中
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讲演提到:“一九八四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莫言为人很谦逊很低调,但他称我为“恩师”,这个话显然过于夸张,与事实不符。我虽主持文学系工作,但我个人也并未受过高等教育,更无任何教学经验。莫言提到的几个中短篇,只能说是他在文学系读书期间写出的,谈不上我的什么启发与指导。要讲受到过谁的恩惠,那只能说莫言有幸,适逢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中国文学冲破重重禁锢,迎接八面来风,包括莫言在内的文学系一批部队青年作者开阔了视野,激发了创作潜力。如同软件来了一个更新换代,于是便开始在升级版性能上再度开发自己。每每读到莫言的新作,我总感到十分奇异,总有些不可思议,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朴实厚道的山东农家子弟,具有天马行空一般超常的想象力,具有电光石火一般敏锐的艺术感觉,是哪来的?你不能不承认,这完全是先天设定的,无须谁来给予启蒙,给予指教。以他的天分之高,注定会受到世人瞩目,谁也阻止不了的。
他的家乡历史上属齐鲁大地,回望春秋战国以降,这一方水土化育了多少传世经典名著,至清代更有蒲松龄的不朽之作《聊斋志异》。我们不难察知莫言小说世界的源流,家乡风土人情、工匠农艺、神话传说、地方戏曲,等等,凡此古来农耕文明之遗风,便是他取之不尽的能源库存。多年劳动生活积累,以及蕴藏丰富的儿时记忆,任他信手拈来。以高密东北乡那片红高粱地为坐标,莫言测定了他未来的文学走向,也就此明确了他的“草根”写作立场,矢志不渝,坚守至今。
《带灯》后记(《东吴学术》2013年第1期)
贾平凹
进入六十岁的时候,我就不顾意别人说今年得给你过个大寿了;很丢人的,怎么就到六十了呢?生日那天,家人和朋友们已经在饭店订了宴席,就是不去,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喘息。其实逃避时间正是衰老的表现,我都觉得可笑了。于是,在母亲的遗像前叩头,感念着母亲给我的生命,说我并不是害怕衰老,只是不耐烦宴席上长久吃喝和顺嘴而出的祝词,况且我现在还茁壮,六十年里并没有做成一两件事情,还是留着八十九十时再庆贺吧。我又在佛前焚香,佛总是在转化我,把一只蛹变成了彩蝶,把一颗籽变出了大树,今年头发又掉了许多,露骨的牙也坏了两颗,那就快赐给我力量吧,我母亲在晚年时常梦见捡了一篮子鸡蛋,我企望着让带灯活灵活现于纸上吧,补偿性地使我完成又一部作品。
整个夏天,我都在为带灯忙活。我是多么喜欢夏天啊,几十年来,我的每一部长篇作品几乎都是在冬天里酝酿,在夏天里完满。别人在脑子昏昏,脾气变坏,热得恨不得把皮剥下来凉快时,我乐见草木旺盛,蚊虫飞舞,意气纵横地在写作中欢悦。这一点,我很骄傲,自诩这不是冬虫夏草吗?冬天里眠得像一条虫,夏天里却是绿草,并开出一朵花了。
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人事。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时我披了牛皮。记得当年父亲告诉我,他十多岁在西安考学,考过还没张榜时流浪街头,一老人介绍他去一个地方可以有饭吃,到了那个地方,却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送他去延安当兵。我父亲的观念里当兵不好,而且国民党整天宣传延安是共产党的集聚地,共产党是土匪,他就没有去。我埋怨父亲,你要去了,你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我也成高干子弟了。父亲还讲,他考上了学又毕业后,在西安教书,那时五袋洋面可以买一小院房的,他差不多要买了,西安开始解放,城里响了枪声,他就跑回了老家丹凤。我当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里人了吗,又何苦让我挣扎了十九年后才做了城里人!当我在农村时,我的境遇糟透了,父亲有了历史问题,母亲害病,我又没力气,报名参军当兵呀,体检的人拿着玻璃棍儿把我身子所有部位都戳着看了,结果没有当成。第二年又招地质工人,去报了名,当天晚上村支书就在报名册上把我的名子划掉了。隔了一年又招养路工,就是拿着锨到公路边的水渠里铲沙土垫路面的坑坑洼洼,人家还是不要我。后来想当民办教师也没选上。再后一个民办女教师要生孩子呀,需要个代理的,那次希望最大,我已经去修理了一支钢笔,却仍是让邻村的另一人调了包。那段日子,几次大正午的在犁过的稻田里犯蒙,不辨了方向,转来转去寻不到田埂,村里人都说那是鬼迷糊了,让我顶着簸箕,拿柳木条子打着驱鬼。十几年后提起这些往事,有长者说:这一切都在为你当作家写农村创造条件呀,如赶羊,所有的岔道都堵了,就让羊顺着一条道儿往沟脑去么!我想也是。
在陕西作家协会的一次会上,我作过这样的发言:如果陕西还算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吧,主要是出了一批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这些作家又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后经提拔,户口转到了城里,由业余写作变为专业作家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已没条件了,应该多鼓励年轻的作家拓宽思路,写更广泛的题材。我这么说着,但我还得写农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几十年的习惯了,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走得开,我就会邀二三朋友去农村跑动,说不清的一种牵挂,是那里的人,还是那里的山水?在那里不需要穿正装,用不着应酬,路瘦得在一根绳索上,我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饭时了随便去个农户恳求给做一顿饭,天黑了见着旅馆就敲门。一年一年地去,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我们是要往农村里跑,真的如蝴蝶是花的鬼魂总去土丘的草丛。就在前年,我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城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再是去了一趟甘肃的定西。收获总是大的,当然这并不是指创作而言,如果纯粹为了创作而跑动那就显得小气而不自在,春天的到来哪里仅仅见麦苗拔节,地气涌动,万物复苏,土里有各种各样颜色呈现了草木花卉和庄稼。就在不久,我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她是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我的手机号,先是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信。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了,但她写的短信极好,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谈更多的书,没有人能与她交流形成的文学环境,综治办的工作又繁忙泼烦,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那深山的日子里,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我是个忠实的倾听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她又领着我走村串寨,去给那特困户办低保,也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她能拽着牛尾巴上山,还要采到山花了,把一朵别在头上,买土蜂蜜,摘山果子,她跑累了,说你坐在这儿采风景吧,我去打个盹儿,她跑到一草窝里蜷身而卧就睡着了,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长上来在风中摇曳鲜艳。从她那儿的深山里回来不久,我又回了一趟我的老家。老家正在修了一条铁路又修高速公路,还有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而也发生了一场为在河里淘沙惹起的特大恶性群殴事件,死亡和伤残了好多人,这些人我都认识,自然我会走动双方家族协助处理着遗留问题,在村口路旁与众人议论起来就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事情远还没有结束,那个在大深山里的乡政府女干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她每天都给我发信,每次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说她的工作和生活,说她的追求和向往,她似乎什么都不避讳,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如我在老家的那个侄女,给你嘎嘎地抖着身子笑得没死没活了,又破口大骂那走路偷吃路边禾苗的牛和那长着黄瓜嘴就是不肯吃食的猪。她竟然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手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所写的检查草稿。
当我在看电视里的西安天气预报时,不知不觉地也关心了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就是从那时,我冲动了写《带灯》。
在写《带灯》过程中,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过程。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既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的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的沟峪。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使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这种想法令一些朋友嘲笑,说你干啥的就是干啥的,自己卖着蒸馍却管别人盖楼。我说: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或许我是共产党员吧。那年四川大地震后十多天里,我睡在床上总觉得床动,走在路上总觉得路面发软,害怕着地震,却又盼望余震快来,惶惶不可终日。
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责挨训被罚,多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地飞来,他们只有两只手呀,两只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污水一样泼向他们。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他们与社会磨擦的危险性。在我接触过的乡镇干部中,你同情着他们地位低下,工资微薄,喝恶水,坐萝卜,受气挨骂,但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上司,极力要跳出乡镇,由科级升迁副处,或到县城去寻个轻省岗位,而下乡到村寨了,却能喝酒,能吃鸡,张口骂人,脾气暴戾。所以,我才觉得带灯可敬可亲,她是高贵的、智慧的,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我们可恨着那些贪官污吏,但又想,房子是砖瓦土坯所建,必有大梁和柱子,这些人天生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想,自然不会去为自己的私欲而积财盗名好色和轻薄会衍,这些人就是江山社稷的脊梁,就是民族的精英。
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为佛。现在地藏菩萨依然还在做菩萨,我从庙里请回来一尊,给它献花供水焚香。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土地神,印象里胡子那么长个头儿那么小一股烟一冒就从地里钻出来,而现在觉得它是神,了不起的神,最亲近的神,从文物市场上买回来一尊,不,也是请回来的,在它的香炉里放了五色粮食。
认识了带灯,了解了带灯,带灯给了我太多的兴奋和喜悦,也给我了太多的悲愤和忧伤,而我要写的《带灯》却一定是文学的,这就使我在动笔之前煎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之前不大理会酝酿这个词,当我与一位“八○后”的女青年闲谈时,问她昨天晚上怎么没参加一个聚会呢?她说:我睡眠不好,九点钟就要酝酿睡觉了。我问:酝酿睡觉?怎么个酝酿?!她说:我得洗澡,洗完澡听音乐,音乐听着去泡一杯咖啡,然后看书,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看着看着我就困了,闭上眼就轻轻走向床,躺在那里才睡着了。酝酿还要做那么多的程序,在写《带灯》时我就学着她的样,也做了许多工作。
我做的工作之一是摊开了关于带灯的那么多的材料,思索着书中的带灯应该生长个什么模样呢,她是怎样的品格和面目而区别于以前的《秦腔》、《高兴》、《古炉》,甚或更早的《废都》、《浮躁》、《高老庄》? 好心的朋友知道我要写《带灯》了,说:写了那么多了,怎么还写?是呀,我是写了那么多还要写,是证明我还能写吗,是要进一步以丰富而满足虚荣吗?我在审问着自己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在呢喃着,我以为是我家的狗,后来看见窗子开了道缝,又以为是挤进来的风,似乎那声音在说:写了几十年了,你也年纪大了,如果还要写,你就是为了你,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我吓得一身的冷汗,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那个声音又响:那你还浪费什么纸张呢?去抱你家的外孙吧!我说:可我丢不下笔,笔已经是我的手了,我能把手剁了吗?那声音最后说了一句:突破那么一点点提高那么一点点也不行吗?那时我突然想到一位诗人的话:白云开口说话,你的天空就下雨了。我伏在书桌上痛哭。
这件事或许是一种幻觉,却真实地发生过,我的自信受到严重打击,关于带灯的一大堆材料又打包搁置起来。过了春节,接着又生病住院,半年过后,心总不甘,死灰复燃,再次打开关于带灯的一大堆材料,我说:不写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呢,让我试试,我没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里向往啊。看见了那么个好东西,能偷到手的是贼,惦记着也是贼么。
于是我又做了别一件工作。其实也是在琢磨。
我琢磨的是,已经好多年了,所到之处,看到和听到的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在写作,在纸质材料上写,在电脑网络上写,作品数量如海潮涌来,但社会的舆论中却越来越多地哀叹文学出现了困境,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实是社会出现了困境,是人类出现了困境。这种困境早已出现,只是我们还在封闭的环境里仅仅为着生存挣扎时未能顾及到,而我们的文学也就自娱自慰自乐着。当改革开放国家开始强盛人民开始富裕后,才举头回顾知道了海阔天空,而社会发展又出现了瓶颈,改革急待于进一步深化,再看我们的文学是那样地尴尬和无奈。我们差不多学会了一句话:作品要有现代意识。那么,现代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当下中国的作家又怎么在写作中体现和完成呢?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而地球上大多数的人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顺着潮流去才是。美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强大使他们自信,他们当然要保护他们的国家利益,但不能不承认他们仍在考虑着人类的出路,他们有这种意识,所以他们四处干涉和指点,到南极,到火星,于是他们的文学也多有未来的题材,多有地球毁灭和重找人类栖身地的题材。而我们呢,因为贫穷先关心着吃穿住行的生存问题,久久以来,导致着我们的文学都是现实问题的题材,或是增加自己的虚荣,去回忆祖先曾经的光荣与骄傲。我们的文学全是历史的现实的内容,这对不对呢?是对的,而且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可能还得写这些。当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盼望的是得到面包,而不是盼望神从天而降,既便盼望神从天而降那也是盼望神拿着面包而来。但是,到了今日,我们的文学虽然还在关注着叙写着现实和历史,又怎样才具有现代意识、人类意识呢?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同样去写地球面临的毁灭、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作品,这恐怕我们也写不好。却能做到的是清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地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只有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我们的生存和文学也将是远景大光明,对人类和世界文学的贡献也将是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我从来身体不好,我的体育活动就是热情地观看电视转播的体育比赛。在终于开笔写起《带灯》,逢着了欧洲杯,当我一场又一场欣赏着巴塞罗那队的足球,突然有一天想:哈,他们的踢法是不是和我《秦腔》、《古炉》的写法近似呢?啊,是近似。传统的踢法里,这得有后卫、中场、前锋,讲究的三条线如何保持距离,中场特别要腰硬,前锋得边跑边传中,等等等等。巴塞罗那则是所有人都是防守者和进攻者,进攻时就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而眼花缭乱地华丽,一切都在耐烦着显得毫不经意了,突然球就踢入网中。这样的消解了传统的阵型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我是那样地惊喜和兴奋。和我一同看球的是一个搞批评的朋友,他总是不认可我《秦腔》、《古炉》的写法,我说你瞧呀,瞧呀,他们又进球了!他们不是总能进球吗?!
《秦腔》、《古炉》是那一种写法,《带灯》我却不想再那样写了,《带灯》是不适那种写法,我也得变变,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那怎么写呢?其实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写得时间长了,又沉浸其中,你总能寻到一种适合于你要写的内容的写法,如冬天必然寻到是棉衣毛裤,夏天必然寻到短裤体恤,你的笔是握自己手里,却老觉得有什么力量在掌控了你的胳膊。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和风格,它没有那么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何况我是陕西南部人,生我养我的地方属秦头楚尾,我的品种里有柔的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令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可这稍微地转身就何等地艰难,写《带灯》时力不从心,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点,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
就在《带灯》写到一半,天津的一个文友来到了西安,她见了我说:怎么还写呀?我说:鸡不下蛋它憋啊!她返回天津后在报上写了关于我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我名字里的凹字,倒对我有了启发。以前有人说这个凹字,说是谷是地是盆里是坑是砚是元宝,她却说是火山口。她这说的有趣,并不是她在夸我了我才说有趣,觉得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火山口。社会是火山口,创作是火山口。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里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我常常有些迷信,生活中总以什么暗示着而求得给予自己自信和力量,看到文友的文章后,我将一个巨大的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摆在了桌上,它几乎占满了整个桌面。我是以它像个凹字而购置的,现在我将它看作了火山口敬供,但愿我的写作能如此。
带灯说,天热得像是把人拎起来拧水,这个夏天里写完了《带灯》。稿子交给了别人去复印,又托付别人将它送去杂志社和出版社,我就再不理会这个文学的带灯长成什么样子,腿长不长,能否跑远,有没有翅,是鸡翅还是鹰翅,飞得高吗?我全不管了,抽身而去农村了。我希望这一段隐在农村,恢复我农民的本性,吃五谷,喝泉水,吸农村的地气,晒农村的太阳,等待新的写作欲望的冲动,让天使和魔鬼再一次敲门。
这是一个人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了,我想要日月平顺,每晚如带灯一样关心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咀嚼着天气就是天意的道理,看人间的万千变化。
王静安说: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