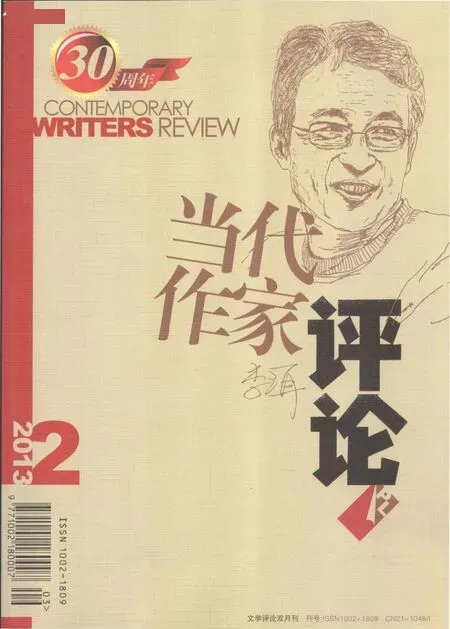朱天文的文学创作精神流变——以《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和《巫言》为中心心
2013-11-14金进
金 进
一、设限与沦陷:花忆前身,还愿胡兰成
朱天文曾说自己对胡兰成的理论“全盘接收”。的确,朱天文太爱胡兰成,她的早期创作亦步亦趋地践行着胡兰成的文化理论。朱天文认为胡兰成给予她最大的影响是视野,一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写小说也是一样:你就是写写写,但却注意着小说之外的世界。我想这样的视野是胡兰成留给我们的最大资产”。胡兰成的自我文化期许非常大,这一点影响到早期朱天文的创作,如散文集《黄金盟誓之书》中动不动就是文化、台湾气质等等,再如“台湾的这三十年来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了我们民族将来更大的事业,台湾的存在便是人事之上更有三分天意。以我办出版社的切身体验,这是极艰辛不易,然又是自助天助的幸运和喜气的。因此,我们不做荆轲的慷慨悲歌,而宁是效法国父的浩然之气。今日在台湾,我是不生此身生何身?不生今世生何世?我就是这里了”(《春衫行》,一九八一)。类似这种写作很多,很多时候带有“卒章显志”的效果,但更多的时候有点言不及义,内涵也少了很多。
胡兰成自曝“我是直接传承得五经与庄子”,纵观其著作,他的文化理论涉及基督的神道、佛教的禅宗、《诗经》的国风、四书五经、《离骚》和老庄的楚文化等等影响,试图弘扬汉文明,并让其与西洋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竞争与对话。朱天文曾称自己的小说集《传说》是对逝世的胡兰成的献礼:“我不能亲至兰师灵前哭拜,兰师仙灵有知,不忘金秋的约定,仅以这本《传说》奉上。所集的二十一篇文章,有七篇兰师读过批评了的,我承教铭记在心……知音不在,提笔只觉真是枉然啊。今我是以伯牙绝琴之心操琴,因为兰师的文章是这样最最中国本色的文章,因为我是从兰师那里才明白汉文章原来是这样的。”一直到《弥撒之书》(一九九六),朱天文回忆自己姐妹受教于胡兰成,“天心是坏学生,我是好学生。胡老师说‘从旁门入者是家珍’,反而旁门左道不按他胡氏教义来的,是珍宝。又说‘见于师齐,灭师半德’,见解跟老师一样的话,倒成了老师的罪人。何况好学生,其实是无趣跟平庸的代称。是坏学生,才写得出《击壤歌》……我很羡慕她行文之间不受胡老师影响,我则毫无办法的胡腔胡调。”
那么朱天文受到胡兰成怎样的影响呢?一方面,她的小说中有着强烈的驻守今日现实的倾向,即入世情怀,一如她自言:“佛去了也,惟有你在。而你在亦即是佛的意思在了,以后大事要靠你呢。你若是芙蕖,你就在红泪轻露里盛开吧!”这种对胡兰成及其文化理论的崇拜被内化为朱天文创作的习惯,《传说》中有很多地方有着这种表达,每每放在篇尾,卒章显志。像《青青子衿》末句“雨继续地下着,落在塑胶瓦上,是一支秋天的小歌,唱在每个人的现世里——唱不完此生此世的多少忧患啊”;《子夜歌》中眷村生活的童年回忆,“那年夏天,我比哥哥姊姊他们知道了什么。因为,因为星星的孩儿从天上下来了,以后我们在的地方要起来许多事情。彩虹横在天空中,荷花八月整整开,世界也要整整的开了,开了呀”;《五月晴》末句“那是一株栀子花。一潮一潮的花气袭人,像是在酝酿着一个盛夏的来临”;《剪春萝》末尾道“婉卿登时已热泪如倾。太阳是这样的大,风滚着阳光哗哗地吹起来,而她只能是这样挥一挥手,这样走了过去,连回头都不能,也不想再回头了”等等。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小说人物的塑造、故事的编排,朱天文表现出对“士”使命的自觉。《传说》中的很多文题都带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如《五月晴》、《腊梅三弄》、《剪春萝》,以及“罗敷自有夫”、“白蛇娘娘”、“青蛇妹妹”、“龙王三太子”、“翡冷翠”、“盗仙草”、“那古老美好黄金的时代”、“水仙花”等一连串文学典故的运用,展示着才女本色,也表达着她向中国古代文化的尊敬。《春风吹又生》中刻画了一个投机的归台留美学生,小说借他的口表现着此人的学识与境界的肤浅,篇末“这样的好天气里,你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被原谅的”,自我安慰中坚定着自己的文化追求。
你看看,士大夫的象牙塔是怎么样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我的天,渔火,你知道,这渔火是什么?渔民捕鱼点的灯哪!你想到他的艰苦吗?想到他们必须晚上出来工作,换一口饭吃,而你这时候在睡觉!在sentimental!王维,王维他又是个什么东西,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是多少劳苦大众服侍出来的闲情。我跟你打赌,他这种有闲阶级,如果连三餐都混不饱肚子,还有心情去弹琴长啸!
长篇小说《荒人手记》是一部朱天文还愿胡兰成的经典作品,“写完《荒人手记》我跟天心说,是对胡爷的悲愿已了,自由了”。写到最后,她自己也发现“《荒人手记》也边写边知道是在回答当年胡兰成老师去世时在写着的《女人论》,虽然小说呈现的完全不是那一回事”。此语一出,黄锦树、邱妙津等人撰文应和,朱天文也很同意他们的论点。这本书展示着朱天文对同性恋、幽闭症等社会问题的思考,小说中涉及到的文化名人有弘一法师、李维史陀、罗丹、麦克尔·杰克逊、小泉今日子、傅柯、宫崎骏、三岛由纪夫、尼金斯基、泰戈尔,文明史上的阿波罗神殿的肛交、日本伊势神宫祭祀的天照大神、源氏物语、刑天舞干戚、拜底比斯阿蒙神庙、海兹佩苏女王墓殿、拉美西斯二世、托勒密犹发知提三世、图坦卡蒙、司芬克斯、北印度拘尸那城、雅典娜神庙、特洛伊旧址、底比斯的先知泰、释迦渡尼连禅河,宗教有基督教、佛教,同性恋者小韶、阿尧、永桔、费多、施、杰、金,这一切都让《荒人手记》这本书中充满着大量的文化评价,凸现出一种知识分子写作的倾向。
朱天文如何还愿呢?其实,“荒人”之义直通胡兰成自居的“谪居”、“亡命”之自喻。胡兰成说他于文学有自信,但惟以文学惊动当世,心终有未甘,“我亡命日本不事生产作业,靠一二知己的友谊过日子,我的人果有这样的价值么?是不是做做厨子与裁缝的华侨还比我做人更有立脚点?”比较起朱天文的个人表述:“一介布衣,日日目睹以李氏为中心的政商经济结构于焉完成,几年之内台湾贫富差距急骤恶化,当权为一人修宪令举国法政学者瞠目结舌,而最大反对党基于各种情结、迷思,遂自废武功的毫无办法尽监督之责上演着千百荒唐闹剧。身为小民,除了闭门写长篇还能做什么呢?结果写长篇,变成了对现状难以忍受的脱逃。放弃沟通也好,拒绝势之所趋也好,这样的人,在这部小说中以一名男同性恋者出现,但更多时候,他可能更多属于一种人类——荒人”,我们可以看出两师徒之间的神似之处。
其次,胡兰成有“女人创造文明”的观点。胡兰成在写《山河岁月》的时候,每每把文章寄给已经分手的张爱玲,“他自比是从张爱玲九天玄女那里得了无字天书,于是会来用兵布阵,文章要好过她了”,胡兰成认为“太初是女人发明了文明,男子向之受教,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七佛之师”。胡兰成还称“若不得张爱玲的启发,将不会有《今生今世》的文章写法。由此可见张爱玲确是开现代中国文章风采的伟人”。《荒人手记》中小韶形象其实是一个被置换了的阴性形象:“我跟守财奴一样,攒着眼前的运气眼前人,一点一点挥霍我们相处的时光。永桔离开我去做他事情时,不成文默契,我们绝不留恋,吻别,最稀松平常的仿佛他不过是到街头超商买些食物马上回来,或他在浴室暗房冲洗照片而我去办公室和学生谈话。我们甚至回避眼光,害怕看见了自己的软弱。别离前夜,我们不做爱,因为,因为那真是太惨了。我们会提早一天两天,且故意草草,严防伤别所掀起的恐怖肉欲将我们歼灭。前夜,我们会去有家庭的朋友家度过。根据经验,切忌族以类聚,言不及义的逗嗔逗笑逗讥,或泡吧泡KTV,酒精声光,轻易便瓦解情绪,搞到一塌糊涂。”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把小韶看作一个女性角色。小说后面“当男人们不再见异思迁,睹色心动,因为麻烦?太累?没时间?没办法就是不想?女人们于是都沉寂了”的表达,也再次标志着小韶的阴性角色。而换一个角度去看小韶与杰之间的爱情,何尝又不是印证着“始乱终弃”这个古老的爱情命题。而另一方面,朱天文认为在日本文化中嫉妒是美人之德,吃醋是另一种形式的沟通,传达着“我真的非常非常在乎你”这一意念,这一点放在小韶身上,可见另一番意思。
综观《传说》、《荒人手记》,运用着胡兰成的文化理论,明显有着“理论先行”的特征,足见胡兰成对朱天文的影响之大。一九七六年秋天胡兰成返日后,因各种原因不能来台,他在给朱西宁夫妇的信中言,三三发展得很好,若他回来,虽只住十天半个月,仍会影响到三三,这封信中,胡兰成还以不为罗马人所容的耶稣、保罗,不为雅典人所容的苏格拉底自喻,自我感觉良好,俨然一世之师。另外,其父影响也不能忽视,朱天文早期的作品必给朱西宁审查,“爸爸看完把稿子给我,我连好坏还不敢问,尽管把错别字或技术犯规的地方一一订正。订正完,没话,那就是这篇完蛋了,自己叹一声:‘好烂喔!’见爸爸温和的笑笑,仍不言,就够我去几天闭门思过了。如果不错,爸爸就会指出缺点说明。如果很好,爸爸倒会先不好意思起来,我才敢问:‘怎样啊?’通常爸爸只是笑笑,说:‘好啊。’好在哪里,也不说,却够我喜欢的去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真的是好的。”(《给爸爸的信》,一九八三)两位文坛大家对她的创作影响是巨大的,朱天文早期创作是处在双重的强大阴影之下的,幸运的是,她自己的艺术感悟,特别是她文笔之细腻、刻画之深刻,使得她的作品能够在阴影下保留着艺术作品最本真的部分,“不幸”之处反而造就了她的艺术成绩。
二、自我沉底与超脱:平凡与华丽并行的人生书写
《乔太守新记》是朱天文第一部小说集,初版于一九七七年,这部小说今天看来确实“青涩”。《仍然在殷勤地闪耀着》(一九七二)讲述大学里面一段朋友情谊,一个略显木讷的我,一个性格乖张的李,一个校园故事被朱天文写得颇有张力,小说中的姐妹情谊使人怦然心动,但因性格不合终至陌路,又给这篇小说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强说的愁》中的骤听同学出车祸、《怎一个愁字了得》中慧兰对男老师的情窦初开、《缘》中的同乡之缘、《女之甦》中小蓝的初恋故事、《丽人行》中的少年心事、《陌上花》中早婚青年的艰辛度日、《乔太守新记》中莎莎的爱情故事以及《蝴蝶记》中返台任教的留学生的心绪,这部小说集中的故事虽然都是青春题材,而且有着“文题不对”(小说内容与题目关系有些牵强)的毛病,但朱天文对平凡人生的生存和情感的把握,初露锋芒。
朱天文在二十六岁之前,生活单纯,主要是在编同仁杂志《三三集刊》、三三杂志、三三书坊,单纯的朱天文遇见颇带平民色彩的侯孝贤,其创作也开始有了新的内容。她的剧本创作颇有平民色彩,基本上都是以平民的视角切入历史或者当下。朱天文步入编剧生涯的第一篇小说《最好的时光》,讲述的就是小毕一家的平凡日子,真实而富有温情,《恋恋风尘》里以阿远、阿云为代表的台北打工青年,结局也是那人世风尘中的情感脆弱。朱天文与侯孝贤合作的“台湾三部曲”,其中《悲情城市》围绕着林焕雄及其“小上海酒家”发生的种种故事以及林焕清身边的“二·二八事件”历史,展示着台湾民间社会中“山头势力”和“派系”的黑社会生活,还有《好男好女》中围绕梁静发生的当代台湾(现实)和戏中戏中的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综合考量这些,我们会发现朱天文所编写的剧本,着眼点都在人的命运之上,通过人的命运书写,带动着自己对整个台湾历史的反思。
其次,与剧本创作同期的小说及散文创作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小说集《最想念的季节》、《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中一系列的城镇人物的书写,以及后来辑在《有所思,乃在大海南》、《黄金盟誓之书》两本集中的散文亦然。《世纪末的华丽》写的是都市人的“颓废”,朱天文自承“是为了一句话而写:‘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不过,我却认为她又犯了“胡说”的老毛病,我更相信她另一句话:“拙作《世纪末的华丽》,借的是上个世纪末奥地利的画家克林姆(Klimt)的画。当时的首善之都维也纳,是什么光景呢?我认为,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不朽》(Immortality)里做了最好的描述。他说:‘羞耻心和恬不知耻在势均力敌的地方相交,这时色情处在异常紧张的时刻,维也纳在世纪的转换期经历了这一刻。这一刻一去不再复返。鲁本斯属于这个养成羞耻心的环境中长大的最后一代欧洲人……’羞耻心如果是旧的好东西,恬不知耻就是新的好东西。我从恬不知耻着手,写出来这本《荒人手记》。我反省我这一代在台湾长大的人,我们属于这个养成羞耻心的环境中长大的最后一代台湾人。羞耻心和恬不知耻在势均力敌的地方相交。这时色情处在异常紧张的时刻。台北在世纪的转换期,经历了这一刻。”《世纪末的华丽》中,“米亚是一位相信嗅觉,依赖嗅觉记忆活着的人”,“米亚也同样依赖颜色的记忆”,而最后一句“年老色衰,米亚有好手艺足以养活。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可以看出这篇小说是典型对胡兰成《女人论》的回应。米亚每次都召集着年轻的朋友,可当她退出朋友圈之后,朋友们也云消雾散,小说中以米亚为模特,用她的穿着串起台湾青年的服饰流行过程,在这时女人就是历史:
那年头,脱掉制服她穿军装式,卡其,米色系,徽章,出入西门町,迷倒许多女学生。十五岁她率先穿起两肩破大洞的乞丐装,妈妈已没有力气反对她。尽管当年不知,她始终都比同辈先走在山本耀司三宅一生他们的潮流里。即使八四年金子功另创一股田园风,乡村小翠花与层层荷叶边,米亚让她的女友宝贝穿,她搭矿灰骑师夹克,树皮色七分农夫裤底下空脚布鞋,双双上麦当劳吃情人餐。宝贝腕上戴着刻有她名字的镀金牌子,星月耳环,一双在宝贝右耳,一双在她左耳。三一冰淇淋那一年出现,三十一种不同口味色彩缤纷结实如球的冰淇淋,宝贝过山羊座生日,两人互相请,冰天冻地,敞亮如花房暖室,她们编织未来合伙开店的美梦……八九年秋冬拉克华推出豹纹帽,莫斯奇诺用豹纹滚边,法瑞综合数种动物花纹外套,老虎、斑马、长颈鹿、蛇皮。令人缅怀两百年前古英帝国,从殖民地进口的动物装饰品像野火烧遍欧洲大陆……人造毛皮成为九○年冬装新宠,几可乱真,又不违反保护动物戒令。
《柴师父》中,柴师父(柴明仪)是外省人来台,即使到今天,“他去安和路替钟小姐家人看治,啤酒屋霓虹招牌投影下的热带莽林中,奇花妍草异色,形如他第一次看到孔硕无比的香蕉,和头颅似的滚满了狰狞狼牙钉的凤梨,样样欺他生,摆出夸张的脸色”。年老后的柴师父不明白自己的孙辈们每天在看什么想什么,小说中,柴师父想念着一位青春的少女,“等待女孩像等待知悦的乡音”,“等待女孩像等待青春复活”,“等待女孩像等待有缘师徒”,少女成为年老的柴师父的精神寄托。《尼罗河女儿》则俨然台湾新生代宣言,林晓阳自言:“我的小档案啊,我是AB型,双鱼座,所以我有四重个性,B型的Seiko,A型的晓阳,天真有着自然卷头发的凯罗尔,以及艳情的尼罗河女儿用冰凉的青铜液把眼线长长描进头发里。白色灰蓝色是我的幸运色,血石和风信子石是我的幸运石,我的花则是叶子和种子都很毒的曼陀罗。我没有崇拜的偶像,我崇拜我自己,因为我不要做别人,我只要做我自己。”《肉身菩萨》则是朱天文第一次公开写同性恋的故事,主人公小佟先是被贾霸鸡奸,一步步堕落的他,自认是一个不要命的渣子,对自己的身体也索然无味到反胃的地步,直到遇到钟霖,让他摆脱了长期的精神创伤。《带我去吧,月光》是一则民主政治风云和都市男女情感困惑,小说开头就展示着台湾民主运动的兴起的图景,抗议队伍导致东西大衢完全瘫痪,满街一片戾气怨腾。在这个充满情感变化的时代,男女之情成了“一种口味上的出轨”,女主人公佳玮在理想中的情人夏杰甫和现实中男友李平两者之间徘徊,经历着物质与精神的取舍与纠缠,这个故事明显延续着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精神谱系。《红玫瑰呼叫你》把都市人的力比多表达了出来,《恍如昨日》反映的是文化界的喧嚣,其主旨都在刻画一个光怪陆离的新都市色彩。
综上所述,在勤耕于剧本创作的时期,朱天文的创作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摆脱对胡兰成文化理论的简单模仿,而是将其继续内化于自己的生命之中,寻找着与自己心灵契合的那部分。《荒人手记》中满浸着朱天文的生命感悟与生活经验,实是她第二阶段作品的高峰,这阶段的作品将外省心态、平凡人生和文化底蕴三者合一,朱天文终于走出自己的文路,“朱因为过分一本正经而显现的天真,未尝稍减,也因此与祖师爷爷或奶奶极有不同。亏得这一脉天真,她终于走出自己的路来”。
三、自我救赎与化境:物的情迷,边缘人的姿态与声音
仙枝谈到对朱天文的印象:“清明那天偕你去看牛,两排牛妈妈蹲下身子来有城墙高,我们在夹道间喂牧草,日色倾得一地斑斑驳驳,牧草的野膻味淹着满屋子都清明粗犷起来;见你闪闪跳跳躲着牛妈妈的长舌舔你裙角……听你亮着大眼睛对牛说‘牛啊,牛、牛牛’,我忽然奇怪自己竟从来都不曾叫过它们。你每次和单单说着‘天语’,我就会觉得单单真不是狗了,它听懂你话,你又和它有那么多话可说,至少单单来世不再会是狗了。”这是目前最早彰显朱天文个人气质的记录,颇有同巫的灵性。另外,“巫”的形象也是经常出现在朱天文的笔下,如:
1、“米亚却恐怕是个巫女。她养满屋子干燥花草,像药坊。老段往往错觉他跟一位中世纪僧侣在一起。她的浴室遍植君子兰,非洲堇,观赏凤梨,孔雀椰子,各类叫不出名字的绿蕨,以及毒艳夺目的百十种浴盐,浴油,香皂,沐浴精,仿若魔液炼制室。所有起因不过是米亚偶然很渴望把荷兰玫瑰的娇红色和香味永恒留住,不让盛开,她就从瓶里取出,扎成一束倒悬在窗楣通风处,为那日日褪暗的颜色感到无奈。”(《世纪末的华丽》)
2、“巫扮演着非社会的角色。他是一种神召,和某些灵,不管邪恶的或强力的,订了契约。他会医病,预知未来。灵守护他,同时也监视他。灵借他的身体显形,全身痉挛,不省人事。他跟灵结在一起,不知谁是仆谁是主。他明白自己已然被召唤,其征兆,体内一股恶臭,他逃不掉了。无从选择,不能改变。正如大多数被征召的,嚎啕起来,为什么会是我!”(《荒人手记》)
3、“是的国民美少女。波浪发泻到腰,渔夫帽覆住大半脸以掩避公众耳目,混搭的多层次衣裙迤垂脚踝,若非美少女,此种装束必沦为一名扫帚女巫灭顶于布堆里。但美少女!全场,惟全场她一人敢目视自己的镜中影,挑衅又爱恋。”(《巫言》)
如果说《荒人手记》是荒人所作,那么《巫言》中继续选用边缘人(或者说是社会边缘人)的角度去探索人生与社会意义,《巫言》实际上可以看作“巫人手记”,实则就是“巫人之语”。朱天文享受着“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自足精神空间。二〇〇三年在一次采访中,朱天文言:“巫之为巫,也许是在能够动员到那未知无名的世界,将之唤出,赋予形状和名字。这动员的状态,令人怯步,总以自己还没准备好准备够做理由,四处晃荡当白痴,料不到一晃十年。再提笔,你问我欲望是什么,是瘾吧,巫瘾。动机呢?我觉得白痴岁月应该结束了,否则,我会真的成了一个无用的人。”
女巫是男性给女性的一个定位,也是当下女作家很感兴趣的身份,“因为她们使受压抑的形象得到复活,据说这些形象是巫婆和歇斯底里患者;这些不缚绳索的女性所带来的灾难,在于她们将成为父权文化语境中的不祥之物”。而朱天文的“巫”不太像森林阴森角落中的“女巫”,倒更像日本神社中的“巫女”。《巫言》可看作朱天文半生经验(社会生活、文章笔法等)的融合,如《巫言》中很多篇章所涉及的内容,其实早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她在《自立早报》的“女性频道”专栏中,就已经初见端倪。其中《女人与衣服》、《再谈日本》中“我要骄傲地宣布,女人就是败在衣服上”与“巫看”(第一节)中购物女狂人相同,《从来不是上班族》、《做家事》、《特殊朋友》中自称有业游民,变成“一个所谓的自由撰述”的我,不就是“巫时”中那个隐身于室的“巫”吗?而《文学的童年》中的父女之情,那种“当时我并不知道谁是张爱玲,谁是沈从文”的感觉,也与《巫言》中第四章“巫途”中父女之情殷殷相通。
第一章“巫看”讲的是菩萨低眉,入世看人的现代版故事。小说中菩萨即“我”,“我”即菩萨,入世的菩萨被置换成搭团旅游的不结伴的旅行者,世间人皆笑话我,第一群人是“那伙比我小十岁,出校门工作了数年薪水三万元上下的女孩们,红酒族”,她们的时尚追求让我出局。第二个会笑我的是乔茵、王皎皎之辈,他们住父母吃父母,可眼见的未来似乎不嫁亦不娶,一年勤勤恳恳,储够了休假日便结伙出游,掷尽千金回国,他们是典型的酷儿一族。第三个会笑我的是老同学陈翠伶,她嫁给了一名长荣航空公司的高级主管,阔太太坐着长荣头等舱飞到维也纳听三大高音的演唱会,定会笑搭团去香港看歌剧的我。第四个笑我的是搞小剧场的阿卡,追求先锋艺术实践,认为听歌剧的我太堕落了。第五个笑我的是我自己,飞到香港看歌剧《歌剧魅影》,自为圆自己幼年人鱼公主的梦想。第六个笑我的是我的家人,我只好撒谎说自己的机票是公司免费套券。这一切的一切让我只感是那低眉的菩萨,一旦堕入红尘,“是这样不自由啊,活在众人眼光之中”。堕入红尘的我并不想与同宿女伴多说话,“‘谢谢’,‘回来了’。或者‘我先洗澡了’,‘好的你先’。‘钥匙你拿’,‘没问题’。诸如此类稀少的发言,绝非人语,倒是符咒。符咒把我们团里为两件互不干扰的物体,窄促斗室,运行得毫不擦撞”。展示着现代人之间的不易亲近和冷漠。接着,旅行者变幻成兽医江医生,面对饶舌的动物主人,他选择“把眼帘放下,目光啣在帘间”,做一个“似瞑非瞑,如笑未笑,坛座里一位拈花人”。再接着,江医生变成了马市长,面对着政治综艺化的台湾政坛,他眼睛低垂,变成了浪迹人间的菩萨幻身。最后,菩萨再变,成为退休在家的前社长,孤零零的老年,他最喜欢的是等待着收报纸的跛汉每月来临,“重新支起的和谐关系里,施与受,施的一方前社长变得很低很低,兼之受者跛脚,施者也许又更低了一些。施比受有罪,他得弯腰更多,低眉垂目。收废纸的跛汉呢,他得站稳另一个支点。惊惧于平衡状态之脆弱易毁,低眉垂目,惟恐一抬眼世界就崩裂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天文执著于现世,再现《世纪末的华丽》的精神。菩萨低眉的慈悲情怀又加注在王皎皎身上,让他战胜了自己的同志迷狂,这个时候的王皎皎,身在异国他乡,心恋着跟最亲的人联络,想来想去,他最想通话的居然是自己去世的父亲,想问他:“你那里现在几点?”小说中堕入红尘已久的男同性恋,最终战胜了自己,成为健康的正常人,恍恍惚惚中,让我们想起了《荒人手记》中的中年小韶。
第二章“巫时”回到朱天文本身,她思考着世人的喧嚣和文明的内涵。一开头就玄思着东方文明高于西方,一开场讲的是奥古斯都时代葛里森炼金得瓷的历史,“他找到坯体的配方,但釉色距东方瓷器的清澄明艳还远得很,釉下蓝和彩釉仍未开发。他苦苦试验用来创造颜彩的金属混合物,不知四百年前中国景德镇人已用氧化钴制作釉下蓝,他的难题才开始”,言语之中已经透露出胡兰成理论中那些东方文化优越感的理论。接着讲的是中文之美,认为他“不过是印证了他之前的成见歪见,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读一位念完英美文学硕士的中国人到美国后以英文写的小说,而这些描写大陆生活的小说现在又被别人翻译成中文出版?”还言“哈金的英文著作可以译成不论哪一国文字,就是不好译成中文。一句话,中文版会见光死,得五个灯,不,五个国家书卷奖也救不了它”,连“哈金震撼台湾文坛”也被认为是文字贬值世代的综艺表达,质疑哈金的“中性的英文”的说法。文中“本来创作就是在跟自己对话,整理自己,自问自答”的文中自语,充分地表现出朱天文对东方文化的自信。
第三章“巫事”恢复到《世纪末的华丽》的“颓废”笔调,“巫事(1)”一节中漫溢着台湾政治的综艺特色,那士林夜市中的小店铺老板的宣传策略、公司老板夫妇自腌的酱菜、在政党讲演空档中出现的国民美少女、第三党党魁的理性而又煽动的雄辩术、忙于竞选立委的老板,还有热情万丈的妹妹,都把竞选里里外外地烘托得热腾腾的,华丽颓废。第二节“Email和V8”讲述的一对都市男女的苦恋,前半节照录着自己发给自己的Email,讲述着当下自己与男友胡丁尼的恋爱琐事,后半节描述着V8摄像机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三日摄制的初次相识,小说中V8摄像机中不断出现的“声音说”,是在用男孩的视角回溯她们之间的恋爱。两段故事中间多次互相印证,互文的效果非常明显。第三节“荧光妹”延续这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绚烂而奢靡,一如《好男好女》中的阿威梁静。第四节“巫事(2)”中继续描写着参选的公司老板,喧嚣异常,但现场我遇到的,第一个是车狂崔哈,第二个是夜游女,第三个是时髦女,明显凑着热闹,最后,参选助选诸人皆迷茫,奉行堂吉诃德主义的老板面对的是“日常的永远无效性里”,他把“自己变成为目的,战斗都在他身上踏过,直到他自己也成为路径”。政治参选究竟是救赎的努力,还是人类的戏梦,还是毫无意义的徒劳?这是这一部分留给读者的思考。
第四章“巫途”显然是朱天文有意地为切题而作,第一节“巫途(1)”讲的是自己与马修的见面,接着是与波赫士的交往,又回到马修处,在一个轮回中想象着纽约之行,整个小说犹如一本纽约地理图志。第二节“不结伴的旅行者(4)”药学博士郝修女来访的时候,讲述的是郝修女的炼药之术。紧接着的第三节“巫途(2)”,郝修女成了炼药的女巫,研究的是抗癌之药。而第五章“巫界”回应着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二二九”,辩论着中西年历的区别。第二节“二二九,浣衣日”把现实中的台湾两党的对垒写了出来,背景是台湾本省民进党的“四百年来第一战!”回应着前面巫人认定的“四百年来这一天,倾国与倾城,佳日难再得”的新气象。小说中,谈到自己的文化的自觉,“那是,台风把树兰整个吹到对邻始终密闭的廊窗外,二楼我窗前遂空掉一大块好像亚马逊雨林又消失了一块。而雨林里每死去一名巫师,就像又烧掉了一部文库”。认为惟有“巫”(巫女)保留着历史,“只有会被火烧毁但仍存留的,是自火中救出的,才能让人学习到某种必要性,某种可能永远失去无法取代之物的必要性吗?神圣之书”。
朱天文开始开口演说,认为“巫言,巫的文字语言,巫师这门行当最重要的工具或说技艺,唤醒万事万物的灵魂,改变现实的面貌”。她自觉过往的创作“太恃才太率性,缺乏责任感也没有纪律,这是暴殄天物……我但愿像你无言闭居淡水十年,出来后便说话说个不停。我应当要有这个作为巫者身份的自觉。它是一个命定,所以它是一个责任,不容逃避”。长篇小说《巫言》通过一个边缘的“巫”的平凡人生,去关怀世界,感悟众生,终于摆脱了围绕她头上的“胡张”的阴影,走出了自己的特色,终成大家。
四、结语
随着《巫言》的诞生,我们可以看出朱天文逃离“张腔胡调”的努力与成功,平凡人事、人生哲思、文字技巧和苍凉文风完美结合,使之成为华文文学的经典作品。但这部小说也暴露出朱天文创作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她的长篇小说名为长篇,实为短制,小说的衔接全靠作者的意识连接,读她的长篇小说完全可以中短篇小说对待之,而且文字技巧运用得让读者喘不过气来。换而言之,如果把她的代表作《荒人手记》、《巫言》中的“水分”减掉(如插入作者的临时感受、对周遭意境的渲染、朱天文特有的“掉书袋”等等),朱天文的长篇小说并不“长篇”。唐诺认为她已经逃出张爱玲的影响,也直言朱天文有一种极特别的书写危机,那就是她过大的目标和她太从心所欲的书写(文字)技艺,而“《巫言》作为她连续三次长篇书写叩关(包括不成降为短篇的《日神的后裔》)的终底于成,于是有着多一点点的不祥——想想这的确是够长的一趟路,一个目标,三鼓不衰,消耗的已不只是心力了,也包括体力”。这也可能是朱天文写作中绕不开去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