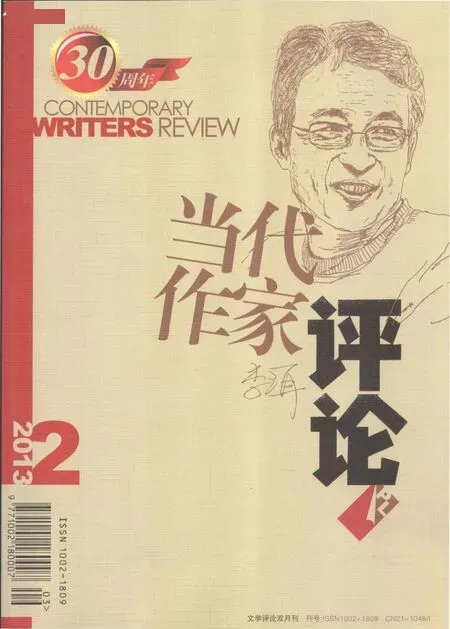到底有没有译者风格这回事?——林源译文集《而译集》①序
2013-11-14杨慧仪
杨慧仪
根据传统翻译理论,译者该无形无色无臭地次存在于无我之别人的世界内,译文不该有自己的风格,有的只能是对源文风格的呈现。
在二十世纪最后阶段,翻译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译文的本体,这对译文和译者来说,都是一种解放。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翻译、译文和译者一连串的反思,其中包括译者风格的问题。
当代翻译学教母Mona Baker对译者风格有精辟的见解,她认为描述译文的语言特点——包括译文中重复使用的句式,常用的词句,甚至构词构句的习性等 ——假如不能说明译者的认知习惯,及其成文的价值观动机,便无法说明译者的风格。她建议评论人先从译者选择翻译的文体及主题入手,并观察译文里非因源文需要或译入语要求必要而为的语言策略,从而尝试了解译者的认知习性和翻译的价值动机,才能参透译者的风格。
拿到林源译文集书稿,喜读。林源选译的,均是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论文,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论题。今日中国文学置身国际文坛之中,文学作品服务的不仅是中文读者,更通过海外销售和翻译,服务国际读者。而国际读者和评论人的意见回馈,不免以外语在海外发表,如果中国作者、读者和评论人因语言隔膜未能得知,实在可惜。评论不是作品的成绩单,而是如罗兰·巴特所说,是一个主观世界与另一个主观世界的交流,意即文学家以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为本,建构出作品里浓缩又浓郁的世界,与之碰撞而擦出火花的,是评论人同样主观的对世界的理解;由此而成的评论,就是两个主观世界的对话。中国文学界要是不理解国际读者和评论人对我们作品的反应,便难以有效服务这群读者。可惜文学翻译是苦功夫,文学评论的翻译更苦,愿意译的不多,要译得好更难;林源此翻译集是非常适时又做得好的实事,非常难得。
特别值得欣赏的,是此翻译文集选译的文章,有效地代表了国外对中国小说评论的不同方位。从所评作品来看,有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莫言的《丰乳肥臀》和《天堂蒜薹之歌》,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兄弟》,姜戎的《狼图腾》,还有张爱玲多个小说,均是不同方面极有代表性的作品;与对冯小宁电影《紫日》的评论一拼起来,立时显出中国小说与电影在处理中国现实上,自八十年代就建立起来的姻亲关系。在此之外,有文章研究李泽厚对中国美学的论述;这样安排,仿佛提醒读者,不要光看国际评论界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更要把中国文学放置于中国美学系统里观照。再除此,还有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文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史等重要讨论。依兰·斯塔文斯的三篇文章表面上跟中国文学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但细看发现,三篇文章讨论的题目包括翻译和为外国作者作传(斯塔文斯是美国人,马歇斯是哥伦比亚人)等,都是今天中国文学在世界传播必须思考的问题。最后一篇说的是人类心理节奏,不就是我们阅读小说时,最主观、最真实的经验吗?把这文章作书的尾章,是不是在挑战评论家,暗诘他们能不能把这最难以言喻、却最为真实的阅读经验,写进他们对文学的评论里?
除了译材之外,此书各论文的源作者均是不同评论方位和方法的最佳代表。开卷即见厄普代克,他的文学观是欧美式的,发挥其中可以合理伸延普适的度量衡,用以理解中国文学,并以创作文学的笔法写成,情理皆浓。白博礼是“中国老手”,对中国和中国文学有长期和纵深的了解,却不忘英语世界读者的视线,具双重视野,是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都非常有意义的评论。周月风、杰斯·洛、刘剑梅、张英进四位跟译者林源一样,都与香港或美洲结缘,地理上游走中心、边缘、海外,视点不断移动,自我辩证成为五位评论和翻译的内在逻辑。顾彬和斯塔文斯两位文学专家,深受中外评论人尊敬,他们所论,无论是中外作品,行文无不处处表现两位对人本文学深刻的信念。马龙科学、文学并重的笔法,把世界的两大维度融为一体,为文学打开新境界。
视野如此多元、范围如此庞大的论文群,译者的风格能否显现呢?质存形自显。首先,这十五篇文章面貌虽异,意义却相通:跳出本语文化视野,把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本身,变成一种文化辩证。在语言运用方面,译文在不破坏源文情味的原则下,以通顺流畅的语言,尽量提高读者阅读的效率,以理导文,以文梳理。这含蓄的翻译策略背后,是对源文意义坚定的信念;这类翻译,是源文最理想的伙伴。成就这翻译风格的,正是译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国际视野,还有对国际文学评论,无私不怠的服务精神。
翻译天才先贤严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容许我在这也说译事三难:谦、和、勤。这译文集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