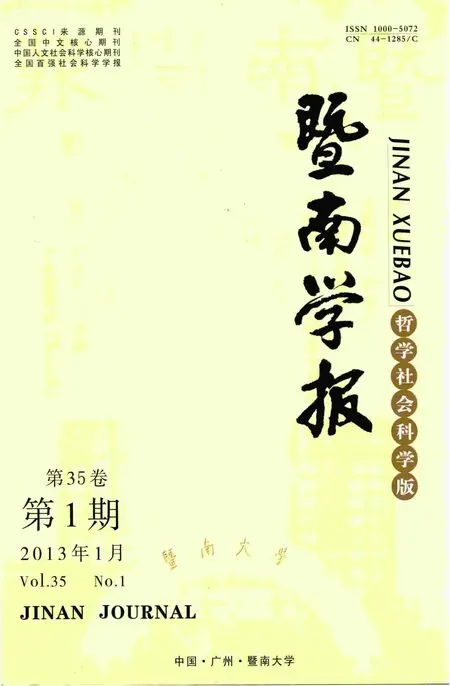当代乡土政治小说新论
2013-11-14樊星
樊 星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乡土小说长期以来是中国新文学的一大看点。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思想解放的这个历史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那便是:旨在关注乡土政治、暴露乡土政治痼疾的作品明显多了起来。文学的热点常常能够折射出时代的呼声。事实上,当代乡土政治小说的繁荣正好与农村经济改革以后迅速凸显的农村政治改革的呼声同步。然而,我们很少看到正面描写农村政治改革的力作(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农村政治改革的成功范例据说不少),倒是暴露乡土政治弊端的批判之作层出不穷。这些作品与暴露城市官场黑幕的“官场小说”一起,给人留下了深长的思考:它们的大量产生意味着什么?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乡村政治的许多隐患,还可以洞悉作家们对于“改造国民性”的悲凉之思。
“官本位”的阴暗图景
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儒家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齐家”是基础,“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高境界。在老百姓中,敬官、怕官、渴望当官的俗语也广为流传,诸如“见官莫向前”、“屈死不告官”、“官大一级压死人”、“朝里有人好做官”、“官官相护”、“读书做官”、“当官发财”、“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之类说法由来已久。有这样的心理基础,中国文学中自然少不了相应的人生图景。《水浒传》中“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流氓理想,《红楼梦》中的“护官符”、贾政、薛宝钗对贾宝玉走“科举仕宦”道路的要求与期待,《儒林外史》对于科举制扭曲读书人心灵的嘲讽与悲叹,都相当典型地折射出了国人对于“官本位”的复杂心态。当代文学中,针砭“官本位”痼疾、反思“官本位”教训的作品更有了空前的发展。这既折射出当代作家对中国政治变革的迫切期待,也足以表明“官本位”痼疾在当代的积重难返。
早在1980年,就产生了一批暴露百姓中“官本位”心态的力作——如白桦的中篇小说《啊!古老的航道》就深刻揭示了历史的荒谬: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恪守着“见官莫在前,做客莫在后,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出世之道,并因此逢凶化吉,平安一生。倒是那些锐意进取、富有政治热情的青年常常为政治的无情饱尝苦头。同年,贾平凹也在短篇小说《夏家老太》、《上任》、《山镇夜店》中以朴素的故事写出了农村日常生活中“官本位”的强大:夏家老太就因为儿子娶了公社书记的女儿而一下子赢得了人们的奉承;新书记就因为为人谦和、正派反被部下看不起,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当官应该“显个威”;而那些因为山镇夜店拥挤而发生争执的农民在后来的地委书记面前倒甘愿退让了……这些作品揭示农村日常生活中“官僚主义”影响的无处不在,笔调以淡淡的讽刺为主。到了1983年的笔记《商州初录》中,也有两则记录“土皇帝”横行乡里的故事:一是《石头沟里一位复退军人》,写出了农民只有给大队领导送礼才能当上兵,当兵几年没提成干部未婚妻就退婚,而有人当大队领导的孙、田两家则可以胡作非为;二是《一对恩爱夫妻》,讲述了山民纯朴的悲剧:妻子被公社书记糟蹋以后不敢反抗,为了不再受辱,只好以毁容来保护自己。在这样的故事中,冷漠、麻木的“官僚主义”似乎已经不再是暴露的焦点,那些“土皇帝”的胡作非为已经无异于恶霸、土匪。而到了1987年的长篇小说《浮躁》中,虽然作家写了土地分包以后,“土皇帝”田家、巩家的权势好像有所减弱,“关着门当‘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其实不尽然。他们仍然可以到处伸手,为所欲为,虽然在彼此的倾轧中两败俱伤,可到头来“田家还是田家,巩家还是巩家”。《浮躁》写出了乡村政治斗争常常表现为家族斗争,在当代乡村政治小说中相当典型。
刘震云一直是乡村专制政治的无情嘲讽者与批判者。他的中篇小说《头人》讲述了一个颇有荒诞意味的乡村故事:第一任村长单凭乡公所伙夫的指派就走马上任了,他临死指定自己的儿子继续当村长,正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家长制”传统。但也从此种下了与仇家冤冤相报的祸根。时代在变迁,可上级指定支书的习惯一直没变。变的只是头人的享受。乡村政治的荒唐因此暴露无遗。到了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中,通过孙、李两家为争夺村长的位置而结仇、而不择手段地冤冤相报,其实说到底也就是为了“做人就得做人头,可以天天吃‘夜草’”的故事,入木三分地写出了乡村政治的残酷、猥琐与可笑、可怜。
周大新也以相当冷峻的笔锋剖析了普通人的政治情结,在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中,廖家祖辈的遗嘱就是“要想法子做官!——人世上做啥都不如做官……人只要做了官……世上的福就都能享了”!廖怀宝做了官,廖家在镇上的声望就高起来了。为了保住官位,他先是咬牙牺牲了爱情,接着牺牲了老婆,将老婆拱手让给了上司,最后与省委书记秘书的妹妹结合;为了保住官位,他知道“尽早摸准上级的意图”最重要,只要上级高兴,“农民不高兴有什么不得了的?”因为“胆小怕事是农民的本性,很少人敢出头公开指出当官的不对”。另一方面,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上,“搞政治阶下囚和座上客只差一步,一步!”遇到风浪了,要文过饰非、委过于人、借以自保。这样费尽心机,他才得以在“向上的台阶”上步步高升。小说中有一段“右派”对于政界大局、领袖谋略的分析,读来耐人寻味:廖怀宝不懂政界大局,并因此而暗暗惭愧。而后来他知道了,更有了政治的眼光,做人却更不地道了!
阎连科则常常写那些想当官也当不上的可怜人:中篇小说《两程故里》聚焦于宋代大儒程颢、程颐的后代之间争夺村长的较量,既有为祖上争气的责任感,也有挣了钱以后的浮躁情绪作祟。而将乡村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置于二程后代之间展开,也写出了人心不古的时代感和传统道德的不堪一击。可小说中对程天青发财以后一心想当权、却常常因为急躁、谋划不够而顾此失彼的描写,以及对于古柏低沉叹息的不祥点染,都写活了一个农民对于权力的孜孜以求与修炼不到火候。此后,在中篇小说《瑶沟的日头》、《瑶沟人的梦》、《乡间故事》中,作家深刻写出了瑶沟人的苦闷:因为村里没人当官而感到窝囊,与邻村打过上百次官司却没赢过一场,因为“自古就是小二做官,邻居有福”,所以为了集全村之力供一个人读书、以便日后出一个“人物头”而不惜闹事、凑钱、娶副乡长的丑女、或者甚至卖身!可到头来,无论怎么全力以赴,结局总是在阴差阳错中落空。小说一面将瑶沟人的窝囊、不满、想方设法写到了绞尽脑汁的极点,一面也通过他们唱的小曲、他们心中所想揭示了普通农民的当官梦想、政治野心:“别小瞧我过河一个兵∕要让天下不太平∕要叫太阳没有光∕要叫月亮蒙黑影∕杀车吃,马赶走炮∕小兵也要坐阵中”!一旦如愿以偿,“山归我,树归我,鸟归我。我走路,人就让到道边。那儿的一切,都在我指缝中夹捏……”看,在窝囊的另一面是狂放,在自卑的另一面是自大,在费尽心机的另一面是为所欲为!普通农民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政客、土匪、流氓!
毕飞宇的中篇小说《玉米》成功刻画了一个乡村少女的形象:她是村支书的女儿,心性好强,“她绝对不能答应谁家比自家过得强”。她在管教妹妹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权力的滋味:“权力就是在别人听话的时候产生的,又通过要求别人听话而显示出来。”父亲因为破坏军婚而倒霉以后,她把东山再起的希望寄托于男友在部队提干上;在男友与她分手以后,她就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了嫁给有权者上,因为她坚信:“只要男人有了权,她玉米的一家还可以从头再来……”一个乡村少女对于权势的孜孜以求,以及乡村日常生活与权势息息相关的微妙玄机,都在此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中国的人格修养不是从来讲“正大光明”、“浩然正气”吗?可为什么一遭遇“官本位”就触目皆是不择手段的下作与卑躬屈膝的奴性?由“礼教”规定的尊卑差别与权力带来的诸多特权自古以来就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一直到已经改革开放达三十年后的今天,时代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变了,可“官本位”的诸多弊端依然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上个世纪初,辜鸿铭就指出:“在欧洲,政治成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孔子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教。”这话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思:当政治成为一种宗教时,一切的谋略、手段、交易、骗局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并且畅行无阻了。
乡村能人的权术刻画
中国传统的政治,是很讲究权术的,夺权也好,保权也罢,都离不了“权术”二字。韩非子所谓“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就强调了“术”的重要与神秘(秘不示人)。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韩非子的批判”一章中概括了韩非子论“术”的几个要点:“(一)权势不可假人;(二)深藏不露;(三)把人当成坏蛋;(四)毁坏一切伦理价值;(五)励行愚民政策;(六)罚须严峻,赏须审慎;(七)遇必要时不择手段。”《韩非子》之后,还有赵蕤的《反经》、汪辉祖的《官经》、李宗吾的《厚黑学》这样一些研究“帝王术”、“为官之道”的奇书,加上“二十四史”中记录的那些帝王、权臣的谋略,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相当阴暗、却一直为人关注、揣摩的部分。我们不仅可以从历代暴君、权臣的事迹中看到这些权术的运用,还可以从许多社会矛盾中、从底层人的明争暗斗中看出这些权术的诡异莫测、根深蒂固。正因为那些权术具有相当阴暗、恶毒的特质,就使得乡村政治也常常充满了阴险、狡诈、狠毒的乌烟瘴气。这样的乌烟瘴气正是封建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不幸的是,这样的乌烟瘴气一直到今天作家的笔下,也依然那么触目惊心。
1986年,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发表。其中的四爷爷赵炳是个很不一般的“毒人”、“贵人”。他聪明过人,喜读《论语》,深谙传统文化;他长袖善舞,在政治风浪中能进能退,出手不凡,因此成为当地的一霸,可他又常常是以德高望重的尊者、长者的面孔出现。他得政治风云之助,打击隋家、李家,却并不出头露面,而是老谋深算于幕后;他危急中能急人救难,但也带有相当微妙的表演色彩。他还善于享受养尊处优的生活。他深知:“什么都在规矩里面。……背了规矩,就没有好结果。……镇上人都在规矩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自己的爪牙赵多多,他也知之甚深:“(他)遇事最下得手去,心倒是诚。可是他常常做过了头,破了规矩。我为这个常训导他,也没有多少用。不过有了一个赵多多,洼狸镇就少一些出规矩的人,也算天大的好事。亏只亏了赵多多一人,他注定没有好结果——他做事情太过。”由此可见他阅世的眼光非同一般,心计也深不可测。而他的预言后来也果然应验。在赵多多凌辱柔弱的含章时,他出面保护了含章,当了含章的“干爹”;他似乎是在行善举,可到头来还是以“干爹”的身份长期霸占了含章。他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我明白我已破了规矩,这个事情上不会有好结果。……我已经‘太过’。古人说‘治之于其未乱’,防在前边。看来这办不到了。我已经没法儿避灾。小章子,你想来做什么,就早些做吧。我知道我没有好结果,我这里等着了。”看,“一切他都知道,一切他都想在了前边”!他的料事如神、高深莫测、恶贯满盈都使他成为一个相当有典型性的“土皇帝”形象。在中国的许多村庄都有这样能够一手遮天的“能人”、“厉害人”。
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以遒劲的笔刻画了一个“土皇帝”的发迹史:比起那些当官就为了“吃夜草”的“土皇帝”,呼天成的人生境界显然高出了许多——他有政治的抱负,他的原则是:“于呼家堡有利的事我干”,这意味着他既是一个“家长”,也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集体主义者。他知道:“在平原的乡野,在这样一个村落里,真正的统治并不是靠权力来维持的。……要想干出第一流的效果,就必须奠定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是靠智慧来完成的。”那是怎样的智慧呢?是从治理偷窃开始的严厉,可那严厉又是与心计、收买、弄虚作假紧密相连的;是在破除传统的风俗时通过孤注一掷、显示自己“不信邪”的魄力而赢得了大家的敬畏的;是在时刻警惕自己失手的坚韧不拔中战胜了“另一个自己”的;是能够作出必要的奉献与牺牲“买下全村人的心”的;是通过开会、建“英雄榜”给全村人套上绳索进一步树立起自己的威信的……小说对于他通过经营“人场”织起自己关系网的刻画相当有人性的深度: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几手同时抓——一方面对于联络领导投资,他不惜老本,“甚至不要求回报”;另一方面他留心培养身边的人才,而且不徇私情、任人唯能,使他们步步高升,为自己效力;在打开经商局面的拼搏中,他也出手不凡,显示了他“超常办事”的能力。他善于把向上级领导的情感投资与经商完美地结合起来。他的能耐大到可以为了呼家堡的利益通过一个电话改变市委的重要人事决定。《羊的门》因此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同一般的“土皇帝”的形象:他有权谋、有心计、有手段,也有眼光、有毅力、有公信力(这后一方面,显然是许多贪婪、自私的“土皇帝”所不具备的)。他因此不同于那些一心为私的恶霸。也惟其如此,这部小说对于乡村政治谋略的深入剖析才格外发人深思。小说还通过呼天成命老曹杀光全村的狗、他死以后全村人学狗叫的情节写出了呼天成的狠气。他为了反对老娘信教甚至不惜缺席老娘的追悼会的情节也突出了他的厉害、心狠。作家力图写出呼天成的深不可测,进而写出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是如何养育出了呼天成的深不可测的:那里,“人的骨头是软的,气却是硬的”;那里,“一直是铁板一块”;那里,“只要你敢想,只要你用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有时候,你必须超常办事,你必须出人意料”,直至可以异想天开创造出逼着猫吃生姜的“奇迹”!《羊的门》因此在为数众多的乡村政治小说中独树一帜。
蒋子龙曾经在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中成功塑造了一个农民企业家武耕新的形象。他经过苦苦思索,从地主赵国璞的发家史中悟到了改变故乡贫困面貌的启迪,走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的道路。他大胆开展“专业承包、联产到户”,起用能人跑业务,改变了贫困的面貌。他的奋斗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和来自上面的政治压力,然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部小说是根据当年名噪一时的大邱庄改革的事迹写成的。到了2008年,作家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剖析了一个农民能人发财致富以后的“帝国情结”。尽管作家声言此作“写的不是大邱庄”,但其中主人公的性格和好些情节都与大邱庄当家人禹作敏的故事相合。这个郭存先胆大、能干,“天生爱折腾”,“从骨子里崇尚力量、胆魄和勇毅”;“能煽呼,会造势,顶上边,骂下边,敢发着狠往疼里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确有当皇上的那股狠劲”,在村里成为说一不二的“土皇上”。“对给他溜须拍马的人,他都是先用霹雳手段后显菩萨心肠,对待得罪过他或对他不那么百依百顺的人,他就只有霹雳手段,外加蛇蝎心肠。”在致富以后,“他最需要的是有足以能驾驭局面的权力。”为此,他豢养了一批打手,还有了自己的“村警”,而他成功以后官员、银行、市场、专家、能人、女人都围着他转,也使他得意忘形,“话越说越大,口气越来越大,架子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大……”,甚至“凡副部级以下的干部来了,他一概不接见”。甚至建成样式堪比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人才园”、比颐和园牌楼还高的“中国第一牌楼”、比北海公园的“九龙壁”气派还大的“世界第一”“九龙壁”!那野心,那霸气,是他骨子里就有的,又何尝不是追捧的媒体、人群骄宠出来的!小说因此深刻揭示了造就“土皇帝”的现实土壤。一直到他指使手下人打人至死,闹出人命,他还煽动村人拘禁执法警察、不自量力地企图武装抵抗国家机器!他的狂妄可谓登峰造极。对此,作家指出:“在郭存先眼里,郭家店就是他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他在里面称王称霸,还不断向外扩张,甚至竖立雕塑把自己当‘皇上’供着,这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不仅郭存先,在那个时代,许多分量差不多的人都在做帝国梦,包括那些西装革履、留洋回来骨子里照样是农民的企业家,他们都想把自己搞成一个独立王国。报载,某地一幢20层的堂皇大楼,只有90人在办公,一层楼里最多四五个人。是什么情结让4个人占一层楼,90个人盖一栋20层的大楼?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我解释不了,我认为这就是‘土皇上’情结。’”正所谓:“一阔脸就变”,“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样的思考与报告文学作家贾鲁生在1988年发现的“商品经济封建化”正好呼应:“一些农民企业家的素质比较低……把大量资金投放消费市场,造房子买地修坟纳妾,于是倒退到地主式的消费方式。……这里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不排除商品经济封建化的问题。”封建的消费方式、封建的专制作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死灰复燃实在是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而郭存先的张狂无忌也与赵炳的伪善、呼天成的谨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为当代文学中的“土皇帝”形象系列增添了新的代表。这些“土皇帝”形象的生动、深刻,远非从前那些小说中的地主形象可比。
而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则以平实的风格写出了当代乡村政治风云在日常生活中的突变。对此,韩石山曾有评论道:“整个村子喧闹着臊腥味十足的乡村欲望:食欲、贪欲、情欲,还有更饱满的政治情结。人人都在表演,人人都在施计,一计套出一计,一‘秀’衬着一‘秀’。本该是剑拔弩张,狰狞凌厉的,因被炊烟缭绕的生活气息裹挟着,被插科打诨的民间智慧充斥着,又时时乒乓出彩,让你乐不可支,差不多快被这一层面的阅读愉悦淹没。直到末后,‘政治’这个更大的主题才挣出了表面的纷杂,有文化、有背景、有象征,几乎是揭秘式的呈现在你的眼前。原来,那个草地上吟诗的光棍羊倌是‘卧龙先生’,善解人意俯首听命的团支部书记才是最后通吃的枭雄。前村长、治保主任、会计、学校校长、村医,甚至二流子、小偷、弱势的村民,个个都似《三国演义》里的某个人物,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自己的行事风格,有自己的计谋套数,都是一张摁紧了未揭的牌,都是大局中的变数。”这里,是一群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农民谋略者!小说中的多处细节都耐人寻味:庆书热衷于研究林彪,因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庆书想当村委主任。”字里行间,已有阴谋的深意了;那个引起工人们公愤的鞋厂厂长“做梦都想当政协委员”,为此“把小老婆都捐给厅长了”,可谓无耻之尤;居心叵测的牛乡长擅长“把县领导的指示精神与王寨乡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一条有王寨乡特色的道路,那‘特色’主要体现在数字上,体现在比例上”,也充满讽刺意味;他向小说主人公孔繁花传授“在官场混,那是隔着布袋买猫啊。公猫母猫,黑猫白猫,花猫黄猫,狸猫波斯猫,你看不清的。所以要小心,不要多嘴”的“秘诀”,还有那副“上台去战战兢兢,下台来轻轻松松”的对联也相当深入地道出了为官的不易;孔繁花“之所以带着殿军在村里东游西逛,就是想让别人知道,殿军赚大钱了,多得花不完了,所以她肯定是个清官,不会贪污村里一分钱。别人要是知道殿军其实是个穷光蛋,她就完蛋了。她就是比包青天还清官,别人也会怀疑她是个贪官。”其处心积虑,也足以看出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为官如履薄冰的心态;“政策决定方向,屁股决定立场”的官场要诀也将为官之道的“灵活”揭示得淋漓尽致;还有“通常情况下,村里面最恨的就是乡干部,乡干部在他们眼里没一个好东西,靠他娘的,就知道向村里要这个要那个。干群之间总是隔辈亲:农民不相信乡干部却相信县领导;乡干部不相信县领导却相信市领导;县里的干部呢,自然也不相信市领导,他们相信的是省领导。菩萨的经都是好经,只是被方丈给念坏了”的描写也写出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十分普遍的一种荒唐现象:“方丈”为什么常常念坏了经?老百姓为什么常常不相信身边的官员,而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石榴树上结樱桃》不似《古船》、《羊的门》、《农民帝国》那样凸显乡村能人的典型恶行,而是还原了普通人争权夺利的心术、手段,这样,也就别出心裁写出了政治权谋在乡村的深厚土壤。
在中国,政治不仅是政治家的权谋,还是乡村能人的运筹帷幄、各级官员的博弈较量。在中国,政治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暗地里谋划、使劲的。那谋划与使劲也常常是与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讲道德紧密相联的。因此,自古以来,中国才有了那么多的宫廷政变、武装暴动、政治交易、官场浮沉。也因此,才有了专制制度早已寿终正寝,可专制的阴魂依然飘荡,皇冠和玉玺已进入了博物馆,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依然在自己的“王国”里称王称霸、为所欲为的奇观。中国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尖锐纠结,与此显然有关。现代民主制度的公平、公开原则常常难以在乡村政治中扎下根来,也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在当代小说中的这些“土皇帝”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暴君与土匪的习气,从而发现普遍存在于暴君、土匪和“土皇帝”、无耻小人中的那些劣根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富不仁”、“无毒不丈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兵行诡道”、“兵不厌诈”、“出奇制胜”,“不按规矩出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是这些流传甚广、尽人皆知的狡狯心术,还有那些宫廷政变、武装暴动、政治交易、官场浮沉的历史故事为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提供了统治的“秘诀”。
民变的警钟
乡村政治的种种弊端积重难返,于是,村民的积怨就常常如火山喷发一般释放出可怕的能量。在当代作家笔下,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个民变的故事——
1983年,楚良在短篇小说《抢劫即将发生》中就讲述了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偶然制止了“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抢劫”的故事,虽然立足点是赞赏新上任的公社副书记余维汉的责任感和处事干练,但已经透露出1980年代初农民对“开后门”垄断化肥的强烈不满。到了1986年初,矫健的中篇小说《天良》则以悲怆的风格正面触及了忍无可忍的农民孤注一掷、反抗“土皇帝”的主题:天良因为反抗陋俗而得罪了“土皇帝”,并被卷入了乡村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在绝望中铤而走险,开枪击毙了横行乡里的“土皇帝”。小说据说是根据生活中的一件真实案件写成。作家在讲述这个悲剧时着力渲染了天良祖祖辈辈脑后长有反骨、并因此而屡屡遭殃的命运感,从而将天良的愤怒写出了某种历史感与宿命感。“祖先的反抗精神在沸腾!”是作品中令人过目不忘的点睛之笔,而天良最后单枪匹马反抗的死亡结局也又一次证明了势单力孤的徒劳——虽然干掉了两个恶人,可那个逃脱了惩罚的恶人不是反而高升了吗?同年,刘震云的短篇小说《乡村变奏》中也有一则“暴动”,讲述了平津县发生的一次民变:县领导强迫农民种棉花,收购时却造成了积压。许多农民排了七天队还卖不上,连牲口也冻死了。忍无可忍中,他们去了省委门前点燃了一辆运棉车示威。事情闹大了,县领导被撤。小说写到暴动的发起者从小无法无天,为暴动游说每家出一块钱的串联。他的体会是:“出谋划策,组织群众,掌握时机,不比‘秋收起义’容易!”那口吻,颇有点非比寻常的自得,也不乏弦外之音。此篇虽然笔墨简单,但也是新时期文坛上较早触及民变主题的作品。1987年,郑万隆在小说《古道》中也讲述了一个当年的支前农伕常六老汉为卖棉苦苦等了十二天,而收购站站长却大开后门,刁难棉农,气得常六老汉一怒之下烧掉了棉花的悲剧。到了1988年,莫言发表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小说也是根据1986年山东苍山县的一起民变写成。农民们响应县政府号召种蒜薹并获得了丰收,却因政府任意征税、压低收购价格而损失惨重。加上县长、乡党委书记的麻木无情终于激怒了大家,人们自发包围了乡政府,打砸一气,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小说并没有正面描绘暴动的过程,而是通过几个参与了闹事的农民被捕以后的遭遇写出了他们的悲愤与绝望:“反正是我也活够了……”“我窝囊了半辈子,窝囊够了!”“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我求你们枪毙我!”小说通过辩护人之口道出了1980年代已经出现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农村经济改革带给农民的好处,正在逐步被蚕食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本的原因,在于天堂县昏聩的政治!”“这些干部,是社会主义肌体上的封建寄生虫!所以,我认为,被告人高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是农民觉醒的进步表现,并不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最后,闹事的农民被捕,而县政府领导在受到处分后调任他职的结局也令人长叹。
上述发表于1980年代的作品足以表明:早在1980年代,贪官污吏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与法制的缺失、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已经导致了悲剧的层出不穷。民变是对乡村专制政治的抗议。然而,到了1997年,仍然产生了鬼子的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此篇在刻画1990年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愤怒情绪方面依然很有震撼力:晓雷有一双“随时都会出事的眼睛”,他自尊,因为父亲的工资被挪用而打印致乡下全体教师的公开信,动员闹事,吓得他的父亲不得不下跪阻拦。他不甘被老板无端剥削,一怒之下,杀死了老板;而他自己也终于被另一个老板暗害。作家写道:“如今的青年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且常常干得叫人不敢想象。”小说题目耐人寻味:“一条曾经在岁月里流水汹涌的河”为什么这几年竟然干涸了?到了2005年,贾平凹也在长篇小说《秦腔》中写到一起因为农民抗税而被抓,导致群众冲击乡政府的风波,结果是警察赶来,平息了骚乱。
这些民变的故事大多写得比较节制,即便是《天堂蒜薹之歌》对于那场大规模民变的描写也是将笔墨主要集中于当事人出事后的逃亡上,但尽管如此,仍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那无数“逼上梁山”的故事,想到那些讲述农民革命的当代小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梁斌的《红旗谱》、冯德英的《苦菜花》、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黎汝清的《万山红遍》……虽然,那些记录现代农民革命的作品与上述反映当代民变的作品在主题上、风格上及历史背景上有诸多不同,但在凸现中国农民敢于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精神气质上,却十分相近。中国农民一向以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著称于世,同时也以敢于反抗、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人熟知。这,也是中国民族性的又一重深刻矛盾所在。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关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告其实也广为人知,可不知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的昏君、佞臣、政客、土匪、“土皇帝”在祸害百姓的绝路上狂奔!这,可算是中国政治的又一大奇观吧。
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事经同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两年后,李昌平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进一步推动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中国的乡村政治改革再一次引人瞩目。而他指出的那些“土皇帝”“坑农”、“害农”的严重问题,其实早已出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矫健、刘震云、郑万隆、莫言的小说,还有一批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如祖慰1980年发表的《啊!父老兄弟》、乔迈1984年发表的《希望在燃烧》、麦天枢、张瑜发表于1987年的《土地与土皇帝》、霍达发表于1989年的《民以食为天》等等,一直到1998年卢跃刚发表的《大国寡民》、陈桂棣、春桃2004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由此可见,在多元化的时代,文学仍然保持了关怀底层、针砭时弊的批判锋芒,并为我们从文学出发探讨民族性提供了生动、深刻的范例。剩下的问题是:中国的乡村政治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告别专制文化的历史阴影、直至实现民主化?那已经被证明是一条很不平坦的道路……
[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韩非子.韩非子·难三[M].
[3]郭沫若.十批判书[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蒋子龙.我写的不是大邱庄[N].京华时报,2008-10-27.
[5]发展商品经济,要有理念的觉醒[J].新观察,1988,(19).
[6]韩石山.乡村政治游戏版:《石榴树上结樱桃》[EB/OL].http:∥ 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7721_201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