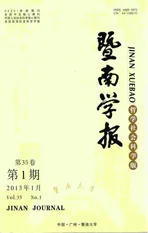怀旧·成长·发展:关于“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
2013-11-14贺仲明
贺仲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与前几代作家比较起来,出生于1970年之后(俗称“70后”。以下沿用此简称)的这代作家对乡村的书写大大地减少了,他们的创作中,以城市和自我生活为背景的明显更多。但是,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数量虽然不多,却也呈现出它们独特的个性。其中既包括这一代作家个性化的叙述视野、叙述方式和叙事态度,也包括他们独立的思想和审美取向,还曲折地隐含着曾经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对他们的影响。无论是就创作本身看,还是从乡土小说发展历史看,它们的意义都不可忽略,值得认真而深入地探究。
一、怀 旧
阅读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感受最深的是其强烈的怀旧色彩。这一特点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它表现在其创作题材颇多对往日生活的回忆,而这些回忆的落脚点多在对乡村伦理的怀恋上。虽然按年龄来说,即使是出生于1970年的作家,在今天也才不过40岁出头,在他们于1990年代末或新世纪初开始创作时则都不过30岁左右,还远远不到怀旧的年龄,但是,他们所描画的乡土世界却大多是1980年代之前(也就是乡村变革之前)的乡村,较之直接描画现实乡村的要突出得多。
比如刘玉栋的几乎所有乡土小说都是执着于乡村回忆,《我们分到了土地》、《给马兰姑姑押车》是代表作品;鲁敏的绝大多数作品以对故乡生活的回忆为背景构成了“东坝系列”;魏微虽然写作范围要广一些,但其重要作品《大老郑的女人》、《流年》等也是关注乡村往事;徐则臣的作品分为“京漂”和“花街”两个系列,后者的内容都是乡村往事追忆。女作家魏微曾经表达过自己较多地沉湎于往事追忆的原因:“我想记述的是那些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它们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它们具有某种强大的真实……它们曾经和生命共浮沉,生命消亡了,它们脱离了出来,附身于新的生命,重新开始。”显然,魏微所表达的不只是她个人,而是他们这一代许多作家的共同心态。
与怀旧题材相一致,70后作家书写的昔日乡村生活主要不在物质层面,而是在伦理层面,传达出的不是当时的现实状况,而是他们对往昔乡村伦理世界的怀恋和温情感受。如刘玉栋的乡土小说集《我们分到了土地》,整个都是回忆式书写,充满了对往昔乡村世界的眷恋以及对乡村美好情感的追忆。同样,徐则臣的《花街》等作品,以充满诗意的笔法书写花街上的妓女生活,甚至乱伦之恋,赋予了它们以美好的爱情色彩,体现了理解和赞美的态度。他的《最后一个猎人》、《失声》等作品,更是充分展现乡村的仁厚道德,表现出对乡村传统伦理态度的赞美之情。魏微的《流年》、《大老郑的女人》、《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等作品,也以自己的方式展现了独特的乡村理想和乡村道德,同情和理解中不无认同态度。其中,《流年》是一首充满着爱和温情的乡村怀旧赞歌,作品中的故乡是充溢着梦想的世外桃源。《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中的乡村守望者陈平子,固守传统生活方式,抗拒生活的变迁。虽然那个城市女孩的所谓“爱情”本质上是虚幻和短暂的,或者说,它只能满足乡村回忆者的一个遥远的梦想而已,但叙述者显然对他身上寄托着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某些留恋。鲁敏的“东坝系列”作品,也基本上是以温情和怀恋为叙述基调,通过众多普通百姓的日常情感生活,“表达出以美德为标志,以宽厚为底色,以和谐为主调的人间至善。善,是这些小说要共同表达的核心主题。”
其二,它体现在作家们书写现实和回忆世界时强烈的情感对比上。70后乡土作家当然不只是写过去,他们也会触及到现实乡村生活。只是在书写现实时,他们普遍表现的是强烈的拒绝和批判态度,与他们回忆类作品的叙述态度形成强烈对比。批判和怀恋态度差异的背后,隐藏的显然是对传统乡村文化“怀旧”的基本态度。
作家们的现实书写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叙述现实乡村世界的。70后作家直面现实的作品很少,李师东《福寿春》、张学东的《妙音山》、畀愚《田园诗》是其中不多的几部。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对乡村现实持激烈批判态度。如李师江的《福寿春》,展现现实乡村伦理的剧烈变化,父亲保持传统的伦理态度,拥有对土地的热爱之情,儿子则完全不一样,对土地和乡村生活充满拒绝和仇恨。叙述者的态度明确地站在父亲一面。而且,作品还借人物之口来批判现实:“如今人变得厉害了,一个个烂了心肝的胆子大胃口,恨不得把天咬下来吃。”(《福寿春》,第267页。)《妙音山》也一样。它以虚构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村庄人们生活的苦难,目的在于展现社会现实的病相,表达出对现实乡村世界的强烈批判。作品所写的表面上看似乎是天灾,实质上则是人祸— —一种物质利益欲刺激下人性私欲的膨胀,一种社会病态的毁灭性发展。《田园诗》则是一篇强烈反讽色彩的作品,它通过一个青年农民在城市文化诱惑下的堕落过程,表达对现实乡村的忧虑和否定情感,借之以表达对“远逝的田园”的追忆和怀恋(作者为作品所写的创作谈就题为“远逝的田园”)。
另一种方式则是“游子还乡”的叙述方式。这类作品侧重于叙述者自身感受的表达,很少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摹,但所蕴含的叙述态度却也都是对现实乡村的批判。徐则臣的《还乡记》,写的是远离故乡的“我”的一次回乡之旅。在叙述者看来,农村世界已经完全“礼崩乐坏”,成了堕落和罪恶的渊薮。畀愚的《田园诗》与之颇为类似,它对乡村现实面貌的描述更直接也更富象征色彩:“乡村就像养老院一样沐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却再也不是那些河滨与绿野。河滨大多已经干枯,绿野中到处沾满着尘土,远远看去就像一个个斑秃的脑袋,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而风中漫卷的也不再是泥土与稻草的气息,却是那些褪色残破的薄膜包装袋。”
无论是直接叙述现实,还是“游子还乡”作品,它们在批判现实之余,经常会将现实乡村与往昔乡村生活进行比照,传达出对往昔乡村的怀恋之情。《福寿春》、《田园诗》都有类似场景。最典型的则是李浩的《如归旅店》,它将梦想和追忆明确放置在昔日的乡村世界,直接对乡村现实表示拒绝和否定:“我有着自己的固执,我一想起家乡首先想到的是那棵老槐树,然后是我们家的老房子,如归旅店。”“我想的家乡只有那么小的一点儿,仿佛在我们家的房子之外,在这棵老槐树略远一点的地方便不再是家乡。”
其三,体现在叙述情感上的强烈感伤和抒情色彩,以及叙述方式上的诗化特征。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在艺术表现上颇多共同特点。一是强烈的感伤和抒情气息。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们的回忆类作品上,这些作品大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儿童或少年视角叙述,在强烈的追忆性叙述中,融入了很强的怀旧情绪,个人青春的怀恋和对往事的感伤融为一体,形成了细腻委婉的抒情风格,具有沉静中淡淡感伤的艺术效果。现实类作品同样具有较强的情绪化色彩,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它主要体现为激烈的现实批判背后内在精神的感伤和迷惘。这些作品不满现实、批判现实,但又都蕴含无路可走的迷惘,怀旧不过是这种迷惘情绪的表现方式之一。李浩的《如归旅店》典型地充满着强烈的迷茫、怅惘和自我怀疑气息。徐则臣、刘玉栋、魏微的作品也都具有类似艺术特点。二是诗化的叙述方式。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回忆类作品中,叙述者从儿童的眼光来打量乡村的习俗风情,赋予个人情感色彩的同时,也习惯性地采用细腻的诗化的叙述,个人成长感受与乡村的童话化美丽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与现实具有一定差异的诗意化特征。如徐则臣的“花街系列”、鲁敏的“东坝系列”,以及刘玉栋《我们分到了土地》、魏微《流年》等作品,它们所描绘的乡村世界都呈现类似的特征。
二、成 长
厨川白村曾经说过:“一个人疲倦于都市生活后,不由对幼少年时的田园风光或纯朴的生活,兴起怀念和向往之情,是属于一种‘思乡病’”。在这个方面说,70 后作家耽于怀旧的原因,既可以看做作为乡村游子的乡土作家的一种精神共像,又与他们独特的生活经验有密切关系。
这首先与中国乡土作家的身份和创作传统有关。由于农村的生活和文化环境等原因,中国的乡土小说作家很少有真正的农民,他们都是有过或长或短的乡村经历,然后都离开了乡村,再开始乡村书写。正像鲁迅当年概括1920年代的乡土作家为“侨寓文学”一样,乡土作家们虽然离开了乡村,但他们的心灵与乡村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其乡村书写中也自然折射出这种情感关系。无论是站在现代文明立场上对乡村的批判性否定,还是借乡村文化表达出现代文明批判的文化守望者,以及乡村现实生活的写实者,都不同程度地蕴含有挥之不去的乡村眷恋,以及对乡村的美好想象(包括像鲁迅这样致力于批判乡村国民性、开创了阿Q文学典型的作家,也曾经营造出《故乡》这样的诗化世界)。乡村文明的宁静自然,始终是远离故乡的游子心灵的最大慰藉和精神回归之地,怀乡,是中国乡土文学一个始终的母题。
其次,它与近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异有关。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乡村世界尽管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变革和政权更替,也有贫穷与富裕的不同程度差别,但乡村的文化形态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乡村伦理也始终以稳定的温馨面貌存在。这使那些离开乡村的游子们在提起笔来描画乡村时困难不是太大,他们记忆中所熟悉的生产劳作方式、生活风习与现实没有什么大的差池,他们完全可以沿着记忆的惯性来想象和书写现实中的乡村生活。但是,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后有了改变。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缓慢地改变(或者说恢复)乡村的土地拥有和生产劳作方式,与之伴随的是乡村逐渐脱离贫穷,与城市生活距离的一步步靠近,现代生活方式开始逐渐地影响和极大地改变乡村社会。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实施,大批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打工,城市生活观念直接而强烈地冲击到乡村社会,乡村传统伦理迅速坍塌。短短的几年间,乡村的文化面貌与传统有了实质型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代后的乡土小说普遍升起浓郁的怀旧情绪。这可以看作是面临毁灭命运的乡村文化一种自然的反应,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乡土小说作家可以看作是乡土文化的某种代言者和守望者。70后作家创作的怀旧色彩背后自然也蕴含着这种时代文化变迁的因素。然而,独特的代际经历,使70后作家拥有自己与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决定他们的创作具有自己的显著个性。
与前辈作家相比,70年后作家不再拥有深刻而牢固的传统乡村记忆。对于他们来说,乡村记忆是不稳定的,是模糊的。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刚好是乡村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也可以说,他们的生活直接而清晰地感受到乡村的变化,他们就是变化中的一员。他们拥有最初乡村记忆的年代是1970和1980年代,那是传统的、还没有很大变化的乡村(至少是在伦理文化上),但是,当他们长大以后,重新回(来)到乡村时,面临的已经是另一种乡村,是与他们的记忆和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乡村。它或者已经开始变得繁华,但肯定不再有传统的伦理景象,不再拥有传统生活方式下的缓慢、宁静和温情。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情感角度,这样的乡村都是作家们不熟悉和不习惯的。于是,作家们的乡村记忆变成了脱节和不完整的。他们的童年或少年记忆与成年后的现实乡村形成了尖锐而巨大的反差,决定了他们心灵中的乡村世界不可能是完整和稳定的。乡村的变迁,记忆的不稳定,既使他们受到的乡村文化影响不是那么深刻,也使他们在书写乡村时,不可能那么轻车熟路地进入乡村世界,对乡村现实生活简单地作出描画。
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回忆,只能寻找他们记忆中的乡村世界。而在他们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以及与现实之间反差最大的,无疑是乡村的伦理世界。伴随着他们童年记忆的乡村生活本身就含有温馨的因素,更何况是在这一文化严重变异的背景之下。因此,他们敏锐地感受着乡村的伦理变化,为之触动,并将笔触集中于此,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一点,李骏虎的表述很有代表性:“这几年,可能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回乡让我魂魄有动,我对乡土的传统情怀越来越珍重了,那来自苏北平原的贫瘠、圆通、谦卑 、悲悯,那么弱小又那么宽大,如影随形,让我无法摆脱……”“每次回乡,一路上乡村的土地就感觉到非常踏实。从村口步行回家,走在村巷里与晒太阳的老汉、抱娃娃的妇女简单打个招呼,就能给我一种力量,心里特别温暖。为什么我要把乡村写得那么诗意、那么美好?是因为在我的心里,乡村就是一个精神归宿。”
70后独特的乡村生活记忆和时代文化特征,除了赋予他们创作题材上的个性,还给予他们创作特征上的显著影响,就是将乡村主题与成长主题相融会。因为他们的成长时代伴随着乡村的变迁,他们的乡村记忆中会自然伴随着他们的成长经验,融入他们的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而且,作为一种从青年时期开始的创作,他们文学发展的过程也是一种他们心灵和思想成长的过程,其中伴随着视野的不断拓展,思想的不断深化,对乡村生活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他们的乡村写作也是他们成长和发展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方面,赋予了70后作家们乡村书写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具体说,它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它提供了独特的审视乡村的方式。
这典型地体现在城乡对立的主题方面。由于乡村和城市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复杂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在乡土小说历史中,二者大多呈现对立的姿态。特别是在近年来乡村社会面临颓圮之际,文化的对立更造就了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同书写态度。70后乡土作家们并没有完全背离这一模式,他们的作品也多有对乡村伦理的怀恋和追忆,但是他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赋予了它一些新的内涵。
也许是源于他们与乡村文化关系不是那么紧密,他们能够更清晰地意识到传统的不完美,认识到过去是不可能真正回去的。所以,他们会经常陷入迷茫和矛盾之中,但不可能像贾平凹等前辈作家那样沉溺于传统追怀之中不能自拔,在城乡文化之间也没有那么截然的选择。他们的小说怀恋往昔的乡村伦理,但却不是对乡村无条件的眷顾和赞美,其中也对乡村的阴暗面有所揭示。同样,对于乡村现实伦理的颓败他们普遍持否定态度,但却并不因此而简单地否定整个城市文化。他们既有融入城市、与现实进行和解的努力,也有对城市文化的某些认同和追求。他们没有深厚的乡村牵系,也就免除了被文化束缚,成为乡村文化的殉葬者和挽歌作者的可能性。
正因为这样,70后作家们对乡村文化的态度不是单向度而是复杂多元的,他们既建构,同时也解构。比如李骏虎的《前面就是麦季》,通过农村姑娘秀娟以蕴藏着爱的内心世界,淡然对待身边的一切困扰,表达了对乡村诗意和美好的建构。李浩的《乡村诗人札记》,通过少年的视角写乡村教师的父亲,表达了对父亲一代人的批判态度,揭示了他们严肃外表背后的平庸和无能为力,对传统乡村文化予以解构。魏微的《异乡》则表达了对乡村与城市文化之间的两难。女主人公因为感觉自己难以融入城市,于是在怀乡之情的感召下回到故乡,试图找到心灵慰藉,但是她最终发现,自己也已经不适应乡村。对乡村怀恋的怀疑和拒绝,已经蕴含着更深的理性,显示了回到城市的新的可能性。
二、它提供了另一种表达乡村的方式。比较起前辈作家,70后乡土作家更少文化的沉重,因此,他们普遍选择更个人化的方式来看待和书写乡村。在他们的笔下,少了大的政治和文化追问,却多了个人经验的追忆,多了对乡村情趣的描述,更多纯粹审美的意味。比如徐则臣的《弃婴》、《奔马》、魏微的《流年》、刘玉栋的《给马兰姑姑押车》等作品,就都撇开了文化意识形态话语,完全立足于个体生活经历,从个人生命感受和情趣角度来展现生活的丰富色彩。
这种个人化的书写,自然会提供对事物理解的独特角度和方式。比如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写的是1980年代初的土地责任制,但其侧重点与一般的政治化书写完全不同,它是将乡村改革放在个人感受下来叙述。在作品中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眼睛看来,改革所分配的土地并没有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应有的欢欣和喜悦,而是死亡和悲痛。它凝结着的是自己个人生命的一个重要印记。再如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以少年怀旧的眼光,叙述了一个特殊的卖春妇女的生活和情态,既折射出时代伦理的变迁,也洋溢着成长小说特有的矛盾感。较之同类题材的传统写法,这种书写的态度更含混,更富个人性,却也更富生活的质感和本真色彩。
70年后作家乡村表达方式的特点还体现在叙述情感的表达上。情感本质上是个人的,但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主题下,它也容易被影响甚至被左右,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属品。70后作家较少意识形态愿望,其情感表现也更自然。较之前几代作家,70后作家们在情感表现上更直接坦率,更单纯,也更少顾虑和遮掩。他们的乡村怀恋融合着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岁月,他们的乡村书写也寄托着自己的人生感悟,因此,他们的感情中有感伤,有痛楚,有迷惘,有幻灭,但很少有虚假和造作,很少有为了某种政治或文化目的去伪饰自己,伪饰乡村的形象。所以,我们在70后乡土小说中感受到的情感也许会局促一些,但却更真切细致,更能够体会到作家的心灵和生命气息,感受到一种真实情感的流动。
三、发 展
当然,从总体来说,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成就还不够高,缺陷也比较明显。我以为,当前的70后作家乡土小说主要存在着这几方面的不足: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就是缺乏较大思想建构的作家和作品。也许是因为缺乏深刻而丰富的乡村经验,70后乡土作家似乎普遍没有形成独立而稳定的文化思想,没有将这种思想贯注到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大多数作家的创作还停留在对他们往日乡村记忆的书写基础上,缺乏对个人生活和感情的升华。因此,他们的作品虽然具有突出的优点,如感情真挚,强烈的个人成长色彩,以及别样的乡村认知方式。但也仅此而已。它们缺乏整体的文化高度,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也未具备更深远的关注,匮乏深厚的历史感。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对时代精神的揭示,也看不到个人之外的大的沉痛,没有大的历史含量和深的历史思考。从作家层面看,也普遍没有形成自己稳定而成熟的创作风格,更缺乏有显著个性思想的大作家。这一缺点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作体裁的选择。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多局限于中短篇小说,很少有内容和思想含量丰富的长篇小说。这自然也对他们的成就有所影响。
其次,缺乏在乡土小说这一领域耕耘的持续性。总览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其数量已经严重偏少,并且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作家正离开乡土生活领域,转到城市或情感题材上。这当然与现实环境有关,随着乡村社会的衰败,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乡村,作家与乡村的关系也越来越遥远。70后作家也一样。这种状况有现实背景,但从乡土小说发展来说却绝对是一个损失。而且从文学来说,这种状况也存在较大的不足。因为作为一个正处于转型期的乡土国家,中国乡村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很值得作家们书写和记取。对于70后作家来说,这种放弃也许意味着某些失职,也意味着机会的失去。
70后作家还年轻,他们的创作路途还很长,他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乡土小说的未来。我以为,对于70后乡土小说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乡土小说这一领域上坚持。正如前所述,在这么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乡土小说创作是有丰富价值的;而且,70后作家的乡村经验虽然有所匮乏,但毕竟有自己的记忆和真实感受,较之比他们更年轻的80后、90后作家,他们的乡村经验算很丰富了。他们若能真正赋予乡村书写以自己的独特经验和个性,从中挖掘出更丰富的内涵,相信能够为乡土小说历史书写上自己浓彩重墨的一笔。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作家们艰难的精神持守,需要对乡土责任的坚持,以及拥有对文学的真正热爱。因为在商业化的时代,写乡村是很难赢得市场的,稍有懈怠,将很快被市场、欲望等多种力量所裹挟,成为乡村梦想的背叛者。
当然,这中间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写的问题。即作家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乡村记忆,如何对既有的创作进行超越和升华。对此,已经有批评家有所针砭,认为70后作家迫切需要深化自己与乡村的关系,强化自己的乡村生活积累。但我的看法不大一样。我以为,70后这种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创作有一定的必然性。社会的发展,使他们已经不可能拥有以往前辈作家那么丰富的乡村经验,也不可能拥有那么深厚的乡村感情和文化联系——正如前所述,这种情况既是缺陷也同时是优点。而且,在现有情况下,要求作家去“深入生活”,要求他们直面现实,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也有赶鸭子上架之嫌。70后作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循着前人的路径去写乡村,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有青年学者对魏微的评述很有道理,对这一代人的创作发展也有启迪意义:“中国传统乡土在这一代人的知识文化结构体系中的意义和价值,其实一直是被悬置的。因为一方面我们无法获得像前辈作家那样和乡土之间的血肉亲情,无法在身心两个方面与传统发生实质性的联系,……同时另一方面,深植于农业文化转型中的‘我’,无疑又时时置身于乡土贫穷、凋敝和丑陋的现状中。”
同时,对乡村的怀旧式书写并不一定就是局限。直面现实是一种乡土文学,书写记忆也是一种乡土文学,它们都可以写得很好,关键在于如何书写。从文学史上看,并不乏以怀旧为中心的作家。沈从文、福克纳是这样的作家,普鲁斯特更是这样的作家,他们赋予了自己的记忆以深厚而卓越的精神高度,抵达了文学的本质。
所以,70后作家们最需要的,也许对自己的记忆世界进行有效的超越,而不是局限和满足其中,不能停留在个人记忆基础上。这种超越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实现:其一,将自己的乡村记忆往细致和宽广两方面拓展,既渗透以更丰厚的个人生命感受,又使之与现实的乡土社会变迁相关联。正如有哲学家所分析的:“怀旧不仅是个人的焦虑,而且也是一种公众的担心,它揭示出现代性的种种矛盾,带有一种更大的政治意义。”作家可以在怀旧中寄托更真切的个人生命感受,也能够传达出更鲜活的现实时代色彩,使这种记忆书写既充满个人生命的印记,也成为时代和更广大大众(农民)命运的某种写照,融个人心灵史与时代精神嬗变史为一体;其二,赋予怀旧以更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理性深度。怀旧,不仅是“怀乡”,更应该是“思家”,是文化的反思与哲学的深入。换言之,由于作家们的怀旧记忆深连着乡土文化,因此,它很自然地会与更宽泛的文化命运相关联,在这种文化命运变迁的书写中,让个人怀旧得到文化的提升,进入文化反思的更高层面。正如有学者对“怀旧”有这样的阐释:“与平庸的、凡俗的、琐碎的现实生活相比,它带有浓烈的诗意化的倾向;与真实发生的、面面俱到的现实生活相比,它又经过了主体的选择和过滤,带有虚构和创造的意味。”怀旧不只是回望过去,它完全可以瞩望未来,可以成为参与现实和未来的重要方式。
这两个方面虽然还是以怀旧为中心,但是却完全可能拥有更博大深邃的开拓空间,能够在怀旧世界中包容更丰富的思想和精神内涵,可以使作家们的创作在不失去自己独特个性的同时,更有效地超越和发展自己。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70后作家的乡土书写也许能够给予文学史以更大的奉献,能够既呈现出他们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也提供出对这个时代崭新的思考。那也许会是乡土小说一次新的发展,甚至飞跃。
[1]魏微.流年·楔子.流年[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2]翟文铖.70后一代如何表述乡土——关于徐则臣的“故乡”系列小说[J].南方文坛,2012,(5).
[3]阎晶明.在“故乡”的画布上描摹“善”[J].小说评论,2008,(5).
[4]畀愚.远逝的田园[J].中篇小说选刊,2009,(3).
[5]厨川白村.西洋近代文艺思潮[M],陈晓南,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
[6]鲁敏.我是东坝的孩子[J].文艺报,2007-11-15.
[7]赵兴红.精神向度决定作品高度[J].文艺报,2012-08-10.
[8]简艾.魏微的小说创作——一个时代的早熟者[J].文艺报,2011-09-26.
[9](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M].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0]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