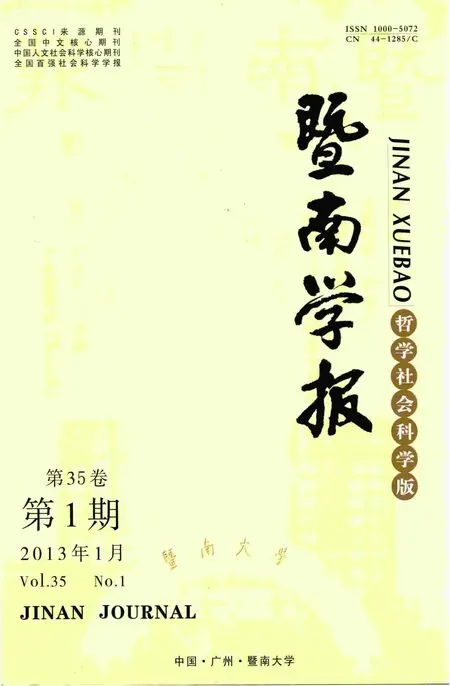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主持人语
2013-11-14栏目主持人
栏目主持人:樊 星
主持人语
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一大板块。从五四那一代人笔下破败的乡村到沈从文的《边城》那样的现代田园牧歌再到革命年代里《创业史》、《艳阳天》那样激励过两代人的浪漫梦想以及改革年代里那些反思农民悲剧命运的文学思潮、记录乡村变革的篇章,还有,那些怀旧、“寻根”的感伤情绪……乡村文学的嬗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缩影。一直到现代化进程加速的1990年代,与“三农”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相伴随的,是一批叙述乡村苦难的力作再度引发文坛的热议。在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乡村的苦难为什么一直没有终结?另一方面,今天的乡土文学创作在讲述农民的苦难时又产生了哪些新的研究课题?显然,乡土文学的研究有待于新的深化与拓新。如何揭示乡土文学的“当代性”,已经成为乡土文学研究的新课题。在我看来,当代文学(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有着明显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重要特质的。一方面,鲁迅式的绝望,沈从文、萧红式的感伤,周立波、柳青式的热烈在当代乡土文学中都有延伸,这延伸昭示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精神的血脉相连;另一方面,当代人面临的社会巨变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排解的困惑又催生了新的时代情绪——既感受到农民减去历史重负的欢欣又困惑于农民浮躁情绪产生的复杂效应(如贾平凹的《浮躁》、蒋子龙的《农民帝国》),既讴歌农民艰苦奋斗的可歌可泣又为那奋斗的一次次落空而喟然长叹(如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既强烈凸现出农民对于现实的愤怒却也看不到抗争的希望(如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一切都十分纠结。而这纠结中,就显示了一个时代的困惑: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不仅没有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反而明显加重了人类的生存负担与精神危机。多年来,中外思想家都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应对之策,可彼此矛盾的种种方案与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热闹氛围却使那些解决当代危机的方案常常显得顾此失彼、左支右绌。也许,这便是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吧。这样的困境在当代文学中也随处可见。作家们面对现实的重重矛盾也应对乏术,在作品中也只能揭示那些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的现实危机——这,便是当今文学的当代特质。
本期发表的贺仲明教授的论文《怀旧·成长·发展——关于“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一文就颇有新意。贺仲明教授一直致力于乡土文学的研究,此文探讨“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打开了乡土文学研究的新视野:“70后作家”如何既执着于对往昔乡村伦理的怀念和对乡村现状的批判,又因为“乡村的变迁,记忆的不稳定,既使他们受到的乡村文化影响不是那么深刻,也使他们在书写乡村时,不可能那么轻车熟路地进入乡村世界,对乡村现实生活简单地作出描画。”于是,新一代乡土文学作家的精神气质、他们的局限性就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笔者的《当代乡土政治小说新论》也揭示了当代乡土小说不同于现代乡土小说的一大看点,那就是乡土政治小说的格外引人注目。许多聚焦乡土政治痼疾的作品揭示了“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扭曲人性的阴暗图景,深入刻画了乡村能人权术心态,而这一切又导致了一批描写当代民变危机的作品的产生。这些新质,从文学的角度看令人欣喜,从现实的角度看却使人忧患。
一切还在发展中。中国的乡土文学源远流长也不断创新。相信新的乡土文学作品会记录下那些在巨变中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