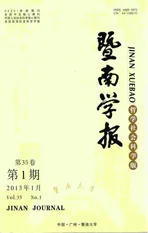方案与实践:清末中央管邮机构的设立与制度冲突
2013-11-14吴昱
吴 昱
(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广东广州 510632)
清代邮递机构本为“官民两分”的格局,自19世纪欧美新式邮政制度知识传播入华,至60年代中期海关试办邮政,再到1896年清廷正式举办邮政,其间过程颇经周折。《辛丑条约》签订后,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清廷推动了最后十年以官制改革为重点的新政,建立统一的中央管邮体系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但此项改革存在两个难题:一是现存的外人管邮,外籍海关税务司是否愿意将新式邮政事业交由清朝自管;二是体制合一,主管传统邮驿的兵部、民间的信局系统以及外国的客邮系统,如何在制度上合为一体,而归由新的中央管邮机构统筹管理。围绕这些问题,清末朝野官吏及相关人士展开了系列的讨论及制度的摸索。
清末驿递体系向新式邮政制度的转型,反映出官制改革引致的部院与督抚之间的权限分化及影响问题。关晓红的研究指出,在清末官制改革的方案中,“由于低估了改革的风险,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清廷最终实际采取了自上而下、先内后外的策略。”这一做法的最大问题,即是难以妥善解决中央部院与地方督抚的权限问题。就本文的问题而言,虽然新官制中以邮传部为管邮专职部门,而驿传事务亦划归其所管,但由于其与陆军部在管驿、裁驿职权上难以归于统一,是留是裁难以适从,故出现中央管邮部院未定政策、而直省督抚已有改驿裁驿之举。从这一事件中亦可发现,清末政情变化剧烈,仓促讨论与匆忙实施的官制改革,显然难以适应救时、救国、救民的需求,则更毋论在此改革过程中,各方还有利益考量、争夺和妥协,则这场改革到底成效几许,可想而知。
一、《江楚会奏三折》的邮政制度设计及其用意
清代的驿传体系虽历有更改,但总不出中央与直省两管理系统之外。为应对条约体制下代递信件责任而出现的海关邮政,则成为传统体制之外的新式制度萌芽。1896年大清邮政开办之外,新式邮政之安全便利与传统驿递的迟滞丢失形成鲜明对比,“官员们都派人来问怎样把奏折公文等往北京发送”,而总理衙门甚至说,“该衙门和北京市铁路矿务局,将取消旧时的官驿站的邮递办法,一切邮件,都将经由我们的邮局传递。”故“裁驿置邮”的构思与需要早已出现,惟新式邮政始终由外籍税务司所操办,虽然其亦隶属清朝职官体系,但其存在之起由却因中外战争所致,无论是从“夷夏之辨”、胜负优劣抑或逐渐萌发的民族主义,都很难令其被清代官场所认同。
虽然对新式邮政争议颇多,但其作用之显著则渐为朝臣所肯定。故在庚子之后,张之洞、刘坤一于《江楚会奏三折》中,即提出以“驿政局”取代“邮政局”之名、而行邮政局之实的做法。《江楚会奏三折》共有三折一片,其中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五(1901年7月20日)所上第三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中,“九曰推行邮政”,以外洋邮政与中国驿政相对应,似有暗指海关主办之邮政名目不正之意:“查外洋各国邮政,为筹款一大端,大率岁入皆银数千万两,而递信最速。中国驿站为耗财一大端,岁费约三百万两,而文报最迟,盈亏相反,迟速亦相反。”而之所以投入巨费而效率低下,主要是“由于有驿州、县马必缺额,又复疲瘦,州、县以此为津贴,管驿家丁以此为利薮,故文报必致迟延,官绅书信间有外加马封附文递送者,有驿官以其非例准之条,又系不费之惠,故既不驳回,亦不收费,浮沉听之州、县,不当驿路者设铺司,武官文报交塘汛,其延搁更甚于驿站。”驿传系统日渐腐败,而列强又多开设邮局于中国内地,为保利权起见,“自光绪二十一年奉旨饬催总税务司赫德办理,光绪二十二年沿海沿江渐设邮局,附于海关税务司兼办,于是沿江沿海公文私信,迅速胜前而信资极省。”可见张之洞与刘坤一亦承认,新式邮政的建立,对革除驿站旧弊、在公文传递及民间私信的发展确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不过,两位封疆大吏亦同时指出,海关所办邮局,“用费不敷尚多。此盖因垄断而生调停,因调停而致赔累。”这一指责明显反映出二人仍以为新式邮政为普通商业之事,而与朝政民情之运转无甚关系。在他们的观念中,还把驿政视为政令传递之必须渠道,故方在《江楚会奏三折》中主张,“于各省、州、县遍设邮政局”,只是这一“邮政局”“应名曰驿政局,以免与税司之邮政局相混”。其管理方式,“应由各省督、抚督饬臬司,责成州、县设局办理”,“由省城总局妥定章程,刊发印花领用粘贴,用过照数报销,即以原有驿站、铺司各经费拨充局用。内河内地分别设立快划、快马、健夫驰递,明定章程,准带官民私信。所有京外文武衙门文报、书信统归此局递送,其文报责成仍照驿站向章,其信资务宜从省,以广招徕。”通过核算是年印花信资收入,即在次年扣发相应数量的驿铺经费,“行之既久,信资日增,驿费日减,十年之后专取信资即敷局费,驿铺各费可以全行省出”,“则每年可省用款三百万矣”。驿政局之局费,“统于驿铺经费内,自行酌剂支用。”其局场地,“即设衙署内,并无另需费用,并须于境内大镇酌设分局。此局不须多人,亦无多事,但派一人驻于客栈即可,或附于店铺代办亦可,但经管发印花、收信函、收信资而已,并无多费。”寄递所用之交通工具,“此时沿江沿海地方,其由轮船者暂归税司,内河无论轮船、民船及岸上陆行者,统归州县。畅行以后,再行体察情形。如能并江海轮船,邮局亦归之州县,勿庸税务司兼管为善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折设计之中,海关邮局最终亦须归并于州县主管的“驿政局”之内,在“海关邮局未归州县之前,邮政局与驿政局彼此互相代寄信件,内地寄内地者只贴驿局印花,内地寄通商各口者加贴邮局印花一分,通商各口寄内地者加贴驿局印花一分,其驿局与邮局彼此往来交易一切细章,随后详酌。”故该折所言“推广邮政”的关键,即在于体制上交由州县兼办:“此事若归州县兼办,则费不另筹,局由州县酌设,进退裕如。若另行委员设局,则廷寄奏报要件设有迟误,必多推诿,故惟有责成州县之无弊也。”
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三折》中的对新式邮政或“驿政局”的设计,在具体寄递方法和业务安排上,多有参考海关邮政。但在其设计中,州县进一步扩大其管理“驿政”的权力,尤其在经费上拥有了更灵活的自主权,而原具体管理“驿政”的机构与人员,正式成为州县官署的下属,与以往州县官聘请幕府师爷管理驿站的惯例明显有别,如此一来,管理邮政的人员更趋专业化。但该方案依然与新式邮政的要求迥异,与旧制相比之进步,在于将非正式机构纳入衙署结构之中,但却将州县官的繁重责任进一步加深,故在其推广计划的构思中,似乎仍与过往“按需设驿”的做法类似,而并非如新式邮政般在人群聚居处即设立相应邮政局点。
整体观之,该设计接受了“邮政收入为国家利源之一”及“开办邮政为国家应有之利权”的思想,但在具体设计上旧制与新法掺混,既想参考新式邮政传书递信、办理银汇的相关办法,又不愿放弃旧有驿站的政治用意。这种新旧掺杂、表里不一的体制设计,正是庚子之后清廷思变、但在财力拮据和保守势力暗阻之下的妥协之举:既保证传统体制不受太大冲击,又增加新的职责以应付日益严峻的变局需要。就邮政而言,其更有一关键用意,在于建立一比海关邮政更为“正统”之新式邮递机构,而将为外籍税务司控制的邮政利权收归国人管辖。故由此亦可发现近代邮权收回上之一吊诡现象:外籍税务司主办之海关邮政与清廷疆吏主张之“驿政局”机构,均要求驱赶客邮而收回利权,但外籍税务司不久即发现,自己原来也在被逐群体之列。虽然邮政利权至有清一代结束依然被实际操纵于外籍人员手中,但双方的斗争在庚子之后则日益激烈和直接,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日渐唤起与觉醒而更加明显。
《江楚会奏三折》中所建言的各项改革措施,在清末新政改革中多有采用,但“推行邮政”一节主张建立“驿政局”与海关邮政分庭抗礼的做法,却没有得到清廷的认同。无法推动的缘故,除了该局实属多此一举外,该计划不仅要从海关的管辖内将邮政利权收回,同时也暗示会改革现有的管驿体系,而把原属兵部的管理职能更多地下放到州县一级,但如此一来,不仅削弱了兵部原有的职权、减少其管理的巨数驿费,而邮传业务亦未见得会有必然的起色。赫德在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1902年2月20日)致外务部的申呈中即分析道,“总税务司驻京如此总理邮政事务,各省之邮政合一,日后必可为国家之一要政,俟其成功,或另设专署,或另设大臣均无不可。”要使如此庞大复杂的系统有效地运转和盈利,则必须要有统一和专业的机构对其进行管理,而《江楚会奏三折》中提议由州县官直接经营邮递业务,“地方官因知邮政可变为官事,自思举行,阻止推广之路,惟各处官员散办,不归一处专办,恐将来成效难期。”而且“数年以来各国在中国通商口岸各设信局,现有推至内地之举,此与中国邮政日行之事多所掣肘,并与中国日后应自办理之事关系亦属非轻”,如果由州县官员各自为政,不仅难以达至将邮政“速行推至内地”的效果,同时还可能让客邮肆虐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所以张之洞、刘坤一的建策,意义不在具体的措施,而是明确了邮政为国家之重要利权、需要从外籍管邮人员手中收回的观点,并开启了之后十年内清廷为收回邮政利权而努力的序幕。
二、直省官员的邮递制度改革
《江楚会奏三折》虽然提出将新式邮政收归自办的看法,但仅在具体的设局寄递方法上有所建议,却没有提及在中央层面设立管邮专部。这看似矛盾的安排,或许正好提示了是时直省官员对官制新政的思路和看法。不过,自此之后,多有直省官员呼吁设立邮政专管部门,以便收回邮政自办及安排裁驿置邮事宜。光绪三十一年后,清廷逐步推动各项新政的举办,开始有官员建议在官制上加以改革,设立专部管理邮政:“闻日前有某大臣呈递封奏,略谓现值朝廷振兴庶务之际,所有商务事宜已经设立专部、议设官职。而农务邮电事宜亦为国家要政,宜增设专部以资整顿而一事权。”不过,设官立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虽有该议,却未必立时付诸实践。倒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三(1905年9月1日)端方的《设法收回关税邮政折》,道出了其中奥秘。他首先指出,由洋人操控关税与邮政之事,乃因为是时新制初立,“情形未谙,一切钩稽之役,自不得不委任西人。”随着口岸增多,“赫德之势力范围遂日益加广,而各关税务司遂为西人独擅之技,中国更无能预其任者。”虽然“邮政亦内政之一”,亦是“原为交通利便而设”,本是皆归国家自办。但如今由外人主办,“设有军国重要机关警密消息,一切不行,是则临时之洩漏阻碍,流弊何穷。”更重要的,是邮政为国家“岁入一大宗”,所以中国“既假人以权,且需津贴其费,所失过多,殊觉非计。”随着“近年学堂另立,民智渐开,邮税所入可望日渐增多,似不可舍此利权,听其外溢。”在“权”与“利”两方面来说,均不能再将邮政任其操于外人之手。故端方建议,一是由外务部饬令赫德交出邮政事宜,由清廷官员接管;一是暂时留任洋员,而同时“专派学生前往日本学习邮务”,“固不虞接办之无人,要政之中辍也。”其在文末更指出了收回邮政自办的意义,“历观古今中外历史,未有税务邮政两事授柄外人而能立国者。”而在新的知识体系熏陶之下,更应意识到“挽回利权一分,即保持主权一分。外人渐知中国于自治之权力能振作,庶几侵占主权之诡谋自然消泯,洵抵制之一端,而图强之一策也。”
从端方此折可见,是时官员对收回邮政之认识,主要是从收回被赫德掌控的海关利权的角度出发,亦意识到邮政为国家本有之利权,不可轻易交由外人主管。但至于收回邮政后的机构设置和日常管理等问题,也未有具体的筹画。而端方的奏折上达天听后,亦仅是“下部知之”的结果 。至于海关管理邮政的工作,并未因清廷官员的奏劾并未停止。除继续在各地开设分局外,还与英、法、德、日等国签订邮政章程,而邮政章程的主旨有二:“一系各该国境内,现允认中国邮票一律通行;一系在中国境内通商口岸外之各腹地,若英法另设局所办理邮务,中国可不承认。”对于德国在山东商埠开设邮局,亦商定妥协办法,以保证客邮局所不至于扩散至其他地区,损害利权。故虽然收回邮政自办的时论甚盛,清廷却罕有实际举动,而推动新式邮政建设的工作,基本还是备受批评的外籍海关税务司在实际操作。
随着官制改革呼声渐高,尤其是1905年9月学部的成立,“成为清末中央行政体制变革突破瓶颈的标志”,“重新划分旧制部院职能的问题提上日程,长期延续的六部架构势必改变,解决新旧体制交替,重新组合新行政体系的需求日益迫切。”但若要设立专部管理邮政,则须妥善处理旧制之中兵部对驿站的管理权限,而后者关涉利益厚重,并非轻言裁撤即可成事。以驿站经费为例,兵部即称“臣部办公经费,向仅恃驿站奏销、朋马兵马奏销饭银、札付饭银数项。各省皆多蒂欠,办公已属不敷,而纸张笔墨等件,庚子后久未承领,既须自行备办,合署饭食仅户帮千余金,尚不逮十分之一。”而即使如今奏请朝廷酌筹办公经费,其相关费用亦无法全额收齐。由此可见,兵部经费不足,以致陷入运转的困境。而兵部又不像外务部、商部等“另有津贴”,历年事务积压太多,不仅清理不易,而且形成一个不停往内耗钱的黑洞,一旦停止又无良法改革,则必定引发部务的动荡。有鉴于此,兵部更不愿轻易将驿站的职能轻易交出,对裁驿之事或移交职能,基本坚持反对的态度。
光绪三十二年,海关管理体制发生变化。清廷为逐步收回海关利权而设立税务处,将原属总理衙门(后改外务部)管辖的海关改归新设立的税务处管理。税务处设“督办大臣一员,会办大臣一员,提调一员。分设四股,每股总办各一员,帮办各五员”,而由“第四股管理邮政事务”。是年六月廿六(1906 年 8 月15日)“政府王大臣会议,迩来中国邮政日见推广,惟无统辖之所,殊难以一事权。应即商之总税务司,将各省邮政归于税务处管理,以便查核而挽利权。惟税务大臣铁大司农,以甫经接办税务,头绪纷繁,一时不能兼管邮政,大不以此举为然。”此时邮务的确未交由税务处接管,两周后刑部制定邮律并奉旨允准后,仍是“由外部照会赫总税司饬邮政总局及各省分局遵办。”而两位新任的税务大臣铁良、唐绍仪,亦“因税务头绪纷繁,故拟另添邮政大臣,以专职任而重邮政云。”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六(1906年8月25日),戴鸿慈等呈递《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在第四条“中央各官宜酌量增置、裁撤、归并”中,建议“因交通之利大开,析铁路、轮船、邮政、电报诸行政而为邮部者。”由于“中国旧有六部,惟户、刑、兵三部最为切要”,而“军(兵)部掌军事行政,为旧制所固有,现在绿营半皆裁撤,各省训练新军,非复部臣所能积核,然既无知兵之实,徒拥掌兵之名,名实不符,殆同闲冗,臣等以为宜仍旧制,以练兵处并入,改其名曰军部,而将各国通行之军事行政职权,应归兵部大臣统辖者,皆责成焉。”在这种设计下,不仅于该部中分立陆军、海军两局,还要仿西制建立参谋本部及推广军事教育,但原属兵部管辖的驿传体系则未见提及,故此职能应属“裁并”之列。为此戴鸿慈等建议设立“交通部”,管辖交通行政:“自轮船、铁路、电报盛行,而交通行政浸已繁多,各国殆无不特设专部以领之者。中国铁路,各国久为垂涎,急起经营,正恐惟日不足,邮政本为交通枢纽,今尚委诸税司之手,办理亦未得宜。其他轮船、电线创办已久,而进步甚迟,欲求整顿扩张,正赖事权统一。臣等谓宜合此数项,仿日本递信省例,特设一交通部。”除中央机构设邮部专管外,戴鸿慈等又建议“变通地方行政制度”,每省设民政司、执法司、财务司、提学司、巡警司、军政司、外交司和邮递司,除执法司和军政司外,“其余六司皆为督抚之最高辅佐官。”
七月十三(9月1日),清廷颁定“仿行立宪”上谕,认为“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因此“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但在官制改革的讨论中,主要集中在建立新的行政体系,尤其是理顺“道咸以降,督抚权力扩张,出现权力下移的趋势”而产生的中央与直省的紧张关系,而对于裁驿置邮的讨论并不太多。是年八月十六(10月3日)曾有报道言,朝廷新定地方官制中,设有邮政司部门:“凡一省之航铁道、电信,均其职掌,而本省驿递亦裁撤并入。”不过,清廷最后的政制设计,采用了“自上而下、先内而外”的办法,直省的改革暂且搁置,而首要对中央各部的职能进行重整和设计,因此如何重组兵部的管理职能、是否设立专部管理邮政及如何处理驿站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之一。
《盛京时报》在九月十五(11月1日)刊登了《定各堂部司各官额缺职掌述汇》的京师要闻,其中透露朝廷将设立交通部,专管交通事务:“……第九交通部。管理全国交通工事(以工部改设,兼有商部、外务部、兵部之职掌)设四司,一曰路政司,二曰邮电司,三曰航业司,四曰都水稽察各省交通司、河道及铁路局、电报局。”从此报道不难看出,清廷初时讨论的方案还相当粗略,其改设思路,基本从原有六部入手,将相近的职能进行重组和整合。所谓兼有“商部、外务部、兵部”的职掌,大概即指邮政与驿递而言,因为二者职能与交通事务重合者即为上述二事。对交通部的职能构思,基本涵盖了后来邮传部“路电邮航”四项职责。而九月十六(11月2日)奕劻等进呈《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在《附阁部院官制节略清单》中,其设计方案与《盛京时报》的消息多有相符,其中“兵部掌绿营兵籍,徒拥虚名,近日时局非有陆、海两军不能立国,而马政应隶陆军,故分兵部为陆军部,以太仆寺并入,而海军暂隶之,以次于学部。”而对于邮传事务,“轮电、交通、邮递络绎,非设专部则运转不灵,故变工部为邮传部,以次于农工商部。”可见《盛京时报》的消息相当灵通,其报道基本涵盖了奕劻该折的全部信息。
而九月廿五(11月11日)的《盛京时报》在改革官制上谕发布后,进一步解释了当初为何以工部改交通部的想法:“交通为增进国势之要政,东西各国咸重之。中国现于电政、路政、邮政、航业亦次第推行,不设专官,曷由进步。今拟以工部改设交通部,即以该部所掌之河工海塘各事宜附入,并以商部通艺司所掌之铁路、设电、行轮,外务部榷算所掌之邮政。”而其具体职能,则是“交通部管理全国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驿传、航路、标织、商轮、民船、水路运输、疏濬河道、河湖海隄工各事宜,并稽查各省交通司河道及铁路局、电报局、邮政局。”由此可见,在交通部的设计内,管理事宜相当庞杂,并不仅仅关注于交通事务。而其所设邮电司,则职掌“一审定电报电话规则、局所章程及修理添设事项;二考验电报电话用品及关于电学之工业管理、电学工程之学堂(拟以工部奏设之艺学馆并入)事项;三考察电报各局委员学生之成绩及稽核出入款项事宜;四稽核全国邮政及研究一切邮政事项;五筹办未立邮局地方之驿传,更定章程,整饬驿务事项。”按其思路,似乎在新部成立之后暂不处理裁驿置邮的事宜,而是保持邮政与驿传的网络,在部分地区依旧采用驿传的方式处理邮递问题。虽然设立交通部的方案最终没有获准,但对于该部职能的构思却未必事出无因,继续保存驿传,很有可能是一种妥协方案,暂不触动实质的利权问题,而首先建立起一套“仿行宪政”的官制体系。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1906年11月6日),清廷发布厘定官制上谕,其中管驿的兵部“著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而之前传闻改为交通部的工部,则“着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而“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着名为邮传部。”从此定制可以发现,原先讨论以工部改交通部的方案基本放弃,而易“交通部”为“邮传部”,则出自总司核定官制方案的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的决定。但是厘定官制中,对管驿权利依然归属陆军部,亦不虑及裁驿置邮之问题。在颁布上谕后陆军部所定《陆军部各厅司处应办事宜》可以看出,该部仍如原兵部,设置捷报处与马馆管理驿站、驿马问题。陆军部军咨处的第四司(此司缓设,归第二司兼办)的应办事宜,即包括与推广邮政相关的各个主要方面:“一考查全国邮政现在情形事宜;一收集全国邮政各项章程规则图表事宜;一核议全国邮政推广办法事宜;一规定军用邮政章程事宜;一规定平战两时邮政与军队联系章程事宜;一筹拟添设邮局以利军事计画事宜;一研究现在全国驿递台站利弊筹拟改良事宜。”由此不难看出,陆军部并未将驿递的相关职责归并到邮传部中,反在其职责内还涉及全国邮政的相关事宜。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官制初定,各部相关交叉职能尚未能明确划分。在稍后陆军部所上《核议陆军部官制并酌拟办法折》中,附有《拟定陆军部章制敬缮清单》,其中军乘司“掌军台、驿站、牌票、贡马、军马各项事宜。凡旧隶兵部车驾司所掌,除各牧场事宜划归军牧司外,其余各项及由武库司内画出遣配等事件皆属焉。区为驿传、销算、配戌三科分理司务。其捷报处、马馆仍旧设立,一切事宜隶属该司。”而该司“设司长一员,承发官一员,驿传、销算、配戌三科各设科长一员,共设一二三等科员十八员,录事十二员。另设捷报处总办一员,办事官六员,录事二员。又马馆监督一员,录事二员。”可见新官制的厘定,并未如之前的方案讨论般将职能调整重组,以驿传事务而言,其主管部门并无改变,依然交由兵部改制而来的陆军部管理。形成对比的是,光绪三十三年六月颁布的邮传部新官制,原设计的邮电司被分为电政司与邮政司,邮政司“司掌全国邮政,凡邮政应行考核调查及筹划扩充,并审议邮律各项事件。”其中亦无涉及驿务,陆军部对此项职权依然牢牢控制,不愿放手。
邮传部的成立,在名义上新式邮政有了中央一级的主管部门,而首任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亦针对地方管邮体系及邮权问题提出几项计划:“邮传部设立布置停妥后,即拟将邮政收回自办;邮传部拟奏于各行省,设邮传使,所需经费,即以各省向有驿站支项拨充;闻张尚书议拟将来派员入万国邮政公会、及万国路政公会,以资讲求,而期联络。”可见是时邮部主官即已将邮政及驿站事务归入其部职责之中,不过二者之间仍有分别,在其看来,似乎收回邮政自办更为重要,宜先举行。只是张百熙仅任职五月即离世,而邮传部在收回邮政自办及裁驿置邮等事务上,尚因人事与利益之轇轕,纠缠直至清亡。
三、总 结
清末邮传部设立后,所进行的收归邮政自办及裁驿置邮等重大事件,本系相互影响、相互呼应,然其二者在联系之中又现各自独立的进程,充分体现了清末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利益人事纠葛。收归邮政自办,主要针对外籍税务司主管下的新式邮政;而“裁驿置邮”,则是解决邮传、陆军两部在管邮管驿权限上的分歧。无论是收归邮政自办还是裁驿置邮,都与清末朝廷的官制改革所引发的政情变化、以及各部人事变动与利益归属密切相关,故其线索繁多,原因复杂,通过厘清这一史实,则可对传统驿递体系向新式邮政制度的转型过程,有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1]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邮政[G].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第六卷)[G].北京:中华书局,1996.
[3]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4]申报[N].1905-03-06.
[5]端方.端忠敏公奏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6]德宗景皇帝实录[G].北京:中华书局,1987.
[7]申报[N].1905-04-24.
[8]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9]关晓红.种瓜得豆:清季外官改制的舆论及方案选择[J].近代史研究,2007,(6).
[10]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末官报汇编[G].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11]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G].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2]申报[N].1906-08-15.
[13]申报[N].1906-08-29.
[14]北京市邮政局史志办公室.京版报刊上的北京邮政[G].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G].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三十二册)[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7]申报[N].1906-10-03.
[18]盛京时报[N].1906-11-11.
[19]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宪政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0]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陆军部档案资料汇编[G].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
[21]汪熙、陈绛.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2]台湾日日新报[N].1906-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