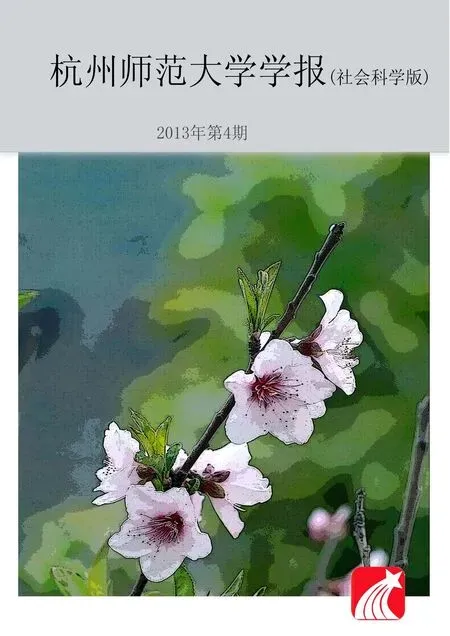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2013-10-28姚永辉
姚永辉
(杭州师范大学 1.人文学院;2.国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姚永辉
(杭州师范大学 1.人文学院;2.国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宋代;礼治;制礼;朱熹;司马氏书仪
一 从“家”到“天下”:礼是秩序整治的通用手段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比喻为如同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丢石头在水中所形成的同心圆性质,而儒家所谓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PP.25-26)因此,从个人到家庭、家族、宗族,再到国家,就形成了一套具有伸缩功能的差序格局。宋代士人相信礼治是贯通并维系差序格局中各等次秩序的根本途径。如果说在礼法隳颓、事功需要极为迫切的中唐时期,“因人以立法,乘时以立教,以义制事,以礼制心”[2](P.118),还多少显得有些无力迂阔,那么至北宋真、仁时期,随着政权的稳固和内政改革开始预热,就确实具有了现实的可能。
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六月,刚被朝廷任命仍知谏院的司马光就在《谨习疏》中论及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措施在“礼”。反思历代政治,让司马光相信“礼”之于国家治理的效用不可小觑,“昔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故子孙数百年享天之禄。及其衰也,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暴蔑王室,岂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与也。于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怀诸侯,而诸侯莫敢不从,所以然者,犹有先王之遗风余俗未绝于民故也”,“降及汉氏,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以行义取士,以儒术化民。是以王莽之乱,民思刘氏而卒复之。赤眉虽群盗,犹立宗室以从民望”,即便是对于天下莫与之敌的曹操,也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敢公然废汉自立,正是由于心有所惧,才“畏天下之人疾之”。然而,魏晋以降,“人主始贵通才而贱守节,人臣始尚浮华而薄儒术,以先王之礼为糟粕而不行,以纯固之士为鄙朴而不用”,“风俗日坏,入于偷薄,叛君不以为耻,犯上不以为非,惟利是从,不顾名节”,及至唐代,“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帅者,朝廷不能讨,因而抚之,拔于行伍,授以旄钺”,“成者为贤、败者为愚,不复论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五年,败亡相属,生民涂炭”[3]。司马光以“礼”为治国之本的观念一以贯之,后来在主持《资治通鉴》的编撰中,又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强调“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绝非仅仅只能维持几席之上、户庭之间之不乱[4](PP.375-376)。家、乡、国、天下,司马光认为礼治在上述不同层级具有相异的功用,它们的作用总和构成理想的国家秩序。
除了司马光等注重通过史鉴论议“礼”之于治理国家的意义之外,还有许多士人试图从“礼”本身的内涵阐发。李觏以其《礼论》7篇与《周礼致太平论》51篇而赢得大名,后人多将其以礼治国的思想与王安石联系起来论议,并认为王安石的《周官新义》正是对其思想的发挥。在李觏看来,礼兼涉“人道”与“世教”,是儒家修齐治平之根本手段,“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5](P.5),并将礼分为“礼之本”(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支”(乐、政、刑)、“礼之别名”(仁、义、智、信),通过问答的方式,逐一阐明观点、问疑辩难。[5](PP.5-6)此外,李觏又在《周礼致太平论》中,从内治、国用、军卫、刑禁、官人、教道等方面阐述统治者如何从《周礼》中获取治国之方。这恰好与后来王安石以《周礼》大行其道的路径相合。李觏的观点偏向于外在的措施,周敦颐所开启的“礼,理也”[6](P.99)的论证则是向内寻找“礼”之于治国依据的路径。周敦颐所说的理还仅仅为阴阳之理,张载、二程所说的“礼即理”,则强调“礼”具有“天经地义”的意义,如张载认为“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7](P.264),二程也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出于性,非伪貌饰情”,“天尊地卑,礼固立矣……圣人循此,制为冠、昏、丧、祭、朝、聘、射、飨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8](P.668)。
北宋时期大部分讨论侧重于论述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合理性,南宋《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则将礼治从家到天下的不同层级的理想构思与礼学著作融合为一体。朱熹与其弟子主编的《仪礼经传通解》是酝酿多年的大工程,其主体构思是以《仪礼》为本经,“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9](PP.687-688),相当于集仪节与礼义为一体、融合古今阐述的合本。《仪礼经传通解》在篇章结构上打破了汉晋以后“吉、凶、宾、军、嘉”的分类模式,以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的模式进行编排,除了学礼、丧礼、祭礼三个方面的礼仪在施礼范围上有其特殊性之外,似乎可以说,《仪礼经传通解》以家、乡、邦国、王朝这样的施礼范围来划分礼仪类别,与朱熹承继《大学》“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模式有着内在的联系。[10](P.130)
二 礼仪文本制作的检讨
依时而制礼仪文本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运用的前提,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检讨前代的礼文和当时礼仪推行状况就成为首要任务。宋人的反思与检讨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礼文繁琐,多不适用。
礼,时为大,古礼零碎繁冗且未因时损益是彼时礼仪文本制作的最大问题。朱熹认同“礼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难行”[11](P.2177)。硕果不食、古礼难行,将礼仪文本化繁为简,掇其纲要最为关键,因此,“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11](P.2177),“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尽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11](P.2178)。
第二、背离礼缘情而作的精神。
在北宋士人对礼仪文本制作的反思中,苏轼或可成为代表。苏轼认为三代之后,“豪杰有意之主,博学多识之臣,不可以胜数”,“然而礼废乐坠”,“相与咨嗟发愤而卒于无成者”,其原因并非是乏才学,而是“论之太详,畏之太甚”。礼之根本,在于缘情而作,因人情之所安而为之节文,人情随时而变,礼文也应因时损益,执人情之所无定而为定论,才是制礼的核心精神,而彼时儒者所论礼文却因人情之所不安而作,当然极难在现实中推行[12](P.49)。苏轼除了抱怨礼文未因时而变之外,更强调“礼缘情而作”却被当时论礼者所忽略的事实。宋代士人的礼论中,对礼缘情说有太多的阐述。此前的研究多从思想上梳理子思、孟子至道学一脉的发展流变,而较为忽略礼仪改革的需要。事实上,彼时朝野涉礼之论对缘情说的强调和关注,一方面,在于以先秦至秦汉时代的言论证明当世礼治的合情合理,使从中唐以后逐渐扩展蔓延的礼为畏途之说得以消解;另一方面,能拉近束之高阁、不明其义的礼文与民众现实生活的距离。上述两者都为礼文改造提供了基础。
第三、礼学专门之家乏见,其余多陷于迂阔。
礼仪文本的制作需要得到礼学论证的支持,然而在宋代士人看来,彼时的礼学远不足以提供参考。宋代三礼学,《周礼》最盛、《礼记》次之、《仪礼》最末。《周礼》有王安石的倡导,著述达百种之多;二程虽然欣赏张载在关中的礼俗教化活动(将传统的礼学向实践方面转向),但同时也认为“举礼文,却只是一时事。要所补大,可以为风后世,却只是明道”[8](P.146),故相对而言,讨论《礼记》较多,尤以《中庸》篇的阐述为重点。除此之外,如李格非的《礼记精义》、真德秀《大学衍义》、卫湜《礼记集说》、魏了翁《礼记要义》、方悫《礼记解义》,司马光、张九成、杨时、晁公武等人的《中庸》相关论说在当世都较为有名。
相比之下,最能为礼仪文本制作提供参考的《仪礼》之学却堪称冷门。《仪礼》之学的衰颓,在宋儒看来,主要是因为礼学专门之家的缺失和王安石的科考改革。“古者礼学是专门名家,始终理会此事,故学者有所传授,终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礼有疑者,辄就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士庶乡党典礼,各各分明”[11](P.2184),“六朝人多是精于此。毕竟当时此学自专门名家,朝廷有礼事,便用此等人议之”[11](P.2227)。六朝以后,朝廷礼典的编撰虽然较盛,《开元礼》更是一代礼文的典范,但《仪礼》之学却问津者不多[13](PP.338-347)*彭林分析了正史礼乐志中涉礼部分的内容编排,认为汉代以后,从目录上看,重视仪而不重视礼,没有理论的依托。。及宋,王安石科考改革,将原来与六经三传并行的《仪礼》,罢去,士人更是读《礼记》,而不读《仪礼》[11](P.2187),“祖宗时有三礼科学究,是也。虽不晓义理,却尚自记得。自荆公废了学究科,后来人都不知有《仪礼》”[11](PP.2225),宋初的礼官均有专门之学,自王安石罢开宝通礼科,礼官的专业性大大降低,“不问是甚人皆可做”[11](P.2183),因此,朱熹认为王安石废《仪礼》而取《礼记》,完全是舍本而取末的做法[11](P.2225)。偶有涉猎礼学考证者,亦多陷入繁琐且乏见地的考证,“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溺于器数而陷于“迂阔”[11](P.2177)。
三 礼仪文本改造的准则
宋代士人在上述检讨与反思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以朱熹的观点较为全面。
第一、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
改造礼仪,是自上而下、吉凶相称的庞大工程。儒家的吉凶两套礼仪系统,在区别中构成整体,“今吉服既不如古,独于丧服欲如古,也不可”[11](P.2188);另外,礼由尊卑降杀而成,对下的改造必须参照上而成,比如冠制尊卑,以中梁为等差,宋时天子用二十四,如果以三、二、二、二、二的标准降杀,至庶人则竟用十二,“甚大而不宜”,最好的方式是“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升朝以七,选人以五,士以三,庶人只用纱帛裹髻”[11](P.2188)。若仅改庶人礼,而不改天子和品官之礼,就不能构成礼仪的等级序列,也就失去了制礼的基本意义。因此,在上者的理解和支持对礼仪的推行尤为重要,“圣贤不得其位”,则“此事终无由正”[11](P.2188)。
第二、综合散失诸礼、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
在宋代士人,尤其是理学家看来,礼仪文本的改造非唯仪节的连缀,还要各有其理、各有其义,即礼仪文本应是仪节与礼义精神的综合体。因此,作为礼仪文本的改造者,应首先综合散失诸礼,错综参考,推敲其节文度数,“一一着实”,再在此基础上“推明其义”,体会礼书的精密义理,也就是修炼内功。只有这样,才能见得礼文深意,不至于“溺于器数”,“一齐都昏倒”[11](P.2186),只有建立在对古礼的深入认知的基础上,才能在改造中知其取舍。比如,古礼称情而立文,就丧礼而言,莫大于哀,哀情是判断是否尽礼的根本原则,因此,朱熹认为,在对丧礼仪文的改造中,“初丧”环节可以不必要求过严,“必若欲尽行,则必无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际,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礼之繁细委曲”[11](P.2285),所以只要具哀戚之心,类似这些部分都可依照今俗而行,删减古礼。
第三、掇其纲正、略去琐细。
制礼者要避免“溺于器数”就要区别礼之小与礼之大,区别变礼和经礼,在掇其纲正的基础上,再往内里填充细节。“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别有个措置,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11](P.2179)。朱熹曾以五服为例,向贺孙说明,“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齐、斩用粗布,期功以下又各为降杀;如上纽衫一等纰缪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纲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会些小不济事”[11](P.2186),“如人射一般,须是要中红心。如今直要中的,少间犹且不会中的;若只要中帖,只会中垛,少间都是胡乱发,枉了气力”。[11](P.2180)
第四、减杀古礼、切于日用。
礼,时为大,因时而制礼,才能切于日用,否则不过是徒添具文。孔子欲从先进,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有意于损周之文,从古之朴。古礼难行,制礼者必须参酌古今之宜,而彼时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为后人“自去减杀”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底本。[11](P.2185)
第五、既要有所本,也要有所创新。
制礼者,须参酌古今。从古礼处领悟礼义精神和掌握仪节流变的脉络,从今俗处选择为人情之所安、切于日用,同时又有裨于风化者,编入礼书之中。无论是古礼、抑或纳入礼书中的今俗,必然都要有所本,“皆有来历”,最切忌的就是“出于私臆”[11](P.2179)。张载制礼,就因为多有杜撰,不为朱熹欣赏,相比之下,《司马氏书仪》则是参酌古今的佳作。有所本的同时,也要具有敢于改变、不因循守旧的创新精神,“不踏旧本子,必须斩新别做”[11](P.2179)。
四 结 语
据现有文献,宋代的私修仪典以书仪、家礼、乡约为主要体裁,包括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旧题朱熹《家礼》,吕大忠《吕氏乡约》,朱熹《增损吕氏乡约》、袁采《袁氏世范》、陆游《放翁家训》《绪训》、赵鼎《家训笔录》、刘清之《戒子通录》、叶梦得《石林治生家训要略》、李宗思《礼范》、高闶《送终礼》、周端朝《冠昏丧祭礼》、庞元英《尝闻录》等。宋代士人围绕着“礼治与制礼”的讨论与私修仪典的修撰同步,事实上,朱熹等提出总结的上述原则已在部分礼书中得到较好的实践。司马光《书仪》正是秉承“严守礼义”与 “因时制范”两大原则,才在宋代众多的礼书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家礼》及其他南宋私修仪典内容的重要来源。《书仪》包括仪注和详细的礼义说明两部分内容,在对仪节的古今损益中,既有保留,同时也因时因地变更古礼,并阐明保留或者变更的理由。*参见拙文《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南北宋私修仪典体例的变化——以丧仪为例的分析》,待刊。胡叔器曾问及二程、张载、司马光所作礼书的优劣,朱熹评价说:“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大抵古礼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难用,温公本诸《仪礼》,最为适古今之宜。”[11](P.2184)
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最终指向都是如何将代表着儒家理想的礼仪渗透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对社会秩序的重整。如果说北宋司马光的《书仪》还带有“经注”的性质(包括仪注和详细的礼义说明),那么至南宋《家礼》时,就已完全偏向“仪注”,即简省对礼义的阐释,突出具体仪节的操作细则,极大提升了仪典的实用性,所以,我们常常在文献中可以见到民众使用这些仪典的事例。相比之下,宋代同样备受瞩目的官修仪典《政和五礼新仪》,虽然首次制定了庶人冠、婚、丧仪,然而基于辨上下、别等差的国家礼典性质,在制作方法上秉承“以多、大为贵”和“降杀以两”的原则,并未精心考虑实用性,或根据仪文不适合民间使用的情况而做出修改调整。因此,尽管政府在礼仪推行的过程中,采用了强制性的措施,仍然在推行几年后被开封府申请停止。这说明,在礼俗教化的问题上,“折中与融合”远比“强权或强制”有效,事实上,这也符合先秦至秦汉儒家之于“因时制礼”根本原则的阐述,在时代变迁中有所损益才是“礼作为规范人们言行的手段”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张说.张燕公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李觏.李觏集[M].王国轩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周敦颐.周濂溪集:丛书集成新编(第60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8]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9]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0]王启发.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及其礼学价值[C]//炎黄文化研究:第3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11]朱熹.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彭林.从正史所见礼乐志看儒家礼乐思想的边缘化[C]//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
《乐学集》第二辑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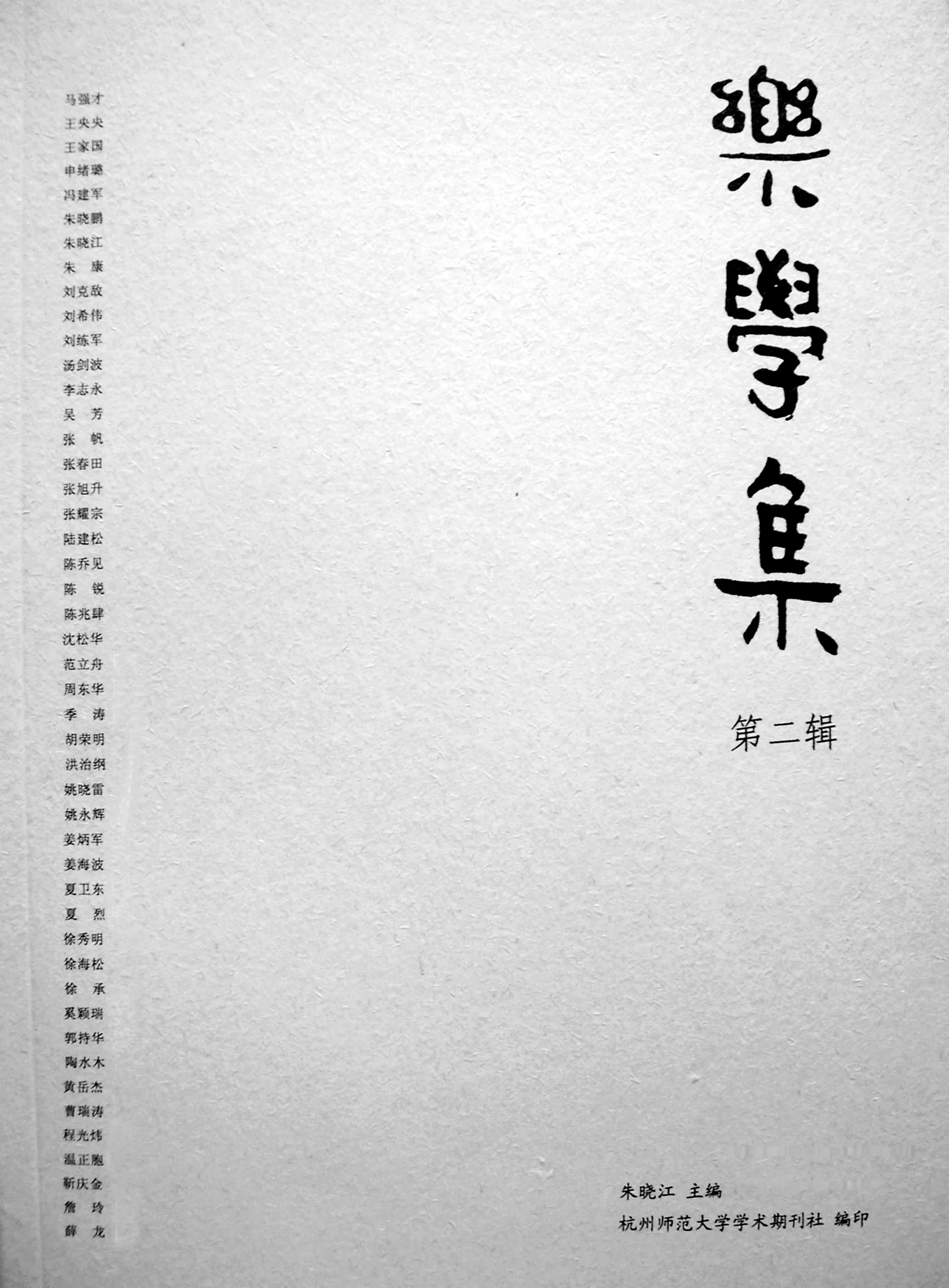
我刊2012年度“人文振兴计划”项目“学报青年作者系列研讨会”研讨内容6月结集印行。2012年我刊共举办6次作者系列讨论会,分别为:“照片与文字背后的日常生活”、“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评估与管理”、“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小说创作”、“西方社会的启蒙观念与现代中国的思想”、“民国想象:知识的转变与典范的确立”、“国学在当代:作用与途径”,共计15个主题发言,65人次参与讨论,内容涉及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诸多领域,为校内青年作者的学术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为学校的学术积淀作出了贡献。
ReflectionandRewriting:TheDiscussionofRuleofRiteandMakingRitualbyIntellectualsinSongDynasty
YAO Yong-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With the discussion on rule by Confucian rites in So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and intellectuals were dedicated to rewriting all kinds of ritual books. In order to apply Confucian rites to the populace’s daily life and readjust the social order, the intellectuals explored it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ate control and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Confucian rit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times, rewriting ritual book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pply classical texts in social practice. Th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actively engaged in promoting Confucian rites in the populace had to answer how to rewrite ritual books in a feasible and practical way. The Song intellectuals discussed this issue and put forward some importan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based on their reflection on previous ritual books.
Song Dynasty; rule of rite; making ritual; Zhu Xi;Shuyi
2012-08-15
姚永辉(1980-),四川泸州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国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传统礼仪和宋代社会文化研究。
B244
A
1674-2338(2013)04-0034-05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