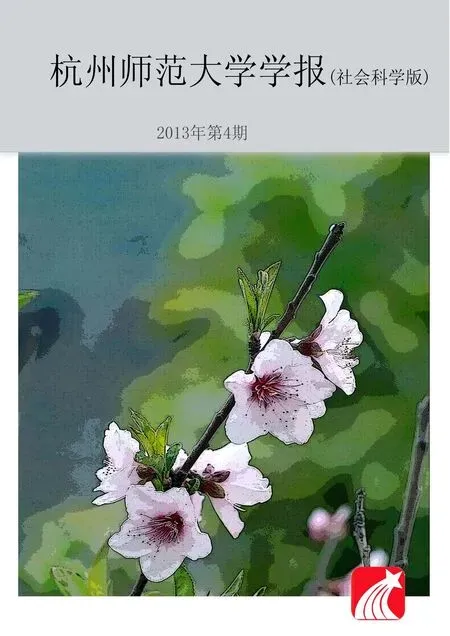为什么不该转过你的左脸:孔子论如何对待作恶者
2013-10-28勇著王央央译陈乔见校
黄 勇著,王央央译,陈乔见校
(1.香港中文大学 哲学系,香港 999077;2.杭州师范大学 图书馆,浙江 杭州 310036;3.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为什么不该转过你的左脸:孔子论如何对待作恶者
黄 勇1著,王央央2译,陈乔见3校
(1.香港中文大学 哲学系,香港 999077;2.杭州师范大学 图书馆,浙江 杭州 310036;3.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在如何对待伤害我们的作恶者问题上,孔子和耶稣持很不相同的看法,虽然他们都反对以牙还牙或者以怨报怨。耶稣要求我们在右脸被打了以后转过左脸;孔子则明确反对这样一种以德报怨的做法,而主张以直报怨。一种通常的看法是,孔子赞成的这种以直报怨的立场介于耶稣的以德报怨和他们都反对的以怨报怨之间:前者过于理想主义,很难做到,而后者过于放任,没有原则,唯有孔子的主张比较实际。笔者反对上述看法,认为孔子所主张的立场实际上比耶稣以德报怨的理想更高,要求更严,因为孔子以直报怨之直乃是正曲为直之直,因此以直报怨就是要求我们想方设法使伤害我们的作恶者不再成为作恶者,并成为为善者。
孔子;以直报怨;仁;德性伦理学
应该如何对待作恶者?耶稣有个著名的说法: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马太福音》,5.39-41)孔子的教导与此极为不同。当被问及如何评价道家“报怨以德”(《老子》,第49、63章)这一观念时,孔子的回答是:“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1](《宪问》)在本文中,我将首先考察孔子推荐给我们的对待作恶者的特有态度。孔子对本文标题的回答是,转过你的左脸实际上为作恶者创造了继续作恶的机会,而这并不利于作恶者。为此,我将考察在何种意义上,孔子相信这不利于作恶者。据孔子的观点,我们不应该转过我们的左脸,主要不是因为我们不想遭受不义,而是因为我们不想陷他人于不义。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有促成他人之德性的道德义务,并且,假如有,如何使他人有德性。
一 以直报怨
尽管孔子“以直报怨”的确切涵义在学术界仍有争议,*要精确译解孔子说此话时的心中所想,是一项既令人气馁也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用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术语说,几乎没有任何材料供我们从事这种心理学的解释。我们顶多能做的是,在解释时不违背厚道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和人性原则(principle of humanity),并根据孔子其他言论来尽可能正确地理解这句话。但可以确定的是,孔子不会赞同耶稣所推荐的对待作恶者的态度:以德报怨。*这里的“德”字,通常意义是德性、美德,在这种意义上,“以德报怨”当然不成任何问题,因为有德之人知道如何在特定的情景中恰当地对待伤害自己的人。然而,这里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否则,没有理由想象孔子反对它的理由,而且很难看出孔子所区分的这种意义的“德”与“直”的不同。这里,我采纳通常的解释,也是何晏首先提出的,即把它理解为“恩惠”(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017页)。那么,孔子是否会赞同耶稣所谴责的态度:以怨报怨?李零认为,这正是孔子“以直报怨”的意思。李零读“直”为“值”,认为孔子原话的意思是:你应该以等值的伤害回报你所遭受的伤害,不多也不少。他援引《礼记》中孔子之言以为佐证:“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2](《表记》)李零认为,孔子提倡第一组中的两种态度而谴责第二组中的两种态度[3]。
这种解释看似有些道理,但毕竟似是而非。第一,尽管“直”确有“值”义,然而,“直”才是《论语》的核心概念,它在16章中出现22次,在其它地方都没有一个有“值”的涵义。接下来我会对其中一些进行更加严密的考察。第二,如果孔子之义真是“以等值的伤害回报伤害”,那么,他可以用一种简单明了的语言,即“以怨报怨”直接说出来,而不必借用有“值”之义的“直”字。第三,如果“直”确应读作“值”,孔子确实认为我们应该以等值的恶回报作恶者,那么,类似地,孔子很有可能推荐我们以等值的善回报行善者。这样,孔子可用一个简单的口号“以值报德、怨”来取代他的两个口号,即“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当然我们知道,孔子并未如此做。
李泽厚采纳了一种更流行也许更合理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在道德要求的严格程度上看,“以直报怨”是对待作恶者的一种中庸的态度,它居于“以怨报怨”和“以德报怨”之间。对受“怨”的人,“以怨报怨”在道德上过于宽贷,“以德报怨”过于苛严,“以直报怨”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李泽厚援引康有为的《论语注》以为佐证:“孔子之道不远人……令人人可行而已……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为大道。”[4]在此,“直”被理解为没有掩饰的真情实感。这似乎与《论语》中另一处“直”的涵义颇为一致:“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1](《公冶长》)*根据通常的解释,微生高应该直白而诚实地说他没有醯。但是,我想孔子认为微生高的问题是他没有说明醯是邻居的而非他自己的。假如微生高没有掩盖醯是借自邻居的事实,而不是直白地说他没有醯而把借醯的那个人打发走,孔子可能也会赞成微生高的行为。
这种解释仍有问题,它假定了(即使就孔子而言)“以德报怨”较之于“以直报怨”是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孔子看重后者仅仅是因为前者太难而不易付诸实践。这个假定是错误的。我在后文将论证,“以直报怨”实际上比“以德报怨”的标准更高。而且,理解为根据真情实感而行动,“以直报怨”就会失去其道德的意义。假如我自己还不是一个有德之人,当有人伤害我,我可能真实地感觉到我应该报复,最好给对方予更多的伤害。难道孔子仅仅因为它源自我的真情实感而会认同我的行动?当然不会。或许持这种解释的人会说,无德之人不会拥有真正的情感,唯有直士才拥有真正的情感。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果如此,我们似乎陷入了循环推理:我们以真正的情感界定直,又以直来界定真正的情感。
显然,理解孔子之教导的关键在于“直”,因此,考察《论语》中他处“直”的涵义颇有助益。有一处,在说明除非试用一个人,否则不会对他作或毁或誉的评价后,孔子说夏、商、周三代(孔子的理想社会)之民正是如此,亦即“直道而行”[1](《卫灵公》)。显然,“直”在此并不意味着根据情感行动,而是以适宜的方式行动:如果称誉一个值得称誉的人,谴责一个应该谴责的人,那么这就是直道而行。换言之,“直”要求坚守道德上对与错的标准。孔子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达”。当被问及何谓“达”时,孔子提到三件事,首要一件是“质直而好义”[1](《颜渊》),这里他把直与义即道德联系了起来。
对孔子而言,“直”仅是德性之一,因此,恰当地理解其义不能脱离其他与此相关的德性。在《论语》中,孔子提到两种与“直”直接有关的德性:“学”和“礼”。孔子说:“直而无礼则绞”,“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1](《阳货》)。因此,真正的直士不会对他人尖酸刻薄(绞)。这得到了子贡的呼应,子贡谈及自己不喜欢的一种类型的人是“恶讦以为直者”[1](《阳货》)。因此,直士与其说是简单地根据其情感言行的人,毋宁说是以正当的方式从事正当言行的人。具体言之,正如荀子所指出:“是谓是、非谓非曰直。”[5](《修身》)职是之故,直德而行的人有时需要克服心中的情感,因为我们心中的情感有可能在道德上不正当。当然,真正有德之人(如70岁以后的孔子)感觉到的总是道德的情感,因此只要他根据心中的情感来行动就是直德而行。显然,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自我修养过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学家所说的“性其情”,而不是“情其性”。
如此,“以直报怨”的真实涵义是以道德上正当的方式对待作恶者。但是,这个解释太模糊而不能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因为我们的讨论一开始要问的正是这个问题:什么是道德上正当的对待作恶者的态度?理解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看看孔子如何把“直”与其相反者对比。孔子在“直”与“诈”、“罔”之间做了对比,他说:“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1](《阳货》),又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1](《雍也》)。因此,直士而非罔诈之士是诚实的。孔子后一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伪诈并不有益于伪诈之人,或者用肯定的方式讲,直德而行有益于直士。我将在下文讨论这一特别有意义的涵义。*在另外一处,孔子把“益者三友”和“损者三友”做了对比,其中一益为“友直”,一损为“友便辟”(《论语·季氏》),因此,直士不会谄媚他人。
然而,真正的直士并不仅仅根据自我利益行动。这可从孔子对“直”与“枉”的对比中看出。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1](《颜渊》)在同篇中,他的学生子夏对此进一步举例说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夏无疑正确地理解了孔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孔子称赞卫国的直臣史鱼这一事实中看到。史鱼将死,告诉其子,他未能向卫灵公进荐有贤德的蘧伯玉而贬黜无德的弥子瑕,因此,他死后不该殡于正室,只能殡于牖下。不久史鱼去世,其子根据父亲的遗嘱治丧。卫灵公询问个中缘由,其子便将父亲所言转告了他。卫灵公听后颇感不安,最终采纳了史鱼的建议,任用蘧伯玉而罢黜弥子瑕。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尸谏”故事,史鱼不仅使自己正直(直己),而且也使他人(卫灵公)正直(直人)。显然,考虑到“直”的双重内涵,孔子盛赞:“直哉史鱼!”[1](《卫灵公》)*《孔子家语》载孔子之言曰:“古之列谏之者,死则已矣,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谓直乎?”于此,我们得知“直”的独特性:直士不仅直己,而且直人。“直”的这一特性为孔子的继承者孟子所高度强调,他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6](《滕文公下》),孟子强调圣人的一个功能就是要使他人正直(“匡之直之”)[6](《滕文公下》)。它同样被《左传》中有关“正”和“直”的说法所确证:“正曲为直”[7](《左传·襄公七年》)。
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直”,那么,当孔子要求我们“以直报怨”时,他到底建议我们如何对待作恶者?例如,当有人打我的右脸,我是否应该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抑或给予还击?孔子也许不会绝对地排除其中的任何一种选择。只要真的有助于使作恶者不再是作恶者,孔子可能两者都会赞成。一方面,如前所言,对孔子而言,还击亦即作为惩罚的“以怨报怨”,可以警告或阻止作恶者进一步作恶。然而,其有效性是高度可疑的。第一,只有中立的组织比如政府来实施惩罚,才能更好地执行威慑的功能。来自受害者的惩罚,即使是正当的,也很有可能被人们尤其是作恶者视为报复行为,这易于招致作恶者进一步作恶。第二,尽管孔子并未排斥作为政府职能的惩罚,但他对其有效性和意义仍持高度怀疑态度[1](《为政》)。另一方面,亦如前所言,对孔子而言,转过左脸即“以德报怨”能够显示一个人的宽厚仁慈。如果受害者仅仅是想以此来展现其自身的德性(这可能是耶稣所要强调的),*至少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是这样理解的:“耶稣教导门徒宽恕70次,不是为了使敌人皈依或者迁善;他把它视为对趋近道德完美、亦即上帝的完美的一种努力。他要求门徒走第二里路,不是希望强迫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发善心并给他们自由。他说应当爱敌人,不是为了使敌人不再是敌人。他不必思考这些德行的社会结果,因为他是从内在和超越的视角看待他们。”Niebuhr, Reinhold.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New York: Scribner’s Sons,1960.263-264.则不为孔子所赞成。然而,如果受害者这种宽恕的德行至少部分地改善了作恶者,使其不再作恶,那么孔子就会赞成它。*这似乎是老子的观点。他不仅要求我们“报怨以德”,而且给出了他的理由:“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经》第49章)尽管孔子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中模范行为的重要性,但他并不教导我们忍受作恶者加诸我们的任何伤害,这不仅仅是(而且不主要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福利,也是(而且主要是)为了作恶者的福利,因为作恶者伤害我们的同时,也伤害了他自己,而且他伤害他自己的程度远远胜于其伤害于我们的程度:他伤害我们的是我们外在的身体,而他伤害他自己的是其内在的人性。孔子担心的是,我们自愿地接受乃至欢迎来自作恶者的伤害,这会鼓励恶人继续作恶,正如“以德报德”可以鼓励好人继续做好事。
孔子的观点在下则轶闻中得到了很好的阐明。孔子的学生曾参以孝著称,有一次曾子耘瓜,误斩其根,其父大怒,以杖击其背,以至于曾参被打晕了。曾子醒来后,到父亲跟前说,他活该受罚,并担心父亲因打他而虚脱。为此,他回到房间,边唱边弹,以便让父亲知道他没事。曾参相信他在实践老师传授的孝道,然而,在知道此事后,孔子并没有称赞曾参,反而责备他,要他向传说中的圣王、同样以孝著称的舜学习。
舜年轻时他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再婚并与新妻生有一子,名叫象。三人都嫉恨舜,不断找茬甚至试图害死舜。舜仍然对父母十分孝敬,对弟弟十分友爱。他承担了所有的家庭杂务,并且当他做错事情时愿意接受适当的惩罚。然而,他很清楚不能让父母害死他。有一次,父亲让他修缮粮仓的屋顶,当舜在屋顶时,他弟弟撤掉梯子并点燃了粮仓。然而,舜用斗笠当作降落伞设法逃过一劫。又一次,舜的后母让他挖井,并让她的儿子象向井里填土,试图把舜活埋在井底。然而,舜提前挖了一条通道,得以再逃一劫。
孔子解释说,舜设法避免被父母和弟弟害死,不是因为他害怕死,而是设若他让他们的计谋得逞,他们就做了不道德的事。因此,通过逃脱被害,舜实际上帮助了父母避免犯下恶行。孔子告诉曾参说,以舜为榜样,当他父亲试图为一点点过失而杖击他时——这显然是错的——曾参应该逃避,这样父亲就没有机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他也就不会陷父亲于不义。(《孔子家语·六本》)
在这两则齐名的故事中,“陷父于不义” 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洞见,虽然“陷人于不义”在现代汉语已是常用语,但是其深刻的哲学意义,不仅西方道德哲学家闻所未闻,而且即使中国学者也缺乏充分认识。在此所特别揭示出来的是:一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不仅会使主体自身道德或不道德,而且也可能使他人(最终还是主体自身)道德或不道德。我们或许会认为,转过左脸展示了我们品质的完美;然而,在孔子看来,如此做,我们创造了或至少没有试图消除别人犯错的机会。换言之,我们的行动陷人于不义或使人不义。*或许有人会说,仅仅避免被伤害,对作恶者不再为恶没有任何贡献,毕竟,恶人不仅通过成功地作恶而且也通过作恶的意图而成为恶人。对此,儒家至少有两点回应:其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犹如好人通过做好事而成为好人,恶人亦是通过做恶事而成为恶人。因此,通过消除或不提供作恶者进一步作恶的机会,我们降低了作恶者变成恶人的机会;其二,不容许恶人进一步作恶实际上不仅是使恶人不再是恶人的第一步而且也是必要的一步,在此之后当然还需要有其他措施。
无疑,在转过左脸给别人打的例子中,我们仅仅容许别人打我们。因此,根据孔子的高标准,尽管消除他人作恶的机会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能还是会认为,至少我们没有做任何积极的事去找打。别人想打我,我只是不抵抗;而不是别人不想打我,我引诱他来打我。然而,在孔子看来,我们之所以陷他人于不义,也可能因为我们消除了或未能创造别人行义的机会。这是蕴含在另一则故事中的道德观。孔子的学生子路,曾为蒲城宰。那儿发洪水,子路领导人们筑坝挖沟;当他看到人们饥肠辘辘时,子路便从自家拿出粮食分发给每个人。孔子听到此事后,马上派他的另一名学生子贡制止子路的行为。子路不解,因为他认为他实践的正是老师所传授的仁道。孔子对子路的解释是,如果看到有人饥饿,他应该禀告国君打开国家的仓廪赈灾。子路分发私家食物,实际上是陷国君于不义,因为他取消了国君承担道德责任的机会或者说创造了使国君不负责任的机会(《孔子家语·致思》)。*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此案例中,大家知道,从国家仓廪中拿出粮食给从事公务的人是国君的义务,因此,子路首先应该禀告国君。这与通常情况是不同的:帮助人是每个人的义务,因此我们不能借口为了让别人有机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自己不去提供这样的帮助 。见Huang Yong. “The Self-centeredness Objection to Virtue Ethics: Zhu Xi’s Neo-Confucian Response.”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84.4.2010.667-668。
既然我们可以做事来陷人于不义,我们也可以做事促使他人行义,或使他们改正错误。这可由另一件事看出。孔子任鲁国小司空时,做了一件改变鲁国先君陵墓布置的事。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尸体被带回鲁国,为了贬低他,被葬在先君陵墓的南面,中间被道路所阻隔。这是鲁国主政者季平子所为,季平子是孔子出仕时的主政者季桓子的父亲。孔子劝季桓子说,以此方式贬低鲁昭公,他的父亲违背了礼。通过改变现状,他的父亲和家族就可免于无礼的指控。这样,孔子得到了季桓子的许可,在鲁昭公墓的南面挖了一条沟渠,如此就使它与鲁国先君之墓连在一起,因为他们同在沟渠的北面。
当孔子要求我们“以直报怨”时,他教导我们对待恶人到底该怎么做?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的答案是,做任何符合直人的事,亦即做任何能使恶人不再成为恶人的事,或者(用一种肯定的说法)做任何能使不直之人成为正直之人的事。
二 为什么不道德不利于不道德者
我们必须看到,在上述所有关于对作恶者该做什么的故事中,孔子首要关注的是作恶者的福利。当然,这里所说的福利显然是指比外在福利更为重要的内在福利。这两种不同福利的区分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真正意义上的自爱者与世俗意义上的自爱者的区分。亚里士多德认为,有德之人不仅是自爱者,而且也是最爱自己的人。他指出,我们经常“把那些使自己多得钱财、荣誉和肉体快乐的人称为自爱者”[8](PP.1168b15-17);然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总是做公正的、节制的或任何合德性的事情……这样的人才最应当被称为自爱者。因为,他使自己得到的是最高尚的、最好的东西。他尽力地满足他自身的那个主宰的部分,并且处处听从他。”[8](PP.1168b25-31)尽管邪恶之人和有德之人都是自爱者,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前者是该受责备的,后者则是值得赞赏的:“好人必定是个自爱者,因为做高尚的事情既有益于自身又有利于他人。坏人必定不是个自爱者,因为按照他的邪恶情感,它必定既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8](PP.1069a12-15)值得注意的是,当亚里士多德说好人通过高尚的行动利己利人时,利己指的是内在福利,利人指的则是外在福利。与此相对照,当他说邪恶之人将会损己害人时,他说的是损害自己的内在福利和损害他人的外在福利。
然而,在两个重要方面,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不同。我将在这一节讨论第一个方面,并在下一节讨论第二个方面。我在这节讨论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内在福利比外在福利更为重要,以及在何种意义上,道德真正有益于有德之人,而不道德不利于不道德之人,虽然道德通常需要一个人牺牲其外在福利,而不道德则经常有助于其外在福利。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试图用他所谓的功能论证来回答此问题。根据亚氏的论证,任何具有某种功能或活动的事物的“好”(the good and the “well”)必定存在于这一事物的独特功能中。因此,人类的“好”亦必定存在于人类的独特功能中,它就是人类的品质(characteristic),或者用约翰·麦克道威尔的术语,是人类需要完成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功能是“拥有理性原则的积极的生活”[8](P.1098a3),好人就是很好地或卓越地履行其独特功能的人,这种人类功能的卓越表现就是亚氏所说的德性(virtue)。这样,德性使人成为好人,也就是卓越地从事理性活动或过一种理性生活的人。
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自始至终不同意此种观点。在早期著作中,他宣称:“如果使用理智和工具改变环境是人的标志,那么,使用理智获取私利和使用工具破坏他人同样是人的标志。”[9](PP.73-74)后来在回应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辩护时,威廉姆斯坚持认为:“邪恶或放纵之人的生活同样是由理智构成的生活,也是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活。迄今为止,还是没有能说明,‘由理性构成’的生活怎么一定会导致温和节制的生活。”[10](P.199)约翰·麦克道威尔分享了威廉姆斯的质疑。在一篇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的文章中,为了阐明理性不能导向德性,麦克道威尔虚构了一头理性的狼。“如果缺乏理性,这头狼在群体逐猎的合作活动中会很自然地承担好它的角色,然而,一旦获得理性,它会考虑多种可能,它会暂时放下自然冲动,并加以批判地审视……它会自问‘我为什么如此做?’……想知道是否可以不参加逐猎过程却仍可以攫取一份猎物。”[11](P.171)在麦克道威尔看来,这头狼顺从其天性会做德性可能要求它做的,然而理性的添加却会导致它对自己天性行为的质疑。由此麦克道威尔得出结论:“即便我们同意,就像狼生来就有合作狩猎的需求一样,人类生来就有对于德性的需求,然而,这种需求对于那些怀疑美德的行为真的为理性所需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作用。”[11](P.173)*有关对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论证的更加深入的讨论,见Huang Yong. “Two Dilemmas of Virtue Ethics and How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Avoids them.”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36.2011.247-281。
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孔子也试图根据“人禽之辨”及其中蕴含的人的独特性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在人之独特性为何的问题上,孔子与亚氏分道扬镳了。我们在上面看到,亚氏有关人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已是老生常谈,即认为理性是人的显著标志,孔子则开创了一个传统,认为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不在于理性而在于德性。
当然,说孔子把人视为本质上是道德的存在,这并非没有争议,特别是当我们把人的独特性与人性问题相等同时。在先秦时期,孟子和荀子就此问题展开了论辩,孟子倡人性善,荀子则主人性恶。在《论语》唯一与这个争辩有关的段落中,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阳货》)。由于孔子没有明说在何种意义上性相近,有时人们认为孔子并无人性善恶的观念[12],或者在善恶方面,孔子认为人性是中性的[13]。
这其实是误解。如果我们所说的是规范性的人性概念,意指人所特有的东西,那么,即使孔子没有明确说它是善的,这也毫无疑问是他的观点。孔子强调人与禽兽的不同:“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微子》)而且,对孔子而言,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在于其道德品质,他称之为“仁”。根据当代新儒家徐复观的观点,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被视为人类世界的显著标志。[14](P.69)确实,《礼记》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因此,人之所以别于禽兽在于人有礼[2](《曲礼》)。《左传》亦云“礼,人之干也”[7](《昭公七年》)。
礼确实也是孔子的一个重要观念。然而,孔子认为有比礼更为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1](《八佾》)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人”与“仁”发音相同;而且,“仁”是由“亻”和“二”构成,表示人际关系。因此,对孔子而言,人之所以区别禽兽的地方在于人拥有仁德,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说“仁者人也”[15](《中庸》)。显然,孔子视仁为人的本质性特征。
在此方面,我赞同徐复观的看法。在其先秦人性论的研究中,徐复观认为孔子实际上持有人性善的观点,因为“孔子是认定仁乃内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内,所以他才能说‘仁远乎哉?我欲仁而斯仁至矣’和‘为仁由己’的话……孔子既认定仁是内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内,则孔子虽未明说仁即是人性……他实际是认为性是善的。”[14](PP.97-98)另一位有影响的当代新儒家唐君毅同样认为孔子持有人性善的观点:“孔子谓人之生也直,我欲仁而仁至,而仁者能中心安仁,此仁在心,更宜即视为此心之善性所在。其所谓相近亦当涵孟子所谓‘同类相似’,‘圣人与我同类’,而性皆善之义。”[16]
因此,尽管孔子没有直接说人性善,但是,他有关“仁者人也”的观念明显地表明他确实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在于人拥有仁德。性相近,是因为他们都拥有仁;习相远,是因为有人保存仁而有人则放弃了仁。孟子在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6](《离娄下》)时,实际上是在阐释孔子之言 。孟子所做的仅仅是明确地提出了一种规范性的人性概念来解释孔子的观念。在解释“几希”时——它不仅使人(拥有它)区别于禽兽(缺乏它),也使君子(保存它)区别于小人(放弃它)——孟子宣称正是仁礼之心使得两者不同。一方面,“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6](《离娄下》);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待君子(有仁礼之德的人)以横逆,君子“自反而忠,其横逆由是,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6](《离娄下》)因此,根据孟子的观点,尽管人民之饱食、暖衣、逸居很重要,但是圣人认识到,“无教,则近于禽兽”,是故圣人“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6](《滕文公上》)。根据孟子,这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6](《公孙丑上》)。
孔、孟的不同在于两者所使用的“性”的聚焦点不同:孟子用它指谓人的独特性,孔子用它指谓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换个角度说,正如钱穆所言,孔子是把人与人做比较,孟子是把人与禽兽做对比[17]。然而,两者都赞同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存在物在于其道德品质。就此而言,即使荀子同样赞同,虽然他经常被视为孟子的论敌,因为他直接反驳孟子而倡人性恶,学者也因此经常就两人的观点谁更接近孔子而展开辩论。
《荀子》有两段话与我们关心的问题直接相关。在一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6](《王制》)在另一处,荀子在回答人之为人的问题时说:“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6](《非相》)
在这两段中,荀子明确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在于道德品质,这与他更为人所知的人性恶的观点并不矛盾:第一,荀子用“性”所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这与孟子用性来表示人的独特性不同;第二,在《荀子》一书中明确讨论人性恶的《性恶》篇中,“性恶”两字经常被翻译和理解为“人性是恶的”(Human Nature Is Evil),但正如狄百瑞最近指出的,它也可以被翻译和理解为“the badness in human nature”(人性中的恶)*Wm. Theodore de Bary. Xunzi(an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Seminar on Neo-Confucian Studies, November,2011).,或者更为恰当地说,人的自然倾向中的恶。
对《荀子》中“性恶”这一标题的新理解的好处是,它可以同时承认人的自然倾向中存在善性,而这也正是荀子在论证人性之恶时明确肯定的。在《性恶》的开篇,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6](《性恶》)显然,所亡之物必定是原先存在之物。因此,正如狄百瑞提及,在人们顺从其自然倾向之前,他们一定拥有辞让、忠信和礼义文理。
这个观察能够被同篇中另外两段文本所支持。在一处,荀子反驳孟子人性本善而可能丧失时,他并没有反驳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而是论证说“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6](《性恶》),这表明“朴”和“资”(孟子称为德之端),即使在荀子看来,也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他只是强调人一生下来就有放弃它的倾向。在另一处,在证明人的自然倾向中的恶时,荀子宣称我们欲求我们所缺乏的东西,正如“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6](《性恶》)。荀子在此试图证明的是,既然人欲求善,这就表明人缺乏善(如果已经拥有了善,则人就不会欲求它)。然而,热烈地渴求善这一行为本身显然是善的。
因此,对荀子观点的恰当理解是,人与生俱来既有善性亦有恶性。事实上,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6](《大略》)*与此相关联,荀子说人民去桀纣而奔汤武的理由是,前者为人所恶,后者为人所好。接着,荀子解释说:“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我们称赞圣王(他们发展了人们的好义之心)和谴责暴君(他们不允许人们如此做)的理由是,好义是人的独特性,好利则是人与禽兽的共同性。而且,荀子说,每个人自然地被赋予了好义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6](《性恶》)
三 有德之人是否应该促进他人之德性
如前所析,孔子独特而重要的地方是,正因为他认识到人的内在福利是人的真正利益所在,所以,当一个真正的有德之人关心他人的福利时,他应该更为关心其内在福利而非外在福利,尤其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宽忍也许有益于作恶者的外在福利,却很有可能损害其内在福利。在此意义上,我的宽忍行为是不道德的,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有德之人。有德之人不仅关心他人的外在福利,而且更应关心其内在福利。换言之,既然做不道德之事并不符合行为者的真正(内在)利益,那么,有德之人亦即关心他人利益的人,就应该尽其所能制止他人做不道德之事。
在此,我想在与西方传统德性伦理学的比较中,突出我们这里讨论的孔子观点的重要性。由于人们不满于在现代世界占支配地位的两种道德理论,即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德性伦理学在最近数十年取得了重大复兴。然而,对它的一个严厉批评(大部分来自康德主义的哲学家)是,它是自我中心的(self-centered)。正如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所概括的:“德性伦理学倾向于过分关注主体……此种理论要求聚焦于单个主体的品质。获得美德之有意义,就在于我们假定了一个人应该成为某种特别类型的人……这种观点要求道德主体将其自身的品质作为道德关注的核心 ……[然而]道德反思的本质应是对他者的关心。”[18](P.169)
无疑,对德性伦理学的这种批评也认识到有德之人是关怀他人福利的。然而,“这种批评指向的是主体对自我品质的关注与对他人品质的关注的不对称性。这里的问题是:既然德性伦理学要求我首先关注我自身品质的状态,那么,这是否表明,我必须把我自身的品质视作我伦理上最重要的特征?然而,如果这样,假如我对他人有恰当的关心,难道我对他人的关心不应该超出仅仅对他们的需求、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的关心,而也应该包含对其品质的关心?难道我就不应该像关注自我品质那样关注邻人的品质?”[18](P.172)所罗门以基督教的观点为例,基督徒视爱(love)或慈善(charity)为人的首要德性。基督徒通过对他人展示其德性成为人,但是,这种德性不要求此人引起周边的人也展示这种德性:“基督教的爱要求我致力于满足他人的需求、需要和欲望,但是,这难道不是暗示了他人在道德上没有我重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但是我要求我自己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18](P.172)*这里有必要做两个说明 。其一,托马斯·阿奎那发展了一种出于博爱的矫正(fraternal correction)的观念,出于博爱的矫正“对有害于罪人本人之罪加以惩治,” 这“与[使朋友]获益一样,而[使朋友]获益是一种慈善的行动,是我们对朋友做的好事”。Aquinas, Thomas. The Summa Theologica, in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s. 19-20.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ica.1952.II-II,q.33,a.1.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通常认为罪人所犯之罪有害于他人,而阿奎那在这里看到,罪人之罪也有害于罪人本身。更重要的是,阿奎那认为出于博爱的矫正是一种比物质善举更好的精神善举(Aquinas 1952: II-II, q.32, a.4)。显然,这样,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可以避免自我中心的批评。然而,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阿奎那把出于博爱的矫正视为慈善的德性,它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论德性和实践德性之外的第三种德性,即神学的德性:“我们无法自然地获得这种德性,也不能通过获得自然的力量来获得这种德性。唯有通过圣灵的渗入,我们才能获得这种德性。” (Aquinas 1952: II-II, q.24, a.2)另一方面,即便阿奎那确实认为有德之人出于慈善,应该关注他人的德性,他仍然认为“人,出于慈善,应该爱自己多于任何其他人”,“人绝对不应该从事任何会抵消其幸福的邪恶和犯罪的行为,即使他因此可以让邻人从犯罪中解脱” (Aquinas 1952: II-II, q.26, a.5)。其二,当笔者在康奈尔大学发表这篇文章的初稿时,听众中有一学生指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仅自己过基督教的生活,而且也努力使他人过这样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一个好基督徒不仅关注别人的外在福利,也关注他们的内在福利。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但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即使在此例子中,基督徒首要关注的是他人精神上的而非道德上的福利。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儒家的圣人,他在道德上比任何人都更完满,但基督徒还是具有同样强烈的欲望想去使他皈依基督教。
亚里士多德的有德之人——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爱者——在此意义上也是自我中心的,因为,如前所言,有德之人“总是做公正的、节制的或任何合德性的事情……这样的人才最应当被称为自爱者。因为,他使自己得到的是最高尚的、最好的东西。他尽力地满足他自身的那个主宰的部分,并且处处听从他。”[8](PP.1168b25-31)有德之人只关怀他人的外在福利,却最关怀其自身的内在福利,虽然他明确认识到内在福利比外在福利更为重要,更是人的构成部分。尽管亚氏确实认为肉体的伤害和快乐是真实的伤害和快乐,但他还是认为它们并不比灵魂的伤害和快乐更重要。然而,正是就灵魂的伤害和快乐而言,亚氏的有德之人仅仅关怀其自身,而且,正是通过为他人提供肉体上的快乐和消除或减少其肉体上的伤害,他自己获得了灵魂上的快乐并且使自己的灵魂避免受到伤害。*因此亚里士多德说:“既然我们说好人会把有用的东西让给朋友,他爱朋友甚过爱自己。不错,但是,他放弃这样的东西意味着,通过把有用的东西让给朋友,他为自己谋求到了高贵的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爱朋友甚过爱自己;在另一层意义上,他最爱自己。就效用而言,他最爱朋友;但是就高贵和善而言,他最爱他自己。”Aristotle. Magna Moralia. trans. by W.D. Ross. In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1212b12-17.
与此适成对照,孔子的德性伦理学显然避免了自我中心的批评,因为他明确认为有德之人应该关怀他人的德性。孔子曾经教导其弟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把他的一以贯之之道理解为“忠恕之道”[1](《宪问》)。根据当代最权威的《论语》编译者杨伯峻,孔子所说的一贯之道实际上就是孔子版本的金律(Golden Rule):忠是积极的版本,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雍也》),恕是消极的版本,亦即《论语》中几处提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管学者对何谓“忠”尚有争议,*实际上据我所知,杨是《论语》解释者持此观点的少数人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杨国荣也顺带地赞同这种解释(见杨国荣《形上学,成人,规范,知识,价值》,《哲学分析》2011年第5期,第42-59页)。另外陈乔见先生也告诉我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对“忠”也持这种看法(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6-317页)。这种解释在孟子那里确实可以找到一些根据,他说:“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念源自《论语》,孔子说:“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但是,对于“恕”之涵义却有基本一致的观点,因为孔子金律的消极版本对“恕”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1](《卫灵公》)。
然而,笔者在此无意参与“忠”之真实涵义的争论。我们的任务是揭示被认为是孔子关于金律的两个表述的独特意义。西方传统所理解的金律并不比德性伦理学更能免于自我中心问题的诟病。遵从金律,一个人应该对他人做他想要他人对他所做之事,不应该对他人做他不愿他人对他所做之事。然而,金律并不要求遵从金律的人使他人也遵从金律。比如,金律要求,如果一个人在患难时希望得到他人的帮助,这个人(甲)就应该帮助身处患难的他人(乙),但它并不要求此人(甲)也要使他人(乙)帮助身处患难的他人(丙);它要求,如果一个人不愿被不公正地对待,这个人(甲)就不要不公正地对待他人(乙),但它并不要求此人(甲)也要使他人(乙)不要不公正地对待他人(丙)。假设遵从金律对遵从者有利(违反金律对违反者不利),那么,在上述意义上遵从金律,就像一个有德之人,同样是自我中心的。
然而,无论你是否把《论语》中的这段话称作金律的孔子表述,孔子显然避免了自我中心的问题。我们首先考察所谓的金律的积极表达。孔子说:“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15](《中庸》)这里很显然,孔子所提到的似乎是金律的外在方面。然而,在其关于金律的更为著名的说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雍也》)中,孔子思考的明显是更为重要的事,而不只是要求我们对他人做我们意愿他人对我所做之事。
“立”的涵义足够明显,在孔子那里,立己无疑更多地关涉内在品质而不是外在福利。当孔子列举一生中几个重要的里程碑时,他提到“三十而立”[1](《为政》),显然他在谈论品质的塑造。关于“达”,孔子的界定是:“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1](《颜渊》)这表明“达”首先与人的内在福利相关。最有意思的是,孔子这里以“直”解释“达”,就像他用同一字来告诉我们如何对待作恶者。既然达者会帮助他人达起来,而达者的本质特征是“直”,那么,当孔子要求我们“以直报怨”时,其真实涵义就是要求我们帮助他人也行为正直;这正是我在本文中一直强调的一点。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继续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视为金律的一个版本,可以继续认为孔子的金律版本包含金律的通常涵义,亦即我们希望别人照顾我们的外在福利,我们也就应该照顾他人的外在福利;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其内在的一面,因为它对孔子而言更为主要。因此,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评论此句时说立与达这“二者皆兼内外而言 ”[19](P.846)。朱熹所谓“外”指的是每个人都欲求的事物,如福乐康寿。这是我们对金律的通常理解:既然我想要福乐康寿,我也应该帮助他人福乐康寿。
然而,朱熹对孔子金律的独到见解是,他强调了它的在内方面,在上段引文紧随其后的话便表明了这一点:“且如修德,欲德有所成立。” 这就表明,有德之人应该帮助他人成就美德[19](P.846)。因此,对朱熹而言,金律的深层涵义是:如果一个人想发展自己的德性,他应该帮助他人发展其德性;如果一个人想成就自己的德性,他应该使他人也成就其德性。在另外一处,朱熹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我欲孝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而慈。……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则是不平矣。”[19](P.361)。在与朱熹对话中,一个学生很好地表达了孔子金律的内在方面,他说:“如己欲为君子,则欲人皆为君子;己不欲为小人,则亦不欲人为小人 。”[19](P.1071)
清代学者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同样把此句解释为不立人就不能立己,不达人就不能达己。换言之,立他是立己的题中应有之义,达人(德性方面)是达己的题中应有之义。用孟子的术语,自我关心的是“大体”,亦即天生的四端(仁义礼智)之心。所以,毛奇龄不仅把此段与《中庸》中的“成己”与“成物”相联系,而且也与《大学》开篇的“明明德”、“亲民”,以及《孟子》中的“独善其身”和“兼善天下”、《论语》中的“修己”和“安人”相联系[20]。在毛奇龄看来,这里成对的两个概念都是相互不可分离的:不成物无以成人,不亲民无以明明德,不兼善天下无以独善其身,不安人无以修己,反之亦然。
相比之下,通常认为,孔子关于金律的消极说法所表达的无非就是其日常意义,涉及的只是外在的方面。第一,在《论语》的几个地方,它仅仅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未突出君子不想不道德的事实(因此也应该帮助他人不要不道德)。在《大学》中,金律的消极版本更加具体,但是它所思考的似乎主要是与外在方面相联系:“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第二,我们看到,孔子用金律的消极表达来解释恕道。然而,“恕”的字面涵义之一是宽恕,这样,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作恶时,我们所要做的似乎应该是宽恕他,而不是试图帮他停止作恶。而如果金律的消极表达式有内在方面的涵义,只要我们自己不想作恶,我们就不能不帮助他们停止作恶。第三,这种解释似乎得到了《论语》中其他一些语录的支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1](《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卫灵公》);“乐道人之善”[1](《季氏》);君子“恶称人之恶者”[1](《阳货》);“攻其恶,勿攻人之恶”[1](《颜渊》)。所有这些似乎都暗示,在金律的消极表达式中,孔子并不要求我们帮助他人避免做不道德的事,即使我们自己并不想做不道德的事。换言之,金律的消极表达式仅限于人们的外在福利而不关乎内在福利。
然而,这种解释不可能是对的。一方面,如此理解,它与孔子金律的积极表达式不一致,后者明白无误地包含甚至聚焦于人的内在福利:既然我们想成为君子,我们就该帮助他人也成为君子。现在,假定我想成为君子,但是那却有个小人,我们如何才能帮助他成为君子(这是积极性的金律所要求的)?难道我们仅仅宽恕或忽视此人的过错,而不试图帮助他克服之?另方面,《论语》中同样有许多语录表明孔子主张有德之人应该关心小人的内在福利。比如,孔子明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述而》);“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1](《宪问》)“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1](《颜渊》);最为重要说法是“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1](《里仁》)。
最后一则语录与我们关注的问题特别相关。第一,它表明有德之人不仅有所喜好,亦有所憎恶。换言之,有德之人不会仅仅宽恕或忽视小人的道德缺陷。第二,既然孔子在他处把仁界定为爱人[1](《颜渊》),显然,这里所谓有德之人憎恶人,正像他喜好人一样,同样属于广义的爱,亦即仁的构成部分。第三且最重要的是,尽管每个人似乎都有好与恶的能力,孔子却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表明,对孔子来说,唯有仁者懂得如何适当地好恶。
同时,有德之人憎恶该恶之人,正如他喜好当好之人。换言之,有德之人的喜好与憎恶是无私的。*这里笔者采纳了程颐和朱熹的解释(见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5页)。尽管它不同于古典的解释,却很接近孔子。根据为众多注家所接受的古典解释,孔子此话的意思是,有德之人喜好人民之所喜好,憎恶人民之所憎恶(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0页)。这种解释所表达的观念虽然非常合笔者的口味,因为它与我所倡导的道德铜律(the moral copper rule,“A Copper Rule versus the Golden Rule: A Daoist-Confucian Proposals for Global Ethics.” Philosophy East & West 55.3:394-425.2005)、差异伦理学 (ethics of difference,见Huang 2010)和以受动者为中心的相对主义(patient-centered relativism, Huang Yong. “Toward a Benign Moral Relativism: From Agent/Critics-centered to the Patient-centered, in Moral Relativism and Chinese Philosophy: David Wong and His Critics, edited by Xiao Yang and Huang Yo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2)的观念一样,但是很难从孔子的原文中看出这是他的意思。在此语境中,理学家程颐把有德之人的心比作“明镜”和“止水”:“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21](PP.210-211)。换言之,有德之人的憎恶与喜爱由事而不由己决定。在程颐看来,这是君子小人之别的主要所在:“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21](P.306)*这类似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些在本该发怒的场合而不发怒的人被看作是愚蠢的 ,那些对该发怒的人、在该发怒的时候而不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发怒的人也是愚蠢的。” Aristotle. Ethica Nicomachea, trans. by W.D. Ross. In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1126a5-6.在这一点上,他的哥哥程颢也说:“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21](P.460)这种解释与孔子的思想颇为一致。当一个弟子问孔子“君子亦有恶乎?”时,孔子回答说:“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1](《阳货》)。因此,有德之人仅仅憎恶邪恶之人。
另一方面,尽管无德之人也可能憎恶邪恶之人,但是,有德之人憎恶邪恶之人并不是在诅咒他们 。在此,至关重要的是,有德之人憎恶邪恶之人,并不仅仅是表达其情绪,而是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表达(或不表达)这种情绪(以及从事或不从事别的事情),从而使邪恶之人不再邪恶。因此,《论语》中的这则“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语录可以与《礼记》中的一段话相得益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2](《曲礼》)。看到所爱之人的弱点,就可帮助他克服弱点;看到所憎之人的长处,就不会放弃对他的希望。
如果这样,我们如何理解,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论语》的其他一些语录中,孔子似乎说有德之人不应当纠正而应当宽恕他人的道德缺点?尽管“恕”有宽恕之义,但孔子显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因为他明确地把恕解释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宽恕他人的过错非常不同。因此,当弟子就此问朱熹有恕道之人是否应该宽恕他人的道德缺点时,朱熹说:“此说可怪。自有《六经》以来,不曾说不责人是恕!……不成只取我好,别人不好,更不管他!”[19](P.701)
有鉴于此,我们对上文所提及的《论语》中教导我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求诸己而不求诸人”、“攻己之恶,毋攻人之恶”等语录需要重新理解。孔子之意是,当有德之人遭遇恶人时,一方面,有德之人应该反省如何做一些不同的事,以便使恶人不再为恶;另一方面,应该把帮助恶人改过自新视作自己的责任,以便使恶人不再为恶。《论语》中记载了一则可能来自武王的谚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百姓有过,在予一人”[1](《尧曰》)。因此,有德之人对他人仁慈宽恕,不是因为他(或她)不关心他人的品质,而是因为他(或她)把使他人变得有德性视作自己的责任。因此,对于有德之人而言,他人有道德缺陷恰恰表明他或她(有德之人)尚未完全履行成就他人德性的责任,因而自己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德之人。孟子在描绘伊尹时最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6](《万章下》)理学家朱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天下苟有一夫不被其泽,则于吾心为有慊;而吾身于是八者有一毫不尽,则亦何以明明德于天下耶!夫如是,则凡其所为,虽若为人,其实则亦为己而已矣。”[19](P.313)
四 结 论
在上文,我们考察了孔子对待作恶者的观点。尽管他没有绝对地排除耶稣所谴责的态度,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怨报怨,以及耶稣所提倡的态度,即把左脸转给别人打或者以德报怨;一般而言,两者孔子都不赞成。孔子的原则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应该有助于使作恶者不再是恶人的目标。以怨报怨和以德报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能适得其反,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或强迫或鼓励作恶者进一步作恶。相反,孔子教导我们“以直报怨”,首先认识到作恶者行为的不道德性,然后防止他们进一步作恶——通过不创造甚至消除他们作恶的机会。对孔子而言,我们对作恶者应该持此态度,首要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外在福利(以便我们不再遭受作恶者的伤害),而是为了作恶者的内在福利(以便使其不再是恶人)。在此,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内在福利比其外在福利更为重要,因为前者使人成为人而不是禽兽。正因为如此,对待作恶者的真正道德的态度不是让他作恶,从而增加其外在福利,而是阻止他作恶,从而增加其内在福利,亦即使他们成为没有缺陷的人。无疑,为达此目标,对我们而言仅仅消除或不创造其作恶的机会、甚至还提供或者至少不消除其作善的机会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感化或劝导他们变成有德之人,以便即使有机会作恶,他们也不愿。这将是我另外一篇论文的主题。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262.
[4]李泽厚.论语今读[M].香港:天地图书,1999.339.
[5]Xun Kuang.XunZi(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Chinese-English)[M]. Changsha: Hu’nan Renmin Chubanshe & Beijing: Waiwen Chubanshe,1999.
[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Aristotle.EthicaNicomachea[M]//TheWorksofAristotle, vol. 9. trans. by W.D. Ro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9]Williams, Bernard.Morality:AnIntroductiontoEthics[M]. New York: Harper,1971.
[10]Williams, Bernard. Replies[C]//J.E.J. Altham, Ross Harrison.World,Mind,andEthics:EssaysontheEthicalPhilosophyofBernardWilli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1]McDowell, John.Mind,Value, &Realit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2]叶经柱.孔子的道德哲学[M].台北:正中书局,1977.294.
[13]陈大齐.论语臆解[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298.
[1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9.
[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
[1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台北:学生书局,1991.
[17]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5.444.
[18]Solomon, David. Internal Objections to Virtue Ethics[C]//DanielStatman.VirtueEthics:ACriticalReade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7.
[19]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29.
[21]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WhyYouOughtNottoTurntheOtherCheek:ConfuciusonHowtoDealwithWrongdoers
HUANG Yong1, tr. WANG Yang-yang2, pr. CHEN Qiao-jian3
(1.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2.The Librar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3.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On the issue of how to deal with those who have wronged us, Confucius holds a view very different from Jesus, although they are both against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While Jesus asks us to turn the left cheek when someone strikes us on the right, Confucius advises us to repay an injury with uprightness.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the position Confucius recommends here lies between the position Jesus recommends and the position they are both against. While the former is morally too demanding and the latter is morally too permissive, Confucius’s position is morally realistic. This essay argues against such a common conception and claims that the position Confucius advocates actually sets a moral standard that is even higher than Jesus’ position, since what Confucius asks us to do is to do all that we can to help the wrongdoer cease to be a wrongdoer and become a moral person.
Confucius; repay an injury with uprightness; benevolence; virtue ethics
2013-06-09
黄勇(1959-),男,上海崇明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库兹城大学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王央央(1983-),女,浙江慈溪人,哲学硕士,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图书馆学研究;陈乔见(1979-),男,云南陆良人,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B222
A
1674-2338(2013)04-0001-12
(责任编辑吴芳)